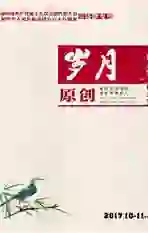近代中国人对于留学的认识演变与发展历程
2017-10-10孙增德
孙增德
摘 要: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日盛,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派遣留学生。可惜由于闭关锁国日久,风气闭塞,此举开始并未得到重视。近代中国人对留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到接受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近代中国 留学生 认识演变
1871年,清政府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作为挑选幼童并加以训练的预备学校。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预定“每批幼童驻洋十五年”,“通计首尾二十年”,作为学习西学的进一步措施,“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显然,留美幼童得以成行是中国官方的破天荒之举,中国开始承认西方有可学之处,不再单纯地嗤之以鼻。这是近代中国人开始成规模、有组织地走向国外,大胆学习西方文化的尝试。它作为一种官方行为,终于在鸦片战争失败三十多年后姗姗来迟,晚来好过不来,实是对传统中国的一次背叛,是对顽固派、对清政府曾经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重大突破。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如同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大坝上打开了两个缺口,历经时间的沉淀,终究催生了中国的新式教育,成为新式教育和后世留学生的拓荒者。
一、留美幼童运动夭折于国人的颟顸无知
近代国人对留学的认识历经由颟顸无知、抗拒到推崇,国人对留学的行为经历了一个拒绝到群起仿效的过程。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国人对西学及西方的认识非常保守,认为西方是蛮夷之地,西学无可取之处;再加上科举是正途,是安身立命之正道,出洋留学是为歪门邪路。即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有偏颇,更遑论一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因此在容闳召集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时候,费尽周折,从家乡及香港才勉强凑足三十人之数,且大多数人出自贫困家庭,属于在传统科举正途很难上升的一批人。在北方他应者寥寥。他不得不另想他途,到南方,到广州、香港、澳门和自己的家乡香山招收幼童,因为那些地方风气开放得早,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相对开明,而且那儿的孩子很早就进行了西学的启蒙。
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父母在,不远游”的惯性思维依旧顽固地束缚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很少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远洋去留学,毕竟他们对那里知之甚少。
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成员之一黄开甲回忆道:“那时的中国被拒于世界的大门之外。没有人知道外交是什么。高官们以为西洋教育是变态训练,在他们的谈话中根本连提都不提。不仅如此,漂洋过海几千里意味着无尽的阻碍和危险,几乎没有人愿意冒死远行。特别是在乡村,那里的人对外界知之甚少,没有学生敢出国。”[2]
第二批留美幼童的成员之一李恩富如此回忆道:“事实上,父母并不想送他们的儿子去那么远,时间如此长,而且是他们并不知道的一块土地,他们听说且相信那儿的居民是野蛮人。”[3]
詹天佑的父母一开始也很反对他去留学。詹兴洪夫妇担心儿子年幼,加上家庭经济状况不好,迟迟拿不定主意。幸亏谭伯村屡次登门劝说,并表示愿意给予经济资助,加上两家结为姻亲,詹兴洪夫妇这才最终同意。
清政府虽然决定了派遣留美幼童出国求学,但天朝上国思想严重,彼时的美国在中国人眼中依然是蛮夷之地,中国官方对此颇多猜疑,所以在选拔出洋幼童时,要求幼童父母必须和政府签订“具甘结”,生死各安天命。
民间对留学一事不甚热心,官方那里也是阻碍重重。1863年,清政府开始就送学生出国留学进行辩论,还是有很多保守官员反对这项计划,除了考虑所需时间和金钱外,清政府还担心承认他们不如欧美,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很丢脸。大多数学者反对送学生出国,因为这项计划强调科技而非循规蹈矩的传统价值观是确保国泰民安的方式。
即便是赞成派遣留美幼童的洋务派,内心里也认为中华文化优越,认为西方科技是奇技淫巧、细枝末节,不得已才去学习,因此他们在实行留学教育的时候秉持“中体西用”的原则。留美幼童在美国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外,还要诵读中国传统经典,向至圣先师牌位叩头,就连负责留学生管理事务的正监督一职,都要派識大体的正统读书人——陈兰彬担任,容闳因为其留学生身份只得为副监督。丁日昌曾对容闳言道:“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4]丁日昌的见地非常高明,后来亦被不幸言中。
虽然朝廷对这一计划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从上海地区看来,很少有人报名参加。因为父母都不愿意让年幼的孩子(年龄在10到15岁之间)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一去就是很多年。“到处都是谣言,说什么美国人会生剥男孩子的皮,然后在他们身上套上狗皮,把他们当作怪物展览”[5]。
在容闳的大力倡议下,清政府虽然决定派遣留美幼童出国,但是颇多疑虑,彼时的中国民众对此更是心存疑惧,视之为荆棘满布的难途。为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得不用传统的功名诱惑幼童的家长送自己的孩子留洋。在他们拟定的留学章程中有如下规定:
“选送幼童出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个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6]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最终夭折,虽与国内的顽固派有关,实则是当时中国国内没有适合留学生存在的土壤,从知识界到社会舆论都相对保守。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中曾曰:“坐令远大图,坏以意气私。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即对留学计划夭折的哀叹。
可惜国内舆论环境保守,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无法为之提供经济基础,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保守最终导致留洋事业半途而废。许多人认为留学外洋是“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极力叫嚣撤回留美学生。“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实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7]。endprint
留美幼童中途夭折,被遣送回国,刚回到上海就受到冷遇。不合时宜的装扮、不合规矩的行为遭到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嘲笑。“公众们知道的全是乌七八糟捏造出来的谎言,我们就这样被诽谤,被人当作卖国者”[8]。大多数学生没有得到曾经许诺的高官厚禄,他们的工资跟卖苦力的相比好不了多少。“其他男孩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继续他们的教育,分配原则既不遵循他们的爱好,又不遵循他们在美国所学的课程,而是看中国官员的意旨,这些无知愚蠢的官员根本就做不出正确的判断”[9]。
二、留学运动渐兴与国人竞相出国
可喜的是,随着西学东渐的日渐深入,近代中国人由被动变为主动,逐渐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以华夷之别为礼教大防的中国人,本来自视甚高,独领风骚数千年,自认是文化中心,洋人属于不开化的夷狄。经历近代以来一系列战败以后,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西式观念——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进而主动承认西方文明,自认中国落后,虽历经苦痛却不得不接受现实,退居到学生的地位。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对西方的态度,也从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发生了急剧而彻底的转变。
到废科举之后,清政府改革新学制,留学更为学子进修的不二之选。胡适在1910年给其母的信中写道:“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10]彼时的胡适与三四十年前的留美先驱们实是有着天壤之别。
留学史专家舒新城认为:“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11]1854年,容闳作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毕业生,也是第一位拿到美国大学本科学位的中国人,在中国留学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2]的教育理想,矢志不移地推动中国学生赴美。1870年,经丁日昌介绍,容闳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1871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政府并很快获准。
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副监督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从清政府的安排中可以看出,并未放心容闳,对留学事业也信心不足,所以派识大體的传统知识分子陈兰彬做正监督。此后三年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近代留学教育虽然从个人行为转变成了政府行为,实则这一举动并未在全国形成风气。以容闳招收的第一批三十名学生为例,大部分来自容闳的家乡,广东籍25人,其余五人为江苏、福建、安徽、上海、山东;偌大中国,招收幼童出洋留学是如此之难,亦可见当时风气未开。
幸运的是,官派留欧生所面对的阻力已经小了很多。就在留美幼童被撤回的那一年,清政府派出第二批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学习,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留学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把留学视为畏途,而是当成优遇和荣光。比留美幼童稍晚几年的官派留欧生走上历史前台,主要出自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由洋务派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发起。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海上的威胁,为巩固海防,清政府希望建设一支近代化海军日亟,1861年因请英国人李泰国代购军舰失败,清政府决定自己筹办海军。洋务派官员因此请求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李鸿章明确指出,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13]。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也附和之。
清朝官方派遣留学生的举动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说明近代化的不可逆转,西学东渐有其合理性。虽然清政府的留学政策保守,留学教育成效不显著,推行者踌躇不前,但毕竟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3-163.
[2][8][9]史黛西·比勒.张艳,译.中国留美学生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14,15.
[3]李恩富.在中国当我还是个孩子时[M].波士顿:罗思诺普公司,1887:94.
[4]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91.
[5]陈琼莹.清季留学政策初探[M].台湾: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36.
[6]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16.
[7][1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29:13,2.
[10]胡适.胡适致母[J].安徽史学,1989(1):75.
[12]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9.
[13]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