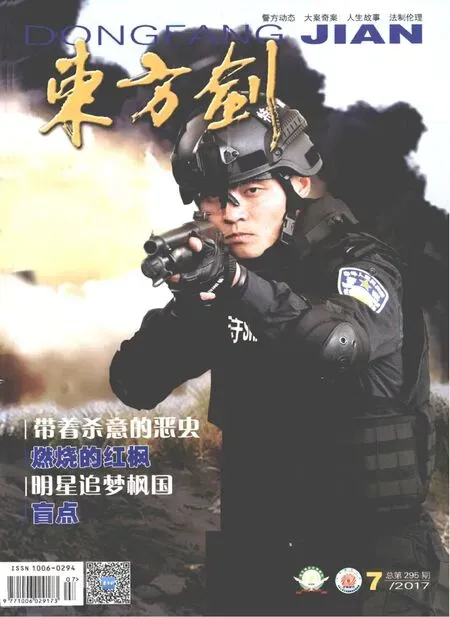一碗挂面
2017-09-21◆乔叶
◆ 乔 叶
一碗挂面
◆ 乔 叶

1
一位女友远嫁外省,久无音信。有一天突然来了电话,报告说怀孕了。待我道过喜,方才悠悠道:“来点儿实在的。”
“请明示。”
“给我寄点儿挂面吧。白象牌的,最普通的那款鸡蛋面。这边超市买不着。”
我莞尔。是啊,换作是我,可能也会如此。既然活色生香的家乡面在千里之外,可思而不可得,那挂面也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以稍稍安慰思乡的肠胃。
——忽然想到“退而求其次”里的那个“次”字,觉得像一个小小的疙瘩。如果挂面有知,会不会觉得刺心呢?
曾经以为挂面是近现代以来才有的新鲜物事,查了典籍才知道,原来它竟然颇有年岁。想来也是。中国内地发现出土的小麦,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中晚期。及至汉代,在《汉书·食货志》上就有了小麦在北方大规模种植的记载,到明代小麦种植已经遍布全国。有了小麦就有了面粉,有了面粉就有了面条,有了面条就有了挂面。学术界便认为成书于元代的《饮膳正要》所记的“挂面”,是中国有关挂面的最早史证。清朝大臣谢墉《食味杂咏》内言:“北地麦面既佳,而挂面之入贡者更精善,乃有翻嫌其太细者。”这种入贡的“太细者”,还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别名:银丝挂面。想来,银丝这种具有富贵之气的爱称去配天家皇权,却也甚是相宜。
作为北方最典型的干粮之一,挂面也是我家中常备。因比方便面要健康,比现擀面要省事,比鲜面条易存放,所以不想出去买食材的时候,没时间去做精细吃食的时候,又厌恶了叫外卖的时候,吃它是最适宜的。只要你有最简单的锅灶,你就可以享受它,随取随用。如果不取不用就随你一年半载地放着,简直就是食品界最贴心的存在。它是面条家族里的备胎,像偶像剧里悲催的男二号,永远不是女一号最心仪的,但又永远是忠心耿耿在为她垫着底儿。于是总是让人想起他的时候,不是喜欢,而是心疼,觉得这哥儿们不容易,挺委屈。
总而言之,挂面是忙人面,也是穷人面,往根子里说,本质上就是懒人面。不过,有意思的是,手工制作这种懒人面的人,却是格外勤谨的劳作者。
2
去年五月,暮春时节,到了陕北榆林的吴堡县。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样,一样是窑洞,另一样就是张家山的手工挂面。窑洞很多,多到漫山遍野,但很多都因空置太久而废弃了,显得萧瑟荒凉。张家山的人们住的也是窑洞,这里的窑洞却生龙活虎。因著名的《舌尖上的中国》摄制组来这里拍过传统的挂面制作工艺,这里如今闻名遐迩。现在,这里每家每户每天都在忙着做挂面:和面、醒面、搓条、盘条……工序异常繁琐,却每一道都马虎不得。
教游客做挂面也是他们的一种日常。比如此刻,面已经成了小拇指般的粗条,一圈一圈地在盆里窝盘好,两根长木棍一左一右伸在我的眼前。我学的环节是像纺线一样把面缠上架。婆婆们缠得轻巧敏捷,看着容易。我有样学样,分明是小心翼翼,却做得破绽百出。总是用力一过,面就断了。这面,须得不徐不疾,举重若轻——想来,就轻和重而言,举轻若轻、举重若重和举轻若重都是容易的,难的就是举重若轻啊。
缠好的面还要挂在廊下,再抻细,让它阴干。《舌尖上的中国》里的画外音如是说:“……撑面杆从中间精准分开,面的柔韧与重力的合作恰到好处。160根一挂,能拉长到3米,银丝倾泻,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最后的塑造之后呢?裁长为短,包装为挂面。
廊下的架子高高的,像晾衣架。他们把面挂上,我能做的就是把面抻细。这可是一个有趣的活儿。我把撑面杆横穿在面的底部,往下抻。他们让我使劲儿,我就使劲儿。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好吧,使劲儿,使劲儿!我的劲儿使得越来越大,面也越来越长,越来越细。你能想得到么,它已经这么细了——每根直径只有一毫米——可是等到完全晾好之后,居然是空心的。这奇妙的空心,是面在持续发酵时内部产生的中空。
干完了活儿,我和挂面合影,发到朋友圈里的闺蜜小圈。
闺蜜甲问:你摸的是帘子吧?什么材质的?
我再发一张,是挂面特写。
闺蜜乙评:乍一打开,还以为手机屏坏了呢。
我乐不可支。手机屏坏的症状之一可不就是密密匝匝的细条么?
谜底揭开,她们惊叹着,问我这么细的挂面摸起来是什么手感?
我答:如丝绸。
怎么会?!
你摸摸就知道了。
——真的。如果凭着想象,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刚刚挂出来的挂面,有着如此让我怜惜的温柔、湿润、细腻和光滑,如这世界上最美的少女的皮肤。
吃完饭,主人希望嘉宾签名,我们推选了一个诗人,他写的是:“面可空心,人要实心。”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快递,里面是一箱子挂面,足有十斤。挂面包装袋上写着“老张家手工空心挂面”。文字介绍只简单且郑重地强调,这面已经是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村老传统手艺”,“每一根面都经过12道工序完成。”
寄面的是吴堡的朋友。我发短信向他表示感谢,他回说:本来走时应该就送的,可是觉得我路上拎着累,不如快递。又仔细叮嘱:“煮面的时候,用旺火,水要宽。水开了再下,用筷子搅拌,别盖锅盖。”
3
据我所见,郑州市的每个居民小区附近都会有一家或者几家“鲜面条”小店,这样的小店照例都是粉扑扑的,因他们的主业就是开着轰隆隆的压面条机来压面条,毛细,二细,担担面,杂面……各种款式,面面俱到。而在这样的店里,也必有几根高悬的横杆,横杆上挂的就是细长的挂面。
老板告诉我,买挂面的人很多。因其不仅是自备而食,也会用来送礼:婴儿满月或者老人生辰,都可以送一把挂面,送礼的面叫“长寿面”,因何得此名?因挂面“长瘦”啊。
这么多人家都有挂面,他们又是怎么吃的呢?有时候我会好奇这一点。没有跟别人交流过吃挂面的心得,以我有限的私人经验,吃挂面的要义就是素淡。煮得将熟未熟之时,放一把青菜,有青有白,这就够了。若在出锅时再滴两滴香油,放些微香菜末,那就是奢侈。更奢侈的是再放一点儿红艳艳的辣椒油或者辣椒酱。红呢,是添了几分欢悦喜感。辣呢,是用来开胃的,是清素的饭食里,那一点点珍贵的热烈。如果还有鸡蛋,再在面里卧上一个圆溜溜的小太阳,那么毫无疑问,这碗面已经是顶尖的豪华。
煮挂面时,我还喜欢放一点点粉条。窃以为粉条和挂面是很相配的,因为它是另一种意义的挂面。我放的粉条分两种,一种是红薯粉,另一种是土豆粉。它们煮好后几乎是透明的,如柔韧的雨丝。这些浅灰的雨丝和雪白的挂面绞缠在一起,无论是颜色还是口感都更为参差有致,别有趣味。
——趣味?
是的。趣味。我必须诚实地说,不是美味。事实上,一想到要去评价挂面的味道我就有些为难,就开始纠结于一个吃货的伦理:虽是面,却没有现擀面新鲜。吃起来也筋道,却没有那么筋道。佐料入味的分寸呢,若是深了,面就烂了。若是浅了,就在面的表层浮着……总而言之,若说它美味,这有点儿违心。若说它不美味,又不忍心。
忽然想起两年前,我和朋友们去俄罗斯旅行。很多天没有吃到面,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嗷嗷待哺。那天,终于在彼得堡找到一家中餐馆,老板说只有挂面。
“挂面也好,挂面也好。”大家异口同声。
如春苗盼雨般,挂面终于来了,一大汤盆。卤是鸡蛋西红柿,口味寡淡极了。但没有人介意,只见群筷齐扎,瞬间,偌大的汤盆里,汤至清而无面。
我看着自己抢到碗里的那点儿可怜的面,深刻地明白,在不和别的面比的时候,在具有独一无二的存在性的时候,此时的挂面,岂止是“也好”,它就是最好啊。
忽然又想起在张家山吃的那顿饭,主食是“炒挂面头”。手工抻面的时候使的劲儿不是很大么?就会抻断一些面。当地人的做法是把抻断的面头捡起来,直接下锅煮个半熟,再拌上肉和洋葱炒一下,这就叫“炒挂面头”。这饭的样子不悦目,挂面头长的长,短的短,但吃到嘴里却口感醇厚,回味悠长,着实惊艳。想来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挂面了。可是,这没有被“挂”起来的挂面,能算挂面么?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