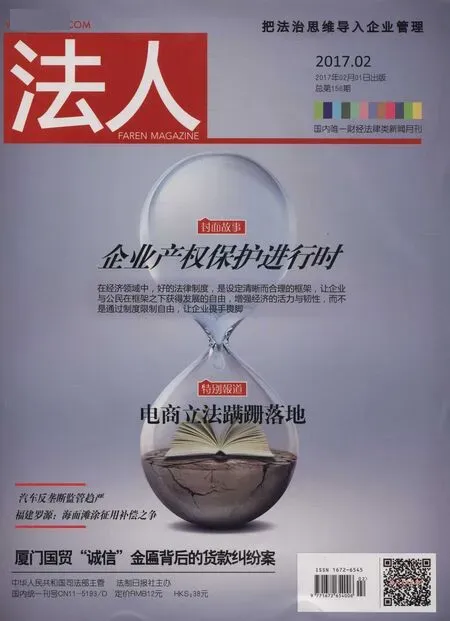2016:观念之争与方向感
2017-09-05法人田飞龙
文《法人》特约撰稿 田飞龙
2016:观念之争与方向感
文《法人》特约撰稿 田飞龙
2016年的中国法治波澜壮阔,亦处于复杂的博弈演化之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以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系统规划最为周全。两年以来,中国法治的观念构成与制度方向在改革的深水区发生了重要的变迁与调整。如,德治与法治重新混合,传统性资源渐次进场,这导致中国法治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感有了新的图景预期;民主法治的国际标杆盛极而衰,法律全球化动力消退,等等。
“东方法律主义”文化战士的学术努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历史大国,对中国的观察和评估历来不能以小国尺度为准。中国深厚的文明根基与顽强的政治自主性决定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尾随者的国度”而必有自身的规范愿景与制度规划。2016年的法律图书中,《法律东方主义》试图提供这样一种观察视角,解析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性逻辑。
《法律东方主义》以中美近代法律关系史为考察线索,呈现了美国法是如何借助帝国实力及帝国法理学而强加给中国一个“法律东方主义”的。这种法律东方主义,在近代早期很可能被作为西方先进文明要素引入和接受,但在中国更多认知世界与自身,特别是中国日益取得发展自信的当代,却可能激发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学术情绪。从观念史来看,“东方法律主义”是中国“去殖民化”和重建法律文明主体性之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宪制哲学层面,儒家宪制论与贤能政治论对民主宪制的比较优势分析也逐步成为中国法律思想界的一种自觉努力。姚中秋等人的《儒家与宪政论集》展示了大陆新儒家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与政治空间的饱满意志。
进一步,贝淡宁教授的《贤能政治》相继推出中英文版,其中预言了基于中国传统和实践理性的尚贤制优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贝淡宁教授以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证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而展开的系统化论述,对西方学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邀请或挑战:中国模式的传统根源和实践理性是否可能成就一种正当化的现代治理框架?
在此意义上,贝淡宁是西方世界出现的“东方法律主义”文化战士。这种“土洋结合”重新理解与论述中国的学术努力,正在结构性地改变中国场域下的法律思想版图,进一步限定和压缩了启蒙现代性的“法律东方主义”。
与姚中秋和贝淡宁相比,赵汀阳的《天下的当代性》则更加具有政治哲学上的原创感和冲击力。十年前,赵汀阳以《天下体系》一书开启中国古典文明“当代化”的努力:作者不是儒家义理的内部信徒,而是从全球治理失败的问题意识出发,试图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资源的再建构提供一个中国方案。
《天下的当代性》论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将“中国”本身处理成信仰对象和神学概念则极具争议性,但原创性思想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若是尾随儒家自身或西方论述亦步亦趋,可能仍然跳不出中西刚性二元对立的窠臼。赵在书中预言“中国生生不息,中国重新生长”,竟然使我瞬间激动万分,无比动容,尽管具体的理论方案和实践路径仍不成熟和明朗。当今世界,真正具有与西方论辩的心智和能力的民族并不多,中国学者处此洪流之中,是大受压力亦大有希望的一群。
中国法治开始兼容“转型”和“创造”
法律的观念之争其实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内部亦不时出现。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启蒙新范式席卷欧洲,潘恩是礼赞的吹鼓手,可是保守主义者柏克却以《法国革命论》截断众流,坚强捍卫英国宪制的自主性。拿破仑输出革命,德意志的黑格尔和费希特亦在“世界精神”的激动之余清醒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包含了对传统和民族生活的特定理解与坚持。20世纪魏玛德国的施米特发展出独特的政治法学和法律存在主义以对抗英法美的战胜国国际法秩序和自由主义法理学。

甚至20世纪末的美国宪法学教授阿克曼亦在“我们人民”系列论著中宣称美国宪法学缺乏自我理解,仍然处于欧洲智识殖民地的范畴,而其“高级立法”“二元民主”“宪法时刻”则依据美国自身宪制经验而来,与欧洲展开智识竞争。这种观念用于中国,就成为对抗“法律东方主义”的“东方法律主义”。
就其理论本质,这种“东方法律主义”具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存在主义的多重构成,在悲情性与历史化的主体性宏大叙事中重新塑造民族性的法律人格,但也存在着对抗客观性及逆转法律全球化的地方主义局限。为此,我们在自觉重返、重述本国法哲学与宪制哲学的同时,一定需要克制过度的地方化倾向而学习西方法律文化的建构、表达与传播技艺。
当然,就中国法治的未来图景而言,中国的文明与治理使命决定了不可能仅仅在自身之内实现自身。这就需要中国的法治规划适当超越民族国家范式。事实上,与赵汀阳式天下主义的理想性论述相比,中国国家行为中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框架以及以高铁与互联网为基础的发展援助模式,已经在尝试一种不同于西方法律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在严格的历史与学术意义上是一种“帝国冲动”,就像美国的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是走出国门的“帝国冲动”一样。
这种对外输出的“帝国冲动”与特朗普美国呈现的非帝国化收缩相叠加,使得超国家法治秩序的需求更加真实与迫切。这就造成了法治发展中民族国家与帝国、民主法治与政治威权、形式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多重张力。
黄钟先生在《帝国崛起病》中展现了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帝国崛起的忧虑。作者考察西方大国崛起中的“帝国病”,但似乎对美帝国的崛起缺乏病理分析和批判,算是网开一面。特朗普就是对美国之“帝国病”的有力批判者,但其自身却日益陷入当选后的帝国权力规训之网,而很难彻底兑现其竞选语言中的洒脱承诺和早期著作《做生意的艺术》中的狡诈快意。
中国法治重新陷入了一种观念之争或观念危机,法学家的移植型理想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被弱化和相对化。密集缠绕于中国法治周边的相关治理观念与制度因素正在系统化改造中国法治的语法和结构,使之与既往的法治想象及规划产生较大差异。法治在中国的观念之争对中国法治的方向感产生了重构效应,但这不足以改变中国法治的规范性议程,而只是使这一议程加插了更多环节和议题。由此,中国法治进入了一个异常复杂多元的对话结构。
远期来看,中国法不可能是一种纯粹启蒙式的“法律东方主义”,而诉诸文明与政治主体性的“东方法律主义”正在生成,但这也不是终点,因为中国内含“天下”(世界),中国的法律文明在本质上应是普遍主义品格,从而经由“东方法律主义”向更具普遍性的“法律主义”进展是无可回避的命题与前景。当然,这是基于可靠而理性之“中国经验”的,是批判性表达和提升的理论化结果。
总之,中国法治开始适度摆脱强形式下的法律东方主义式的单调“转型命题”,而兼容“转型”和“创造”,开始了自身法律传统、文化与经验的会通整合及重新生长。这一新法治时段需要法治新思维,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适应,心态和知识上都存在严重欠缺。法律观念之争是长期的,法治方向的不确定感也是长期的,但创造和希望蕴于其中。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