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词典
2017-08-28河南薛松爽
河南/薛松爽
一个人的词典
河南/薛松爽

即使春天已临,雪的融化有时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朝阳的房坡上的雪已经融化了很久,背阴的屋瓦上的雪还守着自己的白。你站在院子中央,看自家的房顶,黑色的鳞鳞屋瓦,比平日更加整洁清晰;而前方邻家的屋脊,还保留着均匀的白色,像一张没有任何字迹的宣纸,守着自己的凛冽体温。甚至,连麻雀也不去留下印迹,它们只在向阳的南坡唧唧喳喳地跳跃、闹嚷。有时,炊烟从屋子前面升起来,炊烟是温暖的灰,而此刻它们呈现出了清寒的蓝……它的融化是那样的缓慢,几乎像是冻僵在上面了。只有在气温全面升高之后,渐渐地,才露出了瓦缝,仿佛一个人露出了黑色的坚硬骨骼……这时候,你在老榆树的背部,也会见到没有融掉的白,远远地看去,像一个披着麻衣的离群索居的人;而在偏僻的荒野,深深的野沟中,厚厚的碑石后,都隐藏着这些白,像凉风中独自起舞的鹤,像讲台上戴着蓝袖头执着粉笔的夫子,像陋室中抄字人耸起的肩骨,寒风中挺立的一面面脊梁……这寂寞的白,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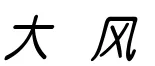
明亮的夕阳猛然沉落。那么大的风,春天的风,吹折了树枝,吹乱了长长的黑发。穿风衣的男人跑着捡拾滚落的帽子,他身边的自行车被风推倒,像一个被时光用旧的人,慢慢倒下来……
风啊,为什么还不折断我手心摇晃的钢笔?不取走发间一丝丝的泛白的曙色?我需要苦涩的墨鱼的墨水,我需要咬牙的黑暗的青春。大风吹落天边一片云,将一只麻雀吹进水田,它灰色的翅膀沾满了泥水……
大风吹着连绵的荒丘,枯草朝一个方向倒伏,像乌鸦的斜翅。大风要刨出泥土里隐藏的东西,揪着它们的领子,把它们连根从土里拔出来,吹散里面的白雪灵魂,远远地一只斑鸠飞起,像飘飞天地间的一片灰纸……
风啊,为什么还不剔除我满嘴的泥沙?不撕破砂纸打磨的粗糙脸皮?我的胃里凝结牛黄的块垒,我的身躯流淌黄河的胆汁。大风吹过近处的白杨,粗壮的树干不动,泛绿的梢头发出了春天隐隐的虎啸……

大雪中一具巨大的马首!绛紫如深厚土地。它的眼睛深邃,湿润,像黑色的井。纷乱的鬃毛垂下来。它一动不动,四蹄立于雪地。纷纷的雪花穿过马首的陡峭山岩。
每一粒雪花都提着一盏小灯,像一个个白色的灵魂。马首的内部也嘶嘶燃烧着一盏马灯。红光从薄薄皮肤内透出来,将热汽传递到漫天风雪之中。
赶车人在大地上沉沉睡去。那么平静,仿佛睡在风暴的眼中。
马首一动不动,纷纷大雪要将马首包裹!

风停息于更深的地方。沉默的地方风声更加猛烈。
我看到石头、树木、皮肤、大地的深处响着风声。一个人的身体内,风卷着雪粒,击打它的内心。他的心脏如同字纸,瑟瑟作响。
大海深处,龙卷风的巨柱就要矗立。它要在青天下竖一座石碑,刻上闪光的鳞的碑文。
在乌鸦翅底,一场旋风揪着一团乌云扭打,像撕碎一个虚假的纸人,降下一场鹅毛的大雪。
在土坟之内,风好像睡了。
一个守墓人抱着自己的木头。木头内,风也垂下了灰色的翅膀。
而在青石上面,那揳入的颜体字迹内部,风高举着大纛,端着闪亮的刺刀,率领呼啸的马队,用雪与血,来反复清洗。

一张纸里有最深的黑夜。
要穿过它,抵达清白的黎明,也许要用上一生的光阴。
有的人一生也穿不过一张薄纸。
有的人永世也迈不过纸的门槛。
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字,自以为写在纸上,其实都写在了虚空里。
当你穿过一张纸,也就是穿过了一生的黑暗,大雪、烈焰、河流、山岳,罪与罚,羞愧与卑贱,高尚与伟大,也就是穿过了一生的昼与夜。
这张纸就成了你的皮肤。
上面写着你的字迹、密码,密密麻麻,如同星辰、跳蚤、芝麻。
它裹起你,带着你飞翔。一瞬间,沉重的身体无比轻盈。双翅展开,洁白,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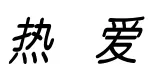
隆冬,深夜,熟悉和陌生的人都睡去了,我独自面对一张贫穷的白纸,小心翼翼说出:热爱……
窗外的黑暗里,路灯已熄灭。我无数次看到千万只飞虫围着灯光跳舞的情景,如今它们都已死去,尸体雪灰般堆在地上。我爱着这些残损的尸体啊,即使垃圾一样将被清扫掉。
池塘里,枯荷朝夜空伸出舌头。在白日,我曾为它们一一命名:屈原,陶渊明,龚自珍。
……现在,我更爱那下面腥黑的淤泥,我愿伸出我冻肿的光足,在深厚的清凉里取暖。
打着鼾声的人们,清醒着的人们……我伤害的人,我深深忏悔;伤害过我的人,我依然祝福,我也爱着你们,我爱你们加给我的伤,这是我在世间赢得的东西。我会带着玫瑰和霜雪,含笑扑进最后的熊熊烈火。
灯光下,白纸洁白,字迹漆黑。我懂得了,热爱,这两个字有多热、多重。浇在心上,心会冒烟;写在纸上,纸会化为灰烬……

我要朗诵身边的这一个夜晚。月亮像大水泡,从寂静的树身后升起。让我就着这些闪光的细盐,朗诵一根根伸展的枝条,朗诵它的黑色,纠结与伤疤,它的灰尘与血迹,甚至肺腔沉默的咳——一枚揳入的久远的钉子。当我的朗诵混合了风声,听,它们一阵阵战栗般地摇摆。
我要朗诵脚跟沾满血污的小羊。眼眶湿润的母亲正用舌头舔干它。我要朗诵粗糙的墙壁,干草,昏暗的灯光,朗诵那只端来稀粥的手臂和皱纹缠裹的眼睛。北风中,我的朗诵会像一场大雪,又一次深深覆盖它们。
我的声音如此柔弱。但我仍要朗诵这些挺立的枯荷,伸出的舌头击穿雪粒的声响,朗诵那一首没有做完的诗,连同里面不合时宜的病句。我要朗诵字迹背后一无所有的白纸,在渐渐清晰的声音中,它们会像荷叶再次伸展、卷起,将诗人清贫的一生,在清水里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