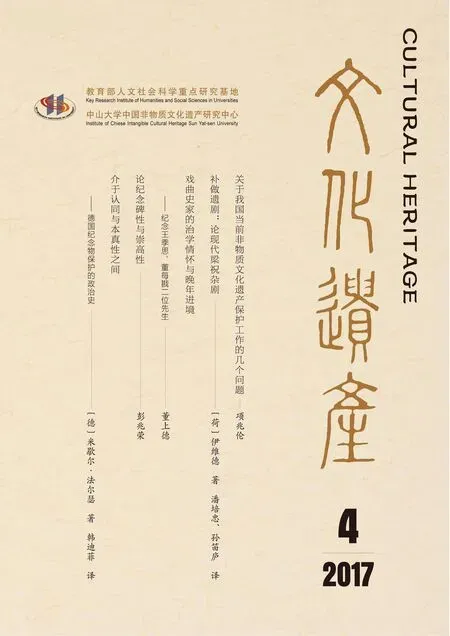介于认同与本真性之间*
——德国纪念物保护的政治史
2017-08-22米歇尔法尔瑟MichaelFalser韩迪菲译
[德]米歇尔·法尔瑟(Michael S. Falser)著 韩迪菲译
介于认同与本真性之间*
——德国纪念物保护的政治史
[德]米歇尔·法尔瑟(Michael S. Falser)著 韩迪菲译
本文为作者博士论文的序言部分,主要阐述了该论文的主题、研究范围和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论。在针对纪念物保护及相关机构所面临的危机,从政治背景出发展开讨论之后,文章基于文化语义符号学的理论,分析了纪念物保护的社会文化功能,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概念如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记忆和回忆、本真性、传统、神话进行了定义,阐释了它们与纪念物保护之间的关系。
纪念物保护 认同 本真性 民族主义 历史意识
一、观点与方法
(一)民族认同与纪念物保护(Denkmalpflege)现象
近年来,德国纪念物保护机构的危机和几近瓦解之象,常常在专业内部和文化政策讨论中表露出来。它们的科学理论基础以及它们在文化遗产和建筑遗产的保护上唯一有资格代表“公众利益”的身份受到了质疑。即便如此,纪念物保护机构的重新定位,直至今日也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铁幕崩溃”的背景下,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回忆”、(文化)“记忆”和“全球媒体时代”等关键词逐渐被识别出来。他们在关注和保存建筑纪念物的物质性、延续性、本真性方面,是存在局限的。在专业上忽视了对纪念物的保护,从而影响到建筑物的记录,重建和回忆。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同时,这种变化也出现在新的政治联盟和公民联盟(Koalitionen aus Politik und Bürgerschaft)的计划上。
对于此项课题的研究,在德国统一后的政策制定上依然占据着中心位置:分裂了40年的德国,似乎始终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在社会、精神和肉体上的统一。第一个研究的结论是惊人的:纪念物物保护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使民族认同和集体认同得到稳固。而事实上,欧洲纪念物保护机构的设立直接与19世纪现代国家的建立是相互联系的。同时,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纪念物保护机构又是日益增长的民族文化在道德上的根基,因此,它必须承受自我审问和反思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公共的行为和任务合法化,同时,可以在快速变化的文化认同建构市场中,得以维持。他们自身的“成就和模式”,通过回顾200多年创建发展史进行自我批评,自身剖析和明确的界限(同时仔细的分析),在文化市场上快速成为的具有竞争力的“供应商”。
目前为止,在德语相关著作中*可能到目前为止,只有来自美国的相关研究。Koshar (1998),还没有全面的关于纪念物保护在政治史领域论著。纪念物保护以其19世纪建立的时间为出发点,还包括距今并不久远的20世纪90年代。但在1989年以后,纪念物保护的作用似乎在重新建立一个泛德意志民族和他们的认同的过程中失效了。
这不禁产生了争议性的问题:
纪念物保护机构在德国的发展与什么有关?它的“真实”感、“价值”的评估和社交策略,与文化遗产在德国的民族构建过程中是怎样相互制约的?相反:在欧洲,已经被证实纪念物保护的发展过程是很特殊的。在德国,民族认同经历了无数次的断层、飞跃和间歇,这对文化遗产的处理有怎样的影响呢?这种重复的意象(Topoi)范畴在民族认同的构建和对文化遗产处理之间的讨论又是怎样的?成功、失败、甚至错误的发展纪念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是目前在纪念物保护机构在德国民族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局面。在何处可以作为命题的切入点?与当前局面相联系的自我批评和展望,如何有助于纪念物保护的自身剖析和提高其感知能力?本文的目的是,尝试通过对难点案例分析,使纪念物保护这一课题敏感化。
(二)方法:纪念物保护作为“现代的”特殊现象和“民族共有的心理状态”的人文科学指标
1.民族认同和纪念物保护机构
在欧洲,纪念物保护机构的基本功能是评估、保存、宣传、行政和管理。同时,它也承担了民族和集体意义的文化遗产(以建筑纪念物的形式)的管理,这直接与19世纪开始的现代国家构建(Staatbildung)的过程息息相关。在嵌入现代化的过程中(聚焦世俗化、经验化和差异化、机械化和官僚化),同样插入了反对和脱离现代化(Entschleunigung:deceleration,减速)的特殊过程,使其成为一种意义和秩序上稳固的集体认同。因此,纪念物保护机构在建筑和文化领域占首要位置。*Dolff-Bonekämper(2004)。
2.纪念物保护作为工具,是对民族共同体(National-kollektiver)的“现象”进行深度解读
这一命题,可以通过了解和认识现代特殊的民族认同和在政策上相对应策略(比如建筑性的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民族认同的危机和重新定义民族认同反映在每个具体时间对文化遗产的处理上。另一方面,这一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民族纪念物保护常常是重要民族共同体心理状态的波动指向。因此,通过对纪念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案例分析,为“深度解读”危机四伏的民族认同,提供了部分重要的认知。
本文将涉及到,一方面是定位德意志民族构建过程中关键点;另一方面,则选择引人注目的纪念物进行讨论。从而,我们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和不同时期内的两极学术观点的交联中得出:在现代化普及的过程中,对文化政治意义重大的纪念物保护的整体感觉;从特殊的德国纪念物保护发展中,获取知识,也包括他们今天所存在的危机感。
3.这种纪念物保护的“现象”是一种人文工具
纪念物保护在文化遗产(城市建筑、建筑设计、建筑纪念物)形式上的分析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首要问题应该是人文上关于象征性历史的继承对象。*见Böhme, Matussek & Müller(2002),第104页。怎样通过建筑设计来诠释纪念物?通过谁?什么原因?什么时间点(或者没有)和怎样的初衷,论据和概念上的选择,哪些社会族群会持反对态度?*见Gerbel,Musner, Wunberg(2002),第13页。在这个社会中,通过纪念物保护可以解释的人文观点,其社会秩序和社会空间是如何产生的。因此,纪念物保护是对人文观点进行的一种实践性翻译。所以,在下文的时间截面分析中阐明了关于纪念物保护的概念,对纪念物保护的讨论和在科技史上的研究。以及对纪念物的讨论与社会政治产生的联系,纪念物保护形成过程的概念,以及纪念物保护在历史语义学中的批评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在民族-共同体(national-kollektive)的危机时期,其中在一个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的隐含部分往往会被列为研究课题,在其文化进程中说多做少,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概念领域的分析。
(三)方法论的局限性
关于纪念物保护这一现象,到目前的研究为止,学术界还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确切的说,本文想要尝试通过科学理论和实践,在德国特殊的背景下,逐步专业化和跨界连接纪念物保护现象。对照规定时间的划分和对意识形态的批评,运用纪念物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对政治目的性集体认同的教育案例进行逐条逐项的分析。同时,收录了同一时代的,来自哲学,艺术,历史,科学和社会学的典范性讨论。从而,产生了新的观点和认知,这些观点有些是批评的,有些是片面的和更有些是挑衅的。在一个最后叠加的时间分割检验结果中,尝试性的将其作为历史价值和某一概念的轮廓。强调德意志的认同构建中的常量和变量与纪念物保护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观点,表达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四)研究范围
本文涉及到的范围是普鲁士,以及后来的西德和1989年后的德国领土。跨越的时间是从1795年到2005年之间的6个时间段。他们越贴近当代,时间跨度越逐渐缩短。同时,题目的范围逐渐扩大。前两个案例研究是关于19世纪的:在拿破仑占领之前和之后的十年(1795-1840年)(1)和德意志帝国的后期(1900年)(2)。本文的第二个重点是关于1945-1949年(3),1968-1975年(4)和1980-1989年(5)这几个战后的西德的时间段。第三个重点是德国统一后(1989-2005年)(6)的全德国的观点。因为,本文中所研究的纪念物保护的发展过程多数是在民主社会的背景下*当然是在结合上下文必须被提及的普鲁士专制时期,德皇威廉二世时期只是作为个例,跟民主社会无关。。不是纳粹时期,也不是以东德时期*见Brandt (2003)。作为自身的时间段,但是纳粹时期和东德时代可以作为参考的来源。本文只是选定重点的国家共同体认同的优秀纪念物讨论并加以解释,从而得到广泛的公众在政治上的认同。规模较小的古迹和文物作为真实存在的实例,更多的用于参考和比较。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几乎很少可以与整体相联系。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本文的目的只是民族共同体在德国纪念物保护的问题和它的第二个层面。更多小规模的,日常的和区域不同的层面不考虑在内。纪念物保护的第二个层面,常常是首先呈现出完全解脱的民族共同体实用主义的层面和因此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和提问。
本文选择分析的案例,分散在德国的领土上:玛丽亚堡和在爱尔福特大教堂(1),海德堡城堡(2),法兰克福老城(3),“1975欧洲纪念物保护年”的范例城市和公民倡议(4),希尔德斯海姆市场(5)和柏林的施普雷岛(6)。
二、纪念物保护作为文化传承的必然过程
(一)社会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语义符号(学)
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Bargatzky (1985),第33页。的内容是,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与他们的表现形式、研究领域、社交群体、规则组织结构以及语义符号之间的关系。由此,通过衍生的系统和信息理论来理解文化,把文化看作是大量的检验标准和检验机制*根据 Geertz (1973)。,他们在社会、物质和美学的因素上相互影响。
纪念物保护重要关系的一个粗略解释,是根据与文化语义符号学相互联系的部分,把“文化”分别划分(根据R. Posner的观点)在社群,文明和情绪或者是在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中(图1)。语义符号学补充解释的文化是生物整体的标志,在符号、象征和编码系统中,其行为属于一个特定的传统。也就是说,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创造和变革、并传递给下一代。*见Bense, Walther(1973),第12页; Schaff (1973),第176页; 和 Eco (1972),第19、56页。语义符号学是研究“遗传的传播机制和传统的传播机制”*Posner(1991),第39页。之间的差异的。社会文化(社群)包括个人、团体和机构,他们在特殊的交际过程中,作为独立的符号的使用者和载体。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部分)对这一文化领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探讨这种认同现象(个体、集体、民族),和社群特征以及社会环境。文物、建筑和纪念物被作为物质文化(文明)来理解。他们被人类发现,并且世代传承。因此,物质文化也是大量的文本,把他们转换成为传统的代码,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人文科学领域(其中包含历史,艺术史)关注的是,备份、恢复、辨认和解释文物(Artefakten),以及他们的生产能力。精神文化(精神状态)描述的概念是精神事物。在精神状态中,大量的代码是被作为集体性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用来解释社会行为和文物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来研究规范性的科学(包括人类学、美学)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思想、价值观和约定:“如果一个社群可以定义为一组代码,在这三个方面必须是相互连接的,因为符号依赖于代码。如果它们使用传统代码的信息产生文本,它使用的符号可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文化的行为方式是以公约为依据的语义符号学。也就是说,其本质是符号形成的过程。”*Posner (1991),第54页。

图1:纪念物保护在社会文化(作为建筑纪念物的感知、评估与交流的实例)和精神文化(作为反映社会价值和本真性约定俗成的实例)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式。在社群、文物和精神事实的层面上把(文化)语义符号学划分为“字符使用者”,“文本的总和”,“代码的总和”时,文化科学与他们是有区别的。这三个层面也分别在社会、思想与规范科学中被研究。
(二)纪念物保护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的角色
“一个物体在作为纪念物的情况下,其特点是:它没有客观的身份,但它确实是一个过去存在的遗迹,具有记载的价值。”*Speitkamp(1996),第82页。(Winfried Speitkamp,管理历史,1996年)
语义符号学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符号中的保留节目。纪念物保护的现象,在这里被视为在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进行调节的工具。
1.纪念物保护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机构、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从19世纪初,纪念物保护机构在欧洲设立。一个机构通常是管理一个特定的领域。社会福利机构,或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组织)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秩序的载体,是公众认可和有保证的。一个机构的主要特征是时间上的恒定。机构监管和控制其成员(包括制裁在内)社会交往的文化和规范性准则的格局。纪念物保护机构作为一个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借助于分配给它的权力(官方的纪念物保护机构、纪念物的保护法),不断对文物资源(这里包括建筑设计,从城市建筑群到独立的纪念物)进行全面收集(入册);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评估(根据主流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公约);最后对纪念物进行选择性的保护(纪念物测绘,编入名册)。因此,纪念物保护机构在建筑纪念物的形式(物质性文本)文化的传导机制中,具有主控功能。同时,这种持续存在机制对交流也起到调节作用。这种交流是社群的——这里是特殊的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标记过程的理解,取决于“Kon-Text”(语境)社群与政治的基本情况。(民族)集体的行为导致了(纪念物保护的)选择标记的模糊。也就是文中所说的提升普通的建筑,使之成为纪念物。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过去、现在或未来选定的保留符号相遇,他们选择的媒介是依赖于交流的情况和目标群体。“传统绑定的信息取决于经久不变的媒介宣传,它有别于与为时局而造就的在传单上和在另一种情况下的信息和纪念物。”*Duroy, Kerner (2004),第270页。不同时间内,对纪念物分析的辩论,甚至涵盖了民族的价值等级制度,并让民族认同这一命题有判断的时间。*见Pross(1983),第 49、51页。人们在社群有约束力的标记和象征上激烈争吵,而如果通过纪念物的形式进行讨论,则经常可以理解并解释清楚集体(民族)价值危机和认同。纪念物保护可以理解为对制度化的集体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分析和管理,对民族有时代象征的纪念物建筑进行加工处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利用这种象征(也通过纪念物保护)通过特殊的方式为自己的权力利益服务。同时,它也承载社群的侵略性代码。一个民族(拉丁语为Nascere,意思为“生出”)是由民族主义的意识作为一种特定的代码,通过建设和建构社群的社会而产生的。在一个机制化的持续选择、淘汰和竞赛中,加速了合适的代码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在整合交换中的主要机构产生,例如,目前的纪念物保护机构(出现于19世纪)就是这种情况。同时,(德意志的)民族—代码同时在迅速上升的社会变革中开始形成(现代化)。“现代的民族理念,刚好是在找寻这种可以停靠的、无条件的和隐藏的现代生活关系。它行使代码的主权,是破译社群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基础,似乎是被剥夺的社会变革。”*Giesen, Junge (1991),第260页。纪念物保护的思想根基是实践文明的批判,“也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批判。所以,纪念物保护现象成为现代社群有秩序的组成部分。”*Speitkamp (1996),第25页。在没有现代化、制度化的国家干预的区域,“这组人(纪念物保护工作者)扮演的外在形象,在我们的社群中是一个关键的角色。”*Beyme(1981)。
2.纪念物保护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建筑物、纪念物和民族理念、修葺
建筑物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现象,——语义符号学上的观察——处于一个有趣的中间位置;因为,其基本意图是在完善社会功能和积极的建立社会空间。其对象也不是表面上的传递,而是行使职责。另一方面,是建筑设计的代码对象的交往关系。“在建筑设计的应用中,也不仅仅是使用可能的相关联功能和含义。同时,在历史上丢失或重新修复的建筑设计的功能和含义,也导致了不同的诠释和纪念物保护的标准。建筑设计是在商品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产品,它与大众交流的功能相同。”*Eco (1972),第320页。因为具有大众交流的功能,所以使得有共识或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赋予、追溯和预见其未来的另一种含义,摆脱了它的原有功能。因此,这种被赋予的含义在意识形态上常常被使用。不仅因为这种功能上的改变,还有原始意义的丢失,导致了建筑物构造上颠覆性的改变:因为重建、继承、发展、不可用和拆除,导致了功能损耗和含义损耗(例如,神话中的巨人是没有意义的)*Eco (1972),第320页。。纪念物的一项任务是通过当前感官原则的过滤,尝试解释和重建建筑文脉的源代码。建筑设计从当代的纪念物保护观点(追溯)出发,是含义丰富的,因此其也是值得保护的。基本上,建筑物改变了他们的原始功能和意义。建筑物成为建筑纪念物(对比成熟纪念物*拿以往的已备受关注纪念物作比较, 曾经未受关注建筑纪念物被理解为有意义和备受关注的回忆性纪念物(例如,在维也纳英雄广场(Wiener Heldenplatz)上的欧根亲王纪念像(Prinz-Eugen-Denkmal)),未受关注的纪念物(像未建完的科隆大教堂, 在19世纪的时候突然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象征性纪念物)始终能够被赋予新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备受关注的纪念物的关联意义从他们被呈现之日起便不可避免的丧失了他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就像那些不知道欧根亲王的人,他们也几乎不了解它作为纪念物的含义)。)具有当代的、更新的意义。纪念物保护机构作为民族认同(民族观念*Nipperdey (1976b),第139页。)的管理机构,在现存的历史遗迹方面,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当代公众的利益。建筑物分配在民族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含义中,有可能晋升为民族纪念物(反纪念物Gegendenkmälern)。把纪念物理解为政治意见斗争的媒介,它便是“政治上公开的档案”*Arndt (1981),第186页。与“一个时代典型的历史意识的证据”*Boockmann(1981),第237页。。
3.纪念物保护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规范、“真实”的-感官规则、本真性
建筑对象在文化文本年代上的增长积累,不断发出与当代关系重大的、新诠释的消息。它们甚至使人感觉到,将建筑物升华为纪念物(或者失去了纪念物原有的纪念状态)和受到保护(或在最坏的情况下拆除)是一致的。因此,也是重要的(或是相反令人厌恶的)。接收到并辨识出来的代码,是“真”接受到或以其他方式拒绝,是由个人的考虑或者集体的现代认同价值观决定的,是合法机构(是在纪念物保护的称呼下)的选择标准。一座纪念物首先是定义对象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纪念保护上的真正文化业绩,不是存在在纪念物的建筑本身上的。而是在原有的,以功能为目标的创造性翻译过程中,在“价值中立的”建筑上追溯和占用成为建筑纪念物:“在这种情况下,它再次被接收者管理,为了可以识别发送者的代码。一些代码被接收者自己的代码所代替,这些被代替的(建筑的)信息就是接收到的噪音。”*Eco (1972),第194页。
建筑物首先是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下成为纪念物(只是过于夸大了仇恨和侵略对象)的。当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认出的”作为噪音)没有被接受,或完全被忽略,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纪念物作为物体所具有的特征是没有客观属性的,而这种特征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归结于来自当代的、特定的、过去的遗迹。”*Speitkamp(1996),第 82页。至今为止,来自对纪念物的观察者*见Bacher (1995),第 265f页。,关于他们“对-评估”(Be-Wertung)的最全面的研究是出自20世纪的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他奠定了纪念物保护的科学基础。(参见案例2)观察对文化建筑遗产的应对策略,少于它本身的陈述,这也是本文的原则。更确切的说,是当事人自身绑定的现实价值体系。在过去五十年对纪念物评级质量与多数原始材料的讨论中,引导出与“本真性”概念相结合: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是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而对什么是纪念物的“真实的”和“本真的”,在此宪章中没有继续完善;对纪念物的申请条件几乎没有讨论。
“没有一个物体或者文档自身是正宗的或本真的……本真性源于一个消息接收者的期望……它总是会被宣布追溯……接收者决定是否一个消息能够传达到……因此,本真性要满足愿望上追溯的可靠性和消除怀疑的反馈。”*Schellin(1999),第 44页。本真性的分类也决定了实际对纪念物的处理方式。例行的表面修复,甚至是对更小磨损的恢复,在纪念物保护的实践中被制定出来。因为,它是(所谓的)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封闭了断裂,作为一个整体记录的建筑代码的信息。高度空想的补充或者完全新建建筑所丢失的部分,又或整个纪念物建筑(重建)在主观的本真性理念科学创建的纪念物保护(从20世纪开始)中被拒绝。建筑信息在纪念物保护研究中,是通过分析增长的信息,从它建立开始,依赖于所追溯与所属时代的显著性,保存干预的规则是在本真性的理念下制定的。通过对作品的诠释(修葺到重建),当代所赋予的,新的含义的原始文本被完成。纪念物保护的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重新设计一个建筑象征性的外形,使其成为纪念物。
在他们同时代社群著述的报告中,建筑提升为纪念物的价值,是重要的——这里涉及到所选择的集中点是,在目前所掌握的著作中,题目是关于纪念物的形成过程的——形而上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的本真性。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语义符号学的实行目标,是表现在与其整体文化相关的纪念物保护现象中的:社会文化作为机构,这个机构是为了物质安全上的民族、集体认同;物质文化上作为感觉(选择性)和建筑物向建筑纪念物的转换实例;精神文化上作为追溯当代的主观的价值导向;这三个方面都是建立在本真性*见Kiesow(1988),第113f页。的理念下的。
(三)概念
在民族认同的构建和文化遗产的认知、评价和处理紧张关系之间的策略,主要有七个关键词,他们作为概念被反复提到:认同、民族主义、记忆与回忆、历史意识、本真性、传统以及神话(构建)。
1.(民族)认同
认同问题对于德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规范,道德,教育和教义方面的反问和警告。*Lutz (2000),第 129页。
认同意味着区分。作为“保持距离的一种手段,它可能首先具有体制和环境的结构差异在相对独立的变化中的意义”*Luhmann (1981),第199页。。认同是被钳制在对过去的诠释、当代的观念和对未来的期望之间的。个体(我和个人),我们(组群Gruppen)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民族认同的标准是不同的。它们建立的过程类似,并且是相互关联的。*Borries (2001)在个体与集体的自我形象的重叠中,激励了民族共同体(集体精神)的想象。民族共同体的自我形象与外在形象在社会和政治服务中具有导向功能。“同样,集体认同作为个人的精确定位和组织原则的参照系统,可以给社会政治带来统一。认同也需要过去和历史,如个体认同。”*Lutz(2000),第 55页。价值决定了民族认同。“价值上得到共识,便可以融入社会;因此,当我们通过价值的纵切面确定民族认同时,似乎我们就可以确定其内容,而这些内容是存在与自我分类和其他集体成员分类之后的。……认同是属于集体所有的。”*Meulemann(1998),第16页。集体认同的产生是通过个人的背景信念以及对想象的重叠或浓缩而产生。“民族认同包括对民族的主观认同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情感评价,或者是某些关键特征和民族共有物之间的相互联系。”*Schmidt, P.(1998), 第270页。社会群体作为其个体成员在社会心理学关系中的扩展和分支,被广义定义为一种(被组织认同)社会态度和公共机构,在社会组织中有经验丰富的社会活动。“一个民族命运凝聚在这些公共机构中,这些公共机构要对其社会中不同的人负责,使其赢得相同的印记和相同的民族习惯。”*Elias (1989),第159页。纪念物的保护单位(选择性的)作为集体物质财产的管理机构就是这样以一个社会构建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它记录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编目、入册、有针对性选择、保存和为此对物质遗产的储存。同时,以“神圣化的文化记忆”*Assmann (1992),第159页。使人印象深刻。
2.民族主义
在德国,对于民族的理解不仅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还包括在20世纪时,被扭曲的民族意识的影响。在德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被证明,它在构建和组织国家中所显示出的力量,正如它的破坏力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强大。*Weidenfeld, Korte (1993),第474页。
民族主义的概念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在德语的日常用语中。它取代了爱国主义的概念,增加了统合民族主义(法国学者查尔斯·莫拉斯创新的概念)中新情感,非理性(准宗教的)元素和神话传说式元素。民族主义在人类学上的特征表现为,语言、血统、文化和地域上的统一。它始终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解放诉求相关联。并且,往往是与陌生人群和其他人群的一种极端对比和矛盾,并对其压迫的理由。在民族,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概念范围中,有社会心理学、现象学和沟通理论的三个层面。*Weidenfeld, Korte(1993),第474-475页。在心理学的层面中,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在德国经历了夸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之后,民族主义在道德上的负面影响一直都被保留了下来。作为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加强了民族主义。”*Kohn(1950),第42页。民族主义将意识形态转移到民族中的政治民众身上:民族主义的兴起作为一种替代性宗教,出现在宗教世俗化过程中的真空地带,特别是19世纪现代主义产生之后。“民族意识(或一个民族)仿佛是自然而然产生,经过“人工”加工和历史的发展。“自然”,是对它的误解。……民族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Vogt(1967),第 22页。民族意识的精神集体很少通过自我的经验,社会本能或经济联盟而产生。它是通过情感教育,通过对自然家园优势意识的宣传而产生的。“民族是被创造的”*Sulzbach(1962),第142页。:构建和传承共同的历史*Vogt (1967),第27f页。,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进行识别并对文化的共同性加以神秘化。*Lemberg (1971),第 200页。
民族在现象学的层面中被划分为文化构建或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在德国,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是以共同的语言,历史,宗教和血统为目标的。民族国家(例如,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君主政体和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定义为,不同种族因命运和情感上的共同体而忠诚的形成一个国家观念。(见案例分析2,Georg Dehio和李格尔(Alois Riegl)之间的讨论)。
在沟通理论层面中,民族主义是19世纪现代主义在欧洲开始产生后才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它也需要通过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增长趋势,匿名的、持续的在象征和准则教育上进行沟通。其中包括国家(民族)节日(nationale Feste)、国歌(Nationalhymnen)和新建立的国家(民族)纪念物(Nationaldenkmäler)。“民族意识同样可以改变,如事实、数据和象征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它是通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被传播的。民族意识不会超越人类的决定范畴和责任范围。”*Krockow (1960),在Vogt (1967),第 45页。
3.记忆与回忆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对记忆和回忆的主题讨论,至今仍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特殊领域。在此,要特别强调一下引起这一现象的三种因素*Böhme, Matussek & Müller(2002),第148-149页。:计算机技术在记录和储存容量上的应用、人类的记忆过程在神经科学的新见解和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对逐渐消失的大屠杀的证人和与他们相对应的历史研究的轻视和局限性。一般来说,记忆是大量的、模糊的“形象和图像的保存地点”。回忆是“唤醒所保存的记忆”,并“对其进行再次思考,是有意识地重现图像,并对图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重新搜索和重新发现”*Jünger (1957),第14-15页。。与此同时,回忆就具有了一种创造性。因为,回忆是被定义为有生命力的,并与现实的内容和重点相符合。回忆是“被过去滋养、在当代和未来传承中的有创造性和充满活力的行为”*Jäckel,Weymar (1975),第190页。。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著作《记忆和它存在的社会条件》(1925年)是当今再次发起对法国和德国之间的集体和文化记忆讨论的起点。哈布瓦赫认为,社会集体框架下记忆是“结果,是总和,是众多社会成员的个人回忆的组合……来重建一个过去的社会和谐时代”*Halbwachs (1966),第195页。。因此,回忆的过程,重建的(规范的)过去,依附于对个人和集体回忆框架的叠合。遗忘可以因此被定义为类似消失或变换,在相同框架的变更、社群的习惯性小动作*Halbwachs(1966),第382页。、社会(集体的)记忆是集体回忆的混合物。集体记忆可以被描述为具有集体特征和持续性(民族的记忆)、有意义、被需求的过去回忆和当前各自有关的框架体系。历史记忆与此相反,是抽象认同的历史。“过去在哪里不被回忆,也就是说,需要被激活,历史就被搬出来。”*Assmann (1992),第 44页。目前,记忆形式命名范围明显增加。历史和记忆作为区分回忆的“两个模式”*Assmann(2003),第134页。,分别被称为功能性记忆和存储性记忆。功能记忆作为“居住的记忆”显示出“群体关系、选择性、价值构建和定位未来”的特点,它失去了“储存记忆”,是“回忆的回忆”、是“充满活力的现代关系”。可以被看作“未来功能记忆的储备”。类似的定义还存在于现实世界和纪念物中。第一个概念是一种液态形式,是现有的、贴近日常生活的、文化上的(个别的)观念世界(近视野)。第二个概念是世代加固的、令人兴奋的建构(远视野),纪念物建筑也属于此类*Assmann & Harth(1991),第14页。。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的“交流记忆与文化记忆”进行划分,过渡区域被描述为履历经验回忆与已经确定、得到论证的回忆之间的浮动距离:“在文化记忆中历史事实被回忆,并以此转化为神话。”*Assmann (1992),第 52页。主观的、个别的回忆世界和感官世界的情况,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它影响了人文学科中备受赞誉的典范转移*Assmann & Harth(1991),第13页。,同时也影响到纪念物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环节:不是更复杂的“集合的—层位”(回忆作为地层学中的沉积物),而是历史处于中心位置。不再是现实的过去(并不是很遥远),而是它们如何被回忆和进入视野的方式与方法。目前回忆作为在(所谓的、可控的)历史之前的本真性过程被讨论:“作为一个文化母体,是历史集体记忆和历史成就,而不是周期性对过去的新诠释的道德化倾向的历史判断和在新的文化记忆中的文化形式。”*Hölscher (1995),第156页。回忆作为一个提示,一切都随着回忆文化被(追溯的)合法化和工具化。回忆的更新是往往通过回想起来的单因的、无复数的、构思的“记忆之场”*在此类书中,有P. Nora法语的Les Lieux de mémoire(Paris, 1984-92); M.Isnenghi意大利语的I luoghi della memoria(Bari, Roma, 1996-1997); E.François 和 H. Schulze《德意志的记忆之场》(München, 2001); E.Brix, E. Brückmüller H. Stekl Memoria Austriae(Wein, 2004-05). 关于德国的记忆之场的研究,参见本文的范例分析6。(不是回忆复数的记忆地点)的传播结构,同时也构建了有问题的纪念物。从科学认知的角度,纳入、选择、保护收集的建筑文化记忆(作为纪念物研究)不再处于中心位置。而是具有情感的、回顾的、追溯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主动的回忆*Boehm (2000),第84页。符合当代的利益格局,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案例分析中,统一后的柏林,新保守主义和民族正常化,用回忆来自然而然的唤起德国的回忆(不是记忆)的一部分,对纪念物保护的影响以及怎样论证这一荒谬。
4.历史意识
每一个挑战自我认知的民族,很少像现在的德国人这样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如此多层次的答案。在德国人的常见经验视域,他们的集体历史意识发展的不健全。人们已经找出了许多答案。*Weidenfeld, Korte (1993),第149页。
“历史意识适应于个人文化和社会需求。特殊形式的意识在个人需求、必然性记传、社会准则和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使之均衡、调整方向、反射、实质性的补充、重估和修改的连续过程。”*Lutz(2000),第35页。个人的历史意识摆脱了集体模式,政治文化表现出的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灵活的系统。历史意识是“一种平衡和转换的系统”*Borries (2001),第240-241页。,它具有五种功能:经验、回忆、定位、阐明和情节*Lutz(2000),第41-42页。。经验沉淀在四个编码层中。当传记的经验回忆在意义和延续性的个人回顾幻想中被加工的同时,个体一生的社会记忆会延伸到集体交流的记忆中。撰写文化(文化特殊的)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从中选择一个作为正式的(文化特殊的)版本,例如,民族史。同时,作为一门有条理的学科,要求对其进行跨文化、多角度和客观的思考。不断的疏远和制度化传记经验,使社会记忆、文化传统和科学方法论阐明了一个渐进的抽象概括和普遍化的历史。纪念物的构建,必须统一个人与集体经验和正式的具有客观的历史观的建筑遗产。记忆重建图像替代过去,整个过程的内在意义被选择、解释和期望所钳制(参照回忆与记忆的难点一段)。历史意识的形成取决于回忆经验的深度和类型。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实践,组成了社会群体。历史意识的导向作用表现在选址、确定过去的连续性和未来的构想上,并且受到特定的社群时间文化的限制。时间层面上的适度连结是360度的视野*Jeismann (1985),第16页。,但是可能被社会禁忌、压抑的历史时期(无力悲伤,没有能力悲伤,米契利希)逐渐隐去、越过与被过分强调所破坏。例如,在历史贬值的美学饰物中作出补偿,是与现代变革和丧失的经验对立的。或者通过怀旧与优美转变的乌托邦来面对对陌生的恐惧。解读,作为对历史的加工,要平衡认知上的理解、道德上的裁决、情绪上的波动和符合美学观点的历史认同之间的关系。解读历史是要努力争取个人和集体的政治行为的(通常是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随着文明的现代化频率越来越高,决定了行动过程是影响深远的,动态的历史关系需求也随之增加*Lübbe(1990)。。(参看案例分析4,未来学与纪念物保护的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再次)产生构建纪念物保护的理由。适应和改造的历史意识是“社会内部所产生的沟通和交涉进程,但也是由内心妥协而产生的。”*Borries (2001),第270-271页。在民族、集体安静的、或者“平常的”时期,很少有存在的需求和理智的讨论。然而,在危机时期,这种对历史准确的、基础的解释和思考(所谓的)的需求会日益增长,从而加强成功的榜样力量。参考历史,这种正当性来自历史也通过历史,属于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现的基本战略之一。所以,历史被滥用的风险很高:“历史给人们的留有民族主义、人种的或者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可选择通过再创新和用神话取代的形象,……以及过去的辉煌背景在现实的意义。”*Hobsbawm (1994)。
5.本真性
没有什么是本真的。没有一个物品或文件自身是本真的,或自身是正宗的。物质不可能存在本真特征。本真性相当于沉着等待消息的接收器……本真性总补充的。他有着双重目的,为了使一个对象形成另一个对象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可想象的、甚至是可能合理的消除对这种言论和行为的怀疑。接收器可以有通信的功能,或在信息的内容上怀疑“他们的(信息)”真实性*Schellin(1999),第44-45页。。
本真性作为接收端可以决定是否接收一则消息。在希腊语中的“本真性”这个词是对创作者、输出者、真实性、可信性、可靠性,或“文章的真正来源”的表述。延续在拉丁文里的“auctor”中,含有创作者、创造者、权力、责任、证据和文档的意思。本真的在艺术史术语中,相当于原件(Original真实的起源)。用于区分复制品(Replik原作者自作的)、仿制品(Kopie)、复制品(Reproduktion非原作者自作的)和假冒品(Fälschung):“原件(Original)含有较高价值的信息,其影响、魅力、光芒和原始的力量可以规避言语上的不足。”*Hoffmann (2000),第 32页。原始价值相当于对神圣的圣人遗骨(宗教文物)的真实性(Echtheit)的辨别,其本真性已由当局确认(教会,最初只有通过他们)和证实。在现代主义出现之前的“传统年代”,本真性主要是关于神秘或者宗教上的崇拜。伴随纪念物保护学科的出现,“现代”的本真性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道德素质”的本真性,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和他们的行为模式有关,另一方面与文化、时代性、历史和物质对象的素质也有联系。事实证明在信仰改变的进程中,有争议性的纪念物理论的主要聚焦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纪念物具有准确积累的时间遗迹,它可以作为真实的、传统的权证;另一方面,纪念物与它推测的原始状态保持风格上的统一,返璞归真。具有本真性概念的纪念物日渐形成,作为物质证物,建设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观,而把这种价值观建设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科学的纪念物价值理论是由奥地利学者李格尔提出,为20世纪的“现代纪念物文化”*Riegl(1903)。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隐喻形象的废墟,同时也反映了人类过去的生存状态。因此,“旧有的价值”扮演着中心角色,它是历史的轨迹和注定的历史状态。特别是在有遗迹的隐喻画面中,人类短暂存在的镜像。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进步的以及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它的序言中,以人性化为任务、历史古迹作为“精神上的过去信息……充分丰富其本真性”*Charta von Venedig 1964。和明确地反对重建。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签订的《世界遗产公约》,用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自1977年起,将评定文化对象的标准制定为:是为了保证本真的形式、材料、技术、功能和地域联系。不断的进步伴随着批评和新双重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纪念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个别的、形象化的、感情上的情绪值。首先是《威尼斯宪章》中禁止重建的局限性、“新的理解、意会”和纪念物的“神话潜力”*Lipp, Petzet (1993)。。纪念物保护的任务是保证将科学文化记忆(作为回忆的潜质)转化为积极的、生动的和具有固定现实意义的回忆,进行塑造。“在后现代社群中,必须考虑他们的历史被辩解是多样性的和多元文化的”*Bacher (1999),第80-81页。,这种历史往往是多重的,廉价而随意的。因此,以科学为基础的批判对此表示不满。纪念物的基本研究是对每个本真性评价的基础,排除了被扩大的本真性。以欧洲为中心立足的纪念物保护的高潮,是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奈良真实性会议”进行的讨论,它是一次对全球化有利的“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Larson (1995),第 xiii页。的讨论。
在欧洲,“铁幕”政策下和战后的相对重新定位的关于重建的讨论,使得尤其是在德国被建立起一个臆想的、更好的历史之前的历史(Vor-Geschichte),一个新的标尺和有效半径。“今天,本真的纪念物和重建的回忆性建筑被看作是相互竞争的,在不同社会的力量与不同的维护认知之间竞争。”*Buttlar (2002),第14页。在模拟虚拟空间的数字媒体时代的新经验世界里,原始纪念物保护的保存任务转变为新商业领域和意识形态上的有积极性的光明世界(失落的“光芒”*Benjamin (1997)。)。
6.传统
真正丢失的传统在美学上是不能被代替的……在真正的、传统的、过去的艺术品形成的瞬间,意识上对它的膜拜就像对圣人的遗物一样。这种意识形态,其从组成部分中分离,在过去和现在被欣赏。除非通过增加奴役和贫困,这样爱就不能被施展出来,很快一种不忠的、使人振奋的误解就招惹了是非。关于目前自身的讨论,他认为并不是如此糟糕……在操作普遍认可的文化财产过程中,臆想的、不难看的都会被并入其中。同时,有意义的古老的形象因为拯救而被破坏。他们所拒绝恢复的,是他们的曾经。*Adorno (1967),第31-32页。
传统(拉丁语:traditum)包含了所有现代对过去的传承,没有关于作者、知识、真理、标准、内容、时间和传播方式。传统作为一个主动的功效过程,是文化动力的结果,具有“世代流传的连续性”。传统包含传世的物质对象、信仰、个人形象和事件、实践和制度——其中包括建筑物、古迹、景观、雕塑、书籍、工具和机器。*Shils (1981),第12页 (M.F.翻译)。通过对传统适应的过程——而不是通过内容上平缓引证传统(参见引文)——人们通过适应、工作和学习,来获得文化稳定和社会稳定(对所处文化的适应,教化思想)。传统也可以通过长期的社会性、规范性的回忆和自我诠释重新建立。传统提供了一个累积性的、选择性的和充实的文化总额(体积)。革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个压缩选择过程得以实现。*Nahodil(1986),第171页。“传统是一种精神社会的机制和人类的社会本能。人们获得传统的方式,是用自己的一生来检验和丰富,与持续不断的辨识,然后在短时间内交给接下来的一代。通过这种交接,社会内在联系的延续性、认同得以完成。”*Fuchs (1975),第177页。传统依据的是一个普通神话的延续。传统可以被定义为持续存在的、认同的文化结构。可是,这种持续必须取得连续的时间作为中断的、忘记的、变化的和局限的维度。传统作为典范适用于普遍的文化记忆:他们建立了并且制度化了集体记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论述与(生活的)时间相关,并持续被构建,认同危机则可以追溯到新旧传统的同时性。传统的概念、当代批评和阻力的变化(通常是在单数)被直接作为在文化方面上的竞争。即使本身传统文化内在发生过程中具有永久性,政治调用的“优良传统”往往标志着文化停滞和不确定性。压抑和没有清理的再生残存的传统可能会导致后代极端肯定与极端否定的冲突(参见案例4,《1968年这一代》)。无论是在传统社群或者高度的工业化的社群中,起到监督作用的有关当局或机构都要被完善,因为他们规范了文化的传播过程。在19世纪,建立保护机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压缩文化(国家)遗产、文化和民族之间的联系。艺术科学开端是整理艺术品与其相关的文化,通常有民族的——记录的风格——传统(例如,哥特式作为德国的风格)。传统通过内源性因素(合理化、政治的变化、道德和信仰)和外源性因素(例如,人口、政治、军事和经济)改变。传统可以改变(分支)合成、修改和更换、吸收合并、分解、重组和稀释。国家共同体积极进取的思想改造的过程(或模拟)的传统经常结合“传统的发明”*Hobsbawm, Ranger (1983)。的现象:通过集体灌输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公约来实现,主要目标是经验、解释和内存的同质化。因此,大多数的起因和动机是因为当代世界持续的革新、不变的尝试创新和没有变化的社会生活。臆造的传统可能从旧有传统的单一部分产生,并带有新的意图。他们往往只填写局部出现的空白——空隙,创建符号(旗帜,国歌,纪念物等)和经常代替真正传统的(带有不正确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臆造传统的动机是自由民族的需求,是宣传教育的主要部分,用来揭穿在一定程度上混乱的、往往是灾难性的(民族)神话。
7.神话传说
“神话”在希腊语中的最初含义是“生动的被讲述的词”*Hochgesang(1969),第11页。。“神话是从历史中被选出的故事……是一种传播体系、一种公告。它不是一个有概念和观点的对象。它是一种说明的方式、一种形式……什么都可以,一种可能把责任放在一边地谈论,这就是神话”*Barthes (1996),第85-86页。:神话没有命题上的限制。任何的物质—特别是纪念物—可以通过神话描述来创作的绘画作品,具有格言的特点。神话没有脱离所选物质的现实意义,它运用他们,“含义失去它的价值,但它仍然活着,作为历史储备的一种形式。”*Barthes (1996),第97页。被分别挂上了所要表达的价值。神话没有隐藏它的变形、历史来源部分和其疏远的意义。它冒充信史和事实,并提供有意义清楚的图像。从而,它被作为“绝对的反—启蒙的”*Schmidt, B.(1986),第115页。来诠释。因此,不仅讨论和“揭露”神话制造的来源,而且包括它的制造者,至今仍是继续发展和宣传的任务。神话的构建是几乎总是与大众媒体相结合的。纪念物通过建筑设计是特别适合被赞扬和被神化的。
但同时,神话也具有“能动”的特征、特殊的辩证的和模棱两可的含义。神话指导和调节了要求上的规范和神话形成的动力:“有些神话只有显著的过去的记忆,也就是说,只记得过去也是很重要的。记忆是一种有用的、基础的语义符号(语义符号学)。”*Assmann (1992),第76f页。神话对反启蒙方面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从而也奠定了基础。并在当代已经产生了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是不可逆转的。它的作用是缓慢的唤醒具有少量现存经验的历史时代。它总是一个被民族主义滥用的工具:“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需要一个神话视角下的过去,用来作为他们赢得政治信仰的手段。”*Sked(1991),第120页。这样神话一再显示出,过去的力量对当代的影响。被宣称不易改变的,同时也被否定了未来:“在众多神话中,尤为重要的是新神话——“一个隐藏过去的行为”,目的是在未来推动人们超越已经习惯的情况。”*Schrödter(1991),第11页。通常,民族神话是在紧要关头被调用的,与其民族回忆相联系:无论是含糊不清的、还是完全纯粹的当代兴趣,使得民族的回忆场所工具化,包括很多重建的“回忆性建筑”,这些建筑常常是利用了新神话。在本文中,也会对他们的背景和拆除做出分析。(尤其是最后一个案例,在时间更贴近1990年以后的历史时期)。
1.Adorno, T.W., 1967, Über Tradition. In: Ders. Ohne Leitbild. Prava Aesthetica, Frankfurt am Main.
2.Alings, R., 1996,Das Bild vom Nationalstaat im Medium Denkmal — Zum Verhältnis von Nation und Staat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871-1918. Berlin, New York.
3.Arlt,H.(Hrsg.),2002, Erinnern und Vergessen als Denkprinzipien. St.Ingbert.
4.Arndt,K.,1981,Denkmaltopographie als Programm und Politik.In: Kunstverwaltung, Bau- und Denkmalpolitik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Band 1. Berlin.
5.Assmann,A.,Harth,D.(Hrsg.),1991,Kultur als Lebenswelt und Monument. Frankfurt am Main.
6.Assmann,A.,1995,Funktionsgedächtnis und Speichergedächtnis — Zwei Modi der Erinnerung. In:Platt,K.,Dabag, M.,1995,Generation und Gedächtnis. Erinnerung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en. Opladen.
1999,Zeit und Tradition. Kulturelle Strategien der Dauer.Köln,Weimar,Wen.
2003,Erinnerungsräume.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München
7.Assmann,J.,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8.Bacher,E.,Kunstwerk oder Denkmal — Distanz und Zusammenhang.In:Lipp,W., 1993, Denkmal,Werte und Gesellschaft — Zur Pluralität des Denkmalbegriffs.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1995,Alois Riegl, A.Kunstwerk oder Denkmal.Wien,Köln,Weimar.
1999,Authentizität,was ist das? In: Arbeitshefte des Bayerischen Landesamtes für Denkmalpflege. Arbeitsheft 100, Sonderdruck.
9.Bargatzky,T.,1985,Einführung in die Ethnologie.Hamburg.
10.Barthes,R.,1996,Mythen des Alltags.Frankfurt am Main.
11.Benjamin,W.,1997,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Frankfurt am Main.
12.Bense,M.,Walther,E.(Hrsg.),1973,Wörterbuch der Semiotik.Köln.
13.Beyme,K.v.,1981,Das Kulturdenkmal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Zur Frage einer inhaltlichen Differenzierung des Denkmalbegriffs.
14.Boehm,G.,2000,Die Gegenwart des Vergangenen.In:Meier,H.-R.,Wohlleben,M.,2000,Bauten und Orte als Träger von Erinnerung.Die Erinnerungsdebatte und die Denkmalpflege.Zürich.
15.Böhme,H.,Matussek,P.,Müller,L.,2002,Orientierung Kulturwissenschaft.Was sie kann,was sie will.Reinbek.
16.Boockmann,H.,1981,Denkmäler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as Geschichtsbewußtsein.Göttingen.
17.Borries,B.v.,2001,Geschichtsbewußtsein als System von Gleichgewichten und Transformationen.In:Rüsen,J.(Hrsg.),2001,Geschichtsbewußtsein. Psychologische Grundlagen,Entwicklungskonzepte,empirische Befunde.Köln,Weimar,Wien.
18.Brandt,S.,2003,Geschichte der Denkmalpflege in der SBZ/DDR.Dargestellt an Beispielen aus dem sächsischen Raum 1945-1961.Berlin.
19.Buttlar,A.v.,2002,Welche Vergangenheit für unsere Zukunft.Anmerkungen zur Reproduzierbarkeit historischer Architektur.In: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sverein zu Berlin (Hrsg.).Berlin.
20.Charta von Venedig 1964.In:DKD 1989,Heft 2.
21.Duroy,R.,Kerner,G.,2004, Wahr oder falsch. Denkmalpflege als Medium nationaler Identitätskonstruktionen.Berlin.
22.Dolff-Bonekämper,G.,2004, Wahr oder falsch. Denkmalpflege als Medium nationaler Identitätskonstruktionen. Göttingen.
23.Eco,U., 1972, Einführung in die Semiotik. München.
24.Elias,N.,1989,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ämpfe und Habitusententwicklung im 19.und 20.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25.Fuchs,W.P.,1975, Brauchen wir Tradition.In: Jäckel,E., Ernst Weymar,E.(Hrsg.),1975, Die Funktion der Geschichte in unserer Zeit. Stuttgart.
26.Gauger,J.-D., 1986, Heimat-Tradition-Geschichtsbewußtsein—Bemerkungen zu einem vermuteten Zusammenhang. Mainz.
27.Geertz,C.,1973,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
1995,Dichte Beschreibung. Beiträge zum Verstehen kultureller Systeme. Frankfurt am Main.
28.Gellner,E.,1997, Nationalism. London.
29.Gerbel, C., Musner,L. Wunberg,G.(Hrsg.),2002, Kulturwissenschaften.Forschung-Praxis-Positionen. Wien.
30.Geyer,K.-F.,1994, Einführungen in die Philosophie der Kultur. Darmstadt.
31.Giesen,B., Junge,K.,1991, Vom Patriotismus zum Nationalismus. Zur Evolution der Deutschen Kulturnation. Frankfurt am Main.
32.Halbwachs,M., 1966, Das Gedächtnis und seine sozialen Bedingungen. Berlin, Neuwied.
33.Haußer,K.,1989, Identität. In: Endruweit, G., Trommsdorff, G., 1989, 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Bd. 2, Stuttgart.
34.Heuss,A., 1959, Verlust der Geschichte. Göttingen.
35.Hobsbawm,E.,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on. Cambridge.
1994, Die Erfindung der Vergangenheit. In: Die Zeit, 34/1994.
36.Hochgesang,M., 1969, Mythos und Logik im 20. Jahrhunder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neuen Naturwissenschaft, Literatur, Kunst und Philosophie. München.
37.Hölscher, L., 1995, Geschichte als Erinnerungskultur. In:Platt, K., Dabag, M., 1995, Generation und Gedächnis. Erinnerunge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en. Opladen.
38.Hölzle, E., 1996, 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 Bern, München.
39.Hoffmann, D., 2000, Authentische Erinnerungsorte oder: Von der Sehnsucht nach Echtheit und Erlebnis. In: Meier, H.-R., Wohlleben, M., 2000, Bauten und Orte als Träger von Erinnerung. Die Erinnerungsdebatte und die Denkmalpflege. Zürich.
40.Huse, N., (Hrsg.), 1996, Denkmalpflege—Deutsche Texte aus drei Jahrhunderten. München
41.Jäckel, E., Weymar, E., (Hrsg.), 1975, Die Funktion der Geschichte in unserer Zeit. Stuttgart.
42.Jeismann, K.E., 1985,Geschichte als Horizont der Gegenwart. Paderborn.
43.Jünger, F.G., 1957, Gedächnis und Erinnerung. Frankfurt am Main.
44.Kiesow,G., 1988, Identität- Authentizität — Originalität. In: DKD, Jg.46, Heft 2.
45.Kohn, H., 1950, Die Idee des Nationalismus. Heidelberg.
46.Koshar, R.,1998, Germany’s Transient Pasts: Preserv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
47.Krockow, C.,1960, Nationalbewußtsein und Gesellschaftsbewußtsein.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1960. Opladen, Köln.
48.Larsen, K.E., (Hrsg.), 1995.Nara Conference on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roceedings. UNESCO, ICCROM, ICOMOS. Tokyo.
49. Lemberg, E. 1971, Ideologie und Gesellschaft. Eine Theorie der ideologischen Systeme, ihrer Struktur und Funktion. Stuttgart.
50.Lenk, K. (Hrsg.), 1976,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und Wissenssoziologie. Darmstadt, Neuwied.
Lipp, W., Petzet, M. (Hrsg.), 1993, Vom modernen zum postmodernen Denkmalkultus? Denkmalpflege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7. Jahrestagung der Bayerischen Landesamtes für Denkmalpflege. München.
51.Lowenthal, D.,1994, Changing Criteria of Authenticity. In: Larsen K. E. (Hrsg.), 1995, Nara Conference on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roceedings. UNESCO, ICROM, ICOMOS. Tokyo.
52.Lübbe, H.,1981, Zwischen Trend und Tradition- überfordert uns die Gegenwart? Zürich.
Lübbe, H.,1990, Der Lebenssin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Über die moralische Verfassung der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n Zivilisation.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53.Luhmann, N.,1981, Identitätsgebrauch in selbstsubstitutiven Ordnungen, besonders Gesellschaften. In: Ders.,1981,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Band 3. Opladen.
54.Lutz, F. P.,2000, Das Geschichts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 Grundlage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in Ost und West. In: Rüsen, J. (Hrsg.), 2000, Beiträge zur Geschichtskultur. Bd. 19. Köln, Weimar, Wien.
55.Marquard, O., Stierle, K. (Hrsg.), 1979, Identität. München.
56.Mead, G. H., 1980, Geist, Identität und Gesellschaft aus der Sicht des Sozialbehaviorismus Frankfurt am Main.
57.Meulemann, H. (Hrsg.), 1998, Werte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Opladen.
58.Musner, L., Wunberg, G. (Hrsg.), 2002, Kulturwissenschaften. Forschung- Praxis- Positionen. Wien.
59.Nahodil, O., 1986, Traditionen als Sicherheit in einer pluralistischen und mobilen Gesellschaft. In: Weigert, K. (Hrsg.), 1986, Heimat-Tradition-Geschichtsbewusstsein. Mainz.
60.Nipperdey, T. 1976a, Die anthropologische Dimensio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1976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and 18. Göttingen.
1976b, Nationalidee und Nationaldenkmal in Deutschland im 19. Jahrhundert. In:
1976,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neueren Geschichte. Bd. 18. Göttingen.
61.Platt, K., Dabag, M., 1995, Generation und Gedächtnis. Erinnerunge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en. Opladen.
62.Posner, R., 1991, Kultur als Zeichensystem. Zur semiotischen Explikation kulturwissenschaftlicher Grundbegriffe. In: Assmann, A., Harth, D. (Hrsg.), 1991, Kultur als Lebenswelt und Monument. Frankfurt am Main.
63.Pross, H., 1983, Hierarchie der Wert- Horizont der Zeichen. In: Reimers, K. F. (Hrsg.), 1983, Zeichenentwicklung-Bedeutungswandel- Handlungsmuster. Zur Semiotik undsthetik sozialer Kommunikation. München.
64.Reck, S., 1981, Identität, Rationalität und Verantwortung.Grundbegriffe und Grundzüge einer soziologischen Identität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65.Reimers, K. F. (Hrsg), 1983, Zeichenentwicklung- Bedeutungswandel- Handlungsmuster. Zur Semiotik undsthetik sozialer Kommunikation. München.
66.Riegl, A., 1903, Entwurf einer gesetzlichen Organisation der Denkmalpflege in Österreich. In: Bacher, E., 1995, Alois Riegl. Kunstwerk oder Denkmal. Wien, Köln, Weimar.
67.Rüsen, J. (Hrsg), 2001, Geschichtsbewusstsein. Psychologische Grundlagen, Entwicklungskonzepte, empirische Befunde. Köln, Weimar, Wien.
68.Schaff, A., 1973, Einführung in die Semantik. Reinbeck.
69.Schellin, D., 1999, Denkmäler und schnellere Medien- Authentizität im Medienzeitalter. In: Deutsches Nationalkomitee für Denkmalschutz (Hrsg.), 1999, Auf dem Weg ins 21. Jahrhundert- Denkmalschutz und Denkmalpflege in Deutschland. Band 61. Berlin.
70.Schmidt, P., 1998, Nationale Identität. Nationalismus und Patriotismus in einer Panelstudie 1993, 1995 und 1996. In: Meulemann, H. (Hrsg.), 1998, Werte und nationale Identitä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Opladen.
71.Schmidt, B., 1986, Postmoderne- Strategien des Vergessens. Darmstadt.
72.Schrödter, H. (Hrsg.), 1991, Die neomythische Kehre. Aktuelle Zugänge zum Mythischen in Wissenschaft und Kunst. Würzburg.
73.Sedlmayr, 1998, Verlust der Mitte. Die bildende Kunst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als Symptom und Symbol der Zeit. (Erstausgabe 1946). Salzburg, Wien.
74.Shils, E., 1981, Tradition, Chicago.
75.Sked, A., 1991, Die Mythen von europäischer Einheit. In: Weidinger, D. (1998) Nation-Nationalismus-Nationale Identität.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rsg.) Reihe Kontrovers. Bonn.
76.Speitkamp, W., 1996, Die Verwaltung der Geschichte. Denkmalpflege und Staat in Deutschland 1871-1933. In: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and 114. Göttingen.
77.Stauth, G., 1999, Authentizität und kulturelle Globalisierung. Paradoxien kulturübergreifender Gesellschaft. Bielefeld.
78.Sulzbach, W., 1962, Zur Definition und Psychologie von Nation und Nationalbewusstsein. In: Vierteiljahresschrift Juni 1962.
79.Tragatschnig, U., 1998 Konzeptuelle Kunst: Interpretationsparadigmen; ein Propädeutikum. Berlin.
80.UNESCO, 197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Paris.
81.Vernant, J.-P., 1984, Mythos ohne Illusion. Frankfurt.
82.Vogt, H., 1967, Nationalismus gestern und heute. Texte und Dokumente. Opladen.
83.Weidenfeld, W., Korte, K.-R., (Hrsg.), 1993,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 am Main.
84.Weidunger, D. (Hrsg.), 1998, Nation—Nationalismus-Nationale Identität.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rsg.) Reihe Kontrovers. Bonn.
85.Weigert, K.(Hrsg.), 1986, Heimat-Traditon-Geschichtsbewußtsein. Mainz.
[责任编辑]王霄冰
[德]米歇尔·法尔瑟(Michael S. Falser),男,哲学博士,已获得教授资格。德国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全球语境中的亚洲和欧洲”精英团队成员,“全球艺术史”项目负责人。韩迪菲(1983-),辽宁大连人,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研究生。
G122
A
1674-0890(2017)04-075-16
* 本文为该作者提交给柏林工业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的序言部分。正式出版的版本信息:Michael S. Falser.ZwischenIdentitätundAuthentizität.ZurpolitischenGeschichtederDenkmalpflegeinDeutschland. Dresden: Thelem, 2008.获作者授权翻译。中译稿因篇幅关系,译者删去了原文中的部分脚注内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