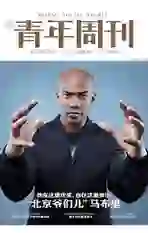一直不变的是一直都在变化
2017-08-15王跃张小斐
王跃+张小斐
人的生命七年会完成一次代谢,得到新生。而对于一项事业,七年也是一次蜕变。青年艺术100,便在今年迎来了它的第七个年头。主题“破折号”,寓意“破局”与“转折”。
8月1日到8月15日,2017年青年艺术100启动展正在今日美术馆二、三号馆里盛大举行。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150余位青年艺术家的400余件艺术品,涵盖了油画、国画、版画、雕塑、装置、影像、行为艺术等,全面、立体地呈现出青年艺术最鲜活的生态。
与艺术家迟群见面的情景至今令彭玮难忘。迟群的同学是彭玮的同学的姐姐,就凭这么一个七折八绕的关系,彭玮找到了她。当时,迟群刚刚从中央美院毕业一年,租住在居民楼里一心搞创作,一进门,彭玮就看到了摆满屋子的画,画中是抽象的直线和格子,屋里弥漫着颜料的味道,有点呛人。那时的迟群默默无闻,只凭着对创作的自信和对艺术的坚持,不停地画。“许多人不理解她的画,正是在备受打击的境况中,我们找到了她。”彭玮说。在迟群如今已颇具规模的简历上,青年艺术100是她参加的第一个展览。此后,她连续参加了4次青年艺术100的展览。终于,从2014年开始,她受到了井喷式的关注,作品卖出的数量也从前两年的每年2、3幅一下增长到20多幅。今天,迟群已被称为“80后抽象一姐”了。彭玮将青年艺术100比作黄埔军校,在它培养出的一批批青年艺术家中,迟群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青年艺术100好像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竞技平台,艺术总监彭玮介绍,“在开展之前许多艺术家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认为它无非是个展览,而当在同一个空间中,看到其他的作品,他们就会有比较。他们很乐意在这个平台分享,同道中人聚集在一起,相互碰撞后也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艺术家们也因此而产生友情。他们甚至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就叫“青年艺术100”,和其他行业的球队打比赛。创始人赵力说,艺术界以前都是以同校同班、同城、同龄而形成划分,而青年艺术100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不一定名校毕业作品就好,无论是科班或是野生力量,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在这里是平等的。最后,他们也会构成一种新势力——从青年艺术100走出来的。
当然,七年之痒也是有的。“一直都是重复以挑选100名艺术家这种模式,长时间工作下来,肯定就会有一种厌倦情绪。”彭玮坦言。所以,今年的主题叫“破折号”,所谓“破”,即打破原有的限制、规范和经验,“折”即寻求一个转折,一个新的开始。
“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一直不变的就是一直都是在变化。所以每年我们在大的选拔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配合不同时期的环境和艺术家的需求调整,不断推出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启动展场地的变化正印证了这一点。从798里几个零散的空间到在农展馆里呈现的三年艺术大party,这次,青年艺术100走进了今日美术馆。在农展馆办展,为的是让艺术走向大众,回归艺术空间,则需要关注作品与空间,以及作品之间的关系,让青年艺术回归到学术的语境中来。
除了在美术馆里举办启动展,青年艺术100还有其他新动作。在城市中不同场所举办平行展,打造一个ARTMAP,全球艺术漂流计划和A80藏家计划也在进行中。赵力说,今年的启动展将会成为一个青年季,“让青年艺术家拿出作品后进行交流,当季100个人见面讨论,还有往届的加起来就有600多人,这是只有青年艺术100才有的交流。相互提出意见,进行碰撞。作品放在农业展览馆和放在美术馆是不一样的。在美术馆,你感受到对作品的不同层次的批评和赞赏,真是一个全新的生态。”

创立者说
Q:七年中,青年艺术100见证了青年艺术生态和艺术家群体的哪些变化?
赵力:上世纪90年代时青年艺术家大多在北京北漂,条件也不好,2000年左右,在中央美术学院周围就有很多艺术家聚集;而近五年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像谢天卓这种艺术家,他们不愿离开自己创作的土壤,让他来北京他也不来,他怕离开后丢失灵感。在这之前,艺术家想要出名就得来北京。但现在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知道他们,这是之前没有的。现在通过网络,地域差别在变小,我们的平台也能够让艺术家找到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如果所有艺术家都聚集在北京,其他地方的艺术怎么办呢?
创作性的生态也是很好的改变。通过与阳光100合作的丽江雪山青年艺术季活动,艺术家去其他地方进行创作,一方面,好多艺术家可以共同交流,改变了创作者的性格。之前艺术创作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孤军奋战,这次,来自五湖四海的藝术家聚集在丽江,40人规模分两期的丽江驻留计划,这种群居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他们离开创作地,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比如在丽江了解到东巴文化,以此为创作灵感进行艺术创作,比如黄启佑,整个风格都变化了。
Q:青年艺术家在创作上有什么变化?
赵力: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觉得青年艺术家更注重个人风格,怎么比别人画得好,画的细,还形成自己的风格。现在艺术家好多是留学回来的,视野很广,面很宽,不像之前拘泥于怎么画得好看。他们并不认为艺术分类是重要的,不计较于某一个东西,都去尝试。第一年他参加的作品可能是架上绘画,第二年是装置等等。
第二是艺术家的低龄化,越来越青春洋溢。时间的积累转为视野、创意,创作具有跨越性,比如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互联网方式的创作,先打印后创作。越年轻可能越活跃,这可能会颠覆靠时间来积淀的方式。
第三是创意思维,不是靠技术、年龄,而是靠思维,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现在这么关注艺术,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联想和想象。我们在展览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以创新为主体的群体,这是不可逆的。

评委说
向京: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也会陈腐天性逼人的作品更容易亮眼
Q:你总共做过四届的青年艺术100的评委,这些年青年艺术有哪些变化、收获让您感触较深?
A: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更容易获取丰富多样的营养,但落实在具体工作,原创性变得更艰难了。早期的艺术家可能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凭空造车,或者在误读中理解,自我编造自我说服,自我系统更强大,现在年轻艺术家出国容易,获得资讯容易,而大家的起步差距拉近,特殊性很难做到。
另外,年轻艺术家的生态看似繁茂,实际出来也很难,选拔的平台很多,但后续相关的生态链依然不够健康完善,专业的画廊、美术馆、艺术批评这些重要环节都很缺失,这样的生态不易持久,尤其在艺术家数量逐渐加大的今天。
像青年艺术100这样的项目也是因为这样的生态基础应运而生的,在国外找不到先例,所以做起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早期它只做简单的选拔平台,海选只能做到粗放地收集,真正的选择还得用更细的筛子和更长线的计划,后续深入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抚育工作,在一百里再次遴选,做一些小型的群展个展,这都会深化对青年艺术家的扶助。在中国发展迅速的这些年,任何项目能坚持做几年都挺值得尊敬。他们在向艺博会式的形态发展的同时,也坚持做一些和国外非盈利机构的合作、送年轻艺术家去国外参加驻留项目、学术讨论之类的活动,都是在针对中国现有生态的缺陷和可能性做些有益的尝试。
我参加青年艺术100的评委工作也是对年轻艺术家的生态有好奇,毕竟平时接触有限,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多做一些观察。每个平台都有它趣味上的倾向性,做过几届之后,自然有些类型的艺术家会自动退出。我目前感觉青年艺术100的选拔,不能简单代表当下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状态,真实的创作应该形态更多元。也能理解每个平台自己的价值取向,只有更多这样的平台出现,艺术家的出口才会更多,艺术创作才会丰富有趣。

Q:作为评委,什么样的作品最能打动你?
A:原本是想做个观察者,对年轻艺术的创作状态做个了解,做过几届之后也会看到,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不见得多年轻,很多创作是很陈腐的,这和我们糟糕的艺术教育有关,和艺术生态很多知识输出缺失有关。艺术家的成长没那么容易,艺术院校都在扩招,但教学并没有太大的改进(某种角度看可能更糟)。青年艺术100因为海选范围非常广泛,所以能看到大量的平庸之作。我深刻回忆起自己当老师时的痛苦,很多孩子在学习艺术的道路上,已经走向腐朽,对艺术的理解是范式和套路。成功学的思维又会影响一大批人前赴后继,现今人人都可以轻易获得信息,可惜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创作里的各种车祸也是评选时的槽点和笑点。
作为“前辈”,很多幼稚的套路会被一眼望穿,那种天性逼人的作品反而更容易亮眼。如同艺术需要学习,需要知识抚育,但好的艺术家和好的作品恰恰都是无可解释的,并不凭借既有套路出牌。这种判断全然直觉化,有时就像一种眼缘,从几千张作品里,有一些品质还是可以透露出来,打动人心。这样的作者不多。
而另一方面,学习能力消化能力强的作者同样令人欣赏,只要他/她擅于整合学到的东西,我认为也是新时代赋予人的能力。艺术家需要全面,虽然我们不过是凭着几件作品的图片来挑选艺术家,但參加这样的选拔对参赛者的要求就是更综合的素质,而且在暂时性的选拔之后,未来的艺术之路也只有靠每个人的综合能力来继续前行,我也相信这是时代对于艺术家的要求之一。
迟群:只用单纯的线来真实地表达自我
对应主题“转折”,今日美术馆三号馆内展出了往届青年艺术100中的19位优秀艺术家的最新作品,呈现他们在艺术实践中的蜕变。距离入口很近,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上,艺术家迟群的作品占满了两面墙。可以说,迟群是这里最资深的一位艺术家,也是与青年艺术100缘分最深厚的一位。
迟群是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美院壁画系。2007年正在读研的她,开始将绘画从具象转向了抽象,因为一直成长在学院中,她很想打破学院里传统的绘画方式,她开始思考,“如果只用单纯的线是否能完成自己的表达?然后,我就把这种具象的叙事慢慢地去掉,回归到单纯的线,渐渐地,线越来越丰富,跟我自身的经历、情感相结合起来。”
在对抽象的探索中,迟群是自信的。2010年,她的毕业创作得到师友们的广泛认可,连谭平老师都收藏了她的画。可是,一走出校园,步入社会,她发觉了落差。当时的大环境是,抽象画是个冷门,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作品。有人劝她改画具象,但她坚持。迟群在美院附近的方舟苑小区租了一个三居室,一年中,她继续画她的线,没有展览,也没有卖画的收入。她要靠家里的接济和偶尔兼职教教画应付房租。

那一阵子,迟群在创作中常使用砂纸打磨画板,这投射出她当时的状态:感受到伤害,却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茫然无措。当青年艺术100的彭玮敲开她画室的门时,看到的就是她已打磨到发光的画面,里面还用了不少切线,寓示挫折。彭玮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又带来了赵力。“当时我很紧张,赵老师看了作品后,说了说他的感受,我觉得他是真的理解我。”尤其在面对了很多质疑之后,这份理解愈发显出珍贵。迟群和青年艺术100从此结缘。
2011年,迟群参加了第一届青年艺术100,成为被主推的艺术家。经历了三年的积累和各种机会的曝光后,2014年,她的事业迎来了高潮。她举办了三次个展,作品还去到韩国、澳大利亚、德国、哥斯达黎加展出。今年,她在国外的首次个展《常在——线的世界》将在德国波恩当代艺术馆举办。
七年来,迟群与青年艺术100互相支持,陪伴了彼此的成长——她已从一位籍籍无名的美院毕业生成为人们口中的“80后抽象艺术一姐”,而青年艺术100也完成了第一个七年的蜕变,已成为艺术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Q&A
Q:你作品中线的变化表达了什么情绪?
A:线表达的是我的态度,不想别人直接看到,要有一种转化。我的创作最初是一条线,表达我单纯的一个人。线之间的交叉,表现了我从独立的个人到家庭,身份给了我一种附加,我在秩序里。我老公家里是一个大的家族,他们注重族谱,所以我从一个人的身份进入到他们家族,就会有脉络关系,这种相交的关系给了我一种秩序,我在这种秩序中完成自身。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包括我跟社会慢慢形成的一种融合的关系,线从浅层到复杂。这是我个人经历的展示。

Q:你新作品《四条线-灰绿》的灵感来自哪?
A:其实我当时想要这个线有秩序的变化,这几条线系列化,并形成很好的衔接,从形式上我怎么把经历放在绘画的背后,它是含蓄,有深度的。去年我生了小孩,从家庭到有孩子的过程,经历了好多身份中的交叉关系,我如何调配自己去适应这种关系,让自己能更加单纯地抽离自身,但这个东西是背后的影响。作为妈妈和家庭的关系,可以说是力量和限制。
Q:你的作品颜色饱和度都很低,为什么?
A:之前浓烈的蓝色、紫色对我的冲击太大,当尝试过浓烈后,想用色彩将它裹挟住,融合在里面,希望远观是灰色,近处看则是有层次、有包容度、有厚度的。我自身的感受是,颜色是一种退在后面的,欲说还羞的状态。
波河沿岸:观看的理想状态,日常经验的非日常化
“波河沿岸”在意大利文中是“Lungo Po”,是都灵市中心一条与波河紧邻并行的街道的名字。波河是意大利最大的河流,那条名为“Lungo Po”的大街就是小组主创张柘、李歌吟、郭梁曾居住生活、各自进行艺术创作的地方。他们都曾就读于都灵国立美术学院,成为朋友,2015年回到北京后,因对艺术的共同理念而创立了艺术小组“波河沿岸”,这名字是对他们过往生活经验的记忆。后来,从加拿大学习版画归国的王雪宜也加入其中,就形成了现在的四人阵容。

他们拥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也会进行版画教学,以及和其他领域的跨界合作。四人个性鲜明,平时他们会进行独立的创作。王雪宜喜欢做与现代生活有一定距离的,有点神秘感,需要想象的东西,她会被中世纪的元素、被纸的古老和自然而吸引。李歌吟喜欢新媒体,会因具体的事件触发而产生一个主题,后续地去创作。比如朋友的妹妹被家暴流产,她便以B超为主题设计出一个装置,后来又用地毯等不同材料进行持续创作。张柘学习的是绘画,后来发现绘画不足以表现其想法,又开始做装置,他对“认知”、“身份”进行着持续的思考。而郭梁进行摄影、装置和视频的创作更多,更关注人的命运和感情。

当然,他们在一起也会经常碰撞出有趣的点子。比如,这次参加青年艺术100的装置作品《不竭之棰》系列。他们用单面反光的玻璃制作出四个盒子,盒子里的每个面是镜子,盒子外面是玻璃,树枝从盒子里生长出来,从任意角度都可以看到无尽的反射,“通过透视反射制造出来的视觉效果,跟你观看的物,有一个互动,它改变了你与直接观看的物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有实体将它禁锢住,你就无法触碰到它。我们试图营造一个无限的观看空间,在这个抽离于日常生活的空间里,有限与无限、連续与分离、实物与虚像、观察与存在都暧昧不清、相互纠缠。也许这恰恰是观看的理想状态——日常经验的非日常化。”这是他们关于“观看”的思考。
彭璐:从作品中看到真实的自己
黑色的背景,没有面孔的肢体,画框中出现的舞台,窗户,这些元素构成了一种暗黑、神秘的气息。彭璐说,它们表面上是暗黑的,其实是将物象拆解,再进行选择。“我想把自己不想明说的东西,找到一个最恰当的方式做成作品。我的作品都没有具体的形象,也尽量把情绪去掉,带有环境的描写,更多的是表达状态。虽然具体的形象和表情都不存在,但性别和肢体语言却被我保留了,我想表达的,是向内深挖的自我,是对周遭环境的一种反应,虽然从我个人出发,但我想许多体会或许置身现实世界的人也许会在作品中找到共鸣。”

1992年出生的彭璐,去年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大学时,她没想过做个艺术家。她花了一年时间辅修服装设计,并在时尚杂志社实习,但一年后,她才发现自己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喜欢衣服的女孩而已,“而做艺术家可以忠于你自己”。彭璐在艺术上天分很高。毕业展览上,她就被画廊相中,一年后的此时,她的个展“乌有之屋”正在Link Gallery画廊展出。
彭璐与男友谭英杰一起在罗马湖附近的工作室里生活、创作。谭英杰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也是职业艺术家。平日,两人会看很多展览,聊一聊社会上的新闻和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反思,“有时候你挺无力的,所以只能做成作品,我的创作不是很尖锐直白,是多层的隐喻,可以传达社会功能。”
彭璐也喜欢和同龄的艺术家聚会,去彼此的工作室转转,讨论创作,互相给予建议和支持。她说,“年轻艺术家需要被鼓励,做事情需要他人的看法,艺术家又坚强,又脆弱。怕拖对方的后腿,就会努力追赶。”
对于彭璐,艺术创作的魅力就是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也许在创作前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做出来的作品中,反过来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她希望在艺术家的职业道路上坚持下去,把作品做好,“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艺术是自由的,但内在要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