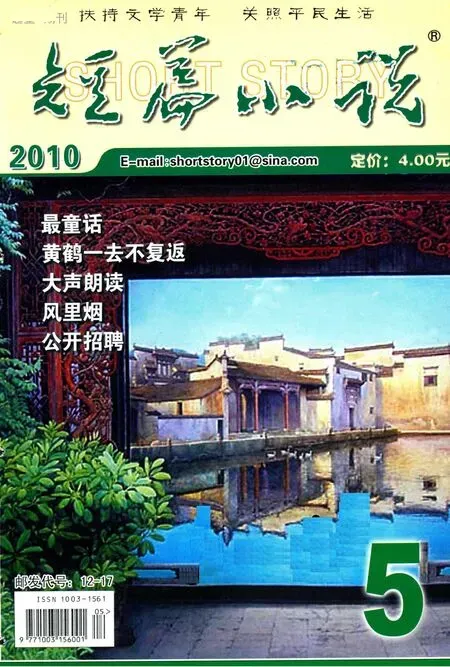壳
2017-08-01薛卫东
◎薛卫东
壳
◎薛卫东

晚上六点,来澡堂洗澡的人最少。这个时间,下午洗澡的人泡了堂子、搓了身上的泥儿,肚子叽咕叫,身子乏透了,迫不及待想回家,端起大瓷碗,盛满稠粥,如一棵春雨后的山笋,吱吱响地汲取汁液。晚上准备来洗澡的人,一般还没吃完饭,正往肚里塞馒头预备洗澡抗饥,或者一边衣柜中翻着换洗的内衣裤,一边高声喊着婆娘准备肥皂洗头膏搓澡巾。
老人卷缩在清雅阁门前的黑影里,等着这个时间。冬夜的风冷,顺着墙角打旋儿,钻进脖子,能把人冻透。老人用手按着棉大衣的领子,把脖子紧紧围住。高高竖起的领子,把脸遮得只留下窄窄的一条,这使得过往的人们只能从老人头顶的白发判断大致的年龄。清雅阁门口的电灯贼亮,偶有车辆经过,扬起的浮尘,在光影里上下起舞。正门口两根长长的钢管斜伸到半空,高高挑起两个大红灯笼,光线在门前笼着一团红云,透着一种暧昧的色彩。
出来的人越来越少。差不多了!
老人慢慢站起来,原本因寒冷团着的身体打开,两只脚轮番跺着坚硬的地,让腿上的酸麻一点点退去。老人抬起头,看“清雅阁”三个字牌匾,一只手努力向上伸着,似乎想摸摸牌匾上的字。但试了几次,还是差了半胳膊的距离。老人收回手,长出一口气,虽然没摸到,但脸上却有一丝笑意。
清雅阁,一个澡堂子,却取了一个文气的名字。老人不认几个字,但这三个字,却在心里,一笔一划描了很久。
售票口,木牌上写着:洗澡十元。
老人有些犹豫。十元,在桥北澡堂,能洗三次了。老人靠着墙,内心来来回回拉锯。
老人再次抬头看看牌匾,黑面金字的匾看着很厚重,斜角有一道裂纹。这是一块历经岁月的匾,也是心里头翻腾了二十年的匾。
买!老人终于下了决心,一只手,有些抖,递过去一张钱。
老人费力掀起大门口厚厚的棉门帘,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脚臭、肥皂、洗发水以及烟味多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是这个味儿。老人站在门口,不急着进来,深吸两口,神情痴迷。
哎,老头,要进来就快进来,掀门帘儿跑风,冷!有个声音喊。
老人用手挥挥雾气,看清是一个跑堂的在喊。跑堂赤裸上身,下身穿一只长长的、与裤子差不多的大裤衩,肩上搭一条分不清颜色的毛巾,手指着老人。
说你呢!洗不洗?不洗就出去,洗就赶紧进来,好狗不挡路咧。
跑堂的话,引起一阵哄笑。有个浴客,站在火炉边倒水,笑得夸张,腰间围的毛巾滑落,露出两瓣黑黑的屁股。
老人狠狠瞪了一眼,慢慢走过来,递过一只二指宽的木牌。跑堂斜了一眼,不接,头一扭,嘴里喊,15号一位!声音悠长,穿透力极强,在水雾弥漫的堂子里迅速传到每一个角落。
15号床铺在中间位置,铺的布单雪白雪白。床呈坡形,有一些角度,人躺上去很舒服。床尾一只柜子,刚刷的漆,泛着明亮的光。柜子上甚至还有把锁,钥匙上拴着一根红色橡皮绳圈,让老人感到很神奇。
不愧是清雅阁,全县城最好的澡堂子,就是不一样。老人脱下棉大衣,伸直腿,惬意地躺着,有些不舍得起来。
老头,要茶不要?跑堂来到床前。尽管他觉得眼前的这个老头不会有多大油水,但还想试试。
老人不情愿地坐起来:多少钱一壶?
一块钱一壶。
自带茶叶多少钱一壶?
跑堂的鼻子里嗤的一声,对自己的判断力很是佩服。果然没错,面前的老头就是一个穷光蛋,榨不出什么油水。
自带茶叶也是一块钱一壶!跑堂的语气有些重。其实自带茶叶五毛一壶,但跑堂就是觉得今天这个老头不顺眼。
老人想说什么,但嘴唇微动,没说出来。拉过棉大衣,从里面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盒,打开后拿出一袋精装压缩茶,放在床头小茶桌上。
拿去,来壶茶。老人语气非常平静。
跑堂的看着这包茶,有些吃惊。本来他以为,这个貌不惊人、甚至有些诺诺的老头,最多掏出一包花碎。来这里,喝花碎的多,一小包花碎两毛钱。不就是给水加个色吗,碎茶叶加茉莉花末,泡出来也香,一样喝。
跑堂的拿过茶包,摸索了半天,茶包光光的,却没有办法打开。老人冷冷地看着,伸手拿过,摸到上面暗藏的豁口,轻轻一撕,几粒墨绿的铁观音跳到手上。
这是好茶,你给我全泡壶里,想喝,从壶里倒,别在手心里藏我的茶叶。老人口气依然平静。
那是那是。跑堂的点着头,声调低了许多。心里有些吃惊,眼前这个老头,看起来是个行家。
跑堂的拿过一只茶壶,把茶叶倒进去,甚至把茶包拿起来,用手弹了弹,示意老人,茶叶确实全部倒壶里了。
老人微侧过身子,从棉大衣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拍在床头桌上。
有火没有?老人问。
大金渠!跑堂的眼睛有些直。来这里的,大都是抽灰色的小金渠,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大金渠。看着红彤彤的烟盒,跑堂的手指微微颤抖,极想伸手摸摸。
老人打开烟盒,大方地递给跑堂的一支,又问:有火没有?
啊?噢,有有有!跑堂的醒过神,手有些抖,火柴连划几根,都没划着。
老人手又一翻,递过一张票子,咳嗽两声:过半个小时,约莫我快从里面出来,到门口,叫两笼刘记包子,记住,要松枝垫底的,不要笼布垫底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跑堂的彻底服了,头如捣蒜。刘记包子,最贵的用松枝垫底,蒸出来有清香,比平常的贵一块钱。跑堂的有些兴奋,这老头干巴瘦,饭量肯定不大,两笼包子吃不完,自己也可以尝尝鲜。想起刘记包子咬一口流出的汤汁,跑堂的有些迫不及待。
洗浴间很大,一排三个池子。一号池最大,水温不高,里面坐了一圈的人泡着。二号池小一号,水温略高,只有几个不怕烫的人在里面。三号池最小,温度最高,水面冒着微微热气,没有人。
老人直接走到三号池。水面并没有太多热气,但水的颜色略深,泛着细微的水花。老人伸手在水里摸摸,手从水里拿出,立刻变得微红。老人却不怕,抬腿坐到池边,慢慢往身上撩着水,一双脚一点一点下到水里。
旁边有人看到,张大了嘴巴,却忘了惊呼。老人眼光扫到了人们的目光,脸上闪过一丝得意,加快了撩水的节奏,身子站到池中,又一点点蹲下身子,水面上只剩下头。
水温确实高。皮肤像一根根刺在扎,老人甚至听到了浑身毛孔炸开的声音,感觉一种痛一点一点蔓延开来,像澡堂抽水的水泵,赶压着全身的血液,迅速流遍全身。
过瘾!老人闭上眼,享受这一刻。
轰隆隆,一阵声响,像打雷,从头顶掠过。这应该是锅炉声,每隔一小时,锅炉要给水池送汽加温。声音又像是铲车声,对,像极了!铲车轰隆隆开过,巨大的铲斗轻轻一提,桥北澡堂的大门就像纸糊似的,轰然倒下。洗澡间墙上的瓷砖,平日里白花花的,但在明亮的阳光下,却斑驳破旧。木床、木凳,支离破碎,烂了一地。泡澡大池子却坚硬,水泥浇筑的异常结实,铲斗挥了一下,只是在池子上打开了一个豁子。池子里水已经放干,但老人看着,却好像看到水哗的一下流出,比晚上放水清理池子时候流畅得多。
放水的时间,一般是在半夜。老人会脱得赤条条,拿着大硬刷子和去污粉,跳到池子清理脏污。池子里不是池底最脏,沉到池底的,都是大颗粒,水一冲,顺着下水道就流走。最脏的地方是沿水线部位。水热,脏东西沉不下去,在水面漂浮,随着小小的水浪聚集在池边,沿水线一上一下跳跃,粘在瓷砖上,形成黑黑的一道线。老人刷上去污粉,用硬刷子使劲上下摩擦。这时候,不能顺着黑线擦,越擦蔓延的脏地方越多,必须上下擦,边擦边用水管冲洗,才能洗得干干净净。
这时候,搓澡的老黑往往会唱起来:“……哟!洗哟洗!洗哟洗!腿没站好摔瓜皮,老汉捂着小鸡鸡……”
最后走的浴客穿着衣服,笑着说老黑,太黄!唱个文雅点的。
老黑哈哈大笑,唱起一位常客教的文雅词儿:“……阿妹生得白花花,两条大腿像笋瓜,两根笋瓜都不要,只要中间芍药花……”
搓澡床和桥北澡堂一样,包着一层人造革,但垫的海绵多,更软乎,也宽大,人躺在上面,不用担心水滑落地。
落地?老人嘴角泛起一丝笑意。那次常来的刘胖子洗澡,喝点酒,一身汗,喊着要搓重一点,去油。轮到老黑搓,老黑直性子,只管下手用劲儿,横搓的时候用力过猛,刘胖子从床上一下子滑到了地上,溅起满地水花,疼得嗷嗷叫。
躺在搓澡床上,老人有些不适应。往常都是自己站着,居高临下看搓澡的人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一团团的肉随便堆着。胯下一团黑乎乎的玩意儿,因为热水浸泡,变得松松垮垮。往常隐藏的枝枝叉叉的一团草,被热水泡得软塌塌,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掩护作用。现在,自己也躺在床上,迎接别人的审视。
搓澡工是个瘦子,有点像老黑。转身拿地上塑料盆的时候,老人看见瘦子左屁股靠近胯骨有块疤。像!像!老黑屁股这个位置也有块疤!蒸汽管从水池子外面一角引入池子,晚上清理池子时候虽然关闭蒸汽管子,但管子余温仍然很烫。老黑光屁股清理池子的时候,累了,坐在池边抽烟,没留神,左屁股挨着管子,烫了铜钱块疤。老黑糊药膏的时候,疼得掉了几滴泪。看的人笑话老黑,说老黑你个大男人,还怕疼?老人却知道,老黑疼的不是肉,而是烫伤后几天上不了班,没法搓澡,每天少挣一二十块钱粮。
想起老黑,老人又想起那个夜晚。初冬的时候,感觉更加寒冷。人们刚刚从秋天经过,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天猛一下寒风起,觉得透心儿凉。老人、老黑,还有几个伙伴,聚在二嫂面馆,对面,就是已经拆除的桥北澡堂。玻璃上有水气,往外看不清楚,但能看见桥北澡堂拆剩的几根柱子。几个人都不说话,一碗一碗往肚里灌酒。
老黑喝醉了,满脸通红,看着老人说:赵哥,澡堂子,没了?
没了。老人长叹一声。
真没了?
真没了!
老黑趴在桌上嚎啕大哭:没了、没了!我该咋办?
老黑抬起头:我他妈干了十几年搓澡,还没正正经经洗过一回澡呢!
这句话,把几个人说得愣了。是啊,澡堂干了一二十年,每天忙着给别人搓澡、洗澡、打肥皂,自己何曾正儿八经洗过一次澡!晚上清理完池子,忙得一身汗,老板却急着要关电关水,几个人只能用大桶里剩下的水,相互用塑料盆舀水泼着身子,算是洗澡。要不然,早上来的时候,匆匆在蓬蓬头下冲一冲。早上的水还不热,只能去掉身上的汗气,却去不了粘黏在身上的油气。
我要洗澡!我要像刘胖子那样,泡澡、搓澡、喝茶、吃包子!
老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惊得一屋子人都回头看。桌上碟子里的花生米被震得乱蹦。老黑从内衣兜里摸出一张红彤彤的钞票,甩在桌上。
洗!洗!我他妈去清雅阁洗!
搓澡工有些心不在焉,搓澡巾上下胡乱搓着。老人强忍着,没吭声,心里却在说不对不对,这样搓不对!应该先用小塑料盆舀起大桶里热水一点一点浇在客人身上,用手轻按皮肤,感觉微微膨胀,指头肚有凹凸感,才能下手搓。搓的时候,应该横七竖三,每个部位横着搓七下,竖着再搓三下,才能搓干净。脚缝、脖子、胯下都要搓到,身体每个旮旯都要搓干净。
还是不说吧,今天就是来享受,服务好也罢,不好也罢,由他。
搓澡工拍拍老人的大腿,示意把两腿张开。老人却下意识地一下子把腿并拢,一只手摇着说不用不用。以前给客人搓澡,轮到搓胯下,一些客人也如针扎般拒绝。当时老人还笑,有什么神秘的!每天澡堂里几百个,都滴里当啷,一个逑样!现在轮到自己,却也不适应。
热毛巾打上肥皂,在老人身体上来回涂抹。舒服!老人感觉自己像一条滑溜的鱼,在热气中晕乎乎、飘飘然。毛巾在身上游走,如一只温热的熨斗,把身体的皱褶熨平。这次老人主动张开了双腿,任由毛巾在胯下肆意涂抹。久不见天日的尘根,被一大团白色泡沫埋着,有一些突破包围的苗头。
淋浴头是超大的蓬蓬头,水下来后呈雨状。水流很快,也很密,打在背上,有一些微微的痛感。不像桥北澡堂,为了省水,把蓬蓬头去掉,只剩一个光秃秃的水管头,很恐怖地从墙里斜刺刺伸出。水流被关得很小,浴客为了冲净身子,只好直挺挺站在水管正下方,费力地洗去身上的肥皂沫。一些身体肥胖的人,不得不夸张地扭着身体,使得一些部位能够接触到水流。
水冲洗着泡沫,老人感到身上原有的一层壳,被水浸泡得酥软,一点一点瓦解。水从头顶流下,哗哗的水声像是泥垢砸在地面。老人觉得自己像一条蛇,扭动着钻出原来的壳,有了新的生命。
老赵头!有人拍老人的肩膀。
正在淋浴的老人一激灵,回头看,一张有些熟悉的脸。
老赵头,你转到清雅阁搓背了?太好了!你的搓澡功夫,没人能比。桥北澡堂拆了,几个老哥们还想着你搓澡呢!
不、不,不是,我不是!老人手摇摆,嘴里喃喃。
你不是老赵头?不会吧,我经常去桥北澡堂让你搓背啊。那次你给我搓澡,专门给我按了腰,很舒服!你脖子上有块红斑,好认。
我是,洗、洗、洗澡。
你是来这儿洗澡的?
不、不是!老人慌乱后退,不顾身上没冲洗干净的肥皂沫,往外跑。老人头有些蒙,精心的计划出了岔子。烟、包子、搓背,花几十块钱洗次澡,不是一个搓澡工的生活。但老人想这一天想得太久了。正儿八经洗次澡的愿望,如一只吱吱叫的耗子,每天在心里四处乱拱。
老人不顾身上湿淋淋,慌乱地穿着衣服,心虚得像做贼。湿身子不好穿衣服,秋衣甚至穿反了,但老人不管不顾,只是快速地穿。一切如同一只吹得大大的欲望泡泡,被突如其来的利刺戳破。自己特地挑这个时间,就是不想碰到熟面孔。
这种生活,离自己很近,却又离自己很遥远。
老人像一只被惊吓的猫,迅速穿过走道。旁边一排排床上,白白或黝黑的肉团肆意地打开,喝茶、抽烟,甚至有人用黄油纸包了几片肉,喝起小酒。
包子!跑堂的在后面喊。
老人冲后摆手,疾跑,掀起门帘,不顾一切来到屋外。
圆圆的月亮,把大地照得一片银白。空气很冷,老人忍不住打个响亮的喷嚏。门帘放下,身后的世界关闭,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老人来回用力晃晃头,感觉有些恍惚。
清雅阁?老人回身看看厚门帘,掐了一把大腿,想起几秒钟前门帘后的世界。
老人仰头长出一口气,气流长得让人吃惊,如同一只手紧紧攥住肺,从肺的底部一点一点向上挤压,把整个肺里积攒的空气都给挤了出来。老人又一次看看牌匾,抖了抖身子,感觉轻快了许多,包裹自己的壳已经留在门帘后。
老黑!老人心里喊:我来过了!
老人脸上慢慢露出笑,弯下身子,揣着袄袖,慢慢前行,月光如水,把身影拉得越来越长。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