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为什么白衣
2017-07-31宋林峰
◎宋林峰
侠客为什么白衣
◎宋林峰

宋林峰,山西高平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评论及小说散见《文艺报》《山东文学》《西湖》《作品》《陕西文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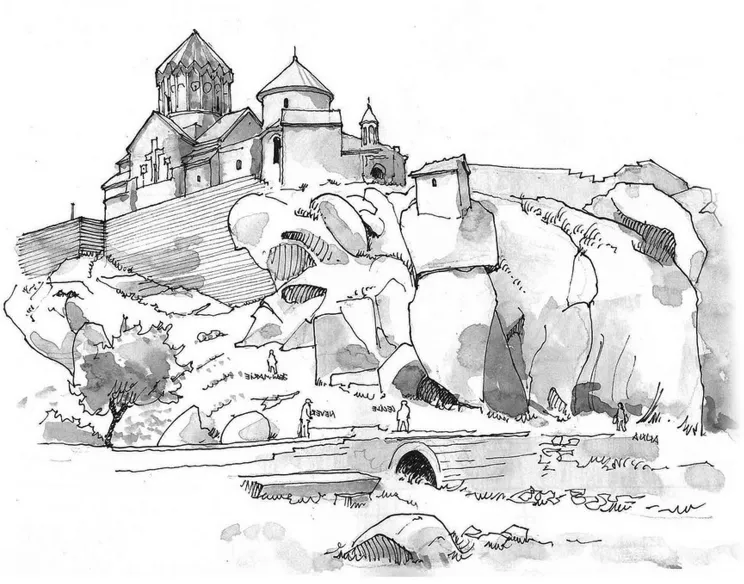
1
沈浪的父亲住在棚户区,公车两个小时,还得穿越大片的农田才能到达。棚户区的建设并不比市区差,只是位置偏些。沈浪的母亲去世有十几年了,老头子这些年一直独居,性格也越来越怪。比方说吧,沈垂在观看别人下棋的时候总忍不住嘟嘟囔囔插句嘴,他控制不住自己,下棋的人渐渐就不让他围观了。有一次,已经围了几个人,他想自己过去别人可能也不会注意,没想到下棋的一个老头噌地站起来,高声地说,沈垂,你还是到别处溜溜,你在这里,我下棋总觉得有狼在撵……后来,他也不往人多的地方挤了,自己在家练字。沈垂的书法不错,毛笔字写得遒劲,后来他又练硬笔。练硬笔有一个问题,他无法写直线。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怎么说呢?其实沈垂没上过学,只在扫盲班混过几天,认识的字实在有限。写硬笔时,他把一本小红宝书放在桌子右上角,用一块石头压着,然后正襟危坐,屏气凝神。他先读一句,然后再写,他总读不完整,磕磕巴巴的,这严重影响他的心情,所以就只能先将认识的字写下来,不连贯的字堆在一起就无法形成一条直线,这让他着急。他一着急,就习惯性用手捋胡子,胡子就掉,起先还是一根半根地掉,没几天,他的山羊胡就凋零得厉害。一次打电话他向儿子沈浪抱怨,沈浪就建议去买一把尺子。尺子也有问题,沈垂试着用尺子写了几次,要么是集体向上走,要么是一路向下倾斜,也就是说,尺子放在纸上,手如果没有按好,很可能写出来的一行字就齐刷刷朝某一个方向拐了去。沈垂又给沈浪打电话,没人接。老头一夜无眠。
沈浪的规律是,两周回棚户区一次,陈蓉也有规律,两个月一次。沈浪租住的那一间屋子,基本上都堆满了书,有的硬壳精装书直接乱塞,昨天他想找博尔赫斯的一本抽出来看看,是胡安·鲁尔福,摇摇头,又塞了进去。屋子里光线也不充足,书堆里的封闭空间埋着一张桌子,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座台灯,还有一个笔筒。沈浪很少用笔写字,笔筒里放的笔是他面对电脑写不下去时抽出来在指间旋转把玩的。有一天,沈浪躺在床上,做了一个真假难辨的梦。他乘着一只白鹤向西而去,可是在天的西边,却有火红炙热的太阳,那确实是光辉万丈的太阳。白鹤拼了命般朝着太阳的方向飞去,沈浪感到越来越热,温度陡然升高带来的口干舌燥让他焦躁,他开始大声尖叫,分贝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嗓子似乎在咔嚓咔嚓地撕裂……满头大汗的沈浪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为什么我认为白鹤是朝西边去的呢?我们平常分辨方向靠的不是太阳吗?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那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又是如何区别东西的呢?如果没有参照物,我们就无法分辨方向,可是为什么我认为那只白鹤是朝西飞去,而又认为太阳是在西边而不是直接认为白鹤飞去的就是太阳原来所在的东边呢?绕来绕去,沈浪也想不通。沈浪的头脑中可以装下无数的书本、知识、混乱的线条与思维,这些东西有时候却也会变成糊状死死地黏在某个地方,由于长久的懒惰惯性,失去活力,那些关于陈蓉的部分即是如此。
陈蓉的小女儿像一只家雀儿似的,一见沈浪就叽叽喳喳个不停。她会缠着他给她讲大海怪的故事,要不就是小萝卜头,还有雷锋叔叔背小学生过河的老掉牙。陈蓉倒是乐于见到如此情景,她最担心的是女儿不接纳沈浪,而这样的和谐局面对她来说简直太出人意料了。陈蓉每周过来三次,周一中午,周三晚上,周六带着女儿一起来待一整天。周三是她最享受的,周三她和沈浪可以有自己的独处空间,夜总是那么漫长,她的呢喃总是软绵绵……沈浪和陈蓉之间有意识地维持着一种平衡,他们两个成年人谁也不会提到那两个字,为什么要提呢?现在的状态不是挺好的吗?有了那一层关系,反而会觉得不自在,会觉得乏味、无聊,甚至会快速地彼此厌倦。那就糟了。
沈浪最近在写的东西涉及到一对恋人,男的暴戾,女的浮夸。这样的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为什么还会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这一点,沈浪也无法解释。他的小说刚开始,这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并且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吵。男的开始摔东西,衣服、被子、花瓶、床头书,女的也同时在扔,GUCCI包、iPhone手机、Juicy Couture耳环、Cartier钻戒,在这一章的结尾,女的还甩了男的一巴掌。在打出最后一个句点的时候,沈浪又想到了那个梦,但很快他的意识又滑到了别处。他纠结于自己的眼镜,他想不通为什么人类要发明那些足以令视力尽毁的高科技产品,然后又发明眼镜来挽救眼睛。不仅如此,人类还会开发各种新奇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食欲,最后又搞出一些运动器材来帮助减肥。还有,原始的人类那么自由,人类就发明了无数的规章制度,可现在的很多人又拼命地追求着自由,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人类的所谓“文明”是在进步吗?就像牛顿所说的那种状态。牛顿说:式中表示质点2受到的质点1的作用力,表示质点1受到的质点2的反作用力。
牛顿的说法太过理想化,马拉着车,车也在拉马,车却在行进(总有其他的力附着在这两种势均力敌的力上面,导致力的不平衡)。假设人类的文明在不断地创造和破坏之中匀速前进,哪一种力是占主导的导致运动的进行呢?很显然是创造的力。那么这种“前进”又因何被判定为“进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的整个文明在某个水平面上运动,它朝哪个方向行进是进步?朝哪个方向又不是进步?——关于方向的一些思考,总让沈浪陷入一种胶着状态。他突然意识到,陈蓉和自己是处于一种动量守恒之中吗?既然他认为动量守恒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那么他和陈蓉怎么可能是处于这一种理想化的(虚无)状态之中呢?总会有其他外力作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导致他们两个靠近或分开。这些外力究竟会是什么,沈浪毫无头绪。头脑风暴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及时弥补的空虚。楼下的小花园渐有人声传来,夕阳西斜,该出去走走了。沈浪的听觉异于常人,极为灵敏。他躺在床上,试图按照声音的大小将花园里的人分类,于是叽叽喳喳的孩童,瓮声瓮气的老人,咳嗽打嗝的胖子都通过耳朵这一特殊的器官进入了沈浪的思维。呆坐了一会儿,沈浪发现夕阳的角度又大幅度倾斜。算了,到处都是嘈杂,还是待在屋子里吧。沈浪还想到了前几天的一件事。他的朋友秦琼,向他讲述了在来的路上一些所见所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沈浪突然就想到了。
秦琼说:“在路上,我遇见一位头发飘逸的瘦小女生在被一个男生打。男生满脸青春痘,左脸局部臃肿,头发散乱,衣冠不整。是什么事情值得诉诸暴力呢?我的第一反应认为这是一对情侣,他们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缝。或许只是一条小的裂缝吧,比如女生昨晚回家晚于平时又说不出正当的理由。女生在低声抽咽,我能做点什么?我很清醒,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管不了这些,我要去喝酒,找十一郎喝酒。你知道的,十一郎家在盛世逸园,十八层,如果逢着停电,那感觉就是地狱啊。当初十一郎买房的时候,曾向我借了三万,那个时候,我在报社混得还可以,几条重大的新闻专稿都是出自我手。有一次,一位副省长来视察,点名要见‘小秦’,于是我们进行了长达半分钟的握手,我既激动也很惶恐,也不过是有一次把副省长的名字加粗放大了一号而已。可领导不这样想,领导注意的是细节。细节不重要吗?当然重要,细节决定成败。
“走到电梯口,我舒了一口气,苍天保佑,没停电。就今年来算,这是我第四次来盛世逸园,前三次来有两次停电。有一次,正巧遇见十八层一家买冰箱的,快递员吭哧吭哧爬了上去,上去发现那家的夫妻俩正在吵架,还就为冰箱的事,男的大声喝斥,买什么冰箱?儿子上学刚交的学费,家里哪来那么多闲钱?女的也不服气,我已经买了,你说没冰箱能行吗?昨天买的菜今天都坏了,你吃是不吃?浪费!两人就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快递员就尴尬了,连插话的空档都没有。快递员委屈地看着我,我能做点什么?我很清醒,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疯狂地按下十一郎家的门铃。你知道吗,我走进十一郎家里,气氛似乎不对。家里乱糟糟的,地板上有些水渍,没有看到周莹。没坐多久,我就到你这来了。”
十一郎与周莹的结合在当初就不被看好,现在果然证明了大家的判断。沈浪冷笑一声,窗外愈加嘈杂起来。
2
(警察打开门的)半个小时前,十一郎的儿子正在写作业,他儿子很聪明,上周班主任专门表扬了他。班主任说:李大天,这节课就你一个人背诵得不错,再给全班示范一遍。李大天就捣蒜似的晃着脑袋又重新背了一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李大天就在写这个,老师说要工整地背写三遍。周莹在卧室试穿网购来的一条浅粉色裙子。上周光棍节,周莹把支付宝里的一万块钱都一次性挥霍掉,仿佛那不是钱,而是存放久了就会烂掉的某种水果,不扔显得可惜。周莹叫十一郎,十一郎放下课本,走进卧室。不一会儿,里面就传出吵闹的声音,有一种尖锐的声音钻入了李大天的耳朵。大天站起来,跑向卧室,卧室的门反锁了,他焦急地喊爸爸,喊妈妈,没有人回答。他害怕了,又很胆怯,再推几下门,丝毫没有任何反应,这道门如同铜墙铁壁将他隔绝开来,他急哭了。李大天毕竟是受过班主任表扬的孩子,他疯狂地跑到电话机前,拨下了110。民警来了之后,十一郎正在客厅喝茶,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民警说有人报警,是个小孩。十一郎以为儿子写完作业到小区花园玩了,慌忙给民警解释,恰好儿子找了几个小伙伴来“搭救”爸妈。误会一场,但民警是白跑一趟,十一郎就道歉,说不好意思,还要从兜里掏点钱被民警给挡了。一个瘦高的女民警不客气地说,好好教育孩子,110是随便乱拨的吗?你们家长也太粗心了!十一郎又忙赔不是。李大天大眼瞪小眼,知道自己犯错了,便跑到自己的卧室反锁了门。周莹敲了几声,里面啥动静也没有。十一郎最了解自己儿子,聪明而敏感。他掏出手机给儿子发短信,李大天有一个只能打电话收发短信的旧手机,有时候同学之间有聚会或学校有事他就用手机联系家里。十一郎说,儿子,我们不怪你。咱家进来老鼠了,我跟你妈刚才关了门逮老鼠呢!过了一会儿,李大天哭着鼻子出来了,嘴里还吭吭哧哧地埋怨着。十一郎又给他讲了个笑话,他才破涕为笑。晚饭吃的鲈鱼,李大天非要吃鱼眼睛。
晚上,周莹躺在床上,说要退货,裙子颜色不正。十一郎拉掉台灯,困倦地推辞明天再说。周莹扭到一边,给了他一个香肩。周莹又开始嘟囔,明天我妈来看咱们,你去菜市场买条鱼回来,顺便买个西瓜,最近菜市场的菜涨价涨得太猛了,鸡蛋和西红柿我都舍不得买了,还有茄子,看着颜色也不好,卖那么贵,你说你吧,不喜欢吃芹菜,可你知道芹菜最近几天涨成啥了?哎,你的嘴高贵,芹菜的味道多好闻,芫荽也是,你说你的忌口怎么这么多,说多了吧,你烦,不说吧,我心里总觉得憋得慌……周莹扭头拍了一下十一郎,沉重的鼻息混着热气迎面而来,他已经睡着一会儿了。周莹叹了一口气,习惯性地帮他掖了一下被角,闭上了眼。
风尘仆仆的宋宝丽脸上虽然笑呵呵,但显然对没出现在车站的女婿感到不满。十一郎要做鱼,宝丽一把抢过,我来吧,我来吧。饭桌上,十一郎切开了西瓜,切成了四瓣,宝丽扑哧笑了,哪有这么切瓜的,来,还是我来吧。其实宝丽这次来是周莹提前安排好的,她俩决定向十一郎争取一项权利,希望十一郎可以点头。周莹今天特别留心,处处留意着十一郎的感受。他们之间的谈判是睡前开始的。周莹说她妈妈一个人在乡下如何如何辛苦,她为自己作为独生女不能常侍左右而惭愧。十一郎安慰她说,他们可以常到乡下去看她。周莹顿时哭溜溜说:“有屁用!万一我妈突然头疼脑热了,身边又没有人,她怎么办?”十一郎吓了一跳,忙说:“嘘,你低声点。”周莹从床上坐起来,把头发向后拢了拢,说:“我想把我妈接来住。”十一郎的脑袋轰然一声,两耳不住地嗡鸣。他明白了,一直以来,他知道周莹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她并未挑明,今天她算是彻底摆明了要坚持这样做。十一郎一时语塞,他想不出自己阻止的理由,说到底,这房子有一半是周莹的,可是,他更不知道自己要接受的理由!这房子也有一半是自己的。他只觉得自己的生活被一种东西梗在中间,就像一颗肿瘤,足以打破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压力如同一块巨石,砰地砸向十一郎,猝不及防。第二天宝丽离开的时候,一直在等待着十一郎有所表示。十一郎支支吾吾,最后说,下周一定带着儿子李大天看望她。宝丽不想听这些,周莹沉着脸,拎着行李,叫了出租车。
周一下班回到家,十一郎回到卧室就摊在床上,他听见周莹在厨房打电话,声音有点激动,不像是平常的周莹。过了一会儿,周莹的声音又提到了一个八度,语带呵责。十一郎走进厨房,关切地问:“怎么了?”周莹竟然在哭,她抱怨地说:“上次的裙子我给了差评,店家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给他差评,我就说尺寸不合适,他又吧啦吧啦一堆,最后我说没法撤销,他急了,就骂我,说是我的身材不合格!各种脏话都骂出口了……”十一郎过去搂住周莹,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头,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似乎又回到了初恋时的小孩子脾气,“不值得,不值得,和他置什么气?等我明天上班让我们组的成员都进店差评,看他怎么办?”周莹在十一郎怀里动了一下,俄而,抬头泪眼婆娑地说:“真的吗?”十一郎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周莹入主这个家的时间并不长,十一郎的前妻离开前,他都没想到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和这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周二,正在上班的十一郎收到周莹发来的一条微信:晚上吃你最爱的鲈鱼,等你。周三,十一郎在和客户谈生意的时候,收到周莹发来的信息:晚上到海底世界去吧,大天一直说他想去。接连一周,周莹通过各种手段在各种出其不意的场合向十一郎表达某种近乎谄媚的关心。十一郎明白,周莹是为了宋宝丽。十一郎的防线正在一点点溃败,这不是好兆头。
借口出差,十一郎去了北京几天,除了必要的晚安,其他时间周莹也并没有专门来信息,这让十一郎觉得回到了从前,但似乎刚从嘘寒问暖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又觉得少了点什么。十一郎的大学同学在北京某所高校教书,他就专门抽出一天去拜访他。在一间饭店,他们聊到了李纯。李纯是十一郎的痛点。十一郎说,三年前她就去世了,只留下李大天和我。两个人哀叹一阵。这是一件小事,却勾起了十一郎的一些回忆。之前,他认为李纯和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所以李纯一直郁郁寡欢,今天看来,自己貌似误判了李纯。他想起儿子大天的脸,和李纯是如此相像,他恨不得立马奔回家去,奋力地强吻他的额头、眉毛、鼻子和嘴角。夜里,十一郎失眠了,他梦到了一袭白裙的李纯站在高高的教学楼上在向他招手……
回到家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周莹睡眼惺忪地开了门,洗了把脸,十一郎急忙跑到儿子卧室,他没开灯,夜里的白光异常刺眼,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床上空无一人。一股强大的失落突袭了十一郎的心房,他愤愤地走回卧室,语带质询:“大天呢?我儿子呢?”周莹一时没搞清楚状况,开玩笑说:“明天我再告诉你,先睡吧。没想到你提前一天回来,我……”没等她把话说完,十一郎就迫不及待地将情绪加了一码,“我儿子呢?大天呢?”他的面目在浅灰的夜色里变得狰狞和恐怖,周莹怯懦地说:“到同学家去玩了,说今天不回来。”十一郎立刻要了电话,李大天在那头迷迷糊糊地叫了几声爸爸。十一郎冷静下来的时候,周莹已经穿好了衣服。“你要干什么去,这么晚了。”十一郎迷惑地问,周莹冷冷地说:“打胎”。
第二天,作为不速之客,秦琼敲开了十一郎家的门。

3
(敲十一郎家门的)几个小时前,秦琼刚从一团乱麻之中挣扎出来。秦琼的女儿秦思源在本地的一所大学读书,昨天下午回家的途中在地铁上遭遇了“咸猪手”,趁着人多,那人十分大胆,在女儿断断续续的哭诉中,秦琼才晓得大概。秦琼简直气到炸,他几十年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顷刻崩塌。报警!必须立刻马上报警!秦思源悲切地说:“爸,算了。”但士可忍孰不可忍啊!秦琼先安抚好女儿,然后找了个借口出门,刚离开家,他就报了警。随后,他专门跑到了地铁派出所。监控很快就调出了嫌疑人作案画面,秦琼闭上了眼。必须抓住,坚决严惩!当然,民警的意思也是这样。秦琼并未意识到他的行为会引起女儿声嘶力竭的反弹。一切都是秦琼回家之后(已是下午)才发生的,秦思源拿着手机给秦琼看,地铁上一个女学生穿着牛仔短裤(头部打了马赛克),背后一只粗糙的大手渐渐接近……秦思源将手机一甩,差点砸到秦琼的额头。秦琼一时蒙了,嘭的一声,女儿关上房门的巨响如醍醐灌顶,秦琼懊悔极了。
晚饭的时候,秦思源一声不响。秦琼为她夹菜,她也不多说什么。父女俩没有平日里的亲切,这一切都如此突然地发生了。秦琼啊,秦琼,你干了多么蠢的一件事!如果学校老师、思源的同学看到了这个视频,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会嘲笑女儿的懦弱,还是假装故意不表露的同情,这一切的后果都不堪设想。视频是怎么传到网上的?这一连串的疑问不断击打着秦琼的头颅和心脏,筷子在他手里不停地抖动,终于,他忍不住了,摔掉了筷子,愤慨地陈词:“我明天再去派出所,让他们想办法把视频撤下来!你相信我。”他心虚地看着思源,秦思源闷声吃着饭,根本没抬头看他一眼。秦琼手足无措,他突然想到上次嘱咐过思源夏天到了,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于是他加倍小心地低声说:“思源,下次……下次回家的时候小心点。”这句话像一根被点燃的引线,秦思源猛地站起来,牙关紧咬:“看在我妈的分儿上,你就饶了我吧!”
看在我妈的分儿上!这一句话如同暗夜的惊雷般轰隆隆穿透秦琼的身躯,他感觉到自己的各个器官正在四分五裂,一个个倔强地向外漂浮着,仿佛有一种力,这股力从中心发出,催使躯干向周围扩散,但更像是有千万种的外力在四边拉扯,他感觉自己要爆炸了、分裂了、撕碎了。秦琼觳觫一震,碗掉在地上,他如梦初醒,赶紧弯腰去捡,一块碎裂的瓷片嗞的一声划破了他的手,殷红的血汩汩直冒,突如其来的局部痛感让秦琼的意识更加失焦,他胡乱地扯了点卫生纸包在手上。疼痛过后,是麻木。麻木更可怕,麻木让人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麻木让秦琼以为自己的手与自己丝毫没有关系,麻木让秦琼反胃。麻木犹如秦琼见过的那许多种似曾相似的眼神。我能做点什么?我很清醒,我什么也不能做!可你是我女儿,我不得不做啊!一个声音在秦琼心里呐喊着,但他缄默不语。秦琼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带给女儿的,是这样令人纠结的二次伤害。
躺在床上,在微弱的灯光下,他痴痴地看着桌边的全家福,光阴如箭,陈小艺不会回来了,女儿也长大了。都说父爱如山,对单亲家庭的秦思源来说,父爱有时候更像一个累赘包袱。秦琼越想越悲凉,越想越痛苦,他关了灯,叹了一口气,脸颊热热的,原来这个男人淌过了泪。
第二天一早,秦琼跑到派出所,质询办案民警,为什么办案是这样进行的?民警矢口否认,说视频并非由官方发出去的。另外一个女民警见秦琼如此激动,走过来劝他要冷静,目前最重要的是缉拿嫌疑人,至于什么手段,不是计较的时候。秦琼再也按捺不住,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就是这样办案的吗?”几个民警一时呆住,空气凝滞几秒后,女民警悄声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不懂吗?”另一个人说:“这里是派出所,要闹事也要看清地方。”这已然明显是威胁了,不管放出视频的是不是派出所,这件事情已经发酵到了另一个层面。秦琼还要说些什么,突然所有的警员集合到隔壁的一间房子,一会儿又鱼贯而出。他听见稀稀疏疏的声音,说是城西发生了命案,似乎正要抽调警员。我的事就没人管了吗?在纷纷涌动的人流中,秦琼傻站着,身体里另一个声音说:“事有轻重缓急!”秦琼紧蹙眉头,傻愣片刻,愤然离去。在门口,秦琼终于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他一计拳头砸在脸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女儿也保护不了!”这一拳头砸得不轻,一颗龋齿狠狠地射向了地面。
张璐此时打来电话,之前她发来截图,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有一条 “女生地铁遭遇咸猪手”,她说她仔细把视频看了几遍,发现那女孩的身材和着装和思源很像。秦琼忙不迭地解释说:“不,不,那不是思源。我不知道……那是…谁。”秦琼的欲盖弥彰更加让张璐确信那就是秦思源。张璐继而安慰道:“不管那个是谁,女孩子嘛,真可怜。希望她不会留下什么阴影,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的,那样的变态……”秦琼怒不可遏,语气已几近斥骂了:“你以为你是谁?就算那个人是思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没和我结婚呢,你还没进我家门呢,你还不是我老婆呢,你管这么宽干什么!”张璐完全没有料到秦琼会将火撒到自己身上,忙挂掉电话。秦琼跌跌撞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世人冷漠麻木的眼光让他厌倦。他在混乱中萌生了一些邪恶的想法,比如突然来一场大地震,这座城市的所有人全部同归于尽,或者是一场肆虐的瘟疫,让他们痛不欲生……秦琼又被自己幼稚的想法逗笑了,原来一向冷静的他,在最爱的人受伤时,竟然也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如此狼狈。思源的确是他的软肋,思源续的是陈小艺的命。
回到家,思源已经返回学校了。桌子上,留下一张便签,上面是思源的几个隽秀小字:爸,对不起。秦琼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此情此景,他能做点什么呢?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想找十一郎喝酒,痛痛快快地喝一场!
他当然不知道,到了十一郎家会遇到那样的结果。
4
(某一个周三晚上)沈浪突然就泄了。
这吓了陈蓉一大跳,她几乎惊坐起来。这样的时刻,谁也不能说话,但又无法做到假装事情从来没发生过,陈蓉故作镇静,缓缓起身,轻声说要去洗手间。沈浪待在床上,没有回应。耳边一阵嗡嗡声,是冲马桶的声音?又不太像,那些混乱的线团又围绕在周围,错乱着,犬牙交错。怎么会呢?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今天是怎么回事。难道和最近做的梦有关吗?沈浪坐在床上,他突然明白,他和陈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了。这一直以来被他视为难题的死结就这样轻易打开了,这是他预料不及的,一身轻松还是心仍有郁积,他不确定。
此时,他接到一个电话,他爸爸沈垂过世了,也许是前几天,他们不确定,电话里说,邻居发现他的时候,他的面目已经十分难看。
沈浪揩掉眼角的液体,他叫陈蓉。陈蓉复又躺在了床上,这一次,沈浪如同一只凶残的虎,贪婪地舔舐着、吮吸着、抽插着……他一波一波地把陈蓉送到了欲望的巅峰,沈浪气喘喘地问她:“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写一部和《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巨著!我可以吗?”陈蓉几乎透不过气来,但他还是可以听到一道细微的声音在应和着。沈浪在最邪恶的欢乐和最诚实的痛苦之中徘徊,在那天人合一之境,他一声嘶鸣,倒了下去。
5
按照之前的约定,不管天气如何,每月十八日,秦琼、沈浪、十一郎三人必须于凌晨五点钟在英雄广场碰头。这个约定是前几年定的,当时他们三个为了避免所谓的中年危机,歃血为盟,每月的这天要到此捡两个小时垃圾。这是一件小事,但不可否认意义重大。
今天,一切如常。
秦琼蹲下来,喘了几口粗气。
十一郎神秘地笑笑:“你们猜,昨晚我梦见谁了?我梦见了我爷。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孝服随着乌泱泱一群人穿过好几片野地,一路上我都被妇女们的低声啜泣包围着,这一切都仿若昨日,还有吹打(乐队),他们奏的曲子很激昂,惊飞了许多野鸟。若不是我爹死死地拉着我,我就跑去追那些鸟儿了。到了坟地,他们将红色棺材用粗壮的绳子放下去,然后填埋。坟头的引魂幡迎风招展,爷爷有了一片自己的领地。我能清晰地听到那幡在风中呼啦作响的声音。我爷上过战场,他背上有几道特别深的疤痕,我亲眼见过。人群离开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我看见我爷又从土里钻出来,站在坟头,挺着胸脯,要与谁斗架似的。再回头,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沈浪说,鬼扯,这倒是个不错的小说素材。
秦琼将一个塑料瓶扔进编织袋,又伸手把里面的垃圾按瓷实了。秦琼戏谑地说:“说不定是真的,小时候我住在农村,听过很多传说,说有一天刮大风,邻村一个在地里锄地的妇女就被刮了起来,刮到悬崖边的一棵树上。”
沈浪摇摇头,他说:“我们已经到了开始怀念少年勇的年纪了吗?我敢说,如果上上上辈子也存在一个我,那我一定是一名笑傲江湖的白衣侠客。”
秦琼瞥了沈浪一眼:“白衣素裹,仇家随时杀来,他随时为自己送葬。”他转身将十一郎的袋子拎过来,把垃圾倒进了自己的袋子,这样就正好凑够了一整袋。不知为什么,在瓷砖的反射下,秦琼抬头突然看到对面有三只巨大的蚕蛹,沈浪和十一郎也几乎在同时注意到这一情况,他们三个人仿佛被透明紧绷而细细密密的丝缠住了,一动不动,只能待在原地,双眼通红。
责任编辑/乙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