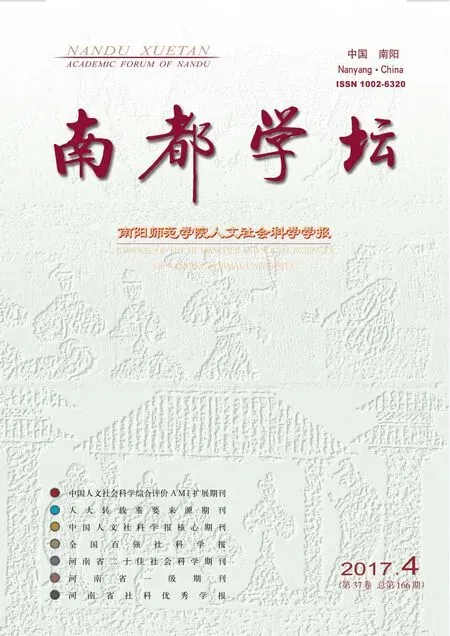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反思与新常态
——对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分析
2017-07-18刘金发
刘 金 发
(曲阜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反思与新常态
——对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分析
刘 金 发
(曲阜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社会治理到底应在哪些方面对已有社会管理实践经验予以继承和超越却较少有人系统回答。为此,以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和文献分析法,发现社会管理创新集中在价值理念、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政府职能整合机制三方面,在行政化推动、项目化运作、网格化管理、机构规模扩大、创新均衡性等方面问题突出。这些经验和问题是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的动力和提升方向。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进入实践创新的新常态,要正确界定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有效规避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的均衡性。
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新常态;试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管理”转型升级为“社会治理”。这种转变对于以往的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延续性又有开拓性[1];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理理念的高度升华[2]、执政理念的新变化和新提升[3],呈现出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4];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政府治理权力最终复归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5],意味着社会治理进入了“新常态”[6]。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6]。而要实现这一系统工程的科学化,就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通过全面总结和提炼已有社会管理创新经验,来明确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方向。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层理论和实践逻辑不仅是对传统管理理念的超越,更是要总结和反思原有社会管理的经验与不足,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借鉴。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对2010年以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的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进行全面分析,从而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入新常态。
一、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的主要实践内容
(一)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
1.凸显服务价值
针对流动人口问题,北京朝阳区建构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以财管人”的“四管”服务模式;整合社区服务,建立外籍人员服务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落实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同城化。重庆大渡口区建立了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对流动人口实行登记办证、技能培训、政策咨询、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
针对特殊人群问题,江西丰城市建立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培训和政策引导;加强对闲散少年、流浪乞讨少年、农村留守儿童等6类青少年的管理服务。湖南长沙市采取“两统两分”管理机制,分市、县(区、市)、乡镇(街道)、社区(村)四级建立特殊人群基本信息数据库,采取分类管理策略。
2.坚持民生优先
吉林延吉市编制实施《民生发展五年规划》,每年新增财力的70%用于民生建设。安徽合肥市实施“33+X”项民生工程(33项为省定民生工程,X为公开征集公民意见的市自选工程),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四个城乡全覆盖”。河南新郑市用民生幸福评价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山东诸城建成208个农村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打造“2公里公共服务圈”。甘肃嘉峪关市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农业劳动者”在保留享有原有农村惠农政策外,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此外还设立“城乡一体化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一站式综合性的社会服务。
3.深化群众工作
安徽合肥市实行拆迁安置“三榜公示”制度,坚持以“和谐拆迁”暖民心,先拆违、后拆迁,“一把尺子量到底”,防止因拆迁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宁夏灵武市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基层服务群众机制,在行政村和社区居委会设立代表之家和民意表达室,掌握社情民意。海南、河南、湖北、贵州等省份设立群众工作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维护群众利益。河南三门峡市走出“截访思维”,实行信访“挂号”、部门联合接访等制度,使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
4.彰显公平正义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实施重大决策农牧民代表常设制和村民、社区居民参与的“四权四制”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四权”是指对所有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党支部履行决策组织权、村民代表会议履行决策表决权、村委会履行决策实施权、村民监督委员会履行决策监督权;“四制”是指决策启动、民主表决、组织实施、监督评议运行机制。。新疆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司法所建立人民调解员资质登记备案制度,加强专兼职调解员、调解志愿者和联络员队伍建设。河南三门峡市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保障司法公正,强化“执法能力、效率和责任心”。湖南长沙市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行政务公开、阳光行政,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山西太原市创建“法治太原建设示范单位”,规范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行使,保障程序公正。
(二)社会管理资源的整合机制创新
1.新设党委机构,加强社会管理资源统筹
早在2003年,上海市委成立了全国首家社会工作委员会,2007年北京市委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北京市委社工委)。2011年,广东省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由24个部门派出委员组成“超级机构”,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2.优化扶持机制,孵化做强社会组织
北京东城区2011年启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资助最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天津滨海新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建构新区、功能区、街镇对社会组织的“三级孵化”服务体系。2011年福建晋江市成立了以致和社工事务所为核心的福建省首个社会组织孵化与创新中心*大多数孵化中心都是政府组织成立的,而该孵化中心在性质上是依托致和社工事务所成立的机构,是一家无业务主管单位直接注册登记的民间支持性社会组织,其提供的孵化服务是一种“社社合作模式”而非 “政社合作模式”。,对其他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指导服务。2010年宁波市成立浙江省第一家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行“政府扶持、民间运作、专业管理、三方受益”的运作模式,为社会组织提供相互交流、登记和项目运作等全程服务。北京市分两批划定22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借助这些社会组织联系、发展民间社团。
3.健全公众参与,构筑群防群治格局
湖南长沙市通过对话长沙、网络问政、网民在线、重大事项社会听证、市民代表列席市长办公会、市政府常务会全媒体直播等方式搭建政府与公众互动沟通平台;推广“五老维稳协会”“红袖章工程”“十店联防”“中心户长制”“户户联防”等群防群治经验[7]。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开展“十户联防”“邻里守望”“村民巡护队”等治安联防活动。
(三)政府职能的整合机制创新
1.新设政府机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
上海市成立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确立“三一两全”的标准化建设和“三度”服务要求*“三一两全”为一门服务、一头管理、一口受理,全年无休、全区通办。“三度”为便捷度、透明度和亲和度。,全市街镇按标准建立213个受理中心、11个受理分中心,1300余个村级社区事务代理室[8]。江苏南通市整合市、县(市、区)、乡镇、村(社区)20多个部门职能,建成集中行政服务和维稳功能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河南三门峡市建设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实现工作“一体化”运作、群众接待“一条龙”服务、问题解决“一竿子”到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整合乡镇政法综治中心、便民服务大厅等资源,在全部74个镇(街道)建成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中心。新疆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建成综治工作中心,整合综治维稳、信访、司法所等资源和力量,实现“一站式”服务。贵州贵阳市建成11个区(市、县)群工中心,实现矛盾纠纷的“一站式”化解、信访事项的“一条龙”办理。
2.划分管理网格,实施网格化管理
北京东城区以10000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全区17个街道205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管理网格,提出“天上有云(云计算中心)、中间有网(互联网)、地上有格(社会管理网格)”的社会管理模式[9]。湖北宜昌市以300户为标准,把城区121个社区划分为1110个网格。青海格尔木市将全市划分为213个网格,按照“一格多员”的模式,整合政法综治、劳动保障、单位内保、民政、司法等单位构成网格节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将全区划分为五级网格,并为网格配备党建工作指导员。辽宁沈阳市以街道办事处为基本方格,每个方格由2—3人负责。浙江宁波市划分管理网格1.1万个,配备1.5万名管理员。四川德阳市实行社区管理网格化,建立社区议事网格、人民调解网格、治安消防网格等。西藏拉萨市创立复合型村(居)网格化、机关单位网格化、街面防控警务网格化、寺庙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全市所有行政区域共划分工作网格636个,实现网格管理全覆盖[10]。
3.构建调解网络,完善“大调解”机制
江苏南通市创建以“整合资源、整体联动”和“一综多专、专业调处”为特色的大调解机制*所谓“综”就是县、乡大调解中心作为综合性的调处平台;“专”就是各种专业化调处机制,包括医疗、劳资、拆迁、交通事故等矛盾纠纷的专业调解,以及公安、检察、法院等与大调解平台的对接机制。。全市9个县(市、区)、121个乡镇、1960个村居共建成三级大调解组织机构2139家,配备调解人员4623名,并大力发展“老舅妈”“夕阳红”“老干部调解室”“快乐调解俱乐部”“平安守望团”等群众性调解组织。山东泰安市构建党委政府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司法行政为主、职能部门参与、联合联动调处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了纵向覆盖四级,横向渗透各区域、各行业的调解组织网络。云南楚雄市建立大调解委员会,完善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行业协会调解等为主要内容的“大调解”工作网络。上海长宁区形成“123X”模式的区域化大调解体系*“一个中心”(长宁区大调解服务中心)、“两个辅翼”(区诉调对接中心、区访调对接中心)、“三级网络”(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X个平台”(若干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平台)。。浙江诸暨市发展“枫桥经验”,建构“点线面”结合的大调解体系,完善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警调对接等机制,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接连互动。
4.加大层级协同,实施“项目化”运作
陕西西安、河北石家庄、安徽合肥、山西太原、江苏南通、辽宁沈阳、山东泰安、天津滨海新区、浙江宁波、河南新郑、湖南长沙等地,在社会管理创新上采取“体系化”*此处的社会管理“体系”是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包括哪些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将这些创新的方面称为“体系”,有的称为“工程”。“工程化”建构,“项目化”运作的机制,即在确立“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对每个体系所包含的实施项目进行量化、细化,明确每个项目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完成时间,并通过自上而下签订“军令状”“责任书”“项目书”等形式,来实现层级动员。
二、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的主要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经验
1.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多样性
各试点地区从不同的角度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从下表可以看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表1)。
2.社会管理创新的项目化运作
在基层行政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上级部门为了完成社会管理目标,往往借助项目制来动员基层政府。与传统的科层体制相比,项目制实现了政府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而“项目管理责任制”通过将上级政府确定的社会管理总目标进行逐级、逐部门的分解和细化,构成了纵向间不同级别“一把手”的上下制约和横向间不同部门“牵头负责人”的刚性任务压力。项目化运作集考核奖惩、职位升迁等多功能为一体,刺激地方政府足额甚至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如图1,项目化运作是政府落实社会管理任务的最普遍途径。
3.社会管理创新的网格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中出现频率高,并被多数地方政府采纳的工作形式。网格化管理反映出政府的三大诉求:一是实现社会问题信息搜集的动态化,以便迅速做出反应;二是整合政府部门碎片化的功能,吸纳社会力量进入社会管理过程,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三是实现社会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盲点、无盲区” 的管理深度和广度[11]。如图1,政府实现无缝隙、精细化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借助于信息技术或群众力量的社会网格化划分。
4.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设机构模式
地方试点依托党委、政府和社会,成立了不同形式的、不同性质的部门或机构。这些新设机构的目的:一是通过党委的领导作用,加强社会管理资源和力量的统筹协调,以更有力地推进社会管理工作;二是通过政府职能的整合,实现社会管理服务形式、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和提升;三是依托社会力量,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机制,孵化培育、带动壮大一批社会组织,以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如图1,新设党委机构、新设政府机构,以及建构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或平台,成为试点地区整合各方资源的普遍选择。

表1 试点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容
资料来源:此表是作者根据本文所述内容绘制而成*试点地区创新举措具有综合性,所以同一个地区会在多个创新内容中出现。表中标注“*”的,是试点地区所属省份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此表尚未包括的试点地区有广西凭祥市、海南琼海市、西藏林芝地区。。

图1 试点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分布
5.社会管理创新的本地化特征
社会管理创新受到当地资源禀赋的约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在社会管理技术上投入更大,社会管理的项目化运作也更明显。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矛盾也更为复杂,往往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以维护社会稳定。例如,同样是网格化管理,北京东城区更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嵌入和整合网格中的资源。而西部地区在网格的衔接上,往往借助纵向行政层级这一“平台”,将志愿者或社会管理工作人员嵌入网格中。同样是大调解,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在整合各方调解力量的基础上,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或平台,并在不同行政层级间全覆盖,而有的试点地区则是形成了大调解的工作联动机制。
(二)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管理行政化推动的风险
社会管理创新最基本的内涵是基于共同价值的互动与合作,创新的实现既要强调国家角色的责任性、引导性,又要强调公众实际需求的导向性以及向社会赋权的重要性。试点地区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把手工程”,这无疑成为工作开展的强劲动力。然而,行政化的方式有可能使国家对社会管理干预过多而挤压社会自主与独立的空间,并有可能伴随决策的个人意志过多、短期政绩追求的意识过浓、社会管理的政策连续性过差、公众实际需求的回应性不足以及社会管理创新成本过高等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行政化的社会管理往往只考虑政府能做什么,能建设什么,完成任务需要多少时间,而较少考虑公众需要什么,建成后的基础设施利用效果如何,任务完成的质量如何。另外,随着“一把手”的换届,新任领导有可能转变前任领导的工作重心,难以实现社会管理的长效运行机制。
2.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风险
“项目制”是国家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运行中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12],是一种能够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关系以及社会各领域的资源整合起来的治理模式。所谓的“项目”,既不同于宏大的社会建设和发展规划项目,也不同于专业领域的技术和建设项目,而是特指以财政为核心的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的转移支付[13]。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绝大部分试点地区都将社会管理“项目化”“专项化”“行政发包制”。这样做的风险在于:省、地级市层级有可能只是项目的“过手”“中转站”,而县及县以下基层政府则是项目“再组织”的社会场域,这样就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矛盾,以至于项目在执行中“打折”。
为了保证项目的落实,一方面要保证项目财政必须对基层政府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形成“项目牵线”下的全面动员机制;另一方面要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管理(如考评、奖励等)的依据[14],并以“责任状”“责任书”等书面形式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本级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层层、环环签订,形成行政上的层级压力机制。“项目牵线”固然可以使项目成为组织协调的中心,从而打破行政资源按照部门科室分配的格局,然而项目的存在也占用了基层单位的大量工作时间和政务经费,导致其他正常业务被忽略或被延迟。而项目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虽然有助于对项目实施进行简单管理和高效监控,但也可能异化为“数字化管理”“指标化管理”[15],导致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一切以“指标”为目标、以指标为优先,尤其是片面重视“数字指标”“效率指标”而忽视社会管理的服务本质、民生改善目的和权利保障宗旨,使社会管理创新失去原则性、方向性。
随着项目制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采用,出现了项目制自我扩张的现象,不仅是政法委、综治委,发改委、民政、人保、卫计、住建、综治、调解、党建等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也有意进行项目化操作。基层政府为了“抓住”项目,打造工作“亮点”或“树立标杆”,往往不是将心思用在实际工作上,而是追求媒体宣传,在“光环”效应下形成项目财政资源的连续输入。有可能形成“宣传—项目落户—再宣传—再项目落户”的政绩速成机制。政府的政绩与公众的社会管理期望之间形成落差,有可能为社会管理埋下失败风险。
3.社会管理网格化管理的风险
网格化管理在完善社会冲突的立体防控体系方面功不可没,在地方试点中被基层政府广泛采用。“网格化”概念中的资源整合和有效控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作为物理状态的网格,有大小,有边界,有活动半径、控制半径等,可以人为划定,也可以是自然的认同;二是作为技术的网络,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三是作为管理的思想,要求打破部门、资源主体和信息拥有者之间的壁垒,促进资源、信息的整合,实现网格之间的认同、开放、协同、共享、互动和合作[16]。然而网格化管理的有效运作,需要政府以大量的财政资源作为支撑:一方面通过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为网格配置相应的人力资源以实现网格间的互动。在地方试点中,北京东城区等经济发达地区网格化管理的财政投入相对有保障,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依赖人力的投入,而且以非固定工作人员为主,这种成本上的压力制约网格管理的持续运行,而人员的不稳定、专业技术的欠缺等也容易造成网格间的互动失灵。
而受维稳压力和传统管理方式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在网格化管理逻辑中凸显管控思维,优先选择管控手段,习惯于将管理对象置于全方位防控的时空环境中。通过行政力量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覆盖整个管理区域,无形中将无缝隙服务转化成了政府对社会的无缝隙嵌入,将精细化管理转化成了全天候掌控。
4.社会管理设立新机构的风险
政府条块分割、信息与资源部门化等问题是社会管理有效运行的“瓶颈”。怎样突破这一瓶颈,各试点地区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设立党委、政府新机构的模式,来统筹协调各方资源。这种模式背后的逻辑是权力越大、越全、越强、越集中,效率就越高;只有资源归属的唯一性,才能使支配资源变得容易。这种通过权力集中来实现社会管理资源整合的惯性思维,有可能放大政府社会管理范围和社会管理职能,促使政府自身不断强化自我作用的话语权。
此外,新设机构的运行必然带来多方面的变化,一是政府财政预算和编制的增加,二是不同层级间基于归口管理的原则设置相应的对口部门,三是新机构与其他相近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问题。从本质上看,新设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加投入、建机构、增编制的思维,以及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手段推进工作的传统路径。
5.试点地区创新策略非均衡性的风险
从图1可见,相对于价值理念的创新和政府功能的整合来讲,社会资源的整合相对不受重视,且每一个创新方向的内部措施也存在非均衡。即有形的(设置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多,而无形的(公民参与的法治化、消除社会组织制度性障碍等)措施少;纵向上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整合的措施多,而横向上向社会赋权、实质化的公民参与和社会组织自主空间的措施少;行政手段运用得多,而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市场的手段运用得少;针对社会稳定的措施多,而针对公民维权的制度化渠道设计得少。
三、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进入实践创新的新常态
(一)正确界定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
社会治理新常态的首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中国当前处于转型期,国家和社会力量不均衡,国家主导的意识强烈。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未来的社会治理应从制度上约束国家权力,不断调整国家社会治理的角色,从过去的统治者、管控者向服务者转变。而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国家应通过不断简政放权、市场化的手段、制度规范的完善和实质化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来实现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的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将国家角色塑造为引导者,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格局。
(二)有效规避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创新战略目标应是祛除政府凭借暴力或暴力性机构消灭差别、将异质性要素归整为无差别的整体的强力控制。通过互动、协商、合作等方式,以各种制度为中介,使异质的主体互动联结、迥异的价值融合凝聚、分散的资源优化组织、主体的功能优势互补,最终实现社会的有机团结。
未来的社会治理创新要以公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形成制度化、法治化的向社会赋权的政府改革机制,防止社会治理工作的过度行政化倾向;要利用好项目制在资源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将政府政绩建立在公众满意的基础上,防止项目制的“指标数字化”,在项目实施中体现社会治理的服务本质、民生改善目的和权利保障宗旨,确保项目实施的原则性、方向性;实现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变,促进资源、信息的整合,实现网络成员之间认同、开放、协同、共享、互动和合作的良性格局;实现自下而上的信息采集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公共服务回应之间的无缝隙衔接。而对于新设机构则应进一步明确其职责边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减少行政成本为原则,从制度层面上变“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
(三)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的均衡性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创新策略,应注重均衡性,实现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实现社会治理质量的全面提升。未来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创新要在一系列价值序列中,即在管理与服务、维稳与维权、排斥和吸纳、控制与自治、纵向行政服从与横向政社合作等多维且冲突的价值间,追寻相对稳定的平衡点。同时,更加注重公民权利与公民诉求机制,把民众破坏性的“事前失语、事中沉默、事后抗争”变为建设性的“事前参与、事中协商、事后协作”,处理好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政府公权力和个人“微权利”的关系,体现社会治理对“人的权利”的终极关怀,让法治和权利的逻辑成为社会治理的“内核”,实现标本兼治型社会治理。
试点地区的政府职能整合实践,倾向于项目化运作、网格化管理、设立新的政府机构等方面。而未来的社会治理创新,应强调政府自身变革和简政放权的重要性,摒弃传统理念中对权力的过度依赖,实现政府职能整合方式从传统的机构合并、生成新机构,转向开放式、契约式、合作式整合,以及按社会需求的整合和非集中控制式整合,实现政府行政化整合手段与市场化整合手段的均衡,实现政府纵向上的秩序维护机制与横向上的秩序协作机制的均衡。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战略部署下,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职能整合更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社会治理相关职能部门政务透明化运行机制,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照法律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政府职能整合也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各部门职能的电子化有效对接,对群众诉求给予高效率、高质量的回应。
试点地区的社会资源整合实践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实质性的公民参与机制、法制化的社会组织协同机制等方面仍然滞后,这显示出政府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政策偏好,即仍依赖于现有的公共资源,形成对公众的行政动员和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扶持,普遍缺少对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以激发公民自发参与的热情,破除社会组织参与的“制度枷锁”。未来社会治理创新应该从政府主导的资源整合转向强调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向社会赋权、发展社会组织自治;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1]李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J].前线,2014(1):14-16.
[2]丁元竹.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N].北京日报,2013-12-02(18).
[3]邵光学,刘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浅谈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J].学术论坛,2014(2):44-48.
[4]戚学祥.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J].探索,2014(2):66-70.
[5]严仍昱.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与逻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1):65-71.
[6]龚维斌.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八个特征[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12):31-35.
[7]魏礼群.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行政管理改革,2014(8):17.
[8]童中贤.长沙模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的新探索[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131-140.
[9]易丽丽.地方社会管理新设机构探索:经验特征与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2):50.
[10]北京市东城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网格化的工作模式 精细化的城市管理[J].信息化建设,2011(9):10-12.
[11]拉萨市实施社会网格化管理,扎实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取得实效[EB/OL].[2014-12-17].http://www.lasa.gov.cn/Item/53876.aspx.
[12]孙柏瑛.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中的适应性变革[J].中国行政管理,2012(5):37.
[13]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114.
[1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7.
[15]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9(2):61.
[16]何绍辉.目标管理责任制:运作及其特征——对红村扶贫开发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75.
[17]马伊里.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9-131.
[责任编辑:张天景]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Reflection and New Normal of Innovation——an Analysis of the 38 Comprehensive Pilot Areas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LIU Jin-fa
(1.School of Manage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76826, China;2.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However, few people can systematically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aspects in practical experience should social governance inherit and surpass social management? For this reason, taking 38 pilot areas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s samples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text mining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se three aspects of value idea 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in social management are a driving force and provide promotion direction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to new normal.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governance; new normal; experiment
2017-05-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管理体系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编号:13&ZD039;山东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国家区域战略交互影响下山东跨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J15WB03;曲阜师范大学校级基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山东跨域治理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XSK201526。
刘金发(1983— ),男,山东省临沂市人,曲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
D630
A
1002-6320(2017)04-00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