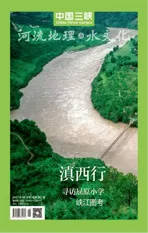废城知子罗
2017-07-12许文舟编辑吴冠宇孙钰芳
◎ 文 | 许文舟 编辑 | 吴冠宇 孙钰芳
废城知子罗
◎ 文 | 许文舟 编辑 | 吴冠宇 孙钰芳

知子罗废城记忆 摄影/许文舟
撤销碧江县制的决定究其原因,一是州府搬迁到六库后,碧江县城变成了死角,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滑坡加剧,在县内又无容纳一个县城的理想之地。后来这里成为知子罗村,到处是废旧的老墙与旧屋。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旋转,实际是像爬楼梯一样地往上登,每一个弯道之后,就会是另一幅美景,逼得你不顾气喘吁吁地感叹。这哪里是一座城,仿佛就是登一条天梯,三下两下就把一朵随心所欲的云置于脚下了,更吸引人的是远山,像刀像剑像戟,似乎都在与云不共戴天。
我的目的地是知子罗,一座废城。
与语录墙老旧的色彩反差极大的是一群一边玩着皮球一边欢笑的孩子,他们是寂静的知子罗十分零碎的欢乐。语录体的红已掺进了时间的铅灰。虽然是周日,孩子们还得去上课,肯定有补课的内容,因为再过几天就要放假了。晒太阳的老人,一手把竹节做的旱烟锅戳在嘴里,一手捻着全白的胡须,手闲不住,胡须是最好玩的东西。孩子们不懂知子罗一去不复返的故事,就像不懂老人家每天按时坐在银桦树下在想什么。两个下棋的老人则顶着树影,屏心静气地杀来杀去,总有一方所向披靡。
原住民大多随政府和机关撤离,留下的房子就分配给附近农民,当他们把猪鸡背进这些机关家属区,才发现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天地。门窄得牛转不过身,人背一床簸箕也会卡在门上,粮食收回来就与人的住处打挤,更重要的是没有可以让火熊熊燃烧的火塘。对和双存老人来说,那些日子真是难熬,虽然只离开原住地几公里,居然夜夜失眠,半夜醒着,那些同样失眠的猪鸡不分时辰地抗议,可能是水泥地没泥土温暖吧,后半夜寒气上升,叫声更密。与和双存老人一样年纪的人,都把那段时间归落到梦中,事实上也像梦一样,当他们从谣传中缓过神,机关单位已经拆得七零八落,装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卷土而去。
与和双存老人一样,留在知子罗的人都有过惶恐,每天晚上都会听见莫名的声音有远而近,像是一列火车铆足了劲爬行,反反复复,他们在莫名的声响中看到了宿命。州县机关撤出的那一刻起,知子罗到处是废旧的老墙与旧屋,对于每一个能坚守在知子罗的人,那应该是一种无边的煎熬。幸好大滑坡只是一个谣传,但他们一定有种劫后余生的触动。
对于生命的珍视,人们不得不在安居上费尽心思,当某种可能的灾难哪怕只是通过谣传的形式播散,再好的火塘也只能浇上凉水了。这不是暴风骤雨,而将是天摇地动的滑坡,对家园爱得再深也会被连根拔起。当然一切都只是可能,知子罗就荒弃给春风了,但蔓草并没有横行,从附近迁来的农民除了安居,还可以做点买卖,头脑灵活的倚旧卖旧,旧就是一个大卖点。这是许多年后的觉悟,然而有些旧物却被人为毁坏,留下来的也只是一个轮廓与影子。在知子罗,我遇见许多人,他们不紧不慢地寻访着一幢幢老屋,像寻找,又像是发现,天晚了就住客栈,特意挑一个临窗的床位,看总是闪闪的星和月。
修旧如旧,政府是铁了心要让废城不再“废”下去,让经过岁月漫漶的老城变成旅游景点,这就是给仍然住在知子罗的人的一种生活奔头。游人三三两两,问题是没有产品拉开那些人腰间的钱包,溜了一圈,末了就撤到福贡或六库。废城有语录墙,有茶文化,有唱诗班,有好客的怒族人自酿的烈酒。问题又来了,零星生产的产品如何步入商品生产的轻轨,散落一地的景如何串成一线。走纯粹的“旧”路子看来行不通,只有赋之以特色产品、茶文化、民俗风情,才能让游人来了就舍不得走。
老墙里的古屋总宜于怀想,野草给它抹上了一层凄清的色泽,并漫上屋脊,乐于被大风打整。那是当年州政府办公的主楼,烟熏火燎,已涂去了条条框框的规定,办公室堆放着刚收的南瓜,收发室拥挤着玉米,小孩在走道滚铁环,老人抱着脸颊不住地咳嗽。光线暗淡,听到有人喊我吃饭,这才知道一户人家正揭锅开伙。有些老屋真的被暴雨欺负过了头,就耷拉着身架落魄在风雨中。站在老屋前,无论如何都该用“恍若隔世”这现成的词了。
到匹河乡政府所在地要19公里,距离福贡县城44公里的知子罗,属于贫因村,多数人仍旧以第一产业为主,多数人中的多数选择到外面打工。海拔2000多米的坡地,庄稼总是歉收,经济作物有茶有核桃,一平均到人,就少得可怜。生活在这里的怒族同胞知足常乐,礼拜天去教堂读经雷打不动,那是他们的信仰,是支撑着他们生活信心的绝对力量。
1949年碧江和平解放,1954年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后改为州),县府、区(州)府都设在知子罗。这里,曾一度是怒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1979年9月20日至10月6日,碧江县连续16天大暴雨,造成60年来最大的洪灾,县城北部和南部出现多处滑坡和开裂,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此后几年里,碧江县多次提出搬迁县城,但因所选地址都出现泥石流而未实现。1985年12月,碧江县第三次提出搬迁县城,这一回,州政府终于同意了,但同时做出了撤销碧江县制的决定。究其原因,一是州府搬迁到六库后,碧江县城变成了死角,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滑坡加剧,在县内又无容纳一个县城的理想之地。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发文同意云南省政府关于撤销碧江县建制的报告,碧江县所属的5个区,分别划归泸水县和福贡县。当时有干部职工1086人,411人去了福贡,466人去了泸水,1987年8月,撤县搬迁工作全部结束。
撤县时,算得上是碧江县标志性建筑的八角楼刚刚峻工,原来是准备用作图书馆的,结果还没来得及购进一本书,就空着一直摆到了现在。后来这里成为知子罗村,当然也就没有比这八角楼更气派的房子拔地而起。八角楼隔着一条街,对面便是工人俱乐部,恐怕也只是那几个字还精神着,横梁变形,门窗锈蚀,鼠迹满墙,垃圾遍地。可容纳千人的电影院才放了3天电影,就沉寂下来。

极具时代特征的建筑时刻提醒着我们知子罗曾经的繁荣与热闹,也让人不禁唏嘘历史的无常与多变。这是位于主街道的一片居民区,如今这里不少的房屋早已荒废,但是也依然有村民居住其中。路上只走着零零散散的少许村民,其中还多是年幼的孩子。 摄影/于Rum


福贡县知子罗废城全景 摄影/许文舟
我来到老州府办公大楼,走廊里都是浓烟,住在里面的每家每户都生火煮饭,那些被夜雨泼过的柴禾总是放出浓烟,呛得烧菜的妇女一手捂着口鼻,一手操着饭勺。而李双妹不把浓烟当回事,骑在火塘边的一条木凳子上,正在给一把吉它校音。我想听听接下来她会弹什么曲子,结果看到我,她就忙着泡茶,直到我离开她家,再怎么劝说,她都说怕我笑话,没弹。下午她要去教堂值事,她是管风琴手,她的任务是伴奏,很多时候唱诗是不需要伴奏的,所以她也会坐到教徒中间。
在县一中,除了墙上“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几行大字,其他已面目全非,宽敞的操场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每一块都盖起了简易房,油毛毡或石棉瓦顶,看上去像一个穿戴邋遢,耷拉着脑袋的老人。差不多每到一户人家,都会烹制好茶给我喝,茶气足,味道不错,一问主人都有些自豪样,说这是老姆登茶,你还不知道?
沿着一条新开劈的路把车子开进老姆登茶厂,总算见到了这个“公司+农户+基地”的管理模式开发的茶叶产品。茶厂老总知道我也是爱茶之人,特意给我泡了一款新产品。看着黄绿清澈明亮的茶汤,再尝香气芳郁的茶水,喝下去,是林木苍翠,云雾缭绕;是碧罗山圣雪,怒江山高水长的情谊。
走在知子罗每一条小巷,遇上的差不多是流浪的狗,无家可归的猫,全放养的猪鸡,当然还有上学路上抓着石子就地玩耍的孩子。我遇上的老人,都可以把不同版本的关于知子罗搬迁的事摆给你听,末了都会是一声轻轻叹气。
县城搬迁后,知子罗全村13个村民小组,除了知子罗下村两个组处于安全地段,其他11个组都获得了分房的福利。许多年过去了,这里差不多没什么新建的房屋,究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发达外,恐怕与这里的人知足常乐的意识分不开。只要雨没往身上浇,风吹不到屁股,还操盖房子的心干什么?况且当时留下的房子都算是上好的建筑,再住几十年没有问题,于是人们一边劳动一边读经。如果嫌知子罗不适合你了,外面的世界是新的落脚点。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女孩子出去之后就远嫁他乡了,而男孩则大都会回到知子罗,这里的土地可以让他们不用担心饥饿,当然,由于人多地少,要富裕,除了按时出工劳作,还得用点脑子,想想生意或其它事情。
逛完知子罗,还剩大半天,还可以到贡山,但我决定住下来。我的这个决定后来觉得很值,不是那一晚老姆登客栈有可以打盹的炉火和自酿的苞谷酒,而是第二天清晨,总共有七种鸟叫我起床,仙女般轻盈的雾一直陪着我洗漱和早餐。离开知子罗时,我又到当年州府办公楼,没有牵挂,却总觉得不想说走就走。一个老头坐在长条石头上,翘着腿,在拉二胡。两根弦,与五个指头搏击,一滑就是凝重,再滑就是呜咽,我知道那是怒族情歌,直到我离开,他也没正儿八经地睁开过双眼。

这里不少的房屋早已荒废(左上)。旧时的图书馆只留下了空荡荡的一座楼,这里是曾经的广场和毛主席像所在地(左下)。一个坐在自家三轮车里玩耍的男孩机警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外来者(右上)。黄昏时分,祷告开始,大家皆双目紧闭,神情庄重,若有所思地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摄影/于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