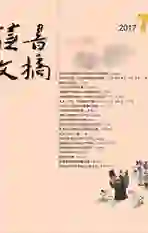父亲丰子恺为何与曹聚仁绝交
2017-07-11丰一吟
一个是挈妇将雏走上逃难之路的书生,一个是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战地记者,两位同是浙江一师出身的故交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意外相逢,本是难得的幸事,岂料共聚晚餐之后,分隔异地的两人忆及此事时,有不同观感。从 《一饭之恩》到 《一饭之仇》,两人在报纸上你来我往,引发一场争论,此后便形同陌路,乃至绝交。丰子恺、曹聚仁两人因何断交,时至今日,仍有相关研究者关注。丰子恺先生幼女丰一吟长期致力于研究父亲生平与创作,本文特摘选 《丰一吟口述历史》 一书中关于此事的回忆,可作一家之言。
1937年11月,家乡石门湾被日军攻占,爸爸下定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带着全家走上逃难之路。我们先是到桐庐投奔马一浮先生,住到离桐庐二十华里外的河头上。在此期间,爸爸收到开明书店到长沙的邀请。因此时日寇进犯杭州,桐庐也不宜久留,爸爸决定接受邀请,远赴长沙。
我们是12月21日离开河头上的,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到兰溪。精明能干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家了。我们到了桐庐后,发现交通并不困难,桐庐到兰溪尚有公共汽车可通。妈妈一路不停地为把外婆落在桐庐而落泪,我们小孩子们也都觉得缺少了一个人。船行至半途,爸爸决定派章桂哥上岸,回船形岭把外婆接到兰溪相聚。逃难诗记曰:听说行路难,其实也平常。连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到兰溪后,我们一家在临江旅馆住宿。低调的爸爸不想暴露身份,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仁”这个旧学名。旅馆把客人的名字登记在牌子上,挂在柜台上方。巧的是,爸爸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比爸爸低两级的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老同学相逢,本是好事,不料却引发一场风波,导致此后两人形同陌路。其中内情,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从爸爸的文章和章桂哥的回忆文章中知曉了一些情况。
据章桂哥在 《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 一文中所说,曹聚仁当时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他对爸爸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赞同。他劝告爸爸,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马上相帮印了名片。他的建议立刻奏效,原来在杭州没领出的中国银行的两百元存款,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爸爸到兰溪后,急于打听路途情况,遇到当战地记者的老同学曹聚仁,自然是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到长沙的事。曹聚仁一听,断然决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以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携老带幼十几个人,就算去了,也定会半途折回。他劝爸爸就近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爸爸听了老同学的劝告,打消西行的念头,打算到仙居投靠一个叫黄隐秋的老同学。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哥哥姐姐共六个人赴宴。吃完这顿饭回来后,爸爸和满娘重新与桐庐一道和我们同行的车汉亮先生商量后面怎么走。车先生是平伯的朋友,决定还是要往西走。爸爸写了张条子,委托旅馆老板转交曹聚仁先生,谢谢其款待的厚意,告诉他仍要西行,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后来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走了。
爸爸为什么临时又改变主意?当时我并不知晓原因,后来读了爸爸的 《决心》 《一饭之恩》 和《未来的国民——新枚》 三文,对爸爸当时的想法有了一些了解。具体说来,主要是聚丰园筵席上曹聚仁先生说的几段话引起爸爸的反感,使得爸爸当时就有些不快。不快的原因有三,一是曹先生认为我父亲带了一大帮人,不可能赴长沙。二是曹先生当时询问我爸爸家中孩子有几个人喜欢艺术后,爸爸回答一个也没有。曹先生表示赞许,说:“很好!”爸爸发现老朋友对自己钟爱的艺术如此不屑,有些恼火。他说: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政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制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妇孺。”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三是爸爸在1938年写的 《未来的国民——新枚》 一文中说到吃饭时,曹聚仁先生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将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又似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毁灭。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掏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顿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
那么曹聚仁先生又是怎么说这件事的呢?他晚年在 《朋友与我》 一文中这样回忆:
我知道和我相熟的朋友,一定以为我该写一位很相熟的友人:画家丰子恺兄。他和我都是一师同学,他比我早二年;别人看来,我和他同出于弘一法师之门。其实,弘一门中弟子,子恺兄以外,该说到刘质平、吴梦非、李增庸、黄寄慈诸兄,还轮不到我这个乡下佬的。离校之后,无论立达学园或开明书店,我和他时常相见,相处颇不错。虽说我对于佛学,他对于唯物史观,各不感兴趣,但彼此谈得来,从来没红过脸,够得上老朋友了。
哪知一件意外的事到来了,抗战军兴,上海沦陷了。子恺兄回到浙西家乡去,也是住不下去;正当杭州危急那一段时期,他带着一家人,还有他的姊姊,沿钱塘江流亡到了兰溪。兰溪,是我的家乡,那时,我恰好在城中,道左相遇,便邀他们在我的亲戚家中招待了一晚,还替他们安排到金华去的交通工具。那晚的餐式,相当齐全丰富,总算对得起老朋友了。(匆忙中,素菜很简单,也是无可奈何的,好在他们一家人,只有他一个人吃素的。) 他们大致在金华困居了一些日子,又经过温州,乘船回上海了。我和他便一直不见面了。
后来,我从江西转到了桂林,那时,开明书店在那里复业,宋云彬兄也把 《中学生》 复刊了。他邀我写稿,我就把旅途碰到了子恺兄的事,还说了他们沿途所见的日军残暴事迹,血淋淋的惨状,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申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我的报告,相当生动,云彬兄颇为满意。哪知,这一本 《中学生》 到了上海,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说悔不该吃我那顿晚饭。好似连朋友都不要做了。过了好久,我才转折看到这一篇文章,也曾写了一篇 《一饭之仇》 刊在上海 《社会日报》 上,他一定看到的。不过,我决定非由他向我正式道歉,我决不再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曾到杭州西湖、庐山牯岭,写了画,题了诗,已经把 《护生画集》 上的旧观点完全丢开了,和我所说的并无不同,不知他见了我,又该怎么说呢!)
后来,我读了鲁迅先生的 《我的第一个师父》……我乃恍然大悟。子恺毕竟是对弘一法师入了迷,一直在吃素的人,我是凡俗的人,摸不透他的怪癖,因此碰了钉子了。好在云彬兄站在我这边,他说:“要是那句话得罪了子恺,我还会刊出来吗?”
这篇文章是曹先生晚年回忆性文字,有许多细节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我们一家后来并没有从温州回上海等等。不过行文之间仍能看出一向对佛教有抵触情绪的曹先生对爸爸为“护生”而抗战的观点始终不认同。
关于爸爸与曹聚仁先生在兰溪相会一事引发不愉快甚而绝交的前前后后,陈星先生所著《丰子恺评传》 第七章第五节有专文作详细解读。在我看来,爸爸这样一个温文尔雅、人缘很好的人跟老同学绝交,除了逃难途中愤激的情绪原因外,还有他对护生观点的执著。在艺术旨趣上本就大相径庭的两人兰溪见面后即分道扬镳,各自发表文章引发对方误解后又缺少直接沟通的机会,以至隔膜渐深。
不管怎么說,爸爸当时坚持西行是明智的决定。尽管我们一路艰辛,但始终没有陷入敌占区,扬眉吐气地度过了八年抗战。
(选自《世纪》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