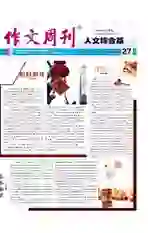地瓜
2017-07-10安宁
安宁
地瓜秧被割下来全部晾晒到麦场上之后,大地便立刻变得清爽起来,像剪了短发、等待生育的女人。一切都是丰腴的、饱满的、温柔的,连地平线似乎都有了“孕味”。尽管秋天的风已经有些凉意,黄昏的时候沿着田间走上一段路会忍不住打个寒噤。女人们在将地瓜秧全部整理干净之后,空荡荡的田地在她们眼里就是聚宝盆,一锄头下去,到处都是宝藏,到处都隐匿着希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刨地瓜和叉地瓜干的运动便拉开了帷幕。
刨地瓜是个技术活,地瓜们爱跟人玩捉迷藏,如果眼神不佳的,看不出地瓜秧被拔出来的痕迹,胡乱刨开来,大致会将一个硕大的地瓜劈成两半,露出红色、黄色或者乳白色的内里。“红心”地瓜是最甜的,生吃味道也好,于是地里便有“碍手碍脚”的小孩子跑过来将那劈开了的红心地瓜抢了去,脆生生地一口咬下大半个。
地里的地瓜堆越来越多,像海滩上潮水退去,忽然间露出的深藏在沙中的贝壳,一个一个,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农妇们尽管不是捡贝壳的少女,脸上却全是心满意足的微笑。抡锄头下去的时候也不觉得胳膊酸痛,只一下一下地刨着,一个一个地捡拾着。
等到将田地翻个底朝天之后,母亲便会找来相熟的女人们,坐在一堆堆的地瓜前边用刨子将地瓜礤成薄片,边张家长李家短地唠着嗑。刨子是特制的,专门用来礤地瓜干用的——一张四条腿的长木凳子上挖一个洞,装上一个镰刀片便完了工。女人们可以坐在凳子上像洗衣服一样弯腰礤着地瓜,我们小孩子当然也不会吃闲饭,全被大人们支使着去晾晒地瓜干。地瓜干像纸片一样,一页一页均匀地在地里铺展开来。于是等到所有地瓜都削完的时候,地里就成了大片的白。女人们直起酸痛的腰,看着面前的劳动果实,颇有又怀了一个孩子似的骄傲。
不过晾晒地瓜干全靠老天爷赏脸,如果秋高气爽,那么这一年也算有个好收成,地瓜干很快就干透了,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磨成地瓜面,以更高一些的价格卖给村里做粉条、粉皮的人家。但是假如老天爷不高兴,连着降上几天雨,地瓜干不等晾干就发了霉,自家吃不了,也卖不出好价钱,礤地瓜干时的喜气洋洋就全都变成了愁眉苦脸。若是赶上响晴的天,忽然间降下一场大雨来,整个村子里都会浩浩荡荡地出动,跑去地里捡拾地瓜干。
好在这样壮观的景象并不太多,晒干的地瓜干很快就进了仓,并换成我们需要的花花绿绿的票子。那些没有被礤、留着自家吃的地瓜,会被父母放到门口的旱井里去储藏。早井其实就是地窖,井口小,但井里面的天地却比一般的井要宽敞很多,好像一个小小的建在地下的房子。当然,能到井里逛上一圈的,也只有我这样小小的人儿。父亲总会将粗麻绳绑到我的腰上,而后牵着绳子,慢慢将我放到井底去。待我站稳后,父亲又将地瓜装到篮子里,以同样的方式放到井底。我的任务就是将地瓜们垒砖一样,一块块整齐地摞起来。忙碌的间隙,我会小心翼翼地用木棍捅一捅那些神秘的小洞,那里面除了藏着各式各样的虫子,还有让我恐惧的蛇。但蛇们似乎更怕我,每次出来露上一面,不等我尖叫就又溜回了洞里。于是我便一边毛骨悚然地摆着地瓜,一边抬头朝地面上的父母喊叫:快完了没,完了赶紧拉我上去啊,否则我很快会被蛇给吃了的!
蛇當然不会吃人,倒是我,一整个冬天都有香甜的地瓜吃。而父母因为小时候家穷,天天吃烂地瓜早就腻了,所以我和姐姐就将地瓜以蒸啊、煮啊、熬玉米粥啊、烤啊、烧啊等各种方式,无休止地吃啊吃,一直吃到冬天快要过去,我终于厌倦了地瓜,将它们遗忘在了有蛇出没的井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