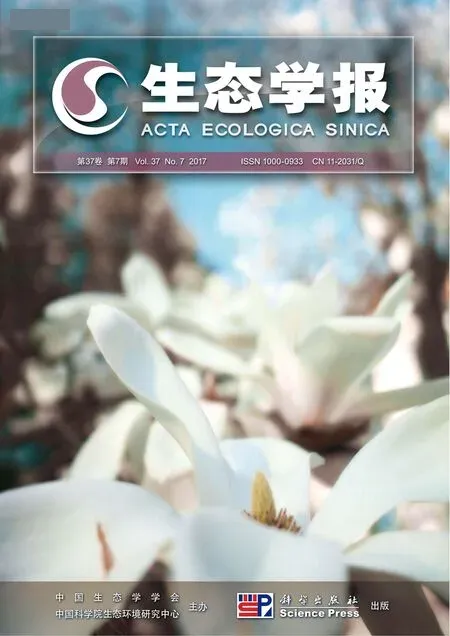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
2017-06-27刘焱序王仰麟
张 甜,刘焱序,王仰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
张 甜,刘焱序,王仰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是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恢复力是指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和重组后,仍然保持原有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的能力。梳理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乡村社区恢复力、空间恢复力相应概念,借助宏观生态学领域中的恢复力相关概念阐释乡村空间演变过程,可以在深化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理论内涵的同时更有效的理解乡村空间的演变过程和重构目标。乡村空间重构并不只是国土或规划层面的景观空间优化,而需要站在强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角度,从乡村空间演化机制入手,提升乡村空间演化动力从而驱动空间重构。将乡村空间的演变阶段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将作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引入乡村地理学研究领域,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学科研究视角,完成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的理论抽象。
乡村空间演变;乡村空间重构;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
随着近40年来中国土地政策的逐步改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和生活空间发生了快速演变[1]。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城乡关系演进的主要动力之一[2]。在一些偏远农村,就业机会减少驱动着人口向城市聚集,农村居民点开始减少;而在城市近郊,郊区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与居住空间的增加[3]。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伴随着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即乡村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改变所对应的乡村空间重构已成为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议题[4]。
中国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是目前全球社会-生态系统快速演变的一个缩影。面对全球环境变化与快速城市化的双重压力,进行适应性管理构建恢复力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5]。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论依托于Gunderson和Holling提出的适应性循环理论,将社会-生态系统演变分解为开发、保护、释放、更新4个阶段[6]。在适应性循环中,恢复力是指在关键阈值范围内社会-生态系统持续变化和适应过程中的维持能力[7];或可以被理解为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和重组后,仍然保持原有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的能力[8]。近年来,生态恢复力[9]、城市恢复力[10]、社区恢复力[11]、空间恢复力[12]等概念的深化为不同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引。
随着恢复力研究逐渐从早期的生态恢复力研究逐步向社会恢复力研究尤其是社区恢复力研究深化[13],提升乡村社区恢复力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主要议题[14]。乡村社区恢复力的构建并不仅是由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而需要关注局地经济与就业、局地环境质量、强烈的社会归属感等多个维度[15]。在这一层面上,乡村社区恢复力的提升结果与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的改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为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综合可持续发展所服务。因此,本研究拟将源于生态学概念的恢复力视角引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中,从而更有效的理解中国乡村空间演变过程、探索乡村空间重构方法,为中国乡村空间重构战略的推进提供理论指引。
1 恢复力的概念内涵
1.1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
恢复力作为物理学名词,在20世纪70年代在生态学领域被抽象化。加拿大学者C.S.Holling于1973年发表“生态系统恢复力与稳定性”一文,首次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中的恢复力视角[16]。Holling指出一个高恢复力的系统可能具有低稳定性,而一个高稳定的系统可能恢复力是较弱的;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并不足以应对种种随机事件造成的环境突变,而管理系统的恢复力可以更有效的应对系统未来所遭遇的不确定性。恢复力关注系统远离稳态时所吸收的干扰总量,是系统受干扰后回复稳态的能力,由于大多数复杂系统具有的稳态阶段并不唯一,管理恢复力显然比维持稳定性更加适用于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17]。
随着生态恢复力的研究内容逐步向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政策[18]、区域对自然灾害的响应[19]、资源与环境经济可持续[20]等宏观视角深化,恢复力概念逐渐被引入对社会系统的管理中,生态恢复力和社会恢复力存在的相互关联逐步被明确[21]。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合,社会-生态系统复合框架以一种跨学科的概念体系理解社会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直接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22- 23]。而恢复力视角作为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的有效途径,被认为是构建区域可持续性的必要环节[24]。G.S.Cumming将社会-生态系统的要素组分与关联总结为图1[25]所示。该框架着重明确了土地资源要素在社会-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图1 社会-生态系统关键要素组分与关联[25] Fig.1 key components and relationships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25]
1.2 乡村社区恢复力
与生态恢复力相对应,社会恢复力是指社区或团体应对社会、政治、环境变化产生的外部干扰和压力的能力[26]。社会恢复力主要涉足于社会系统、社区、企业等对象的描述,其中社区恢复力是关注最为广泛的社会恢复力类型[13]。在高速城市化的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化模式。针对局地人口经济与环境变化,立足于城市发展转型规划的城市恢复力研究受到了较多关注,地理空间中的信息通讯技术、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基于协同响应的创新设计、气候规划、城市蔓延控制、短路经济途径等策略被陆续提出[27]。相对城市恢复力而言,对乡村社区的恢复力研究较多关注社区和个体应对自然灾害或环境变化的能力,以适应风险、保障健康作为恢复力构建的目标[28- 29]。但是,与城市恢复力(Urban resilience / City resilience)的内涵逐步明确不同[30- 31],乡村恢复力(Rural resilience)的概念还相对模糊,多指以乡村社区为对象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15]。
本研究认为,“乡村社区恢复力”的提法相对于“乡村恢复力”而言更加明确并实用。这是由于在恢复力研究中,有必要首先确定恢复的对象(resilience of what)和恢复的目标(resilience to what),然后构建评价模型并识别系统动态过程[32]。高密度的人类活动是城市的基本特征,因而当以城市作为恢复力研究对象时,保障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福祉成为必然的规划目标。而乡村则不然,对一些乡村的生产、生态管理方式不一定是以本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为根本导向的,很可能牵涉更大尺度的要素流动与统筹[33]。由于并非所有的乡村空间都分布着大量社区,如果仅以“乡村恢复力”进行叙述,则乡村的居住功能容易被弱化,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类活动的主体特征难以被体现,尤其是在一些人类活动少的区域可能重新回到生态恢复力的研究内容中。因此,相较 “乡村社区恢复力”的提法,“乡村恢复力”一词不易直接体现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行为主体对外界干扰的适应。
在狭义层面上,乡村社区的恢复力被理解为区域在遭受外部打击如气候变化、环境灾害之后通过适应性维持原有状态的能力。但近年国外研究案例表明,乡村社区恢复力并不仅是一种回复到原有状态的反弹力,系统的转变能力值得被纳入恢复力研究范畴[34]。例如苏格兰居民通过土地信托制度完成了前瞻性的改变,而不是被动的对打击事件做出反应[14]。在墨西哥,历史时期所遭受的多次干旱与洪水事件促成了该地区水土资源管理方式的不断革新,农户的混合耕作模式有效保障了粮食供给[35];1992年以来的公共农场土地使用制改革有效提升了土地价值,但城市化导致的人口迁移也为公共农场恢复力的保障带来重要挑战[36]。环境因子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乡村社区恢复力的精准测度,对环境变化的定量与乡村环境重构一直以来是乡村社区研究的关注焦点[37]。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区所遭受的外部打击已不仅限于环境变化层面,城市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乡村社区所面临的特殊外部打击值得被高度关注。然而,由于社区恢复力研究起源于处在后城市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关于乡村社区恢复力对城市化打击的响应研究相较于全球环境变化主题而言依然较少。与之对应,国内研究在该领域也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很少以社区恢复力这一明确主题进行表述[38]。
1.3 空间恢复力
基于景观生态学研究视角,关注社会-生态系统空间格局与过程交互的空间恢复力日益成为恢复力研究的一项重要分支。空间恢复力是指系统相关变量空间变异的、系统内部和外部利益在多时空尺度被影响的系统恢复力;其中空间恢复力主要的内生要素包括系统组分及其交互的空间布局、系统的空间相关属性、内在阶段的空间变异、局地空间位置中的特定功能等;主要的外生要素包括背景基质、连通性、所引致的空间动态等[12]。也就是说,空间恢复力所描述的是社会-生态系统在异质景观中的格局与过程、结构与功能变化,而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则成为了空间恢复力的集中反映[39-41]。因此,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中的土地资源管理方式、强调自然与社会资源的空间匹配和持续利用,可以借助空间恢复力的研究视角。同时,虽然一些社区恢复力研究中并未明确指出空间恢复力这一概念形式,此类研究对社区景观/土地的类别、分布、演化、权属、价值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实际上与空间恢复力的理论内涵是相似的。
空间恢复力视角强调同一尺度内空间要素的差异性和社会-生态过程的跨尺度关联,乡村社区的演化空间差异与演化过程关联即良好的反映了这一特征。一方面,在多重驱动要素的复合影响下,即使景观管理政策等宏观变量相同,不同区位的乡村景观变化也是不一致的[42]。例如对西班牙两个自然保护区的乡村文化景观演变研究表明,恢复力的下降既可以归结为稳定景观下的社会经济衰落,也可以归因于景观演变后的土地使用多样性下降[39]。另一方面,全球和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存在的遥相关特征逐渐被关注[33],乡村社会结构与环境的演化过程可能是与更大尺度的土地利用决策背景相关联的。例如对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显示,城市的蔓延虽然不直接占用乡村土地,但与工业用地增长相同步的水污染风险严重威胁着乡村社区[43]。通过乡村空间格局的优化构建社区恢复力,在实践中即表现为乡村区域规划与乡村景观管理[44]。鉴于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与管理对策与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存在高度关联,借助空间恢复力视角分析乡村土地演变的空间交互作用与多尺度关联机制可以有效指引乡村空间重构中的乡村景观布局,从而基于土地利用空间规划的方式增强乡村社区恢复力。
2 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
2.1 乡村空间演变进程
乡村空间的演变是社会-生态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短时间尺度内经济、文化、制度对乡村空间演化的作用往往大于自然因素[45]。因此,以土地利用或景观格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乡村空间特征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和过程在空间维度上的投影,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空间快速演变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经济要素集聚、人口资源流动、城乡制度二元化的空间表征,而城乡地域关系的空间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乡村人口与用地演化方式[46]。在中国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在区域居住空间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而农户消费空间结构的变迁加速了村落自然经济的瓦解,农户生活对重点镇和重点村的依赖加强[47]。在中国西南岩溶山地,可达性差的乡村聚落因人口流失逐渐衰败,聚落空间在演化中表现出沿公路线呈线状聚集的形态[48]。在西北丘陵地区也同样发现了乡村聚落向道路集聚的特征[49],而在西南灾后重建区这一特征体现的更为明显[50]。在旅游景区周边乡村,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由封闭转向开放,乡村居住空间快速转型[51];乡村生活方式如能源消费模式等相较传统农区出现明显变异[52]。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城市要素不断向周边乡村渗透、跳跃、蚕食和延伸,乡村空间演变展现出入侵、竞争、反应、调控的生态地理过程[53];而一部分有文化的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形成了特殊的乡村社区空间形态[54]。

图2 乡村空间演变的适应性循环过程Fig.2 The adaption cycle of rural space evolution
刘彦随等认为,乡村地域演化符合生命周期演进规律,农村空心化将经历出现、成长、兴盛、稳定和衰退(转型)等阶段[55];也有研究将该生命周期简化为逻辑斯蒂生长曲线,从而借助空间算法有效实现乡村景观演变的模拟与预测[56]。如果从恢复力视角理解该生命周期,则恢复力所驱动的适应性循环包含的开发、保护、释放、更新4个阶段恰恰也可以构成类似的循环,如图2所示。①在地区发展初期,城市与乡村均迎来了经济增长与居民增收的过程。尽管城市发展速度高于乡村,但乡村空间也同样迎来大规模开发的阶段。伴随着乡村的开发,聚落开始逐渐扩张,乡村人口逐渐增长,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出现,适应性循环中系统的潜力上升。而路网密度的增大加速了村落居民与外界的交流,乡村社会网络的开放程度随之上升。②由于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乡村,城乡差距不断加大,乡村经济对居民的吸引力逐步下降。这导致乡村人口增量放缓,小学逐步被撤并,乡村人才快速流失,一部分宅基地由于住户举家外出打工而空置。而乡村中年和老年居民仍遵守从前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对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沿袭和保护。适应性循环中系统的潜力和连通度的增速放缓,拐点即将出现。③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持续,乡村劳动力大量迁出,聚落空心化现象日益明显,部分质量较低的耕地因不便机械化耕作而被撂荒,乡镇企业在与大中型企业的竞争中全面落后,年轻人对乡村空间失去文化认同感。乡村开始走向衰落,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所引致的高度复杂社会网络依然存在,交通网络依然密布但使用频率降低,适应性循环中系统体现出低潜力而高连通度的特征。④在大量人口迁居城镇后,村镇体系规划和土地整治工程使乡村空间得以重组。通过撤村并点设置中心村,配套相应政策扶持优势企业,可以实现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发展。通过废弃建设用地的复垦与土地平整,则可以完成乡村景观的优化,并进一步保障粮食生产。由于中心村便于基础设施的集中配套,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加之乡村经济活力的吸引,有助于遏制劳动力流失,实现人口再次增长。同时,中心村与中心镇之间的路网连接更为快捷,信息交流扁平化;从业稳定、居住集中的农户其社会交往形式也会相对简化。因此适应性循环中系统最终体现出低连通性高潜力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重组后的低连通性是指乡村内部的自组织结构得到强化,受城市化的干扰降低,与开发阶段的落后乡村封闭结构并不等同。
2.2 乡村空间重构方向
乡村空间重构是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龙花楼将乡村空间重构定义为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4]。这一描述与国外乡村空间研究与社区恢复力研究对该研究议题的定义是基本一致的。例如,T. Marsden指出对乡村空间的治理必须首先理解形成当前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过程平衡性,以及明晰三者在特定地域的交互关系[57];则在恢复力概念框架中,乡村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和环境恢复力所整合得到的平衡构成了乡村社区恢复力[58]。因而,在恢复力框架下依托经济恢复力构建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依托社会恢复力营造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依托生态恢复力优化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合理途径。
由于区域、社区、个体的属性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空间恢复力的多尺度关联特征值得在乡村空间重构中被重视。换而言之,在社区整体进入适应性循环中的衰退或重构阶段时,农户家庭与个体可能尚处于稳定阶段,因而乡村空间重构容易牵涉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权衡。有学者提出,乡村社会恢复力包含着抵抗过程和重构过程两种形式,其中抵抗过程是指农户对传统农耕土地管理方式的传承和保持,而重构过程是指农户改变现有的社区结构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59]。而事实上农户个体的决策差异是始终存在的,重构和抵抗过程会始终同时存在于乡村社区的演化中。因此,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需要以加强乡村社区恢复力为前提,考虑居民的传统习惯和文化感知,而不是简单的土地用途改变,或建设开发成本效益的考量。尽管对乡村文化传承和地域认同感等抵抗力因素的强调可能会降低乡村空间变化更新的速度与幅度,但可以更有效的保障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稳步演化。
在发达国家,二战后至今的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方式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有效指引。在德国,尽管农场和农民就业人口数量下降,农业生产率却成倍提高,高科技农业、可更新能源、生态公园和非农业化成为乡村发展规划的目标;然而,德国东部城市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未遏制乡村居民外迁,乡村向生态空间转型成为一种独特的规划方案[60]。在英国,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乡村发展战略的制定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地方需求与社区建设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所推行的乡村验核(Rural proofing)制度中要求任何政府部门在制订新政策时均必须评价其对乡村环境和需求的可能影响,从而构建乡村政策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过程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61]。
在中国,土地是乡村转型的活动载体,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重构形成了互馈耦合关系[62]。龙花楼认为,乡村重构以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为核心,以当地地域空间格局的调整为表征,其本质上与乡村转型发展这一概念有着相似的内涵[63]。在重构主体上,中国乡村空间重构也需要突出村民在村域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认识到村内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在原有自上而下的战略基础上突出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64-65]。在重构途径上,在中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空间出现功能区块布局,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农民新村、农业专门化生产导向下的农业专业村镇和生态旅游导向下的民俗旅游村等3类发展模式可以成为乡村重构的重要路径[66]。在重构保障上,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紧密依赖于土地整理相关规定,结合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进行乡村重构是城乡快速转型地区居民土地需求的关键保障[67]。
3 乡村空间恢复力的强化
3.1 经济恢复力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
国家和地方经济结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与乡村生产空间演化三者存在着耦合关系。由于第一产业的附加值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普遍低于非农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种粮积极性下降、迁入城市务工成为必然选择。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改变了局部耕地种植方式,而乡镇企业由于难以发挥集聚优势容易在与城郊大型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使得乡村生产空间的经济活力下降,进一步引致乡村劳动力的外流,乡村人口结构失衡、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基于此,强化乡村经济恢复力有必要从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园区化两方面进行优化[4]。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优化农田空间布局成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土地生产率的有效途径。为有效抵御旱涝灾害、增强农业灾害恢复力,有必要继续加强农用地综合整治力度,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田块空间结构,进行土地平整实现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布局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大型农场相较于小型农田并不一定具备更高的恢复力[68]。这是由于管理大农场所需的资金投入大导致其灵活性差,大农场的发展更加依赖于跨尺度的区域宏观经济形势。因此,针对农业产业化的经济恢复力强化不仅涉及农田景观的优化,而且需要保障国家和区域的农业经济的战略地位。例如,国家稳定的粮食价格会加强农户对农用地整治的支持意愿;反之,下跌的粮食价格会导致农户失去管理乡村生产空间的信心,削弱乡村经济恢复力。
乡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可以直接为乡村社区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促进合作和交流、提升生产附加值,也可以间接的增强经济体与社区的联系、提升地域空间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培训机会、完成对社区活动的支持或赞助[58]。然而由于乡村企业在规模上相对有限,构建非农产业基地实现工业园区化成为发挥集聚优势、保障乡村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同时,发挥乡村区位优势打造特色品牌成为提升乡村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郊区,“种、养、加、旅”(种植花卉苗木、养殖种猪肉猪、农产品加工、农业观光旅游)四业并进的乡村产业结构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非农就业,耕地向商服与工业用地转变而非传统农区中的全部向居住用地转变,加强了乡村经济恢复力、实现了乡村生产空间重构[69]。
3.2 社会恢复力与乡村生活空间重构
中国农村居住空间“散、乱、空”的现状决定了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重点在于优化农村聚落布局、配置农村基础设施[4]。然而,乡村聚落演化的动力机制在不同地域空间内并非是均等化的,仅从工程意义上进行空心村土地复垦或重复的路网、林带建设可能并不能达成区域整体的乡村生活品质提升。乡村生活空间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乡村社区中居民的社会主体行为,然而相较于英国威尔士地区等乡村社区重建的成功案例,中国当前的乡村社区重建工作重心仍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为主体,居民的主观整治意愿缺乏引导[70]。为此,有必要首先识别乡村生活空间演化的内外动力机制,通过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实现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恢复力强化,驱动乡村生活空间重构[64]。
在大城市周边和偏远乡村,社会恢复力的强化和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方式是有明显差异的。在大城市附近,人口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引致乡村居住空间的不断扩张。年轻村民在村庄外围建设大量新宅,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管控导致这部分村民的居住空间用地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此类乡村空间重构应采用“填实插建”的土地整治方式,鼓励村域内基于民众充分参与的居住空间自发调整。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的相应探索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周边乡村居住空间用地紧张的现象。这种政策引导是社会恢复力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在偏远乡村,随着村域大量人口流失,“迁村并点”的土地整治方式成为高效重构乡村居住空间的有效途径。然而,虽然村民普遍同意对村庄进行统一规划,但涉及中心村建设中的搬迁问题是,大部分村民考虑到补偿条件[71]。也就是说,在补偿金额不足时,农户参与中心村建设并不能提升生活质量,反而会由于经济压力增加脆弱性。在经济保障机制不到位的前提下,“迁村并点”的土地整治方式也可能会削弱社区恢复力。例如在山区生态移民搬迁过程中,居住到中心村的居民将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搬迁后社区的恢复力并未得以有效提升,移民搬迁的惠民效果被大幅弱化。因此,乡村生活空间重构需要与乡村社会保障充分结合,从而使乡村生活空间重构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提升。
3.3 环境恢复力与乡村生态空间重构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是导致乡村生态空间恶化的直接原因,而土地利用行为又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空间呈现,因此对乡村生态空间的重构与乡村清洁生产、居民健康生活紧密相关[4]。在乡村生态空间重构中,有必要针对农村不同生态系统自身特点,完成乡村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即环境恢复力的强化。此处采用“环境恢复力”的表述方式,也正是考虑到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导向已超越了传统生态恢复力研究所关注的生态系统研究对象。换而言之,乡村生态空间重构是包括景观管理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增强、污染综合治理等多重目标的土地综合整治。
乡村生态景观管护和建设是提升乡村空间恢复力的有效方式,宇振荣等将其总结为恢复农业景观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加强灾害适宜性管理提高水土安全、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四个方向[72]。其中对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对自然灾害的适应均可形成乡村环境恢复力的直接提升。近年来,中国多项大型生态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生态空间重构。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牧民定居工程等项目在改变乡村居民生计方式、部分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了局地山清水秀生态空间的重塑。
随着化肥农药施用量的不断加大,乡村非点源污染已经成为破坏乡村水土资源质量的主要风险源。同时,乡村高能耗、高污染的中小企业对局部乡村地区人类健康构成明显威胁。而矿区生态风险的产生更是土地利用行为导致乡村生态空间恶化的直接体现[73]。有学者发现,村域转型发展中的环境污染指数曲线具有倒“U”型特征,资源投入从低效率向高效率转变,环境污染从高污染向低污染转变[69]。因此,随着乡村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乡村清洁化、绿色化生产成为提升环境恢复力的必然要求,而工矿用地整治是景观尺度上乡村生态空间重塑的直接表征。
4 结语
面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需求,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是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恢复力是指系统吸收干扰、经历变化和重组后,仍然保持原有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的能力。借助宏观生态学领域中的恢复力相关概念阐释乡村空间演变过程,完成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的理论抽象,可以在深化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理论内涵的同时更有效的理解乡村空间的演变过程和重构目标。本研究将乡村空间的演变阶段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中,从而将作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引入乡村地理学研究领域。乡村空间重构并不只是国土或规划层面的景观空间优化,而需要站在强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角度,从乡村空间演化机制入手,提升乡村空间演化动力从而驱动空间重构。针对适应性循环的动态特征,在进一步研究中有必要加强对乡村空间重构过程的动态监控,完成乡村发展转型中社会-生态系统演化临界阈值的定量识别。
[1] Fang Y G, Liu J S. The modification of North China quadrangles in response to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villages: 1970—2010s. Land Use Policy, 2014, 39: 266- 280.
[2] Li Y H, Westlund H, Cars G. Futur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comparison in a global context.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0, 2(4): 396- 411.
[3] Tan M H, Li X B. The changing settlements in rural areas under urban pressure in China: patterns, driving for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3, 120: 170- 177.
[4]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 1028.
[5] Garmestani A S, Benson M H. A framework for resilience-based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013, 18(1): 9.
[6]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7] 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Scheffer M, Chapin T, Rockström J.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15(4): 20.
[8]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Kinzig A.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2): 5.
[9] Peterson G, Allen C R, Holling C S. Ecological resilience, biodiversity, and scale. Ecosystems, 1998, 1(1): 6- 18.
[10] Chelleri L, Waters J J, Olazabal M, Minucci G. Resilience trade-offs: addressing multiple scales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urban resilience.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2015, 27(1): 181- 198.
[11] Berkes F, Ross H.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3, 26(1): 5- 20.
[12] Cumming G S. Spatial resilience: integrating landscape ecology,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Landscape Ecology, 2011, 26(7): 899- 909.
[13] 郭永锐, 张捷. 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及其地理学研究议题.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 100- 109.
[14] Skerratt S. Enhancing the analysis of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community land ownership.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1: 36- 46.
[15] McManus P, Walmsley J, Argent N, Baum S, Bourke L, Martin J, Pritchard B, Sorensen T.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resilience: what is important to farmers in keeping their country towns aliv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1): 20- 29.
[16]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 1- 24.
[17] 孙晶, 王俊, 杨新军.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综述. 生态学报, 2007, 27(12): 5371- 5381.
[18] Chapin Ⅲ F S, Lovecraft A L, Zavaleta E S, Nelson J, Robards M D, Kofinas G P, Trainor S F, Peterson G D, Huntington H P, Naylor R L. Policy strategies to address sustainability of Alaskan boreal forests in response to a directionally changing clima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6, 103(45): 16637- 16643.
[19] Adger W N, Hughes T P, Folke C, Carpenter S R, Rockström J.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coastal disasters. Science, 2005, 309(5737): 1036- 1039.
[20] Mäler K 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 in ecosystem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8, 39(1): 17- 24.
[21] Adger W N.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3): 347- 364.
[22] Binder C R, Hinkel J, Bots P W G, Pahl-Wostl C. Comparison of frameworks for analyzing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013, 18(4): 26.
[23]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2009, 325(5939): 419- 422.
[24] Fol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53- 267.
[25] Cumming G S, Barnes G, Perz S, Schmink M, Sieving K E, Southworth J, Binford M, Holt R D, Stickler C, Van Holt T. 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resilience. Ecosystems, 2005, 8(8): 975- 987.
[26] Adger W N, Kelly P M, Winkels A, Huy L Q, Locke C. Migration, remittances, livelihood trajectories, and social resilience.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2002, 31(4): 358- 366.

[28] Sherrieb K, Norris F H, Galea S. Measuring capacities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0, 99(2): 227- 247.
[29] Smith J W, Anderson D H, Moore R L. Social capital, place meanings, and perceived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Rural Sociology, 2012, 77(3): 380- 407.
[30] Pickett S T A, McGrath B, Cadenasso M L, Felson A J.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resilient cities. Building Research & Information, 2014, 42(2): 143- 157.
[31] Ernstson H, van der Leeuw S E, Redman C L, Meffert D J, Davis G, Alfsen C, Elmqvist T. Urban transitions: on urban resilience and human-dominated ecosystems.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2010, 39(8): 531- 545.
[32] Gunderson L, Kinzig A, Quinlan A, Walker B, Cundhill G, Beier C, Crona B, Bodin Ö. Assessing resilience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workbook for practitioners. Version 2.0. Resilience Alliance, 2010.
[33] Challies E, Newig J, Lenschow A. What rol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research in governing global teleconnec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27: 32- 40.
[34] Wilson S, Pearson L J, Kashima Y, Lusher D, Pearson C. Separating adaptive maintenance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013, 18(1): 22.
[35] Endfield G H. The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of social-environmental systems in colonial Mexico.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10): 3676- 3681.
[36] Barnes G. The evolution and resilience of community-based land tenure in rural Mexico. Land Use Policy, 2009, 26(2): 393- 400.
[37] Woods M. New directions in rural stud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1): 1- 4.
[38] 杨新军, 石育中, 王子侨. 道路建设对秦岭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一个社区恢复力的视角. 地理学报, 2015, 70(8): 1313- 1326.
[39] Rescia A J, Willaarts B A, Schmitz M F, Aguilera P A. Changes in land uses and management in two nature reserves in Spain: evaluating the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8(1): 26- 35.
[40] Frazier T G, Wood N, Yarnal B.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n land-use strategies for adapting to climate-change-enhanced coastal hazards: Sarasota, Florida. Applied Geography, 2010, 30(4): 506- 517.
[41] Kelly C, Ferrara A, Wilson G A, Ripullone F, NolèA, Harmer N, Salvati L.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land degradation in forest and shrubland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evidence from Gorgoglione, Basilicata, Italy. Land Use Policy, 2015, 46: 11- 20.
[42] 肖禾, 张茜, 李良涛, 郑博, 宇振荣. 不同地区小尺度乡村景观变化的对比分析. 资源科学, 2013, 35(8): 1685- 1692.
[43] Chiang Y C, Tsai F F, Chang H P, Chen C F, Huang Y C. Adaptive society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resilience of a rural region of Taiwan. Land Use Policy, 2014, 36: 510- 521.
[44] Morrison T H, Lane M B, Hibbard M. Planning, governance and rural futures in Australia and the USA: revisiting the case for rural regional plann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015, 58(9): 1601- 1616.
[45]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 1213.
[46]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变化. 自然资源学报, 2010, 25(10): 1629- 1638.
[47]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微观机制——以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为例. 人文地理, 2012, 27(6): 56- 61.
[48] 李阳兵, 罗光杰, 邵景安, 程安云, 王成, 白晓永. 岩溶山地聚落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化模式. 地理学报, 2012, 67(12): 1666- 1674.
[49] 郭晓东, 马利邦, 张启媛.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经济地理, 2012, 32(7): 56- 62.
[50] 任平, 洪步庭, 刘寅, 周介铭. 基于RS与GIS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变化特征与景观格局影响研究. 生态学报, 2014, 34(12): 3331- 3340.
[51]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王鹏.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353- 1360.
[52]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乡村旅游诱导下农户能源消费模式的演变——基于六盘山生态旅游区的农户调查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26(6): 981- 991.
[53] 祁新华, 程煜, 胡喜生, 陈烈, 林小阳, 周燕萍.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以广州市为例. 生态学报, 2010, 30(16): 4512- 4520.
[54]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刘斌.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 1056.
[55] 刘彦随, 刘玉, 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193- 1202.
[56] 季翔, 刘黎明, 李洪庆. 基于生命周期的乡村景观格局演变的预测方法——以湖南省金井镇为例. 应用生态学报, 2014, 25(11): 3270- 3278.
[57] Marsden T. Rural Futures: 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and its regulation. Sociologia Ruralis, 1999, 39(4): 501- 526.
[58] Steiner A, Atterton J.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to local resilien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40: 30- 45.
[59] Paniagua A. Farmers in remote rural areas: the worth of permanence in the place. Land Use Policy, 2013, 35: 1- 7.
[60] 孟广文, Gebhardt H. 二战以来联邦德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演变.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644- 1656.
[61] 龙花楼, 胡智超, 邹健.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地理研究, 2010, 29(8): 1369- 1378.
[62]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 138.
[63] 龙花楼.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64]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 地理学报, 2012, 67(6): 771- 782.
[65] Long H L. Land consolidation: an indispensable way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4, 24(2): 211- 225.
[66] 韩非, 蔡建明. 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形态演变与重建. 地理研究, 2011, 30(7): 1271- 1284.
[67] Long H L, Li Y R, Liu Y S, Woods M, Zou J.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fueled by ‘increasing vs. decreasing balance′ land-use policy for dealing with hollowed villages. Land Use Policy, 2012, 29(1): 11- 22.
[68] Hammond B, Berardi G, Green R. Resilience in agriculture: small-and medium-sized farms in Northwest Washington State.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13, 37(3): 316- 339.
[69]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郭艳军. 大城市郊区村域转型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与优化调控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北村为例. 地理学报, 2013, 68(6): 825- 838.
[70] Long H L, Woods M. Rural restructuring under globaliz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Wales?.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1, 6(1): 70- 94.
[71] 陈玉福, 孙虎, 刘彦随.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地理学报, 2010, 65(6): 727- 735.
[72] 宇振荣, 张茜, 肖禾, 刘文平. 我国农业/农村生态景观管护对策探讨.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2, 20(7): 813- 818.
[73] 潘雅婧, 王仰麟, 彭建, 韩忆楠. 矿区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述评. 生态学报, 2012, 32(20): 6566- 6574.
The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a resilience view
ZHANG Tian, LIU Yanxu, WANG Yanglin*
LaboratoryforEarthSurfaceProcess,MinistryofEducation,CollegeofUrbanandEnvironmentalScience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strategic needs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recently, reasonabl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 is fundamental for rural area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present study, a major concept was emphasized, where resilience was defined as the ability of a system to maintain its origin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feedback, and function after absorbing interferences and experiencing changes and reconstruc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 is determined by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however, mor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local economy and employment, lo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stablishing a strong social sense of belonging. At this level, the promotion of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 is intrinsic with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the integr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mphasized and integrated a series of core concepts about resilience, such as social-ecological, rural community, and spatial resilience. A more suitable re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for the Chinese rural area could be established if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concepts is developed, with the combined resilience method from the current study. We interpret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village space using the resilience concept, based on the macroscopic ecology. Simultaneously, an abstract comprehension of the rur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as perform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coul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rural spac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a more eff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reconstruction target for the rural area. Furthermore, the present study embedded the evolutionary phase of rural space into the social-ecological adaptive cycle, which will elucidate the adaptive social-ecological cycle in the geographical research. We emphasized that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was optimized for landscape space at the land-planning level; moreover, we need to improve the socio-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develop the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s. Under a resilience framework, we should construct an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rural production space based 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develop a comfortable living space relying on social resilience. The ecological space should also be optimized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ese could be identified as a suitable way to reconstruct the rural space. Based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aptive cycl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ynamic monitor for the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in future research. The critical threshold of socio-ecological evolution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also be quantified in further research.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resilienc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adaptive cycle
10.5846/stxb20151118233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2014BAL01B01E)
2015- 11- 18; 网络出版日期:2016- 08- 30
张甜,刘焱序,王仰麟.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生态学报,2017,37(7):2147- 2157.
Zhang T, Liu Y X, Wang Y L.The rural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a resilience view.Acta Ecologica Sinica,2017,37(7):2147- 2157.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ylwang@urban.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