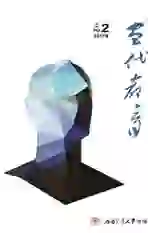沉潜与突围:纳雍诗歌创作群印象
2017-06-24雷越
雷越
在文学发展史的链条上,纳雍文学的崛起对黔西北文学的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而纳雍文学现象的生成则可以作为一个标本透视出黔西北文学的演进和成就。因此,当我在2011年的秋天读到《纳雍跨世纪新诗精选》这本诗集时,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对纳雍文学的认知与理解。《纳雍跨世纪新诗精选》是一本汇集了纳雍老、中、青三代诗人的诗歌选集,它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当代纳雍诗人的群体风貌和文学才情。同样,作为一本捍卫记忆、立足当下的诗歌选集,它以文学备忘录的形式对纳雍诗歌的创作实绩进行重估和审视。无疑,这是对诗歌的正名和对诗人的致敬。
作为黔西北文学的一个支流,纳雍文学在短短几十年间以燎原之势赢得了在朝和在野的作家和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对于沉潜在纳雍这块土地上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鞭策;这是对诗歌精神的价值认同,也是对诗人心灵的切肤感知。以我之见,与其把这本“档案式”的诗歌选集看成一本“备忘录”,不如把它看成一本“心灵史”,因为它记载的是几代纳雍诗人对文学持续不变的热情和始终如一的关怀。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纳雍就出现陈绍陟、周西篱这两位全国知名诗人,随后的空空、睁眠、曾居一等人的诗歌创作又把纳雍文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本诗集中展示的“60后”诗人的作品,是迄今为止纳雍诗歌创作所抵达的最高峰。我把“纳雍60后”诗人的创作看成是纳雍诗歌的第一次“突围”。
在我看来,这些对写作怀有崇高敬意的“60后”诗人们,他们是民间苦难的见证者和当事人。在那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时代,这一群沉潜在民间的写作者,以笔为旗,在苦难的历程中磨砺出了圣洁光亮的品性。不管外界是喧嚣还是沉默,他们依然以其赤子的情怀、倔强的品质守护住心灵的最后一块处女地。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无论是自省还是忏悔,都表明了他们寻求“光明之子”的渴望。这是一群在暗夜中穿行的孤独者,他们把生命贴近泥土,把根脉植入大地。尽管他们的身上背负着时代的铁条和生存的伤痕,但是他们依旧在海拔2000多米的云贵高原上诉说着人性的美好和生命的高贵。正是这群诗人的坚守,才使得诗歌独立、自由的品质得以延续和传承。
也许,他们最初的诗文发表并不是在正统的期刊上,或许是发表在母亲悲苦的眼神里和情人的倾诉之间,或许是发表在父亲苍老的额头上和友人真诚的微笑中,或许是发表在清风的低吟里、流水远逝的刹那和花朵绽放的瞬间……甚至可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诗友和诗友之间流亡。一方面,他们以诗歌的名义感谢生命的馈赠和上苍的怜悯;另一方面,则以诗歌的名义作为弱者反叛的武器,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僵死制度的掘墓人。循着那些在黑夜里咏叹的文字,我们能嗅出玫瑰的馨香和百合的余韵,我们能听到燕子的呢喃和夜莺的歌唱。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夜莺。在孤寂的夜里独自悲鸣和自我疗伤,这中间负载着高原男人的汗水和女人的眼泪。
“纳雍60后”的代表诗人中,陈绍陟像一个彳亍地穿行在历史中的朝圣者,他的诗歌有一种沉潜于大地的厚重感和坚实感。《西部大书》是一曲遥远的绝响,历史的冲突、文明的磨合、心灵的焦灼、贲张的血脉,在强烈的家国意识中得到了延展和升华。而周西篱则像是从古代《西洲曲》中涉水而来的采莲人。她的长诗《随水而来》,在美丽与哀愁中倾吐着内心的忧郁与惶惑,其温婉舒缓的笔调下流出娟娟细腻的情思。而空空、睁眠、曾居一、王家洋的诗歌现实感极强,他们都善于经营诗歌的意象,把叙事、抒情、哲理杂糅在一起,透露出深邃的思考和忧患的意识,折射出一种至善至美的人性回归。
纳雍诗歌的第二次“突围”,应该是以“纳雍80后”为主,其代表人物有徐源、李光明、闵云霄等人。这一代人处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他们接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能够获得更多的精神同道。和外界零距离的接触,也使得他们的诗歌在思想的高度上与语言的技巧上,都给前辈们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纳雍80后”并不是“垮掉的一代”,相反,他们以其“怀疑一切,反叛一切”的姿态去撕开时代的丑陋面目,在沉痛的生存体验中感知社会的脉搏和呼吸。他们把根系植入村庄和岁月的深处,把笔锋指向人类尴尬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并通过敏锐的观察,站在城市和村庄的临界点上,反思后工业化时代肆掠下所引发的社会灾难。在“带血的文字”中充满着对自由、理性、正义、公平的向往与追求。在纳雍崛起的“80后”诗人中,徐源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他喜用短句,诗风多变,手法多样,意象交错叠起,如兔起鹘落,错落有致。其诗歌语言的张力和密度在“纳雍80后”诗人中,目前无人能出其右。徐源的大诗《西部,西部》浮出地表,标志着纳雍诗歌又一次跳出了低吟浅唱的小我抒情,汇入了诗歌的精神灵地,在时间的黄昏中,在辽阔的西部大地上绵延着的是苍凉的挽歌和史诗般的呐喊。
从“50后”到“80后”,纳雍诗歌并没有出现文化上的断层。在精神跋涉的领域里,纳雍诗人凭借自己对诗歌写作的热忱始终守望着心灵的故乡。因此,纳雍诗歌的崛起实际上是一種诗歌精神的复活和诗歌品格的延伸。在我看来,无论是高楼林立的城市下一切才刚开始破土而出的新生事物,还是故土的沦丧所带来的喧哗与骚动,这一切已经内化成他们内心的虚空和沉静。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精神超脱,也不是一种躲避崇高的现实姿态。这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和人生的情怀,这是一种真性情和真生命。
这样的生命状态一直沉潜在民间,扎根在底层。在黔西北这片静默的土地上,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坚守着这样的信条。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比金子更可贵的人格力量。这是一群纯情的抒情歌手,他们的根深深地潜伏在每一条河流底部,镌刻在每一座山峦的背后。这是对写作的虔诚、生命的敬畏和对大地上苦难的悲悯。可能外界的作家们还在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黔西北的作家们则安静地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反复地书写着乡村的麻木、苦难、善良和慈悲。同样,对语言的迷恋使得他们的写作一度陷入狂欢之中,指向一种形而下的虚无,缺乏那种大作家体内散发出来的大悲悯和大愤激。但是在复原人类至善至纯的心性这一工作中,其心灵指针是一致的。在他们的笔下,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劣,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清晰可辨,这是一种至真至爱和至情至性的人格彰显,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和对自由精神的认同。尽管在语言的修辞上还显得粗糙,在思想的境界上还需要更为真切的体认。但是这种良善的秉性可以弥补他们文字上带来的缺失。
当然,纳雍的诗歌在精神视野的横截面还较为局促与狭窄。敏感的、忧郁的、愤怒的诗人们并没有真正的从宏观上透视出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性,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思考还显得苍白与乏力。而“纳雍80后”作为纳雍文学第二次突围的生力军。在复杂而多元的文化语境下,如何在不同的颜色中分辨主体和个体,如何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拯救自己从而获得一条精神重生之路。是继续沿着生命审美的轨迹凸显人间的温情,还是沿着思想的脉络寻找栖息的家园。是继续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呼吁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还是俯下身子同普通的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地去体验生存的苦难。这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