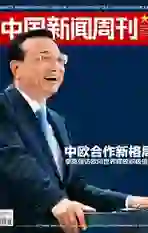葡萄干就是新疆手抓饭的“冰雪之气”
2017-06-15邝海炎
邝海炎
炒饭加羊肉,偏干和咸,有了那几粒葡萄干,“手抓羊肉饭”入嘴才温润,下咽才甘醇。新疆人用自己种的葡萄干给抓饭提味,哀怨苦乐要从抓饭里出来,人生才有分量
上个月,与同学结伴去新疆搞了圈自驾游。途经戈壁、沙漠、绿洲、草原、雪山,一路原生态,惊艳连连,嘴巴都“哇”麻了。
作为吃货,我们在欣赏美景之余,自然也少不了品尝新疆美食。旅程结束时,哥儿几个众口一词,最恋恋不舍的还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上那家“手抓羊肉饭”。
单论羊肉,这家的还不如机场的肥美大气;单说米饭,也不如乌鲁木齐的糯软精致。为什么却迷倒了我们?就是那几粒葡萄干放得好。“手抓羊肉饭”的“主角”是炒饭和羊肉,偏干和咸,有了那几粒葡萄干作“配角”,入嘴才温润,下咽才甘醇,整个味道就提了出来。
甜食可以提味,是烹饪史上的常识。西敏司的《糖与权力》一书写道,“以復合碳水化合物为核心主食,同时佐以调剂味道的外围辅食,这是人类饮食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在法国人喝下午茶配马卡龙,就是调味。上海人做菜喜欢放糖,也多是用糖来提鲜。
那新疆“手抓羊肉饭”用蔗糖来提味行不行?不行,葡萄干是一大粒的,不会融化,因此不会破坏羊肉和炒饭的味道。而蔗糖是粉末状,一加热就融化在羊肉和炒饭里,手抓饭就变成糖炒饭了。
在离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刚好放了一部谢霆锋主演的电影《决战食神》。葛优在里面演七叔,也是美食家。有一天,他看到两个小和尚在津津有味地吃馒头,还争论谁的馒头好吃。葛大爷就过去掰了点小师傅的馒头吃,然后断定:“小麦是河套的小麦,可是发酵时间长了,揉面的时间短了,蒸的时候火太大,现在已经出锅五个小时了”。小和尚也慧根壮硕:“您真厉害,一口就吃出了这个馒头的前世今生。可有一种味道你没品出来,这小麦是我自己种的,面是自己发酵的,蒸也是自己看着上锅蒸的,所以我这个馒头最好吃”。我当时在飞机上就想,新疆人用葡萄干给“手抓羊肉饭”提味,大概也有小和尚的美意吧。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讲得更透彻:“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像对竹的爱意,惟因见父亲那么殷勤地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分量。”新疆人用自己种的葡萄干来给抓饭提味,哀怨苦乐要从抓饭里出来,人生才有分量。
人与土地的亲在关系,艺术作品有更微妙的表现。一般人翻齐白石画册喜欢围着虾啊,螳螂呀,边看边赞叹,艺术家徐冰却被齐白石《白菜辣椒图》里红得不能再红的辣椒吸引了,“什么人能把辣椒看得这么红?只有那种对生活热爱至深,天真、善意的眼睛才能看到。我好像看到了白石老人艺术的秘密:他为什么可以是在艺术上少见的、越老画得越好的人?因为,他越到晚年对生活越依恋,他舍不得离开,对任何一件身边之物都是那么爱惜。万物皆有灵,他与它们莫逆相交了一辈子,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一切都是那么值得尊重与感激。他晚年的画,既像是第一次看到红辣椒的感觉,又像是最后再看一眼的不舍之情。爱之热烈是恨不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带走的。这是超越笔墨技法的。”齐白石对辣椒如此厚爱,肯定也与湖南人嗜辣有关,如果老齐是不爱吃辣椒的江浙人、广东人,他画的辣椒断不会红得这么可爱吧?
俗谚有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在日本吃鱼片不可无芥末,在韩国吃拌饭不可无泡菜,在河南吃饺子不可无蒜瓣,在山东吃大饼不可无大葱,在新疆吃“手抓羊肉饭”也不可无葡萄干呀!
明末散文大家张岱主张,文章要有冰雪之气。他认为,鱼肉一类的食物,见到风和阳光就容易变质,放入冰雪中就不会腐烂,这说明冰雪能保鲜食物。吴承学先生解得好:“冰雪之气,就像剑之光芒、山之空翠、月之烟霜、古铜之青绿、玉石之胞浆,是诗文的生命和特征。”(《晚明小品研究》)
这葡萄干不就是新疆手抓饭的“冰雪之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