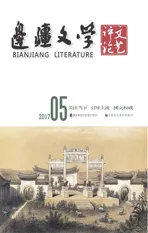“文革”小说必须对“文革”深刻反思
2017-06-07姚全兴
姚全兴
“文革”小说必须对“文革”深刻反思
姚全兴
近年来,上海“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各有其面目。例如金宇澄的《繁花》富有上海地方语言特色,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刻画了一代人的心灵成长,王承志的《同和里》突出体面是上海的精神,胡廷楣的《生逢1966》描写了“老三届”少年的艰难成长,吴亮的《朝霞》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艺青年的自画像。它们涉及上海“文革”期间平民生活,但存在内容不真不美和碎片化等严重问题,和文学作品应有的思想品质、审美要求有很大距离,并由此衍生为之辩解和开脱的故弄玄虚的托词。《繁花》尤其如此。
一、无可置疑的不真不美
首先指出,关于“文革”早有彻底否定的历史决议,反映“文革”的小说决不能违反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正确态度,小说创作决不能例外。彻底否定和深刻反思“文革”,是“文革”小说创作的前提,也是它必须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它的历史意义永远不会过时,它对当下现实的积极影响更毋庸置疑。上海“文革”题材小说(以下简称上海“文革”小说)离此甚远,不能不令人深深遗憾。
还要说明,《繁花》等上海“文革”小说,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革”小说,但它们和“文革”题材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小说中对“文革”的叙述和描写,基本上体现了作者对“文革”的观点和倾向,因此可以称为“文革”小说。近年来上海“文革”小说有一种方兴未艾的景象,这当然是好事,总比对“文革”题材讳莫如深、不敢问津好。而且,许多评论家对它们的赞美声不绝于耳,让人有繁花似锦的感觉。但如果一味赞美,肯定不利于小说的健康发展,更何况它们存在这样那样的硬伤,需要发一点针砭的声音。
上海“文革”小说的一个特点,是没有真切反映“文革”几乎波及每个家庭的大内乱、大浩劫、大灾难的铁的事实。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不愧为写“老三届”生活题材的大手笔,热情啊敏感啊躁动啊迷茫啊都有所体现。不少情节例如小老大沙龙里的各色人物出言吐语比较精彩,性格特征相当鲜明,而他们讨论的话题也在奇特中有一些智慧和俏皮,表明作者具有刻画人物心理和形象的功力。但是读者在欣赏诸如此类的描写时,不免怀疑当时“文革”思潮冲击所有生活领域,难道真有这样肆无忌惮的沙龙,可以让人们天马行空地口无遮拦?难道不怕隔墙有耳,担心告发和秋后算账?当时小范围的聚会也不是没有,但人们只能悄悄地议论时局和臧否人物,哪能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放浪形骸?所以,那种绘声绘色的沙龙情景只能是虚假的,只能是那种“文革”时10岁左右没有真切经历“文革”的人的想当然。作者没有也不可能表现“文革”的社会动荡和人生苦难,想真正表现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心灵成长和历史命运,勉为其难。
金宇澄的《繁花》小说腰封上,有“有关上海最有质感,最极致的长篇”一行字,其中充满小家子气的描写很多。第五章中津津乐道阿宝和蓓蒂在淮海路的“伟民”中看邮票的过程,作者关于邮票的知识尽情发挥,似乎要让人知道“文革”时期也不乏太平盛世景象。第七章中关于南京天王府的宫女、宝石、黄金和金锣开道的叙述不嫌其烦,卖弄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趣闻轶事来填充篇幅,吸引人的眼球。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那一桌桌流水席,请客吃饭的故事里还穿插三个桃色新闻,以酒场欢场和不少黄段子吸引眼球和博取阅读率,就更不要说它了。奇怪的是,这种对日常琐事的迷恋和沉溺居然好得无以复加,“经由他的讲述,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世俗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第11届【2012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授奖词)但不敢苟同者也大有人在,有人把《繁花》讥为皇帝的新衣,有的说“繁花如麻”,有的说“看过繁花,男男女女吃吃喝喝无聊透顶”。更有人认为《繁花》“经验过剩而内里虚无的内核”,“沪生、阿宝虽然从历史中走来,但这其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历史。”而且,小说中人物屡屡的“不响”,这种“沉默的大多数”,“正指向了社会存在中人道主义的缺席”,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创意和笔法。
王承志的《同和里》中,同样充满了市井生活味,有些读者还以为这种味道真不错,上海小市民的日子可以嘛。特别是九岁男孩“大耳朵”捣蛋鬼的种种恶作剧描写,让人以为当时的小孩子都很天真活泼可爱,哪里知道他们中有许多狄更斯笔下那样可怜的“雾都孤儿”。这无疑是作者用生花妙笔加工了的味道,大大的夸张了美化了“文革”期间的平民生活。我们不否认小说中也写了爱吹牛的阿陆头因为一句触犯天条的话,一个打碎天字第一号人物头像的特大事故,被当局严厉制裁。但是,这种人生悲剧被小说的市井生活冲淡了掩盖了,并不能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和痛苦的思索。一部应该揭露“文革”真相的小说,为什么写成这样几乎略去了那个时代残酷一面的血淋淋描写?原来作者着力要写的是“体面”,认为“体面才是上海精神中最宝贵和根本的东西。”这就奇哉怪也,“文革”压力山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还有平民百姓的体面?难道“文革”中极少数上海女性“活得很体面,生活艰难,但背脊挺直,有担当有定力”,当时上海人的精神就是体面了?
比较起来,胡廷楣的《生逢1966》还具有相对的真实性。“老三届”学生陈瑞平典型地经过了父亲自杀、母亲病逝、女友分离等人生劫难,却还要以革命青年的姿态要求参加红卫兵。他没有觉悟过,也不可能觉悟,但在迷茫和无奈中保持了固有的纯真心灵。父亲自杀了,陈瑞平真诚地对母亲说:“妈妈你不能哭。你这样哭,是为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派哭泣。”妈妈很惊讶,不知不觉就停住了她的哭泣。厂里开他母亲批斗会后,晚上回家妈妈很迟疑地看了看瑞平,说:“瑞平,有话你就说好了。”“你不能叫我瑞平。我和你划清界线了。”“那么叫你什么?叫你陈瑞平同志?”妈妈两只眼睛瞪得很大,很有些怕人。“你不能叫我同志。”妈妈的两行泪珠像黄豆一样滚到地板上,“我除了叫你儿子,还能叫你什么?”“可以叫我小将陈瑞平。”妈妈想明白了,对他说:“陈家还有一个是革命的。这就好了,好了……”什么叫黑白颠倒?什么叫惨绝人寰?还有比这对话更真实的写照吗?
陈瑞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他和当时千百万青少年一样,已经被“文革”的思潮洗脑了裹挟了。为了证明自己“背叛家庭”,他必须在批斗会上站出来,当众揭发“地主分子邵玉清”的母亲。因为,“就算你是真心革命,你也需要揭发你的母亲,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你的革命,你革命了,你就清白了。”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书中没有太多骇人听闻的血腥场面,它撕裂灵魂的力量来自作者人性化的观点,和对书中人物暗含悲悯的现实主义描写。”
可悲的是,“文革”把中国变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普遍说假话成为反文明的盛宴,但说假话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销声匿迹,直到现在依然畅行无阻。例如有人推荐《同和里》说:“这是一部献给上海弄堂的传奇,只属于上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理所应当成为《新民晚报》的推荐首选!”“文革”时期的上海是暗无天日的日子,怎么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善良的人们,可不能被诸如此类的假话迷惑和蒙蔽!
上海“文革”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过分渲染花花绿绿、嘻嘻哈哈的上海小市民的小日子生活。
据说,《繁花》是“用优雅质地梳理上海往事的话本小说”。怎么个“优雅质地”?金宇澄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上海,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很难想象民不聊生的“文革”时期的上海,竟然给人这样“花团锦簇的印象”。即便劫后余生的有些上海人日子过得还可以,也不能以偏概全,以表面的繁华掩盖“文革”生活的丑恶。而且,把“人生如花”来形容上海女性,也太歪曲上海女性的形象了,仿佛她们都是上海滩上“珠环翠绕”的香艳女性,一百年来从来如此的“海上花”。所谓“优雅质地”,是如此不堪。
和《繁花》描写的人和事相反,评论家程德培在《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中,说吴亮在“《朝霞》记录了什么样的人与事?一群被称之为寄生虫、社会闲杂人员、多余的人、卑微者、罪犯与贱民、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他们像废品一样被遗弃,或者像丧家之犬无处藏身。他们都是革命之后的残余之物,能察觉的只是一丝无可名状的不安,露出的是一种惊惶般的恐惧面容,做着隐藏在旧道具中的梦,过的是紧张不安的日常生活。”吴亮自己也在《隆巴耶与他的侄子的对话:关于〈朝霞〉》中说:“我写的是多余的人、归来的人、释放的人、离散的人、幽闭的人、双重人格的人、无用的知识人……”吴亮是因为看到《繁花》后创作《朝霞》的,为了和《繁花》中人物有所不同,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不少“革命之后的残余之物”,似乎想别出心裁。然而,这又把上海人写得太猥琐太窝囊了。不要忘记,当时虽然许多上海人在默默地忍受,但他们心中的怒火并没有熄灭。不少精英人物以知识和信仰支撑自己,用文字、乐曲或线条、色彩,表达对现实的鄙视和反抗。还有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少男少女,他们相信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繁花》等一些小说热衷于写弄堂里小人物琐碎而平庸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生活可以写的,问题是不是通过这样的生活揭示了背后的悲惨世界。正因为他们被上海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油盐酱醋生活遮蔽了眼睛,而不敢看不敢想当然更不敢写另一类人物死于非命:上海“文革”中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怎么被杀害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是怎么上吊自杀的,圣女似的林昭怎么被判处死刑的,以及她的母亲怎么精神失常、父亲怎么服毒自杀的,林昭在龙华枪决后公安人员怎么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的,等等。值得称道的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也写了上海平民,但没有那种得过且过、嘻嘻哈哈的所谓上海小市民腔调,更多的是表现当时青年人怎么顽强而莽撞地寻找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因此有人认为在王安忆多部以“老三届”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最有深度的一部。这不仅是艺术手段的高出一筹,更是思想意识的不同一般,尽管它在“文革”反思的尖锐和透彻方面,还远不尽如人意。
从审美社会学视角看,《繁花》等大部分上海“文革”小说虽然在局部上反映了“文革”生活的不正常,但总体上不值得称道,因为没有真切地反映“文革”几乎波及每个家庭的大内乱、大浩劫、大灾难的铁的事实,以小市民腔调和小日子生活的琐碎描写,削弱了消解了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彻底批判和深刻反思,从而无可置疑的不真不美。不真必然导致不美,这是对“文革”生活审美的严重偏差,也是被错误的“文革”思想控制后小说艺术审美的重大失误。还需要说明,有人也许认为强调“文革”小说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彻底批判和深刻反思,是只重视小说的政治性,而忽视小说的艺术性,因为小说有自己的艺术手段,突出政治性无济于事。此话看似有理,实际上是用所谓的艺术性排斥应有的政治性。事实上有些作家正是煞费苦心地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在小说中压制和抵消政治理念,企图达到小说去政治的目的。“文革”小说去政治了,还是什么“文革”小说?
二、耍弄花招的碎片化
有些作家为了歪曲“文革”真实性,在所谓艺术性上耍弄各种花招,碎片化就是其中显著的一种。
《繁花》问世后,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其中评论家毛时安有一定代表性。他说金宇澄:“他不赶任何时尚,不加任何标签,在不少人忙着要标榜创新时,他采取沉着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写作和人生;在许多人追求高深和思想性时,他更重表象和现象的罗列,通过点滴表象汇成关于时代的宏大叙事。”这里所说的“更重表象和现象的罗列”,已经有人指出,“《繁花》中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时代风云变幻中人事,是自由随性,饭局一写一章节,邮票一写一章节,旗袍一写一章节,机器一写一章节。人情世态,市井日常,一五一十,活色生香,况味地道,喧哗骚动。”这个特点当然是赞美其好,但是如果有其他作者这样写,十有八九会被金宇澄这样的编辑大人斥之为“事无巨细,罗里吧嗦”,而不屑一顾的退稿了事。为什么人家这样写会遭灭顶之灾,而你这样写是妙笔生花呢?用一句“文革”中常说的话,因为你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文坛中居然有不知高低者有所微词,“也有文坛人士表示读不下去,语感陌生,内容琐碎”。说明小说到底怎么样,还是有所共识。但这共识不起作用,因为“它成功了,在各种年龄的网民中,在南北各种奖项及至茅盾文学奖中。迄今已热销近百万册。”原来“热销”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评论标准,一部小说火了,就是大大的成功了。以此类推,凡·高生前一张画也没有卖掉,有人说只卖了一张,在有些人看来当然不火,那么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可见,不少人还是以所谓成败论英雄,殊不知一时的成功者未必是真正的英雄!
为了具有繁花似锦的效果,金宇澄动足了脑筋,除了在字里行间充分运用上海方言的拿捏转换,他承认还借用了“鸳鸯蝴蝶派”种种旧词汇,那可是被文学史判“死刑”的旧文学元素。应该说,如果为了文学创作中有声有色的需要,借用一些旧文学元素未尝不可。但是为了在“文革”题材的小说中,有意识运用“鸳鸯蝴蝶派”那种甜腻的文字,来化解或冲淡“文革”时期的惨无人道的生活,以便营造所谓繁花似锦的生活,那就另当别论,甚至可以怀疑作者如此这般的用意是什么。当然,这用意即便不是心怀叵测,作者也应该对此作深刻的反省,是不是这种文字色彩和“文革”色彩的反差太大了一些?
能够和《繁花》碎片化媲美的,是《朝霞》。据《新民晚报》2017年3月15日报道,一次沙龙式交流中,作者吴亮自称那是一个“庞杂的、语焉不详的、半途而废的、断断续续的东西。”并称,自己问过,读者“十个里面有八个没看懂”,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地表示:“我想这本书我还是留给未来,所以我不着急。”的确,这部小说令人惊艳,不,令人惊讶。因为你看到它很多地方,与其说是一地鸡毛,不如说是一地破铜烂铁或断垣残壁。那乱七八糟的叙事线索、匪夷所思的沉思冥想、缠绕不清的语言逻辑、似是而非的人物关系,实在难以卒读。这也许是艺术,有位批评家就美其名曰“一种矗立在时间瓦砾碎片之上的‘废墟艺术’”。他毫不客气地说:“尽管作者本人对自己的小说信心满满,他几乎要向所有人宣告,他的写作将给当下文学界投下一缕‘曙光’,给在昏暗中坚持文学阅读的人明亮的盼望,但我仍从这种急迫的宣告中看到了某种幽暗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种语言缠绕和分裂的征候”,小说“插入的片段形成了小说重要的构件,这让本来就不怎么完整的故事显得更为破碎”,“让叙事呈现一种罕有的破碎性和残阙性”。可见作者对“文革”生活非常陌生或故意回避,却又想让人称赞其花好稻好,只能脑洞大开,天花乱坠,以致笔下碎片化一片乱象,岂不叫人唏嘘不已!
碎片化有一种现象,是有时突如其来的写到某个人的某个遭遇。例如有人说《繁花》小说中也写到“文革”中“一个教师自杀扑到公车上,眼珠飞出来,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像零度写作一样,震撼”,但“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有点像当年阿Q被杀时看客的麻木不仁,并不令人真正有思想上灵魂上的震撼。《繁花》中有关于“文革”残害人民的文字,非常有限,更不用说对“文革”强烈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为什么这样?因为作者本来就不想揭露、批判和反思“文革”,他感兴趣的和想表现的,只是心向神往的繁花似锦的小市民情调而已。
碎片化还有一种现象,是写人的某种状态时,故意不表明为什么有这种状态,让人莫名其妙。《繁花》中的有些人物在“文革”期间,经常出现上海人说的“不响”。不知道作者是故作高深呢,还是人物真的没有话可说了。为什么人物应该要把话说出来的时候“不响”了?“不响”,是为了让读者去猜测弦外之音,以显示佯作失声的高明。但真正的原因只能是作者大大的狡猾,唯恐祸从口出。但是即便“不响”,此时无声胜有声,人们不难感受其中内心的焦虑和对禁言的恐惧。事实就是这样,作者不是说得很清楚:“小说可以大声疾呼,我也可以一声不响。”问题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为什么在必须大声疾呼的时候一声不响?如果都像你那样,国外的小说《格拉古群岛》哪里来?国内的纪实文学《夹皮沟纪事》哪里来?小说中人物不响,实际上是作者不响,表示自己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免得惹是生非。这就是好人的沉默。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再听听同时代江苏作家沈乔生在《一个知青的声音》中发出的声音吧:“我认为,“文革”是以革命的名义,控制人的思想,践踏人权,残害生命。”作为一个作家,让人物实际上是自己对这样的“文革”“不响”,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吗?一个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家吗?你还能够因为写了这样的小说而洋洋自得吗?
幸亏文学评论界对近年来的小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在评论家雷达看来,现在长篇小说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直面灵魂,二是思考生命,三是进入深度的文化反思。”另一方面评论家孟繁华的看法则相反:“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坍塌了,不再有史诗性、整体性的长篇小说出现,作家不再有在小说里建构整体世界的野心,像《白鹿原》《尘埃落定》《古船》那样的小说越来越少,写作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个人化,依靠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写作,文学这面镜子越来越碎片化。”的确如此,《繁花》之类的小说就是“依靠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写作”的,从而看来繁花似锦,实际上是问题严重的碎片化东西,一塌糊涂。金宇澄说他的小说中,不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对人物言行举止的行为描写,对“文革”环境和生活的描写,很明显的是依靠他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写作的,从写作个人化走向写作碎片化。《繁花》的大量情节就是用大量碎片化的经验感受堆积起来的,恰如七宝楼台,炫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那么,为什么有些作家对小说的碎片化非常感兴趣呢?说穿了,他们知道现在要人向前看,回望过去谈“文革”写“文革”是一种在脸上抹黑的忌讳,真正的“文革”文学是一个心知肚明的禁区,于是就在小说中耍弄花招写“文革”中的人和事,也就是碎片化。当然,他们的上海“文革”题材小说对“文革”表面的浮光掠影的反映还是有的,但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反映远远不够。对“文革”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反映绝不是区区小事,它涉及在小说中对“文革”的深刻反思问题。要知道,对“文革”反思得不彻底不深刻,“文革”在今天或明天可能发生的危险依然存在,这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我们的小说家难道是不吃人间烟火食,只满足于笔下碎片化的舞文弄墨吗?有趣的是,文学的碎片化本来是一种负面现象,如今竟然成为时髦玩意了,有些评论家对碎片化不仅津津乐道,还不遗余力的辩护,似乎是时尚服饰的新款。不,那只是皇帝的新衣!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上海“文革”小说,不要说达不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的高度、深度和力度,就连严歌苓的《陆犯焉识》那样的思想性,卢新华的《伤痕》那样的境界也达不到。更可怕的是,《繁花》之类作品的碎片化,会给后人造成一个很大的错觉或误解,以为“文革”时期的平民生活本来就是琐碎的,“文革”小说因此而碎片化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你们说“文革”时代是百姓的悲惨世界,可这些作品中碎片化描写的明明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虽然也有极少数人惨遭迫害,绝大多数人过的生活还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那么,“文革”有必要彻底否定和深刻反思吗?彻底否定和深刻反思不是歪曲了历史事实吗?创作这些作品的作家,是否想一想,你们有意无意的在和否定“文革”的有关历史决议唱反调,不害怕吗?你们唱反调的碎片化作品就像一地支离破碎的玻璃,不感到内心不安和无地自容吗?
小说是感性地形象地反思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现在有些作家故意排斥文学应有的思想性、批判性,造成作品没有高度、深度和力度的碎片化弊病,削弱了消解了人们对“文革”必要的深刻反思。除了《生逢1966》、《启蒙时代》等还可以看看外,大多数上海“文革”题材小说谈不上宏大叙事,更不要说是史诗性的不朽篇章。“文革”小说对“文革”不反思,必然流于平庸,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反作用。
小说碎片化现象的出现,和有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审美社会学方面的资质有很大关系。他们识别不了把握不了社会中的真假、善恶、美丑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把“文革”生活中碎片化的东西,当作真善美的东西,从而在小说中进一步碎片化,铸成以假乱真、善恶混淆、美丑不辨的大错。
上文指出,不真必然导致不美,这是被错误思想控制后小说艺术审美的重大失误。这涉及美学的艺术审美与社会学的错误思想关系的审美社会学问题。当前社会还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必然存在社会生态环境某些方面的幽闭,这种幽闭必然造成社会错误思想的滋生,促使审美错误观念的繁殖。有些作家由于学养缺失和品格修炼不够,更由于没有闪光的思想,在审美社会学方面出了不可原谅的偏差,使他们的小说艺术审美出现这样那样的误区。社会客观现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些作家主观本身也脱离不了干系。
有些作家之所以这样,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外在环境压力相对稳定的情况,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定向,并由此形成了他们的审美观念。这种价值定向和审美观念,使他们不得不创作和“文革”真相相距很远的所谓“文革”小说。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他们的宿命。
三、故弄玄虚的托词
文坛上有些作家和评论家频频以故弄玄虚的托词,巧言令色地辩解和开脱,以此作弄读者,并自以为得计,在一旁偷笑,也是一道让人看不懂的风景。
上海“文革”小说的不堪景象,看来是作家的个人行为造成的,但从深层次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上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这就是不少人认为“文革”这种巨大的伤痛,是见不得人的,最好回避,最好让人忘记。如果形诸文字,那不得了,弄不好鸡蛋碰石头——吃苦头。所以,有人不但觉得“文革”题材不好写,还想出不是理由的理由:““文革”中的事,很不好写,一不留意,就容易写成控诉文。假如写成怨气十足样,就不好看了,因为现代人,无论吃过点苦或没,好不容易把时间用来看小说,情愿从轻阅读中找些启发,也不愿被怨气文弄坏心情。”轻阅读,就是轻轻松松、甜甜蜜蜜的阅读;阅读的文字,当然是花花绿绿、嘻嘻哈哈的文字。有些上海“文革”题材的小说,就满足了轻阅读这种文字。如果有人不识相,把“文革”中的事写成“控诉文”,“怨气十足样”,就会“弄坏心情”,遭到排斥也就理所当然了。
一般浑浑噩噩的人这样想就算了,如果是大编辑大作家也这样想呢?一次访谈,透露了其中消息。《南方周末》:《繁花》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为什么要这样写?金宇澄:我觉得好像小说不应该有政治主张,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要去强调什么东西。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人生好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张树叶,一朵花,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人是非常脆弱的。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你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描写好就可以了。原来,小说不必有正义感的政治主张,只要有树啊花啊的生活主张就可以了。如此说来,鲁迅写有政治主张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岂不是多此一举吗?还有人认为,《繁花》中的“不响”,大有奥妙在焉,“不响,类似晚期风格之‘归零’‘逃逸’”,按评论家吴亮说“是一种更丰富的喧哗”。金宇澄倒说得很坦白:“很多事情大家都是懂的,可大声疾呼,也可以闷声不响,说了没有用,何必放到小说里搞到不能出版。”看到吗?“闷声不响”是为了不“大声疾呼”。为什么不愿意“大声疾呼”呢?“大家懂的”。说穿了就是不想做鲁迅那样抨击时弊的小说家。还有一个,是“大家懂的”而他更“懂的”,就是“搞到不能出版”。现在我们终于“懂”了,为了出版,可以抛弃作家的历史使命,可以拒绝作家应有的正义感。由此可见那些衍生出来的故弄玄虚的托词,内在究竟是什么心思了。
无独有偶,当有人说《同和里》是本“天真之书并不为过。语言诙谐、遍地烟火之气又透着荒诞。大人可以看门道,小孩可以看热闹,王承志几乎略去了那个时代残酷一面的血淋淋描写”,王承志说:“我不想写得太血腥、残酷,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不愿把人写那么坏。写‘“文革”’残暴的作品有很多,但用嘲讽、放大其荒唐的方式也很好。嗓门大未必立得住,淡淡一句话点到为止有时候反而能戳到心里。”为了不想把“文革”中的坏人写那么坏,“淡淡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么,鲁迅刺向黑暗势力的杂文像匕首和投枪,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王承志还这样举例说明说:“如果你带着怨气愤恨去写那个时代,其实也写不好。就比如战争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最长的一日》已经是很优秀的战争片了,但还是不如《辛德勒的名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震撼人心,让人感动,只是渲染残酷是没有太大意思的。”《辛德勒的名单》等作品里,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残酷场面吗?作者不正是通过触目惊心、嫉恶如仇的描写,使作品“震撼人心、让人感动”的吗?王承志的意思是今天的小说没有必要揭露“文革”的血腥和恐怖,一揭露就是“带着怨气愤恨去写那个时代”,还是和风细雨、轻描淡写的“淡淡一句话”就可以了。不禁要问一句:为什么对罪恶滔天的“文革”有这样温情脉脉的论调?我们不否认《同和里》在反映“文革”时期上海石库门生活方面,比较努力,有所斩获,但决不认同作者上述“淡淡一句话”之类过分淡定的话,它和对“文革”应有的深恶痛绝的态度背道而驰。
还有更稀奇古怪的托词。因为金宇澄的《繁花》,评论家吴亮动笔写出小说《朝霞》,吴亮的创作体会是:“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不要求你们全部看明白。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故意扭曲了,是为了故弄玄虚,怕有人以为讽刺当下的政治,我故意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置入,随便加进去一个词,让语法变得不通,让有些人看不清楚。”他还说:“我希望里面大部分信息对读者有用。一小部分信息他们看不懂,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不要求你们全部看明白。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故意扭曲了,是为了故弄玄虚,怕有人以为讽刺当下的政治,我故意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置入,随便加进去一个词,让语法变得不通,让有些人看不清楚。”
吴亮认为他的《朝霞》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它不是文字,它是用文字做的巨大的装置,它有许多碎片,就像现在的涂鸦艺术,你能看到里面有很多符号,但是每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很难知道。”为了避免写“文革”血淋淋的残酷事实,“不讽刺当下的政治”,作者煞费苦心地弄虚作假,像涂鸦艺术那样,让读者“看不懂”、“看不清楚”。那么,你“故意扭曲”、“故弄玄虚”,让读者“看不懂”、“看不清楚”,你辛辛苦苦写小说干吗呢?你不是成心把读者搞得稀里糊涂,故意寻读者开心吗?
归根到底,以上故弄玄虚的托词的目的,只能是通过自我粉饰迷惑读者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看不懂“文革”的罪恶真相。还有就是便于炮制吸引眼球的廉价作品,在名利双收的同时蛊惑人心。君不见当今许多影视和舞台上充斥着搞笑的无厘头的节目,这些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节目娱乐至死,以麻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神经为能事。现在一些小说受到了感染,用花里胡哨、打情骂俏的故事吸引青少年,还美其名曰适应社会需要。岂不知这种演艺节目和小说故事,让青少年泯灭良知、担当、使命感和正义感,丧失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能力,忘记过去的灾难和前辈的痛苦,浑浑噩噩的及时行乐,能不令人担忧和痛心吗?所以,有些以上海“文革”题材的小说糟蹋了极为重要的“文革”题材,也是对“文革”题材的严重歪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触目惊心,我们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德国汉学家顾彬贬低中国当代文学,认为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不少人脸红耳赤的不以为然,实际上不无道理,值得养尊处优、迎合时尚、自以为是、感觉不要太好的作家三思。
需要指出,出现为《繁花》之类小说辩解和开脱的托词现象,还因为有些作家和评论家在审美社会学方面,失去掌控小说艺术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审美能力,然而又想显示自己审美能力的过人,于是以种种托词企图把读者蒙在云里雾里,以表明自己高明。实际上这些托词弄巧成拙,恰恰暴露了他们小说艺术审美的重大失误。这也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四、题外话
走笔至此,想到一次关于上海“文革”小说的讨论会上,有人认为《繁花》等小说已经不错了。言下之意是期望值不要太高,对写“文革”时期边缘人物生存状态的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应该满足了。但是,为什么应该满足了?为什么不能期望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那样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下横空出世?为什么可以在“文革”小说中装腔作势地“不响”,而不能像鲁迅那样理直气壮地“呐喊”?如果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难以问世,也不可以大声“呐喊”,是不是叫人困惑,以至失望?
有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上海“文革”小说有个共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文革”没有深刻的反思?对“文革”没有深刻反思的“文革”小说,还有资格称为“文革”小说吗?这个共性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作家自身,还是在于社会现实,抑或是作家自身和社会现实的合成?可能这个问题成为当下文坛一个类似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很多人不想破解、不敢破解,或没有能力破解。但是为了文学事业的推进和发展,这个难题不能不破解,现在不破解,更待何时?否则对不起广大读者,对不起我们的时代,也对不起世界文学之林!
还有个问题,有些作家自认不凡,却为什么不能很好创作上海“文革”小说?他们曾说“文革”中的事,很不好写。既然不好写就别写,硬写肯定写不好,因为力不胜任、力不从心、力有未逮。写“文革”中的事,绝不是你随心所欲、口吐莲花就能奏效的。写好“文革”中的事,除了有一定的思想维度、精神境界外,还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真切体验。否则凭空想象、胡乱杜撰,只能隔靴搔痒、贻笑大方。质之有些作家,不知以为然否?
想起吴亮先生谈自己小说《朝霞》时说的一句话:“我不会刻意去提‘“文革”’,因为政治总要过去的。”这话基本上代表了有些作家对“文革”的态度,怪不得他们即便写了“文革”的一点皮毛,也是轻描淡写、无关痛痒的。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历史上那些诗人、作家如屈原、曹雪芹,怎么那么愚蠢,在《离骚》、《红楼梦》中刻意去提过去的政治,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他们高明、伟大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么请吴亮先生说说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
可能有人会问,你这样一一数落《繁花》作者的不是,可人家是在一片叫好声中的得奖专业户,你不知道?但得奖专业户就批评不得吗?不少人不是对某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说三道四吗?如果数落人家不是,就是个另类,那是不是要像“文革”时期那样被打入另册?不至于吧?否则近年来一直嚷嚷文学界要有批评的声音,岂不是糊弄人?还有,你为什么不能聪明一点,像那些巧言令色的人那样,或者叫好或者“不响”,而自讨苦吃呢?所以心中不免惴惴,怪只怪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冥顽不灵的脑袋?
也许有人会说,你不要看人挑担不吃力,你是不是也创作一部上海“文革”小说让我们看看?不想说。只说一句:如果创作的话,肯定不会像上述有些作家创作的那样。当然,即便创作出来了,其命运肯定是金宇澄说的那样,搞得不能出版。岂止不能出版,还很有可能……你懂的。所以,是不是也学学人家的门槛精,不“大声疾呼”,而“一声不响”。特别是要好好考虑考虑——得吃一堑长一智啊!
【注释】
[1] 金宇澄:《繁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王安忆:《启蒙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王承志:《同和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胡廷楣:《生逢1966》。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吴亮:《朝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2] doc88.com/p-9843444431373.html
[3] culture.china.com/reading/news/11170643/ 20160928/23656037_1.html
[4] blog.sina.com.cn/s/blog_4dd04ec101007re5. html
[5] time-weekly.com/story/2013-04-04/129375. html
[6] ⑾ news.163.com/16/1011/16/ C342c5mr00014SEH.html
[7] h i b o o k s.c n/c a c h e/b o o k s/2 3 9/ bkview_239154-724181.html
[8] [9] book.ifeng.com/a/20170206/20957_0. shtml
[10] culure.taiwan.cn/mrt/201702/ t20170206_11691867.htm
[11] 张闳:《吴亮的〈朝霞〉,或废墟时代的废墟艺术》。《上海采风》2017年第3期。
[12] book.douban.com/review/6155572
[13] news.163.com/14/0326/17/9O9H8lR9000 14jB6.html
[14] doc88.com/p-7748768129705.html
[15] blog.sina.com.cn/S/blog_4868179co102ebu d.html
[16] cul.qq.com/a/20150816/020040.htm
[17] 360doc.com/content/16/0915/02/115073 67_590877894.shtml
[18] dushu.com/news/1705
[19] news.163.com/16/1011/16/c342c5mR000 14SEH.html
[20]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2784
[21] 姚全兴:《我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世纪》2006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 林

杨艳鸿 工笔画 在地愿为连理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