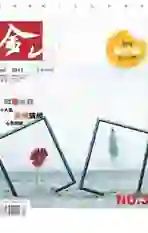老屋
2017-06-02戴智生
戴智生
小南门,琵琶洲古城墙脚下的一条老街,城墙早已不存,遗址的叫法则沿袭了下来。老街最南端,有处独家小院,断砖碎石垒起的院墙齐眉高,背阳处长满了青苔。三间坐北的正屋,粉墙黛瓦,古朴沧桑。院里有棵老樟树,径围需多人合抱,树冠郁郁葱葱,覆盖了半个院落。枝杈上鸟巢密布,鸟儿整日在院子里追逐盘旋,啁啾鳴啭。
房屋主人姓古,少人知晓,如说樟树底下的铁匠,那是远近闻名。老古年过花甲,铁匠世家,他有祖传秘方,自配冷却水,独门淬火手法,经他锤打的铁器光亮耐用,刀刃斩钉不卷口。老古的父亲更是了得,琵琶洲原有一座关帝庙,关公泥塑握把真刀,就是他父亲打造的,青龙偃月刀同画上一般模样。父亲的绝活只传了他一人,可惜老古手艺慢慢荒废了。屋檐东角仍保留了打铁的家什,只是风箱炉灶都布满了厚厚的尘埃。
据说他爷爷的爷爷就住在这里。自古创业容易守业难,琵琶洲为此衍生一个习俗,家业大凡由长子继承。老古有两个弟弟,同样跟着父亲学手艺,绝活是学不到的;弟弟成家之后,还必须搬出祖屋。他们分家时出现一些状况,还好不甚激烈。“兄弟阋于墙”,琵琶洲常见的事情。
老古一儿一女,分家不成问题。琵琶洲的习俗,女儿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祖业也与女儿无关。
儿子上初中,一边读书一边学打铁,十五岁能抡大锤,“叮当、叮当!”儿子打铁有模有样,简单的马钉、扁担钩,他一学就会。
这到底是力气活,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常常用豆豉煮几块豆干,抑或烤只红薯给儿子当点心,嘴里则常在老古面前叨唠:
“不学打铁吧?学些别的!”
老古心里也挣扎:儿子学打铁,一准没出息,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淡了;不传儿子吧,古家手艺就要断送在自己手里,那是对祖宗的忤逆。
儿子高中时,班主任来家访,表扬儿子刻苦聪颖,是块读书的料儿。老古猛然醒悟,儿子如能考上大学,岂不更是光宗耀祖的事。
老古问儿子:“你有本事考大学?”
儿子干脆:“有!”
老古心里又戚戚起来。他点着一支烟,吧叽吧叽猛吸几口。忽地,他拉住儿子的手,来到列祖牌位前,先敬炷香,再双双跪下。老古向牌位念叨打铁难以为继的原因,请祖宗原谅,并求列祖保佑儿子金榜题名。
父子磕了三个响头,儿子的命运就此改变。两年后,儿子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他进了深圳一家外资银行,已然是白领。
邻里说起子女的话题,屡屡称赞老古:“数你儿子最出息!”
老古不搭腔,脸露灿烂,心里甜滋滋的。
铁匠活实在维持不了,老古改行种菜。眼下精力尚可,能做一点是一点,既锻炼身体,又能自食其力,何乐不为?
出门五十米,便是护城河,河床一年比一年高,沉积的淤泥肥沃,老古在河床边开垦了大片菜地。护城河天然而就,通信江,活水,有鱼,不多。老古种菜,也捕鱼。鱼网得多,拿去菜市场卖,少许的鱼,自己改善生活。
老古生活很简单,每天在叽叽喳喳的鸟语声中醒来,侧耳听一阵斑鸠的低鸣和画眉的欢歌。他能用树叶模仿各种鸟的声音,闲时总爱端坐在樟树底下,逗得满院的鸟语声。院子的门向来是敞开的,有空暇的左邻右舍会集聚过来,听他与鸟对鸣,或坐在一起家长里短,日子很容易打发。
女儿照例要回娘家,嫁得近,回来方便。女儿是娘的小棉袄,回来同娘有说不完的话。老古也盼女儿归,也喜欢外孙,而外孙坐在膝盖上他会走神,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
外孙是外姓吧!
儿子结婚三年,儿媳还没有动静,这是老古郁闷的事情。儿子来电话,他不关心别的,每次都是问:
“什么时候要孩子?”
“买了房再说。”
那得猴年马月,深圳的房子贼贵,儿子积攒的钱,不及房价涨得快,年年要买房,首付总差一大截。老古自从明白什么是首付,就再也没有安生过。
这天吃晚餐,饭扒了一半,老古突然放下碗,眼睛直瞪瞪地望着老伴,他边嚼嘴里的饭边跟老伴说:
“把房子卖了吧?”
“为啥?”
“给崽付首付!”
“崽会肯?”
“房子迟早都是他的!”
“房子卖了我们住哪?”
“活人还会被尿憋死?”
“行,听你的!”
是夜,老古辗转难眠,声声叹息。老伴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次是老伴先开口,她用脚碰了碰老古的腿,问道:“喂!是不是舍不得房子?”老古答:“不是!”
“舍不得这樟树?”
“不是!”
“那为啥?”
“唉!我舍不得树上的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