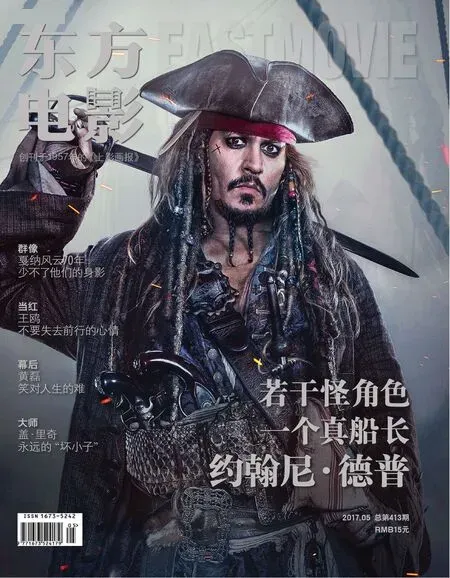《八月》:怀旧影像的动作难题
2017-06-01聂伟
文/聂伟
《八月》:怀旧影像的动作难题
文/聂伟

著名学者、上海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电影产业与中国故事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代表著作:《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 等
刚刚过去的3月,《八月》没有爆冷成为票房黑马,也未带来在去年金马奖上突然的惊喜,然而关于《八月》的观看必然是不平静的。这不是一部平庸或伪劣的电影,而是包含了对于个体记忆迷恋的艺术创作。同样,观看《八月》也很难获得完整流畅的认同感,片中基于个体怀旧与影像表达之间巨大的失配感,还是暴露出了一点核心问题:银幕上的人物,为什么很难真正地动作起来?

《八月》的视角定位于12岁的张小雷身上。在最开始的地方,影片就赋予少年一个动作片的图腾—双截棍。意象显然来自港片,是李小龙的遥远回想,也是对远在漠北呼市的在地化表达。可惜,这个被赋以主要象征意义的器具,始终也无法真正作为少年的肢体延伸部分而挥舞起来,哪怕是稍微动上那么几下,甚至连虚张声势都没有。
仔细想来,张小雷在影片中有两次机会挥起了双截棍,然而这两个可能性都被摄影机刻意进行了遮蔽,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了。
场景一。为了升入三中,张小雷和母亲偶遇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和几位家长一起围堵到了具有一定话事权的刘老师。从人物的对话来分析,刘老师没有表现出任何逾越常规的回应,没有烦厌,没有拒斥甚至没有常见的官话套话。在这个矛盾激化的情节动力并不充分的场景中,做梦都想升入该校的小学生张小雷竟然高举双截棍,从楼梯的下位向上冲啊冲……

接下来,突然转场,张小雷出镜。从观众的视角看,无法判断他究竟打了老师与否,也无从描述或者猜测他与处于围堵中心位置的老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影片只用下一组镜头模糊而暧昧地暗示确实有一场冲突—因为小雷的妈妈回到家后生气地拆坏了双截棍。
场景二。父亲带着张小雷聚在电影院的售票处前,希望靠熟人刷脸进场看好莱坞动作大片《亡命天涯》。影片搬出市场经济“认钱不认人”的冰冷面孔,似乎还有意无意地强化了1990年代初期15元票价对低收入者内在心理的碾压。此刻,电影厂的韩胖子(韩主任)施施然带着孩子进场看电影。两个成年人之间存在上下级落差,从来的工厂管理者在改革大潮中没有失去权杖,与其说他的身份改换了,倒不如说他获得了另一种更能够突出自己作为责任制组织者的权威身份。张小雷的父亲显然从内心深处拒斥这份剥离于旧体制之外的权威压力,却又不敢也缺乏有效的反击方法。就在这个时候,张小雷突然沉默地爆发,代父寻仇般地举起双截棍,在电影院的高台上对韩家的胖儿子展开追打。此前一直采用近景和人物面部特写的镜头,在下一个动作画面切入的时候,转换为突然拉开的中远景。电影院台阶上的景与人被斜枝入画的盛夏树叶半遮半掩,画外的人物对话也全然是静观式的反应。既不合乎常情常理,更没有表现出来这个特定情境中的必然。于是,将这种终于运动起来的片刻情境陷落进了怪异的遮挡之中。
为什么号称基于真实个体记忆的影片,一旦进入人物动作环节就会脱轨、脱节,不再具有递进式的逻辑动力?究其实至少有一点,主创者还没有最为准确地寻找到时代矛盾聚焦于未成年人身上时的影像呈现方式。而时代记忆与个体的经验遭际,又何曾单靠镜头画面就能切换开来?我们注意到《八月》对台湾新浪潮的借鉴,就像《风柜来的人》采用固定机位和摇镜头的组合来表现男孩们的斗殴,那是一种沉静而漫长的凝视。而《八月》将观众推向摄像机之外,成为别别扭扭的世代文化窥探者—就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文化怀旧潮长潮落之间,90年代的怀旧风就这样不冷不热地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