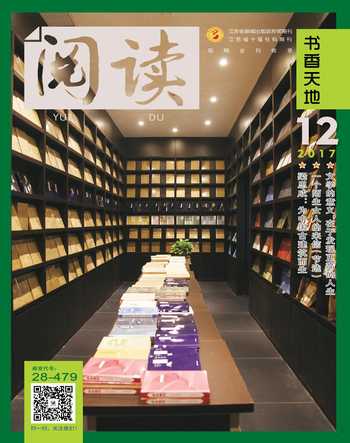梁思成:为中国古建筑而生
2017-05-30贾元熙
贾元熙
梁思成(1901-1972),清末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
“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
几十年来,这些话语如同有魔力的音符,时时敲击着人们的心弦。说这些话的人叫梁思成。
1972年1月9日,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在北京逝世。40年飞逝,2012年1月27日,媒体传来消息:梁思成和林徽因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的故居已被拆除。
历史似乎总要用这样的画面来提醒我们记住一个人。而我们记得梁思成,绝不仅仅因为他是启蒙领袖梁启超的长子、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丈夫,更是由于这位建筑学大师一生痴心的事业是一种中华文明的救赎——他调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竭力挽救这些东方智慧与艺术的结晶于没落、战火以及狂热的破旧立新之中……
清华园中
翩翩少年展才华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在日本出生。这一年,正是“百日维新”失败后的第三年,他的降生为四处流亡的梁启超带来了莫大安慰。11岁时,梁思成回到北京,并于14岁入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走入了清华园,聪颖的梁思成立刻就成为了老师和同学眼中的“活泼少年”。
梁思成的老同学陈植回忆:“在清华的8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在《清华校刊》任美术编辑,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跟随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却引以为乐。约1918年,清华学校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经梁启超校阅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会乐器、能画画,文采也不错,本就出众,梁思成竟然还是运动场上的高手。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后,梁思成曾和学生们提起该段往事:“别看我现在是又驼又瘸,可是当年我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
而在所有的愛好中,梁思成最得意和最拿手的还是美术。在做各类校刊时,他常常“一次同时做几种(不同风格和不同手法)画,以从中获得新的浪漫感”。正是由此,再加上后来受林徽因的影响,梁思成后来才选择了学习建筑。
南长街前
纪念国耻遭车祸
当年的清华学校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马上就要完成学业的梁思成正在做赴美准备,但就在5月7日,不幸发生了意外。
那天,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骑一辆摩托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纪念日”活动。行至南长街时,他们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金永炎甚至连车都没下,仅从窗口扔出自己的名片给前来处理后事的警察,便扬长而去。这次事故最终导致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受伤,落下了跛足的残疾。并且因为脊椎病,他不得不长期装设背部支架。
这场意外让梁思成只得推迟一年赴美,他自己很焦急,但梁启超却认为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些国学也是有益的。于是,就在这一年,梁思成为自己夯实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当然,若要说因祸得福,这次车祸也间接促进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梁林两家是世交,1920年,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19岁的梁思成初识17岁的林徽因,一见倾心。在医院养伤期间,林徽因常去看望梁思成,坐在床边给他拧手巾擦汗,两人的感情日渐亲厚。
大洋彼岸
遨游建筑天地间
在梁林的接触中,林徽因提起以后要学建筑学,梁思成后来回忆:“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集艺术和工程于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这个专业。”
1924年,这对年轻恋人结伴赴美,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而刚到宾大不久,梁思成就迎来了一个影响了他一生选择的提问。
据他们的好友、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开课不久,梁思成就参加了建筑史教授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的一门课。上了几堂课以后,他跑去找古米尔,说非常喜欢建筑史,从来不知道世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古米尔反问他有关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梁思成回答,据他所知还没有文字的记录,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从不重视它,但他本人不甚赞同。
此后,梁思成一边回味着古米尔的问题,一边尽情徜徉在建筑艺术的世界。宾大建筑系一位年轻的教师约翰·哈贝孙(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师)曾报告说,梁思成、林徽因的建筑图作业做得“棒极了”。费慰梅也回忆,在梁思成的大学时代,他的才华可由两枚设计金奖及其他奖励得到证实。
1925年,梁启超专门寄给梁思成一本古籍善本《营造法式》,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册。梁启超在附信中评论:“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梁思成从此下定决心把中国建筑史研究透。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毕业。第二年,梁思成为完成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而与林徽因回到祖国。同年9月,他们首先来到沈阳,梁思成受聘成为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在这所洋溢着改革生气的大学,梁思成以宾大建筑系毕业不到一年的学生的身份,与林徽因一手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近三年后,他们迁居北平,继而奔走大江南北、荒山野岭,开始了他们梳理中国建筑史的事业。
烽火大地
千年瑰宝重出世
到野外寻访古建筑,不可能是轻松浪漫的事。道路艰险,土匪、军阀更是横行一方。梁思成腿有残疾,脊椎也要常年穿一个铁马甲支撑,炎热季节非常痛苦。野外和农村环境的恶劣对世家出身的夫妻俩来说,是超乎想象的。正如1936年考察洛阳龙门石窟时梁思成写到的那样:“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沙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
梁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发生在1932年。他的好友杨廷宝见到一幅古怪的寺庙照片,图注“蓟县独乐寺”。这令梁思成十分兴奋。回忆那次行程,梁思成说:“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经历。”
此后,从1932到1940年,梁思成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踏遍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江苏、陕西以及京内、京郊,到过200多个县,调查古建筑2700余处。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和林徽因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两部书稿,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一路考察,梁思成一次次地为这些遗世独立的古建筑所折服。1933年,他看到应县木塔时,不禁赞道:“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而对于他和林徽因来说,最惊喜的是发现了佛光寺。
1937年6月26日,他们一行四人在山西五台山一个偏僻村落找到了这座古老寺院。梁思成惊喜地发现寺院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这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种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而两天以后,林徽因又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发现了很淡的墨迹,依稀可读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此时,林徽因猛然想起,大殿前耸立的经幢上有同样的字迹,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横梁和经幢上的字迹吻合在了一起。佛光寺,一座最迟建造于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们更是独一无二的。”梁思成在发表于1944年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这样写道。
不过,可惜的是战火在此时已焦灼不堪。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上登出梁思成发现唐代建筑寺院的消息的同时,还报道了“七·七事变”。国难当前,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顿时显得无足轻重。直到1961年,佛光寺才和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门、故宫等一起被列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太客厅
岁月静好叙情谊
1931至1937年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如果没有出外考察,就会住在北京的北总布胡同3号(今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在他们的好友费慰梅笔下,这里是座格外美丽的四合院:“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
而提起这个门牌号,当年的文化圈中,人们莫不为之神采飞扬。梁思成和林徽因开朗友好,文化素养深厚,很多友人喜欢到他们的客厅来畅叙一番。当时,他们的常客有直率的张奚若、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陈岱孙,还有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在伦敦留学的社会学家陶孟。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林徽因的机智善谈在这些聚会中显示了很大的魅力,梁家“太太的客厅”逐渐因为众多学者夫人的参与,渐渐在北京文化圈中有了名气。
就是这样,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3号度过了一生中难得平静的6年时光,而也就是这6年,使他们成为了如今人们印象中的梁思成、林徽因。
从这座庭院,他们一次次出发,发现了辽代的独乐寺、隋代的赵州桥、唐代的佛光寺……在这里,他们热情会见好友,书写了一曲才子佳人的爱恋传奇;而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逼近,他们又是从这里起步,无悔颠沛流离、双双病倒,拼死完成了中国人的第一部建筑史。
改天换地
短暂飞扬归炼狱
1946年7月,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北平,梁思成夫妇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底,第二次赴美讲学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此时,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党也要造房子。”
1948年,他们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解放军军官给梁思成一份地图,请他标出当必须使用大炮的时候要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并表示:“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梁思成和林徽因因为这两位解放军的到访而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此后,梁思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向往。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回忆道:“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的梁思成似乎走向了人生的再一次辉煌,他担任着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负责中南海改建、国徽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他是建筑学界的泰斗,是受人尊敬的大学者。
然而很快,这众多的光环就将他的心反衬得越来越痛。北京城面临着重新规划,梁思成的心中却笼罩着不祥的预感。他向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兼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建议保护北京旧城,另辟新区,提出“梁陈方案”,但却没有被采纳;他心中明白北京古老城墙危在旦夕,饱含深情地描述着它们可以化为公园,“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然而,他等来的却是“这些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經无用”,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势在必行。
拆北海团城时,梁思成在争论中勃然大怒,最后径直去找周恩来总理才把团城保留了下来。拆天安门南面东西三重门时,为堵住梁思成的嘴,主张拆的人甚至召集了几百名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开控诉三座门大会,把梁思成推到“人民”的对立面,让他作声不得。
就这样,在以后的20年中,北京的牌楼被拆除了,城门楼被拆除了,“文革”时,所有的城墙也被拆除了。它们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消失在梁思成痛苦的抗争中。并且很快,梁思成连抗争的权利也丧失了,他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从1966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历了一次次的批斗、抄家、勒索甚至殴打,屈辱、病痛、孤独与幽深的迷茫如恶魔一般萦绕他的左右。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留下了众多凝聚着心血的价值极高的学术成果,也留下了作为理想丈夫和理想人格代表的杰出形象,更留下了他沧桑的背影以及从灵魂深处迸发出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血泪呐喊。
而今,梁思成对于古建筑保护的声声叹息,依然飘荡在喧嚣的城市上空,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