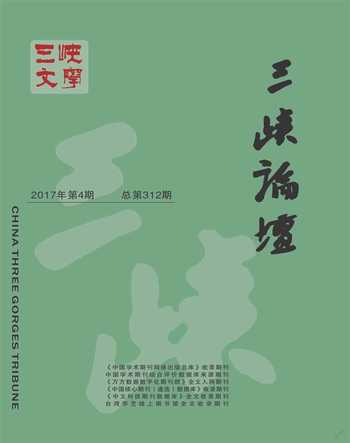宜昌开埠二说
2017-05-30王玉德��
王玉德��
摘要:
宜昌开埠是近代长江流域的一件重要事情,从生态环境、人文社会这两个角度展开分析,提出宜昌开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客观上对宜昌的社会转型起了积极作用。建议对近代中国各地的开埠展开新视角的研究,宜昌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城市发展史,在改革开放中加快走向全球化与现代化。
关键词:
宜昌;开埠;社会转型;史观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4-0013-03
人类社会的步子迈入到近代,西方卷起了工业浪潮,世界上欠发达的国家被动地出现了“开埠”现象,晚清的中国也在所难免。开埠,福兮?祸兮?好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三缄其口,讳莫深焉。其实,了解开埠,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历史的进程。研究宜昌开埠现象,[1]必定有益于建设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笔者对宜昌开埠的具体过程没有研究,然而,拟从地理与史观两个角度发表拙见,愿闻批评与商榷。
一、说地理
宜昌的开埠,一定要从生态环境说起。宜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宜昌的历史定位,也决定了宜昌的被开埠。宜昌处于中华过渡性的关键地带。所谓过渡性,就是宜昌处在中国三级台阶之中的过渡性地带,鄂西属二级阶梯,江汉平源和鄂东丘陵属三级阶梯。宜昌以西有隆耸的大片山脉,东边是低平的江汉平原。所谓关键性,宜昌城区所在的位置,是周围一大片地区最重要的结点。宜昌这个地理特征,是我们认识宜昌全部文化现象的出发点与基础。
因为这个地理特征,使得宜昌既有大山文化,也有大平原文化,还有长江大川文化,这三“大”,构成了宜昌文化的宏大气场与变动不居的内涵。在大山之中,有人类的史前文化,有巴文化。在大平原文化之中,有楚文化,有江汉平原文化。在长江大川文化之中,有6000公里的水文化因子。宜昌的地形可以与北京相比。北京处于燕山与华北平原之间,燕山虽然没有大巴山与大巫山厚重,但也是蓄藏与缓冲文化的重要地带。江汉平原不及华北平原之厚实,但亦具有特别的灵气。宜昌开埠,从军事上、商贸上、文化上,意味着左挑荆楚,右携巴蜀,游轫有余,可进可退,纵深运送。资源方面可以得到多样性的取材,商品可以得到更大的市场,传教士们更是可以通过这个跳板向深山老林的原著民宣传上帝观念。这里有多元而宏大的气场,必然不会被历史的脚步所遗忘,西方列强贪婪的眼光更是不会放过这块地方。
宜昌处于中华文化的沉积带。宜昌深入到内陆,处中华文化之堂奥,是中华之中。这里是中点,也是阶段性的终点。在广阔的沟壑之间,在无数的平坝乡镇,巴楚文化凝结于此,一些民俗信仰、观念均保存于此。这里到可以嗅到大山大江大湖的气息,也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考古工作者在长阳县境内发现20余万年前居住的“古人”;在宜都城背溪等地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长江西陵峡两岸和汉水以西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大溪文化”(因与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相近而得名,其特征是定居的农业、大量的石器、红色的陶器,大约属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楚文化发源于此,且与巴文化在此交融。在当阳季家湖发现楚城。正因为有这些考古发现,所以楚学大家张正明先生提出,在长江中游与上游交接的地方,有一条文化沉积带,“此地有连山叠岭,险峡湍流,偏僻,贫瘠,易守难攻。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时迁则势异,保存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的古代文化事象。或多或少变了形甚至变了性,但总能使人察见古代文化事象影踪或者线索,此今彼古,‘情与貌,略相似。”[2]651-652宜昌开埠,打破了沉闷的时光,唤醒了封存的岁月,掀开了蒙面的历史,有利于发掘沉积的文化。
宜昌处于中华文化的缓冲带。宜昌是川鄂交通咽喉,长江三峡的出口。宜昌在湖北的西部,湖北西北部是秦岭东延部分(即武当山脉)和大巴的东段(即神农架、荆山、巫山)。神农架海拔3105米,有华中第一峰之称。宜昌以东的江汉平原,海拔只有零米左右。平原与高山之间,渐进有错落的山脉,丘陵。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气息,在这里放慢了步子,减缓了速度,变换了身法,调整了呼吸。文化在此接力,在此传承。由于是川鄂通道,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在此来来往往。李白经过宜昌时写下了《渡荆门送别》对宜昌一带的形胜描写得很生动:“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宜昌开埠,形成为巴山与江汉平原之间新的重镇,发挥西蜀门户、荆襄要冲的作用,承接着引入西方文化的缓冲,使之古老而年轻,传统而近代。
宜昌有大山的厚度,也有平原的开阔,也有长江的流畅。宜昌人有很强的适应性,背靠群山,有压力,但也是依靠;俯瞰平原,神开气爽。面对开埠,宜昌人不会惊慌、茫然、迷失,而是从容应对,从传统农耕社会步入到近代工商业的洪流之中。
二、说史观
开埠,狭义的说就是形成通商口岸,广义的说就是要全面敞开城市及周围的一切。西方人进入到中国,一定是会深入到長江腹地的,宜昌的开埠在所难免。从上海入袭的欧风美雨,还有从广洲翻越过来的传教士,他们一定会进入到汉口、荆州、宜昌。联点成线,这是一个商业带,也是一个文化带。宜昌是个中点,江汉平原西端的终点,这里必须建立转换的城市,亦为集散中心。不论是对于传教,还是经商,还是管控中华腹地,都是重要的位置。应当看到,是时代的脚步,把宜昌推进到了近代文明的门槛。
说到宜昌开埠,时下仍然有一些不同的史观。有的人极力痛斥西方列强对宜昌的恶劣影响,如鸦片泛滥,导致许多宜昌人被毒害。有的人大加赞扬西方文化给宜昌带来的新变化,似乎宜昌的变化全靠列强。我们认为,以阶段观点、民族观点、世界观点看待宜昌开埠是必要的。然而,历史演进到21世纪,我们应当采用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宜昌开埠,至少可以采用文明史范式。所谓文明史范式,就是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开化的的范式。在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从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过渡过程中,跟进到历史潮流的行为,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对宜昌开埠的认识,应当采用执其两端的态度。既要有批评,也要有肯定;既要有情商,也要有智商;既要有道商,也要有德商;既要两点论,也要允执厥中,坚持中庸的观点。中庸的观点,就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说出恰当的话。要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摸到了象的脸,就说“宜昌开埠,象在伤感流泪”;摸到了象的足,就说“宜昌开埠,象有了坚实的圆柱”。只有从多角度审视历史,才可能避免片面性。
宜昌的开埠,对于西方人来说,意义不亚于汉口、荆州的开埠。荆州比宜昌开埠晚,说明西方人很看重宜昌。宜昌开埠之后,列强活动的空间更大,面对的文化更有多样性,以上海为起点的圆直径明显延长。长江流域每个埠点的开启,从南京、九江,到汉口、荆州、宜昌的延伸,都是西方人阶段性的成果,意味着一个个节点被打通。宜昌在内陆,有大量物产吸引着西方人。例如,宜昌远安的苟家垭,在明清时期盛产垭丝。明弘治九年(1496),苟家垭以“垭丝之乡”闻名全国,垭丝出口海外。《远安县志》记载:“明弘治九年,《夷陵州志》载:远安田赋以‘缎匹地一丈五尺、农商丝二斤八两二分为‘贡。清同治至光绪年间,湖北丝绸由汉口经上海出口,远销英、法、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其中以远安苟家垭的‘垭丝最为著名,其色金色熠耀,质地柔软纯洁,条分好,拉力强。”[3]宣统《湖北通志·货类》记载:蚕丝“各郡皆产,唯以‘垭丝为最著,西欧人购之……黄丝出口由上海销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由此观之,远安“垭丝”在清代就已远销欧亚各国。西方人向来垂涎中国的垭丝,垭丝作为土特产品牌,增加了中外商业交易的竞争力。此外,宜昌还有好多矿藏,受到洋人的垂涎。
宜昌开埠,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一时间不情愿,面子上过不去,但实际的效益却是明显的。开埠前的宜昌,沿街排列古老的木板房,前店后室。街上青石板上有独轮车碾压很深的凹槽,撒着一堆堆驴屎。农民赶集,用鸡蛋、柴、菜、米换取土布、煤油、红糖。城内的碾米厂、榨油厂、酒厂,都是为农业及居民生活服务的。城内人几乎都互相认识,或者沾亲带故。在城里,人们穿着黑色土布,在江里、井里挑水,烧灶做饭,点煤油灯。宜昌开埠,意味着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内陆经济迅速解体,手工作坊转换为使用新机器的工厂。农耕社会性质的城市蜕变为近代意义的城市。
开埠,要从主客观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还要从当时的与现在的两种不同的背景分析。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话语。从表面上看,开埠是西方列强强加给清朝的耻辱,但从历史发展看,客观上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随着外国的商品进入,中华内地的物产可以出口,封闭的内地人视野洞开。海外的异文化进入到宜昌,让宜昌感受海的气息,宜昌文化从开埠之时,就意味着开始步入世界。洋油、洋火、洋布、洋車、洋船、洋画、洋教、洋学、洋医、洋行、洋字逐渐充斥责街头。宜昌海关不仅收税,而且在城市管理的职能方面也起了作用。宜昌的洋化与近代化,应是从开埠开始。能够作为埠口,宜昌地位的重要性再次得到证明。开埠是好事情,虽然是被动的,但中国人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把消极变为积极。这是中华文化同化力在发生作用,中华生命就是在调适中不断获取生机。清末的宜昌人,也许是以抵触的眼光看待开埠;现在宜昌人,大多会伸开双臂,迎接着开埠,恨不得开埠来得更早、更深,更广、更奇一些。
宜昌开埠,确实有了变化,不宜把功劳都归功于西方人,而应多注意中国人的努力。宜昌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宜昌人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宜昌历史上有奇人,屈原就是极有个性的文化伟人,他爱国爱民,求索自强,最后以死唤醒楚人,是中华伟大的奇男子。王昭君是兴山县人,远嫁蒙古草原,肩负和亲使命,传播内地文化到边疆,其功甚伟,堪称中华伟大的奇女子。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嫘祖就是宜昌人。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濮,生高阳,高阳有圣惠焉。”《山海经》所载奇事,有许多与宜昌地区有关。宜昌作为近代新城,起点就是开埠,开埠之后就是宜昌人不断创造奇迹的新时段。
因为宜昌有好地理、好人文,就有好故事、好声音。开埠之后的宜昌,迅速成长,纳入到了近代城市的行列,周围的农村文化如冰山溶化。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统治,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宜昌从开埠之后获得了自由的“人生”。1949年,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背景下,宜昌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三线”建设中让宜昌怀揣“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之后,宜昌利用千载难逢的大型水利工程机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时下讨论“开埠”现象,建议国内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各地的开埠展开新视角的研究,建议宜昌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城市发展史,在改革开放中加快走向全球化与现代化。随着思想的解放,相信宜昌将有更大的变化,更大的发展。宜昌是个开放之埠,是中部的高地。随着宜昌做大,其对中国梦的实现,将发挥不何低估的作用!
注 释:
[1] 1876年,英国人在《烟台条约》增设商埠的城市中首选宜昌。1877年二月十八日,宜昌关成立。第一任税务司由英国人狄妥玛担任。1937年10月中国人杜秉和接任,1946年宜昌关奉命闭关。
[2] 张正明:《张正明学术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湖北省远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远安县志·卷四·农业》,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
责任编辑:杨军会
文字校对:向华武
作者简介:
王玉德(1954-),男,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献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