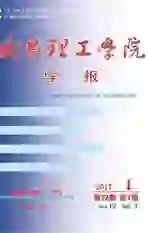《诗经》“四始”说辨正
2017-05-11祝秀权
祝秀权
摘 要:《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四始;诗大序;正诗;乱;正变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一
《诗经》“四始”说最重要的出处有二。一是《毛诗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后人据此认为,《毛诗序》所言之“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毛诗序》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毫无疑问,《毛诗序》认为,“四始”是最好的诗。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四始”是最好的诗,那么,如果“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难道《诗经》之外还有诗?那些非“始”的诗又是指哪些诗?
就《毛诗序》这段话本身而言,我们有如下证据证明《毛诗序》所言之“四始”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
首先,《毛诗序》先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而后言:“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显然,按照《毛诗序》的文意,那些能做到、符合“主文而谲谏”之礼仪规范的“风”,是不包括变风的。所以,“故曰风”之“风”,只能指“正风”,即《诗经》中的《周南》《召南》。
“故曰风”之“风”含义如此,下文的“谓之风”、“谓之雅”含义也应如之。《诗大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毛诗正义》:“《小雅》所陈,有饮食宾客,赏劳群臣,燕赐以怀诸侯,征伐以强中国,乐得贤者,养育人材,于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陈,受命作周,代殷继伐,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饱德,能官用士,泽被昆虫,仁及草木,于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很明显,孔颖达亦完全是以正《小雅》、正《大雅》阐释《毛诗序》所言之“小雅”、“大雅”的。这说明,孔颖达知道《毛诗序》所言之“小雅”、“大雅”所指的内含。
又,《毛诗正义》曰:“正经述大政为《大雅》,述小政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变雅”之中的小、大之别是由音乐区分的,“正雅”之中的小、大之别是由政事的大小区分的。既然如此,那么《诗大序》所言“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无疑是指“正小雅”和“正大雅”了。
又,《诗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迩咸服,群生尽遂其性,万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验也。……此解颂者,唯《周颂》耳。”
第二,今人对《毛诗大序》“四始”的理解认识,只注意到“是谓四始”数语,却大多忽略了《诗大序》在此数语之后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在当时被作为“正始之道”,即《毛诗正义》阐释的“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亦即郑玄所言“王道兴衰之所由”。显然,这被称为“正始”的二《南》,即是《诗大序》所言“四始”之一。这就等于《诗大序》明言《周南》《召南》是《风》之正始,即《风》之始。“二南”被称为“正始”,那么“四始”中的其他三者也是“正始”。
《詩大序》在这里提出了“正始”的重要概念。既然称之为“正始”,那么就说明,在毛诗这里,“正”和“始”必然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毛诗的“正”就是“始”,“始”就是“正”,故曰“正始”。那么,“四始”之“始”,无疑就是“正始”之“始”。说的更具体一点,《毛诗序》认为,“四始”就是《诗经》“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中的正诗。在《诗经》中,没有“正”,就没有“始”。“正”和“始”,概念、表述不同,所指内容则相同。它们分别从两个方面对《诗经》四部分“正诗”加以表述和概括。《诗大序》整篇文字,洋洋六百余字,从头至尾几乎都是论正诗的,极少言及变诗。
又,《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不难看出,郑玄是纯以正诗阐释“风”、“雅”的。故唐贾公彦《疏》曰:“郑云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者,郑据《二南》正风而言,《周南》是圣人治道遗化,《召南》是贤人治道遗化,自《邶》《墉》已下是变风,非贤圣之治道者也。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者,谓若《鹿鸣》《文王》之类是也。”
二
《诗经》“四始”说的另一个出处是《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于是,后世有了《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诗经》四始的说法。且人们提及《诗经》四始,基本以此观点为主。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禁要问:司马迁为什么要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呢?后人认为,“《关雎》之乱”是指《关雎》的末章。那么,为什么只有《关雎》的末章才为风始呢?显然不通。实际上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解释。
“《关雎》之乱”不仅见于《史记》,也见于《论语》:“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黄式三《论语后案》引金吉甫《考证》云:“辞以卒章为乱,乐以终为乱。此统言《周南》之乐,自《关雎》终于《麟趾》也。”
黄氏之解几为确解。只是我们认为,“《关雎》之乱”不仅指《周南》,也包括《召南》,即指被视为“正风”的“二南”。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圣人举乐于殷周,皆其正者也。夫‘师挚之始,殷之正乐也;‘《关睢》之乱,周之正乐也。夫子殆从其朔而举之。”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乱,合奏也。交响,故乱。”此亦为确解。笔者推测,“师挚之始”和“《关雎》之乱”,是相同的表达,相同的含义。重复言之,欲以强调之意。古人自有这样的表达。按照孔子之意,这被称为《风》之始的“二南”应该与其时的乐师太师挚有关,或许为其编辑而成,甚或为其创作亦有可能,故称“师挚之始”。
乱是周代典礼仪式上乐舞尾声时的合乐。《辞源》:“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叫一成。以升歌始,终于合乐。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汉语大词典》:“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话。”《离骚》:“乱曰:‘已矣哉!”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总撮其行要也。”《汉书·外戚传》“乱曰”,颜师古注:“乱,理也,总理赋中之意。” 周代礼乐繁杂,各种典礼都伴有音乐演奏。这些音乐演奏在结尾时合乐,以使演奏在高潮中结束。合乐时各种乐器齐鸣谐作,故有“洋洋乎盈耳”的感受。《论语》孔子所言“洋洋乎盈耳”的,绝不仅仅指《关雎》一篇,更不是指《关雎》的卒章,而是指包括《关雎》在内、被古人视为“正歌”的那一类诗,那一组诗。《礼记·乐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孙希旦《礼记集解》:“‘复乱以武,乐终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论语》曰‘《关唯》之乱,彼谓合乐为乱,此谓合舞为乱,盖合乐、合舞皆在乐之终也。”
明李陈玉《楚词笺注》:“凡曲终曰乱。盖八音竞奏,以收众声之局,犹涉水者截流而渡,将到岸也、故亦曰乱。”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意乱者,盖乐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孔子曰‘洋洋乎盈耳,大旨可见。”后人只注意到“乱”的曲终、乐终之义,却忽略了“乱”的“八音竞奏”、“众音毕会”的含义。实际上,“乱”的含义更偏重于合奏、总奏。最早为“楚辞”作注解的两汉经学家们,如刘向、扬雄、班固、王逸等都不曾说过篇末之“乱”是指乐歌之卒章或尾声一类的话。这种针对全篇而总括题旨、总结文意的话只能处于篇末,但“乱”并不就是篇末或者终章的意思。唐陆龟蒙《野庙碑》:“既而为诗以乱其末。”如果乱是末的意思,这句话岂不成了“既而为诗以末其末”?
《尚书·泰誓》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前儒将“乱”解释成“治”,方向是对的,但未必是确解。所谓“乱臣”,大概就是将十人比作一个乐队,众治世能臣通力合作,精诚团结,共同演出如同“《关雎》之乱”般洋洋尽美的治国乐章。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曰:“既履端于倡始,亦归余于总乱。”可知“乱”亦含有“总”之意。
郦道元《水经注》中有很多“乱流”一词,如:“清、漳乱流而东注于海。”“祖水又东南乱于沂。”“又东历泽,乱流为一。”“与夷水乱流东出,谓之淇水。”《尚书·禹贡》:“入于渭,乱于河”。这些“乱”都是汇合、汇总的意思。
郑玄《诗谱序》:“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毫无疑问,“《鹿鸣》《文王》之属”是指正《小雅》和正《大雅》。而“《关雎》之乱”,正是和“《鹿鸣》《文王》之属”相同、相近的表达方式。另外,《国语·鲁语下》闵马父曰: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今所见《诗经·商颂》五首诗以《那》为首,《国语》闵马父亦明言,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师之时,也是以《那》为首,而闵马父所引“自古在昔”数语,正出自《那》。可知“其辑之乱”的“乱”绝不是卒章的意思。
所以,“《关雎》之乱”,意指以《关雎》为首的一组诗、一类诗,即指《周南》《召南》,而非仅仅指《关雎》一篇。这组诗的特殊性在于,它们经常在典礼演奏的结尾加以合奏,因而被其时之人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关雎》之乱”,其含义就类似于《周礼》贾公彦《疏》所言“《鹿鸣》《文王》之类”,它是古人对一组诗、一类诗的一种简略的表述。
《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下文的“《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显然是一种省略的说法,即:“《鹿鸣》之乱为小雅始,《文王》之乱为大雅始,《清庙》之乱为颂始”。它们分别指《诗经》的《正小雅》《正大雅》和《周颂》。
由此可见,《史记·孔子世家》所言之“四始”,与《诗大序》所言之“四始”,其含义是相同的,并无二致。以《关雎》等四首诗为《诗经》之“四始”的情况并不存在。《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之前有“始于衽席”一语,笔者以为,“始于衽席”的意思,即如同说始于《周南》,或者说始于二《南》,它与“《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句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接近,故二语相承。
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孔颖达《疏》:“二《南》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无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鸣鸠,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义,妻妾有序。”可见,孔颖达以“二《南》”解郑玄“风之始”之意,“风之始”指二《南》,不单指《关雎》,其意甚明。又,孔颖达《毛诗正义》曰:“《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
三
《诗经》古有正变之说。《诗大序》曰: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郑玄《诗谱序》:
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关于《诗经》正变说,我们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其一,正变说并不仅指《风》《雅》,也包括《颂》。其二,“四始”说和“正变”说虽然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有很紧密的联系,“正变”中的“正诗”就是指“四始”。试申论如下。
《诗大序》“变风变雅”之言完全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前后照应的、互文见义的表述。其表述语言之巧妙,非细查其语义、文理不能知晓,非圣人不能有此精彩表述。也就是说,《诗大序》虽未出现“变颂”之言,但由于其语意的前后互文,“变颂”是隐含在内的。
《颂》有正变,毫无疑问,《周颂》是“正颂”,《鲁颂》是“变颂”。《商颂》比较特殊,本文阙而不论。郑玄《诗谱序》的意思很明白:“谓之《诗》之正经”的诗篇,就是指:风之《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以及《周颂》。而“《诗》之正经”,就是《毛诗序》所言之“正始”,也就是《诗》之“四始”。
《毛诗正义》于郑玄《周颂谱》曰:“颂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诗经》为什么会有“四始”的概念?“四始”概念的提出有什么重要含义和重要作用?
其一,“四始”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毛诗序》作者和《诗经》的编辑整理者对这四部分诗的强调和重视。而对这四部分的强调和重视,是《诗经》的编辑整理者欲以此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一个典范,树立一面旗帜。《诗大序》认为,“四始”是“诗之至”,它们是《诗经》中最早的诗和最早的《诗》,是最好的诗,最重要的诗,是《诗》之纲领,《诗》之精华,是理解、阐释《诗经》文本及其编排之意的门户。这些诗都创作于西周盛世,完全符合儒家提倡的“主文谲谏”的做诗标准。
其二,笔者推测,最早的《诗》文本只有“正诗”,即只有二《南》、正《大雅》、正《小雅》和《周颂》。所以,“四始”概念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些诗篇是今人所见《诗经》的四部分之始,更重要者还在于,这些诗篇是最早的《诗》文本,是《诗》之“始”,故称“四始”。宋代程大昌《诗论》曰:“《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从最早的《诗》文本的角度而言,这话是正确的。
其三,“四始”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编《诗》者对这些诗篇的一种强调和重视之意。而这种强调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当时典礼仪式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王小盾先生认为:
其实《毛序》的说法与《史记》同出一源,不必视为二说。它们的共同渊薮即周代礼乐制度。“始”在西周礼制中又表述为“重”:因升歌是儀式上的始奏之歌。由此可知,“始”的涵义是始奏,作为第一奏,它在典礼中具有特殊意义。
其四,“四始”概念之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风、雅、颂之名亦与“四始”有重要关联。《毛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前文已指出,“故曰风”之“风”,只能指“正风”,因为只有“正风”才完全符合儒家“主文谲谏”、“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作诗标准。像《鄘风·相鼠》这样的诗作,显然与儒家“主文谲谏”的作诗标准相去甚远。风化、风(讽)刺、风教,最初都是正人的。而“雅者,正也”,顾名思义,雅最初就是指正雅。雅即正的意思,那么雅的得名一定与正诗有关,一定应该取其是正诗的含义而得名。而《诗大序》释“颂”之言,孔颖达《毛诗正义》已明言:“此解颂者,唯《周颂》耳。”可见风、雅、颂之得名,一定与正诗、“四始”有关。即:风、雅、颂之名,最初是指“四始”(即正诗)而言的。
《诗大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大序》是意欲把《诗》之正、变与世之治、乱对应起来,以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一种鉴戒,也以此使“正诗”(即“四始”)成为后世诗人创作的典范。
前人亦有明《诗经》“四始”之义者,只是未引起后人重视和接受。唐人成伯玙《毛诗指说》:“《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为《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菁者莪》为《小雅》之正始,‘文王在上至《卷阿》为《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为《颂》之正始。此诗陈圣人之德,为功用之极,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正由此始也。”魏源《诗古微》:“夫《毛序》‘四始之说,即其‘正始之说。‘正始之说,即其‘正变之说。何以明之?毛以正风、正雅、周颂,皆周公手定乐章,故举平王、成康溢法,皆以别义释之。而二雅则自《六月》《民劳》以下,皆谓之变。观‘《周南》《召南》,正始之道云云,然则毛以四部正诗为四始明矣。”清戴震《戴东原集》:“诗之部分四:《风》,乡乐;《小雅》,诸侯之乐;《大雅》《颂》,天子之乐。而燕飨群臣嘉宾,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礼经。其后因旧部而颇有附益。于是目其定于周初制作礼乐时者,谓之四始。”戴震《经考》又曰:“四始自《毛诗序》《史记》已言之,盖经师相传之遗语。后儒因之又有风雅正变之说。今考《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驺虞》,《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颂》之《雝》《酌》,逸篇之《九夏》《狸首》《采荠》《新宫》之属,见于《礼经》者,皆周公所定之乐章。而太师教六诗,瞽蒙掌六诗之歌,并定于周公制作礼乐时矣。余窃谓: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其定于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后之诗,后人所采入,因旧部而各隶其后。则周公初定之篇章是为《诗》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诗》之正经,惟有所谓四始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师采而增益之与?村鲁太师所得者与?《鲁颂》之名必非列于周太师者。”
刘勰《文心雕龙》在评论《诗经》时有三处使用了“四始”一词,一是《宗经》篇:“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二是《明诗》篇:“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三是《颂赞》篇:“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在《颂赞》篇中,刘勰认为,《颂》是“四始”之极。根据刘勰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四始”中必有《颂》。其二,这居“四始”之极的《颂》不可能仅指某一首诗,也不可能《诗经》三《颂》全包括在内。显然,此应指《周颂》。
对“正诗”、“四始”的理解、认识,对于理解、阐释《诗经》至关重要。《小雅·鼓钟》云:“以雅以南,以钥不僭。”这里以“南”“雅”并称,无疑“雅”指的是“正雅”。《仪礼·燕礼》及《乡饮酒礼》中“二南”与《雅》诗合奏,奏毕称“正歌备”。《礼记·乐记》师乙答子赣之问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此亦指大、小“正雅”而言。所以魏源《诗古微》认为:“‘四始固全《诗》之裘领,礼乐之纲纪焉。”此语非了解、熟悉《诗经》者不能道出,绝非虚言。
综上所述,《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诗经》“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很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式三.论语后案[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2]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王小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4] 魏源.诗古微 [M].长沙:岳麓书社,1989.
[5] 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9.
(本文审稿 罗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