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富有越郁闷?
2017-04-26罗伯特·莱恩苏彤李晓庆
罗伯特·莱恩+苏彤+李晓庆
社会病了,生了一种叫做“GDP崇拜症”的病。症状表现为: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你抑郁了,我抑郁了,大家都抑郁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目前全球各年龄层共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且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國家。
尽管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主和市场制)是基于幸福的功利哲学——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制定的,但这些体制似乎并没能发挥其功效,即填补人们的欲求之壑,反而将人们引向了一种更加不幸的境地。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市场和政治制度都无法让我们快乐?如果财富与民主都无法依靠,我们能依靠的是什么?
罗伯特·莱恩,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于耶鲁大学执教近50年,就职期间曾任政治系主任。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是罗伯特·莱恩在政治、心理学界的代表性贡献之一。
收入越多的人就越幸福吗?
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中,金钱对于人们来说可能意味着某种快乐的凝结物,能够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它能够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作出选择,满足人们的偏好,从而将“效用”和“福利”最大化。但是,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虽然带来不少好处,但它却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幸福。
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当金钱相对匮乏的时候,金钱可以买到幸福;当金钱相对充裕的时候,这种购买力就停止了。纵观现代文明史,我们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曲线关系模式:在现代化之前“你增我增”,之后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互不增减”,而后发展为“你增我减”。
如果我们对同一个社会中的富人、穷人以及不穷不富的人进行比较,我们往往会得出与一些跨国研究相当一致的结论,即:在贫穷社会中,个人收入和幸福之间的相关非常显著;而在富裕社会中,这种相关却弱了下来,甚至几近为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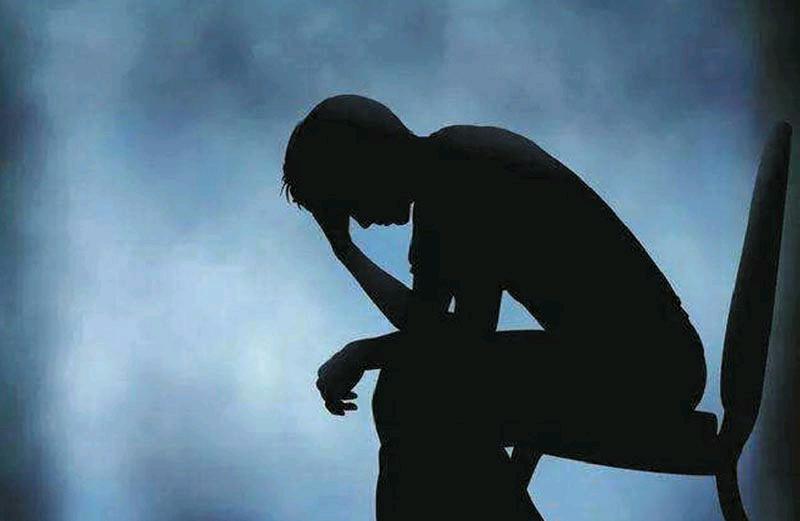
一组来自美国的研究发现:当一组受访者被问到是否同意“金钱是我最为在乎的东西之一”时,有60%的人回答是否定的;在英国,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变得富有是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是15%和38%。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两则启示:第一,英国人对安全和自由的渴望更甚于对物质的渴望;第二,一个国家“富过”的历史或“富着”的现状会使得这个国家的人们生发出一些其他的非物质性需求——相一致的是,最古老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是贪欲最少的,第二古老和富裕的国家(美国)排第二,而新近崛起的富裕国家(日本)是最具贪欲的。
为什么金钱并不能买到幸福?
许多关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指出: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让中产阶级人士体验到更加强烈的幸福感,除非他们能够从内心承认自己因此而提高的身份地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能够提高幸福感的并不是较高的收入,而是较高的身份地位。
但是金钱是否能够买到“自我掌控感”(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仍然无法确定。专家们发现:人们的职位越高,他们对工作的掌控感反而越小,甚至,升职反而会使人们感到更加不满。这是因为,由于一次升职人们会开始迅速期待下一次升职,并拿预期与现状进行比较。对金钱、职位、声望的追求就像是在一台全力开动的跑步机上,永远处于不停歇的奔跑状态。人们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使得人们在每次收入增长后,都能立即创造出一种新的衡量自己的标准。而这种永不满足的、随时调整自己期待的适应性,则正是市场主义所需要的。因为,是渴望而非满足,令市场充满活力与商机。
但这种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循环产生的渴望,却令人类感到不幸。受这种渴望驱使,人类在市场中永远处于与他人抢夺资源的竞争与比较状态。市场并不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存在,而是把人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在市场交易中,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赌博的老虎机。既然人只是一种生产要素,那么自然他们与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决于怎样做更有利可图。市场遵从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其中完全没有乡情、友情和亲情的位置。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宗族和邻里关系,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
如果说人在劳动市场中付出,那么消费者市场则应该是人们获得回报的地方。但事实是,人们能够在消费市场中得到的幸福也极不稳定。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被激起的消费欲望总是此起彼伏,似乎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而消费主义的盛行,也更进一步挤占了人们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间,人际关系也更可能被买卖关系所取代。
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
这些年来,中国最时髦的词汇是“增长”、“发展”、“市场”、“自由”、“民主”、“改革”、“转型”等等。我们把它们当作目标苦苦追求,但是,现有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其实,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逻辑推理和各国多年来积累的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所钟爱的“增长”、“市场”和“民主”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答案很简单:情谊。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从那时起,右派偏爱“自由”,左派偏爱“平等”,而答案却很可能是“博爱”。
多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当被问及“你认为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一问题时,超过一半的人回答是“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排名第二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其次才是“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我们会发现,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关键需求——自尊感、价值感、被爱、被接纳的感受,都需要与在他人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而这种互动关系并非市场主义中的利益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
如何在现有的市场民主体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情谊”,或者说,尽可能地减少市场及民主制度对“情谊”的破坏,是增加人们幸福感的关键。田园诗般地充满情感的过去,可能根本就不曾存在,而显然,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建立一个情感的乌托邦似乎也并不可行,过分强调情谊也会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比如感情负担、裙带关系、法纪松弛等。
那么,合适的、可行的做法应当是,对现实的市场以及民主制度进行适当改造,尽量增加其中的情谊(人情味);在追求其他阶段性目标的时候,尽量避免损毁情谊。
对于“情谊”关系与现阶段的种种矛盾,也许人们应该站在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来看待问题。他说,经济体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胜利。同样,为了实现情谊和市场的和谐共生,社会必须经过一个个人主义阶段以达到必要的繁荣水平,这样人们才能再次发现家庭和朋友的好处。
(张雪荐自《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