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鲍勃·迪伦,为何是你?
2017-04-25张伸,李皖,邱大立等
本期话题:鲍勃·迪伦,为何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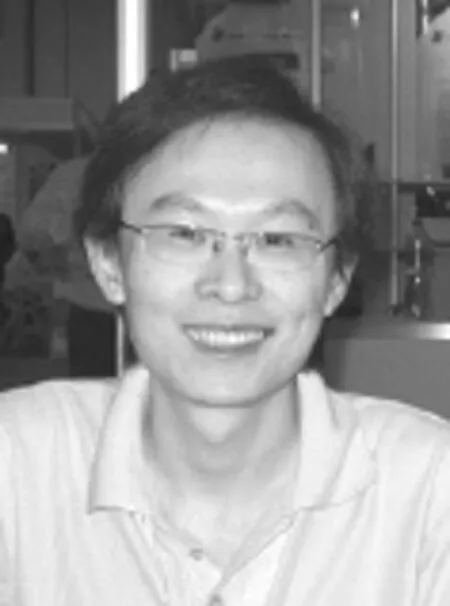
▲主持人
张 伸
(自媒体人,80后)
▲ 观察者
李 皖(乐评人,60后)
邱大立(乐评人,70后)
于 坚(诗人,50后)
杜思尚(诗人,70后)
张 楚(音乐人,60后)
小 魏(音乐人,80后)
陈 村(作家,50后)
朱 个(作家,80后)
朱振武(文学教授,60后)
张 莉(文学教授,70后)
陈 仓(媒体人,70后)
吴 桐(媒体人,90后)












背景
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民谣音乐人鲍勃·迪伦。不只是在中国,此举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文学奖为何会颁发给音乐人?在这个广受关注的文化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单独陈列的一面之词。本期非常观察,我们邀请了两位乐评人、两位诗人、两位音乐人、两位作家、两位文学教授和两位媒体人,来共同探讨:鲍勃·迪伦,为何是你?
一
张 伸:得知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时刻,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李 皖:迟到的颁奖。早该颁给他。
邱大立:鲍勃·迪伦唱了55年,终于可以被列入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了。一个人在75岁时得到这个奖,是一个合适的时刻。
于 坚:当时我在微信写了这段话:“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唱歌,要忧伤。于是,鲍勃·迪伦来了。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六十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一一致敬。世界醒了。”这段话在网络上传得比较广,这是我最初的反应。我有点激动。
杜思尚: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之后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原因很简单,因为得知自己喜欢的歌手、诗人、跨界艺术家获了奖,并且是个大奖,世界文学的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接下来,心里还多少有一些扬眉吐气的感觉。亲眼看到鲍勃·迪伦这个令无数人发自内心喜欢与爱戴,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几代人的民谣诗人、摇滚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得到了应有的认可与尊重。
张 楚:听到鲍勃·迪伦得奖,觉得有一点意外。想一想也觉得正常。
小 魏: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挺蒙逼的,文学奖怎么给了个唱民谣的?那些辛辛苦苦窝在家里写一辈子书又不会弹吉他唱歌的作家是不是都得气死?
陈 村:网上看到鲍勃·迪伦得奖的消息,为他高兴。但是,立刻又感觉到难过,为约翰·列侬。我更喜欢列侬和披头士乐队,可称爱死。鲍勃·迪伦获奖,我马上想到那个卑劣的凶手打死了一个诺奖获得者。
朱 个:好玩,有点意外,想“啊,终于成为诗人啦?”。意外之后随即脑补了很多画面:微博、微信铺天盖地的转发链接之类,朋友圈里会看到不少从没发现过有跟鲍勃·迪伦及那种音乐气质接近的人都在转发这些东西。
朱振武:尽管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常跑偏,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意外。毕竟这么多年来各种主义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已经把读者和大众搞昏了头,使大家都安之若素地接受各种脱离读者视线的文学创作。一些人甚至认为似乎只有小说才是文学,诗歌其次,散文是不是文学都引起了一些文学工作者们的争议。但转念一想,鲍勃·迪伦获得诺奖,这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暗示着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的回归?迪伦算是个吟游诗人吧,他的诗作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获个诺奖有什么不可?
张 莉:还是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此前大家都猜测是阿多尼斯嘛。我虽然对阿多尼斯获奖的消息半信半疑,但还是受了影响。所以听到鲍勃·迪伦获奖时有点儿吃惊。但这个吃惊不只是关于授给了鲍勃·迪伦,也包括对获奖的不是阿多尼斯的吃惊吧。
陈 仓:恐怕因为我有作家与媒体人的双重身份,这几年每到十月那几天我都很注意而且心跳加快,似乎自己与村上春树一样入围了这个奖。但是每次答案揭晓之后我又非常平淡,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获奖者,早期除了马尔克斯令我信服之外,这几年他们的答案与我心中的获奖者没有什么重叠,我在心里把这个奖发给了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刘醒龙、余华等等,我的名单里至少有二十多个人。不是我没有世界眼光,在我有限的眼里还没有多少外国作家能超过中国作家。中国作家作品里的博大精深与高天厚土是村上春树这样的线性作家无法相比的。就拿中国诗歌来说有一大批人,包括入围的北岛和70后诗人沈浩波在内,你去读读他们的诗,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艺术上来说,都是十分接近诺贝尔的价值准则的,都可以打败外国许许多多的诗人,当然包括打败鲍勃·迪伦——除了中国诗人不会唱之外,你说老鲍有哪一点是我们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对手?
吴 桐:是一个朋友通过微信告诉我的,第一反应,觉得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转念又想,不会是假新闻吧,因为前一天关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获奖的假新闻已经被疯转过一轮了,于是上网去核实。直到确认迪伦真的获奖了,我就打开音乐播放器,戴上耳机听了一遍《手鼓先生》来庆祝,那首歌是我的最爱之一。
二
张 伸:您第一次知道鲍勃·迪伦这个名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途径?
李 皖:1986年,大学二年级,在上海复旦大学6号楼宿舍,读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中文版。书中迪克斯坦以三分之一的主题大篇幅谈论迪伦——美国60年代的非凡人物,一个时代符号。当时,《答案在风中飘》正在校园中流行,旋律优美,声音洁净,和声动人,很热门。
邱大立:我从1987年夏天开始听美国热门音乐排行榜,1990年夏天开始听英国排行榜,但鲍勃·迪伦的歌曲从来没有上过榜。1994年1月,我去北京,买到了黄燎原、韩一夫编写的《世界摇滚乐大观》,第一次看到鲍勃·迪伦的名字。当时我非常好奇,一个民谣歌手为什么占据了那么多的篇幅?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音乐巨人。1994年6月,我去广州工作,在东二电器城,我终于买到了鲍勃·迪伦的打口唱片,他于1992年10月16日在美国麦迪逊花园广场举办的踏入歌坛三十年演唱会的专辑。
于 坚:大约在1990年代初吧,通过打口带。我记得昆明翠湖边上有个专卖打口带的小店,脏兮兮的,像个作坊,昆明听地下音乐的人都知道那里。
杜思尚:第一次知道鲍勃·迪伦是在1995年。当时我还在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读书,在周末的大学礼堂里观看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当听到阿甘青梅竹马的女友珍妮怀抱吉他,深情吟唱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时,惊为天籁,当时整个人都被镇住了。在这部电影的众多乐曲中一下就记住了这首歌,之后四处查找,终于找到了原作,就是鲍勃·迪伦的名作《答案在风中飘》。
张 楚:第一次听到他是1989年,一个磁带的专辑。
小 魏: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淘碟儿,复旦大学图书馆附近,一到傍晚时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纷纷出来摆摊儿,其实当时我对于国外乐队并不非常了解,淘碟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基本就是看封面儿,哪个好看买哪个。有一天我挑了半天也没相中一张“好看”的碟儿,明显摊主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问我听什么风格的,我说偏向摇滚民谣啥的,这时候他熟门熟路地从众多碟儿里抽出一张扔在面前说,你就听这个吧,鲍勃·迪伦,准没错!我一看封面,一个卷毛小伙架着口琴抱着吉他,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一副很忧郁的样子……这时摊主立刻呈现出一副很鄙夷的样子说,鲍勃·迪伦你都不认识?!我连忙装作很懂的样子说,当然认识,我就看看这张里面的歌我有没有都听过……后来匆匆付了钱,灰溜溜地滚回宿舍听了歌,其实当晚真的没有觉得鲍勃·迪伦的歌很好听,可能是因为当时还不是很能接受这些带有布鲁斯音阶的旋律或者这种慢悠悠连念带唱的表达方式吧,没听两首就关掉了。后来随着自我修养的逐渐提高和耳闻目染,再次重新聆听鲍勃·迪伦、甚至认真去网上寻找歌词大意的时候才明白他的伟大之处,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伟大之处。
陈 村:较早看到他名字,忘记何时何地。是看到一大串西方歌手名字,中间有他。《答案在风中飘》容易听到,但不知是他写的。“像一块滚石”的说法也多次看到,不知是他说的。
朱 个:第一次知道鲍勃·迪伦的名字,是读初中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首先是我在新华书店偶然买了一盒唐朝乐队的卡带,忽然觉得耳目一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音乐。于是会有意寻找,然后陆续接触到国内的一些地下音乐。有一天在音像店找红星生产社,无意间发现有一本叫《音乐天堂》的有声杂志,非常喜欢,几乎每期都会买。好像就是在这里面知道了Nirvana、鲍勃·迪伦,还有Patti Smith等等很多后来很喜欢并且对个人成长影响至深的音乐人。
张 莉:应该是很多年前了。我有位兄长辈的朋友喜欢他,他哼起过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这首歌曲,很好听,我后来还特意去找了歌词看。
吴 桐: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我能确定的是,我不是先听到他的歌,而是先看到他的歌词:《答案在风中飘》《敲天堂之门》《像一块滚石》……就像第一次读波德莱尔或者金斯堡的时候,被文字击中的那种感觉。我对旋律和节奏的敏感不如对文字的敏感,所以我喜欢一首歌的先决条件是歌词要好。
三
张 伸:鲍勃·迪伦的歌曲给您的感受是什么?您如何理解他的歌曲?
李 皖:迪伦最了不起的,是他在仅有20岁时,即拥有一副像一个民间黑老头那样的苍凉声音。他用这种声音,唱出了像经历和见证了整个人类分分合合、打打杀杀、沉沉浮浮历史的“古老”歌曲。他是这一百年来,全世界最伟大的歌手,影响整个流行音乐。他写出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最重大的歌,其磅礴的信息量、山洪暴发般的情感烈度、大时代的关怀与悲悯,器量惊人。如果说许多优秀的歌手是单车独行,那么迪伦却像是一列火车。一句话,他的歌曲就是一部现代启示录:容纳了整个时代,抚慰了万千众生,启发了各路神人。
邱大立:55年来,鲍勃·迪伦一直在用他的民谣寻找着他探索的方向,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河流村庄,他始终深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他心中的上帝。当他抚摩自己亲手调制的琴弦时,他其实更想去测试内心的一次次冲动,这时候,他同时也找到了一大群温暖、可以共鸣的听众。他像一个早已忘记疲倦的农夫一样,走到哪里,民谣就生长到哪里。
于 坚:对生命的热爱,有点忧郁但不做作。让人灵魂出窍。鲍勃·迪伦是屈原那样的现代巫师,他唱的是灵歌。他告诉我怎样生活,怎样爱,怎样面对死亡。一种声音的宗教。他是一种灵性生活的榜样。他的歌曲是一座声音的祭坛。
杜思尚:我在听鲍勃·迪伦的作品时,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他的一首歌能包含一个时代、一个世界,比如《苦雨将至》《盲眼威利·麦泰尔》等。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诗人艾伦·金斯堡是这么形容他的:“一串串灿烂夺目的意象”。许多美国人都认为鲍勃·迪伦是能代表美国文化、超越时代的杰出诗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听他的歌,有时候似乎听懂了,有时候又觉得不是这样,在我每一个年龄段的理解也很不一样。很像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我们虽身处其中,却又望不穿,看不懂。他歌曲中的句子,乍看起来很简单,仔细听却能听出不一样的沧桑与无奈,当然也有悲悯与爱,这就是鲍勃·迪伦与众不同的地方。
张 楚:觉得他和我们常说的乡村歌曲不一样,后来持续地听他的专辑,觉得他在写作音乐上做了很多尝试,歌词也很追求诗歌性。
小 魏:他的歌给我的感受就是歌词写的真心挺好的,思想性特别强烈,而且唱出来很流畅。有些人的歌词也写得好,但不一定就能和旋律契合得很好,可能这个就是他的歌传唱度这么高的原因吧!
陈 村:他的歌跟他的时代、他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摇滚对时代发声。西方的一代人听他的歌,唱他的歌长大,对他自然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我们对这个背景不熟悉,他们听歌的时候我们在闹革命,要非常感同身受很难。但歌曲是越界的,哪怕听不懂歌词,哪怕过去了几十年,音乐一起,那音调中的惆怅就打中自己了。
朱 个:真挚、淳朴、情绪充沛,早期鲍勃·迪伦的歌曲配器只有吉他和口琴,甚至有些只有最简单的和弦崩崩响——可能正因为如此,加倍凸显出歌者的声音之单纯美好。我现在的车载音乐还有放着他早期的歌,有时行车半路听着听着常常觉得他的歌唱情绪像泉眼外涌,控制不住地往外冒。后来他跟着潮流插上了电,就开始华丽很多,也招致不少争议。迪伦也有很多与爱情有关的歌,但他并不把爱描述得沉溺在感情里,用我好朋友皇后大盗的话来总结就是:“迪伦常常抽身事外像一个人拿着地球仪观察地球一样,与天真的披头士乐队歌唱爱与和平激动得要死要活相比,迪伦似乎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保持沉默与安静,伺机而动地指出目前的现状以及做一个揭穿皇帝没穿新衣的小孩。”
朱振武:迪伦的歌曲激荡人心,但我更关注他的歌词。这些歌词本身的魅力正是他成功的堂奥之一。
张 莉:我听得不多。有几首很喜欢,除了《答案在风中飘》,我觉得《大雨将至》也很好。我喜欢鲍勃·迪伦的歌词,他是优秀的诗人,这毫无疑问。
陈 仓:他的情绪与声音都很纯,他把自己整个人都当成了一种乐器或者一个音符。像夏天的蝉鸣或者秋天的蟋蟀,都是从毛孔与骨头里流出来的沙哑和颤抖,不过这不是杂音,而是一种磁性——因为身心与世界、命运摩擦之后生产的那种磁性。虽然我听不懂他唱什么,一个词都不明白说什么,但是我依然觉得他唱得很好。在写不好小说与诗歌的时候,我都有点想学习他买一把二胡唱唱歌了。我说这些正好印证了我刚才的观点,说明他除了音乐并没有其他,就是一个自然天成的民谣歌手。我在想一个问题,即使他唱的是心经或者是诅咒我们的话,我感觉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不会影响他对我们的打动力和感染力。对他而言,除了存在艺术表现上的技术性障碍之外,在他的歌曲里并没有文字的力量,或者文字的力量并不明显,除非有人非得胡搅蛮缠,说音乐就是文学,文学就是音乐,诗歌既要有诗又要有歌,这之间是可以纠缠不清的,就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跨文本一样是无法严格分离开来的,那我自动举手投降认罪。
吴 桐:高中的时候,我还不能体会迪伦嗓音和口琴声音的魅力。直到上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跑步的时候耳机里循环播放鲍勃·迪伦,这才觉得那和弦那嗓音越听越耐听,越听越上瘾。这些歌让我开始像一个成年人一样思考,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爱情?为什么要歌唱?为什么要反叛?
四
张 伸:文学奖本该是颁发给作家的,您如何看待音乐家获得文学奖?
李 皖:这次的文学奖,和历史上历次颁奖一样,颁给了一个作家。这个作家的确切身份是一位诗人。并且,在诗歌之外,他的叙事作品也分外杰出。当然他还有一个身份,歌手,但他并非是凭歌手身份获得此殊荣的。以为一位音乐家获得了文学奖,这是对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误解。要看本质而不是看表面。比如,我们不能说画下了无数杰作的齐白石是位好木匠。
邱大立:在我看来,文学应该具有多种表达方式,可以是小说,可以是诗歌,可以是口述历史,可以是街头艺人的沿街卖唱,甚至也可以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聊天。文学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冷冰冰的词语,它应该是流动的。
于 坚:这要看怎么理解文学了。鲍勃·迪伦就是文学。换个立场,你可以说屈原的招魂是乱音,不正,不雅,语怪力乱神。对迪伦的质疑像当年将爱伦·金斯堡送去法院一样,人们已经忘记了一切叫做文学艺术的东西,都起源于古老的祭祀、招魂。诗是一种祭,屈原不就是远古的一个鲍勃·迪伦么?只是现代社会文本与空间脱离了,成为纸上的修辞游戏、知识记录。鲍勃·迪伦是在场的,20世纪中后期的“垮掉的一代”,可以说是世界现代诗的最后一道灵光,这道光仅在鲍勃·迪伦等少数几个人身上幸存。
杜思尚:在我的理解中,音乐和文学是天然不分家的。在咱们中国,自商代始,诗、乐、舞为一体的说法就有大量的文献记载。更何况从本体上讲,音乐性本身就在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以摇滚和民谣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鲍勃·迪伦来说,他的歌词本身就是文学化的。 感谢瑞典文学院,用这么一种奖励与荣誉,纠正了人们心中长久以来的偏见,还给诗与歌,摇滚与民谣,这些用生命来吟唱的艺术应有的尊严与光荣。
张 楚:我以前也很喜欢纯文学,把歌曲作为文学,也是文学奖的尝试吧。
小 魏:虽然他得奖大家都挺蒙逼,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问题,鲍勃·迪伦要是不会弹吉他唱歌,现在他就应该是一诗人身份吧,岂不也是名正言顺的获奖吗……我记得哪年某个大媒体就把什么年度最佳诗人之类的有关文学的奖颁给了民谣歌手周云蓬?当时好像也没什么人出来质疑吧。
陈 村:中国的诗与歌是联在一起的,传统上是可吟唱的,西方有游吟诗人的传统。鲍勃·迪伦获奖很西方,又很中国。颁奖给词的作者,并非颁奖给曲的作者。只是不巧这个作词的还作曲还会唱。这算是文学的野合吧。
朱 个:啊,难道不是颁发给作为诗人的迪伦的吗?
朱振武:迪伦是个音乐人,他当然也是个作家。诗歌,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唱的韵文。因此说,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授予了文学家。迪伦的诺奖授奖理由是“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诺奖评委显然看中的是他的诗性表达。迪伦的获奖,与其说是开拓了文学的疆域,毋宁说是恢复了文学的本来面目。
张 莉:鲍勃·迪伦不是纯粹的音乐家,他是诗人。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那些优秀的作词者本身就是诗人。今天我们喜欢分类,喜欢说这些人属于音乐家,那些人属于文学家。这其实是人为设置的壁垒。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壁垒呢,没有的。在古代,诗与歌是不分家的,诗本来就是可以唱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视那些诗人为作词者的。那么,反过来说,今天的作词者被视为诗人有何不可?
陈 仓: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想找一个站台的,诺贝尔文学奖发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吧?应该找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通俗的站台者了,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在新书发布会上,会请一个明星到台上表演一点魔术或者其他歌舞节目一样。在几个书展上,我看到请了站台的效果与不请站台的效果还真不一样,不请站台的就有些萧条了。我是这样将心比心的,如果他们真想找个站台的,总不能把这个奖发给克林顿或者其他什么政治明星吧?鲍勃·迪伦那绝对是最佳人选了,起码还属于艺术门类范畴,那么牺牲一两个奖也没有什么,我们想想如果这个奖没有发给站台的,而是真发给了村上春树——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但是对于焐热文学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
吴 桐:他本来就是一个诗人。
五
张 伸:您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这次的文学奖跨界,颁发给鲍勃·迪伦?
李 皖:颁奖词说得明白:“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
这句话,深谙迪伦诗歌作品的人当有以下解读:第一,评审团出于对迪伦诗歌成就的肯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第二,具体来说,迪伦对诗歌创作的历史性贡献,是将美国歌曲(歌词)的伟大传统引入了诗歌,由此刷新了诗歌史的部分面貌。第三,曾有诺奖评委提示,“新的诗歌表达”是复数。这即是说,迪伦在诗歌上的成就和创新,不只是仅限于上世纪60年代。他一直在创造、创新,他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中的创作,同样值得文学史肯定。
邱大立:我相信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应该很早就注意到了鲍勃·迪伦,但他们一直在考验这个人的耐心,同时也在考验他们自己的判断力:这个人思考的是什么?他是否掌握了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他的音乐有没有一种审美的概括力?最后,他们得到了结论。
于 坚:也许那些教授和院士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想赶赶时髦?这是一个极有广告效应的标题: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利物浦街头的某位戴耳机的小瘪三都会闻之一愣。这个奖的影响力正好悖论式地意味着它对文学的无足轻重。也许是神启吧。今天这个世界需要鲍勃·迪伦的声音,需要迪伦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生活,什么是死亡。这种声音其实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他的歌唤起的是我们对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灵性时代的记忆。比如李白、莎士比亚们的时代。
杜思尚:当然是从文学的角度考虑,同时兼顾影响力。我认为诺贝尔文学终于在文学性和影响力的平衡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人选之一。更重要的是,诺奖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创举。当大家更多地讨论为什么会把这个奖颁给一个音乐家的时候,已经局限了文学的范畴。好的歌词本身就是诗性的。我们经常会把鲍勃·迪伦称为“游吟诗人”,表面上看是一种浪漫的称谓,实际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包括我们这个世界早期的诗人,只不过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以作家为标示的文学领域。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一个世界级的大奖要想长期赢得民心与更多的认可度,他需要持续地关注在文学艺术的大家庭里,究竟有哪些作家、诗人的作品在推陈出新,在影响着人类的精神风向,而鲍勃·迪伦恰恰就具备这样一个优势和特点。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是在提醒我们,文学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更丰富广阔的世界,就如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授予过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一样。鲍勃·迪伦也是用他一生的坚持、生命的热情,用他诗与歌的完美结合,用他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张 楚:诺贝尔是一个传统的奖项,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跟上现代的节奏。
小 魏:个人觉得一方面可能本年度评委们没有找到他们认可的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鲍勃·迪伦的作品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且在当时也真正掀起过一股思潮的!算算年纪,估计评委里应该有他的粉丝?只恨没有诺贝尔音乐奖,想来想去只好给他文学奖了。其实这么算来,诺贝尔和平奖给他也行啊。
陈 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吧。而且评委们只代表自己投票,似乎并无协商求同机制,没有在个人之上的“评审团意志”。
朱 个:肯定是出于好玩。文学圈那么多大咖的竞争,让你们一个个流口水去吧!
朱振武:诺奖评委经常出人意表,揣度他们的想法往往如镜中揽月。每年诺奖的猜测基本上都是差之千里。但这次的评奖是对文学本体的回归和彰显,还是说得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范围再收窄的话,其关注度会越来越小的。这也是文学发展的趋势,即不应该躲进象牙塔,更不能钻进死胡同。文学是个很宽泛的概念,远不止是朦胧诗、意识流小说、什么魔幻写作或妖魔叙事,更不是恶搞、拼贴、戏仿等所谓的后现代。
张 莉:奖项都不会心血来潮随意颁发。我认为,鲍勃·迪伦的获奖是有某种指向性的。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刺激今天公众思考何为文学、何为诗人,刺激公众思考文学如何参与社会生活是有意义的事情。话说回来,没有悬念、不给人刺激的评奖也是无趣。
吴 桐:一个朋友说,鲍勃·迪伦哪里冷门了?至少三年前在博彩网站上的赔率就低得跟村上春树差不多了。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莫言比他冷门多了。虽然难以揣度瑞典文学院的老头们的想法,但这看上去是个不坏的决定。至少我周围几乎所有人,不管喜不喜欢文学、爱不爱好音乐,都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和鲍勃·迪伦。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变得更开放了,本来不就应该这样吗?政治家可以得文学奖、记者可以,歌手当然也可以。
六
张 伸:鲍勃·迪伦说他有别的安排,缺席了诺贝尔颁奖典礼,对此您如何理解?
李 皖:迪伦是个很真实的人。首先,他认可这个奖项。从他内心一直在追求的目标来看,文学追求或者说文学上的肯定,一直是他的至高追求之一。其次,对于他来说,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可能他真有别的事,在他的价值天平上重于参加诺奖颁奖礼这件事。迪伦是一位蔑视世俗和公众看法,特别特立独行的人。他一生都不服从于俗见,一生都表现得这样。
邱大立:我在想,鲍勃·迪伦在少年时代就应该知道了诺贝尔奖,他逐渐了解了它的严肃使命。从少年到今天,他应该对诺贝尔奖心怀敬畏。在获悉自己获奖的一刻,他可能有些触动了,他需要理一下心情。
于 坚:与他的歌比起来,这事真的是无足轻重。他并不是为这个奖而歌唱的。这是一个意外,他当然是优先去做他一直在做的事。
杜思尚:我个人认为鲍勃·迪伦是一个兼具历史沧桑感和平民情怀的艺术家,他的一生经历无数,战争与和平,贫困与繁荣,叛逆与落寞都是他人生的常态。相信他是个超然物外的人。一个艺术家,对荣誉和奖励都有自己的认识与态度,我们只能尊重。我们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这就足够了。
张 楚:缺席颁奖典礼我觉得是一些人的习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和谐。
小 魏:我觉得他应该是挺不好意思领这个奖的,毕竟那么多作家都还不一定温饱呢……这可能也是他个人表达对广大作家朋友的一种尊重的方式吧!
陈 村:有事去不了,害羞去不了,忽然懒得动去不了,被又一段感情绊住去不了,怕坐飞机去不了……种种状态都正常。去或不去是他自己的事情,我都理解。他写了好歌,唱了好歌,大家听了很开心,还要怎样呢?
朱 个:人家大概真的有事吧。干吗揣测他为什么拒绝领奖,还把萨特拒绝领奖的演讲安插到他头上?这么做的人,代入感也太强了吧?不就是一个奖,他爱怎么领就怎么领好了。
朱振武:历史上缺席诺奖的不只他一个,有的干脆拒绝了诺奖。迪伦虽然没有露面现场,但还是请人宣读了他亲撰的受奖辞。从受奖辞中能够看出他对这个奖还是非常重视和认同的,他也说出了个中的意义和价值。
陈 仓:他缺席却不拒绝,说实话就凭这一点,我还是很崇拜他的,说明他情商与智商都比我们高出一个头,按照我们中国人平衡的处事方式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说白了应该得的好处,包括奖金、奖状、荣誉,他统统都纳入怀中了,同时又不得罪诺贝尔评委会,还显示了视奖如水的人格魅力,更厉害的是这种模糊的态度恰如其分地应对了各方面的质疑。如果有一天,因为我小说里涉及了一些教人从善的宗教内容,而把诺贝尔和平奖或者医学奖发给我的话,我肯定没有坐怀不乱这个定律的,也许立即表态辩解一翻,或者非常高兴地发一个朋友圈,炫耀一下和拍几句评委会的马屁,那样肯定会让人讨厌,也暴露了自己对获奖的期许之心。不过,有人不想获诺贝尔奖那纯粹是假的,或者是没有这个自信而已。
吴 桐:比起在辉煌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被一群穿着礼服的人包围着,他更适合抱着吉他吹着口琴出现在某个乡村酒吧里。不过,见到帕蒂·史密斯代替迪伦领奖,也算是一种惊喜。帕蒂·史密斯闭着眼睛唱那首八分多钟的《暴雨将至》。中间有地方唱错了,她就停下来,道歉,像个孩子一样说自己太紧张了。
七
张 伸:前些年,中国摇滚明星崔健曾被国内的文学奖提名。请您预测一下,今后中国的文学奖项会不会颁发给音乐人?如果会,您觉得会是谁?
李 皖:会的,肯定会。其实从“纯”文学的品质来说,崔健不是文学上最突出的。中国文学奖颁给音乐人,很可能另有其人。会是谁?我也不知道,很可能是尚未诞生的某部作品的某位作者。
邱大立:如果我们预测会颁发给崔健,说明我们是乐观的。如果我们预测会颁发给左小祖咒,说明中国文学也是乐观的。
于 坚:我想不会。对诺贝尔这样一个奖来说,它肯定要计算广告的成本。它本来就是瑞典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广告。中国音乐人还没有对评委们构成那么大的投资诱惑。中国摇滚只是中国的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实和京剧差不多。在我看来,如果奖给音乐的话,就其已经达到的伟大与深厚来说,应该讲给黄梅剧方面的大师,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杜思尚:中国的文学奖如果具有诺奖的胸怀与情怀,也应该适当考虑杰出的音乐人,尤其是终其一生,用心去歌唱我们时代,歌唱我们人性光辉与尊严的艺术家。用汉语演唱的音乐人里面,符合或接近文学奖评选标准的,就我的聆听范围和感受,台湾歌手罗大佑具备一定的能力。罗大佑的歌曲无论是题材的广泛度、歌词的深刻以及影响力,都应该是华语音乐难以超越的高峰。他曾经像鲍勃·迪伦那样批判政治、世事,反思文化、教育、传统、都市情感,吟唱乡愁,倡导和平与爱,相当多的歌曲都超越了一般流行乐的标准,歌词也兼具诗歌的特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张 楚:中国也这么做是可能的,会给谁这要看人们对文学的价值基础的理解吧。中国有自己的选择模式,选择良心还是才华,就不知道了。
小 魏:张楚啊、万青啊、周云蓬啊、PK14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都挺合适的。其实我们现在当做文学作品的古诗,在古代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音乐形式,所以这两者其实还是相通的,文学奖给词作者应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吧。
陈 村:中国的事太不好说了。如果颁奖给音乐人,我期待罗大佑得奖。他的歌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我很少听流行音乐,但知道他。他第一次来上海开演唱会,我居然也去了。许多人从各地赶来,气氛热火朝天。只可惜他没唱那首我最想听的歌。
朱 个:第一个问题,随着时代演进,我不确定有更大的包容度吧。我不知道,没有想法。第二个问题,我想,太介入现实事件、太介入魔幻中国的音乐人不会有机会在国内得奖吧。还是颁给汪峰吧,帮他上头条。
朱振武:文学奖始终是文学奖,不会颁发给音乐人。诺贝尔文学奖这次也不是颁发给了音乐人,只不过作为诗人的迪伦恰好是个著名音乐人。
张 莉:崔健在我眼里不只是摇滚歌手,他也是诗人。我在大学教当代文学史,每年也都会讲到崔健和他的歌。至于中国的文学奖会不会颁发给音乐人这个问题嘛,其实也不是问题,因为已经颁发过了。获奖的是民谣歌手周云蓬。《人民文学》2011年3期上发表过他的诗《不会说话的爱情》,当时李敬泽先生是主编,我记得他在封面语上特别推荐了这位诗人。也是在那一年年底,周云蓬获得了“《人民文学》2011年度诗歌奖”。至于下一个文学奖会颁给哪个词作者,我就不猜了,可能性很多,很可能那个获奖者早就被视为诗人,也很可能那位作者还在乡野或酒吧歌唱,还没有来到公众眼前呢。
吴 桐:没有什么不可能,而且音乐人里向来有许多是真正的诗人。我能想到的是周云蓬、胡德夫。
【责任编辑 刘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