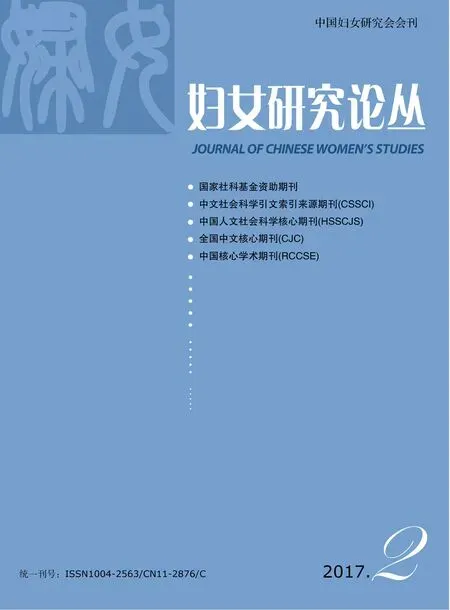闺情·启蒙·市场·学校
——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说的多元书写
2017-04-15马勤勤
马勤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闺情·启蒙·市场·学校
——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说的多元书写
马勤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说;多元书写
文章从闺情、启蒙、市场、学校4个角度,以陈翠娜、刘韵琴、高剑华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7位女学生为中心,展现“五四”现代女作家登台之前,女性小说创作的多元面向,并借此思考“近代”与“五四”女作家之间的混沌地带,梳理清末民初小说女作者在文学史上的角色与位置。
一、引言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依体裁而论,女性小说创作的成就最为突出。然而,在中国前现代的文学语境下,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看作品格趋俗、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规塑。20世纪以前,已知为女性所作的小说仅有3部:汪端的《元明佚史》、顾春的《红楼梦影》和陈义臣的《谪仙楼》。其中,留存下来的只有《红楼梦影》,却未敢显露作者的女性身份。对此,有论者认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恰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1](P1)这一表述强调在辛亥革命的“政治弑君”之后,女作家以“五四”的“文化弑父”为契机,借着一场“文化断裂”瞬间“浮出历史地表”。然而,任何文化上的偏见都不会消除于一夕之间,这种“断裂”说无法弥合女性从事小说创作的禁锢是如何逐渐消除的,从而失之于简单。
事实上,女性开始撰写小说,自晚清就已出现。据统计,清末民初至少有小说女作者56人,小说作品141篇(部)[2](PP266-272)。 尽管较之冰心、庐隐这些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长期以来,勿论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即便在几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也都难以觅得她们的踪影。但是,在“五四”以前,这个女性小说家群体的确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一出现在“五四”前夜的文学/性别现象?这些女小说家以及她们的创作,与之后的“五四”一代究竟是接轨还是断裂?而这又可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例如,受教育的女性在晚清民初的小说文坛,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男性作家有何不同?在个人修养与时代潮流之间,她们如何做出个人选择?就每一个个体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否只能以“冲击”或“取代”模式来进行阐释?事实上,在短短的一篇论文中,不大可能全面回答上述提问,但至少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作为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起点。
本文从闺情、启蒙、市场、学校4个角度切入,以陈翠娜、刘韵琴、高剑华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7位女学生为中心,展现“五四”现代女作家登台之前,小说女作者创作的多元面向以及“她们”所继承、指代或开启的不同的传统——古代闺秀创作、晚清“小说界革命”、民初的通俗文坛、“五四”新文学。借此,本文不仅致力于追踪还原“近代”与“五四”女作家之间的混沌地带,也希望重新梳理清末民初小说女作者在文学史上的角色与位置。
二、当“闺秀”与“小说”相遇
在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化中,“闺秀”与“才女”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但二者的含义不尽相同:“才女”可以涵括具有文艺素养而身份、地位各异的所有女性;而“闺秀”则特指才学、品行俱佳的世家女子①对此,女性自身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清代道光年间完颜恽珠在编辑《国朝闺秀正始集》时,自始至终以昌明“圣朝文教”为职志,恪守“闺秀”壁垒。参见[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本文讨论的陈翠娜,就是这一拥有千年历史的“女性传统”在近代中国得以延续的一个典型人物。她原名陈璻,字翠娜,又字小翠,生于1902年,浙江钱塘人。其父为近代著名小说家、实业家陈蝶仙;母朱恕,字嬾云,擅吟咏;兄陈蘧,字小蝶,也为文坛写手;另有一弟,名次蝶,亦擅诗画。可以说,陈翠娜出生在一个商儒结合、满门风雅的家庭,“时人誉之者,辄比为眉山苏氏”[3]。
与同期其他小说女作者相比,陈翠娜的出身算不上是高门大户,但她自小得到了来自长辈的无限呵护,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故而养成一种清逸出尘的品格和卓尔不群的气质。在《翠楼吟草》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捕捉到这种闺秀气息,诸如“雪压阑干花压雪,最高山阁独梳头”[4](P1);“泰山有孤竹,霜雪凌其姿。一生自孤直,落落无旁枝”[4](P15);“美人在天末,仙袂从风扬。 遗世不一顾,冰雪填肝肠”[4](P40);等等。特别是到了成年,陈翠娜的诗艺已臻成熟,这种气质更是呼之欲出,溢于纸上。
事实上,以诗词抒发情志,建构闺秀的主体身份,在古代女性的创作中并不鲜见;然而,作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道”的小说,却是传统闺秀不曾涉猎的领域②明清之际,闺秀才女也写作韵文体的弹词,但事实上,“弹词”与“小说”有着明晰的文类界限;只有将它们同时置于“通俗文学”或“叙事文学”这一大的概念之下,二者才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统摄起来。参见谭帆:《稗戏相异论——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与“通俗性”辨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然而,据笔者目前统计,在“五四”之前,陈翠娜发表的著、译小说总计11篇③篇目为:《劫后花》(《申报·自由谈》1915年4月30日-5月12日)、《新妇化为犬》(《礼拜六》第76期)、《法兰西之魂》(《小说海》第2卷第9号)、《望夫楼》(《申报·自由谈》1917年2月15-19日)、《自杀堂》(《申报·自由谈》1917年2月25日-3月21日)、《情天劫》(中华图书馆,1917年)、《熏莸录》(中华书局,1917年)、《美人影》(《申报·自由谈》1918年7月26日、27日)、《粉垣埋恨记》(《小说丛报》第4卷第7期)、《露莳婚史》(《小说大观》第13、14集)、《疗妒针》(中华图书馆,时间不详)。。关于如何走上小说创作之路,她曾回忆:“时父兄方译著小说,八口之家,所入惟赖砚田。予亦试为之,家君以为可用。”[5]可见,陈翠娜最初写作小说,有以之谋生的需求,其作品也存在一定的商品化属性。然而吊诡的是,在陈翠娜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如其他职业小说家那样努力迎合市场、俯就市民的痕迹。换言之,尽管陈翠娜涉足了小说——这一传统闺秀绝不染指的文类,却始终不肯放弃闺秀身段,努力恪守着传统文化的壁垒。这在其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均有所体现。
纵观陈翠娜的小说作品,言情小说可达半数以上,这与当时小说市场的流行风尚十分合拍。民初时期,各种贴着“悲情”“哀情”“苦情”标签的畸恋、虐恋故事非常畅销,其“哀感顽艳”之特色,“能以至情发为妙文,以赚人眼泪”[6](P2)。 处于这种时代氛围中,小说女作者也未能免俗,吕韵清、徐畹兰、汪咏霞等皆有言情之作;但她们大多会讲述一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故事——在“情”与“礼”的冲突中艰难地选择后者,而这也正是“情”之所“悲”“惨”“哀”的原因。然而陈翠娜与众不同的是,她不仅自觉地服膺于礼教,并且乐观地展示出“情”与“礼”融洽调和的一面。
小说《劫后花》讲述了青梅竹马的兄妹江素雪与骆锦云的爱情由受阻到圆满的故事。在陈翠娜笔下,家境败落的素雪之所以能够赢得爱情,凭借的就是良好品行,谨遵“父母之命”的传统伦理。另一部小说《粉垣埋恨记》,则讲述了伯爵夫人与西班牙青年贵族向帝亚的一段不伦之恋,最后双双赴死。在小说末尾,陈翠娜发出了这样的议论:“嗟夫!此少年者,英姿壮岁,正当有为,乃以偶然渔色,而竟埋殁于粉垣之中,灵魂有知,又安得不自悔耶?而白雷夫人,则犹以为五十年后,必已骨化形消,可无遗秽于人间;殊不知悠悠之口,正不可以万金堵塞也。”[7]在她看来,背离伦理、纵情自欢之人,最终难逃身死名伤的结局;相反,守礼有节则是获得幸福的重要保障。可以说,《粉垣埋恨记》与《劫后花》恰好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传达了陈翠娜对礼教与情欲关系的立场。
如果说这种对“情”与“礼”的态度,体现了一种外在的闺秀准则;那么,小说内在的闺秀气质,则主要体现在艺术性上。首先,陈翠娜的小说具有古典主义的美学倾向,讲究适度、谐调与含蓄的美学原则。例如两篇“滑稽短篇”《新妇化为犬》与《美人影》虽皆有讽刺,却不失善意,全然出自童心、得其童趣,颇有“乐而不淫”的特色,与民初颇为流行的“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8](P14)、“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9]明显不同。而立意警世的《粉垣埋恨记》也没有肆意鞭挞有违道德的男女,笔墨间饱含节制之美,与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相当一致。其次,陈翠娜的小说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例如《劫后花》对主人公恋爱场景的描写:“晚云如黛,微露孤星数点,灼灼而窥下界。则此少年者,方以指环,加诸女郎纤指之上。桃花之瓣四飞,集女郎额,一若为女郎添妆者。”[10]试想,倘若此处的爱情被表现得卿卿我我、你侬我侬,不仅有违创作主体的闺秀身份,也会授人口实。然而,陈翠娜却将两性之间的爱意萌生,通过彼时的自然世界的浪漫氛围来烘托,不失为一手妙招。有时候,陈翠娜甚至会以写诗之时雕琢字句、炼字炼意的状态来作小说。例如《劫后花》第三节中“其时新月色初上,写女郎婷婷之倩影于地”[10],一个“写”字尽得风流,颇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之神采。
然而,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出现了,陈翠娜何以能够在小说中表达闺秀情志,坚守闺秀身段呢?在笔者看来,这与她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陈翠娜自小备受家中长辈宠爱。祖母脾气暴躁,唯独见到她“恒有霁色”,对她有求必应[5]。父母更视她若掌上明珠,“尤有非宋玉、卫玠不许之意”[11]。她与父亲感情最深,陈蝶仙曾说,“予生平寡交游,不喜酬酢……而可与言诗者,则惟吾女一人”[4](P2)。1927年翠娜出嫁前,陈蝶仙又悲又喜,自陈“不知来日光阴,如何排遣”,故而尽刊女儿作品,为《翠楼吟草》《翠楼文草》《翠楼曲稿》,以慰老怀[4](P2)。 可以说,尽管陈翠娜写作小说的初衷是替父分忧、赚取稿费,但沐浴在温暖优渥的家庭氛围里,且有父兄在前,她不会存在真正的生活压力,因此无需在小说中低就俯身,可以安心坚守自我。
此外,在近代中国,女学堂是“新女性”养成的重要场域,女学生在此接受现代化的知识谱系,习得诸如“女国民”“自由结婚”“男女平权”等新式观念。清末民初的小说女作者也不例外,她们基本都有学堂就学经历,且一般读至女子教育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师范学校。而陈翠娜的经历却不大一样,迁居上海之后,她也曾就读于崇文女子高小;但毕业后未再深造,于家中自修国文,名列陈蝶仙的“从游弟子”名录[12]。可以说,在陈翠娜的文学道路上,父亲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导师角色。她的首篇小说《劫后花》刊于《申报·自由谈》,此时陈蝶仙恰为该刊主笔;《情天劫》《粉垣埋恨记》《薰莸录》等几篇也均署“天虚我生润文”。由此可见,陈翠娜的知识习得与文学的生产、传播诸环节,与古代闺秀需倚仗父兄、丈夫和儿子来彰显文名的方式十分相似。
陈翠娜通英文,上过新式学堂,最后却回归家庭自修,以父为师;她懂得运用小说这一受众更广的文学体裁,以及报刊这一新的文学传播载体,却致力于在公众面前建构闺秀的主体身份。不可否认,这种闺秀身份意识将她的小说导向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今日也许会被视为倒退;但这也正是她在“国粹千年一旦亡”之危急时刻的责任感之表征。而且,恰是这种对身段的坚守,陈翠娜才得以将传统女性诗词中的美学特质导入小说文体,为近代小说文坛增添了一抹温婉清丽的闺秀气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以凌叔华为代表的“五四”女作家中“新闺秀派”的创作。笔者以为,这种新中有旧、旧中含新的文学特质,不应被文学史上新旧女性“两分法”的叙事模式所遮蔽。
三、作为“启蒙”“反袁”的小说
如果说陈翠娜的文学观念与小说作品更多指向传统闺秀的文学特质;那么,同期另一位女作者刘韵琴,则十分贴合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晚清以来,自梁启超倡言“小说界革命”并指出小说具有支配世道人心的“不可思议之力”,小说艺术性便退居其次,如何以之来宣传政治、启发民智,反成为作者写作的第一要义。尽管刘韵琴的小说均发表于民国之后,此时的文坛主流已然发生转向,但她依然坚持以小说为启蒙工具,“抨击帝制,警惕国人,庄谐杂作,惩劝并施,不求艰深而意自远”,“以一弱女子而能于春容吟咏外,举不律,与欺罔一世之奸人袁世凯抗”[13](P3),表现出了与晚清“小说界革命”相似的价值取向与思维逻辑。
刘韵琴,原名刘羽诜,生于1884年前后,江苏兴化人。其祖父为近代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刘韵琴自幼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1904年前后,与同乡李宜璋完婚;后因夫妻感情不睦,大约在1907年脱离家庭,入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在学期间,刘韵琴初步显示出了关注时事、忧虑时局的思想倾向,“时势衰微今已矣,谁人江上挽狂澜”[14](P12)、“自由不得毋宁死,孰能抑郁长如此”[14](P22)等诗句直抒胸臆,沉郁慷慨。民国之后,刘韵琴曾短暂地为新政权的建立感到欣喜,随后也为袁氏窃国的行径感到痛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故地重游,目睹了甫经战乱的南京城,写下“触目处颓垣残井,劫灰而已”[14](P24)的惨象。 同年冬天,刘韵琴怀着悲愤心情只身前往日本留学。1915年,因抗议袁世凯政府“二十一条”归国,开始担任《中华新报》的撰述工作。从刘韵琴思想的内在理路观察,她后来写出大量以爱国、启蒙为旨归的反袁小说,可谓水到渠成。
1915-1916年,刘韵琴总计发表小说作品 19篇④篇目为:《白虎汤》《大公子》《报夫仇》《痴人梦》《新华宫》《皇祸》《湘民苦》《爱国童子》《商人忿》《奇臭》《行路难》《烛奸》《水国春秋》《约瑟芬》《望帝魂》《临时侦探》(载《中华新报》1915年11月18日至1916年8月4日),另有《琼华第二》(《民权素》第17册)及《侠义女伶》《孝女奈杰娜复仇记》(载《国民日报》,时间不详)。,在当时的小说女作者中堪称高产。关于以小说为工具,刘韵琴从不讳言,第二篇小说《大公子》的篇前“小引”言道:
我这小说,不是捏造出来的,不是有营业性质的,是要使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知道,于今政界种种的黑暗事实,都是由这万恶政府酝酿出来的;我绝对认为于人心世道上有绝大关系,决非浪费笔墨,供人玩笑[15](PP2-3)。
可以看出,刘韵琴不仅对小说商品化持有批判态度,也不满读者将小说视为消遣,更明确宣称自己写小说是为了与“万恶政府”做斗争。纵观她的小说作品,可以视之为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斗争的产物,具有十分鲜明的时间特征——她的矛头始终跟随反袁斗争的实际情况,并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叙事的重点。例如作于袁世凯称帝前夕的《大公子》,嘲讽为复辟制造舆论而四处活动的“求暗会”(筹安会),他们到天津去请梁阮公(梁启超)作两篇主张帝制的文章,结果遭到冷遇。而写于袁世凯称帝期间的《皇祸》,则讥笑了因称帝而导致的袁氏家庭内部的争斗:先是大夫人到得宠的十一夫人处大闹,遭到奚落后,又联合其他众夫人一起杀奔到十一夫人的宫内,气得袁世凯口吐鲜血、晕了过去,后来灌了一盏童便、一盏回龙汤(尿的谑称)才苏醒。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之时,刘韵琴也没有松懈。在《爱国童子》中,童子携一束报纸回家,面色喜悦地告诉母亲“袁氏取消帝制”。母亲却告诫他说:
儿不观帝制派中人口吻乎?不曰“取消帝制”,而曰“帝制停顿”,袁逆亦曰:“姑且取消看看”。以此觇之,袁逆非诚心取消帝制并退位以受国民裁判可知矣……汝须知袁逆皇帝之名虽去,而专制之实尚存。国民习于苟安,癸丑之役,均徘徊观望,不思群起讨贼,以至有今日……此时千钧一发,吾国人应无男无女,无老无幼,皆宜群起以杀贼[15](P47)。
如此长篇大论,与其看作是母亲对孩子的教导,不若视为启蒙者向民众发出的呐喊。
与《爱国童子》这种假小说人物之口道出政治观念不同;在《烛奸》中,刘韵琴直接站出来发言。当写到袁世凯因美国政府电告本国商人取消借款的约定而欲自尽时,说道:“老袁常想自尽,却又舍不得就死,这真教做至死不悟呢!但是那独夫一天不死,或一天不退位,著者这支笔,也是一天不能放下,必要把他种种奸谋,揭了出来,在报纸宣布,以尽我笔诛的天职。”[15](P74)一个多月之后,袁世凯病逝;刘韵琴也在最后一篇小说《临时侦探》的结尾,为自己的小说生涯做了总结:“黎大总统下明令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此四年中惨淡无光之中华民国,依然庄严灿烂……记者对于袁氏叛国称帝之口诛笔伐责任,亦于是告终。”[15](P93)《临时侦探》刊于1916年8月2日至4日,8月15日刘韵琴即就任于上海中华高等小学校,正式开始了教师生涯[16];1918年前后,又前往马六甲培德女校任教⑤1918年5月5日的《妇女杂志》第4卷第5号上,刊出一幅《南洋马六甲华侨公立培德女学校校长刘韵琴女士小影》的照片,可见,至迟于此时,刘韵琴已是培德女学校的校长了。。可以说,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作家之从事小说创作,大体上是时事政治的需要,而并非源于自己的偏爱。因此,当共和危机解除之后,她自然放弃了小说这种形式。
尽管刘韵琴的作品与晚清小说风尚比较接近,但相较于晚清追求的通俗“只是落实在文体上,而不是在审美趣味上”,更不在意小说的娱乐功能[17](PP100-105);刘韵琴小说的趣味则相当浓厚,甚至难免恶俗之讥。在她的作品中,有一整套动物化的人物角色体系,建构方式主要是谐音——常常以“老鼋”“羊肚”“猪”来指代袁世凯、杨度与朱启钤等谋划和参与复辟帝制诸人。如《大公子》中办“求暗会”的“羊肚”,与大公子接近的“古鳖”“孙小猴”,另如《商人忿》里“姓猪的小子”和“羊公馆里的羊虱子”。刘韵琴十分擅长滑稽小说,常常寥寥数笔,即刻画出一个现世活宝。如《痴人梦》里对着乌龟磕头的王憨、《商人忿》与《烛奸》中惧内的涂利与周噬脐以及多篇小说均描绘过的袁世凯的抓耳挠腮、愁眉苦脸。在形式上,她亦不抗拒游戏文体,《皇祸》即是一例,该篇标为“滑稽一字短篇”,全篇句句含有“一”这个字。尽管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刘韵琴的小说常常显得不够严肃,与晚清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言甚其词”等弊端颇为相似。不过,刘韵琴毕竟只是将小说视为觉世工具,自然首先考虑社会效果;如此一来,写作形式必然退居其次。
至此,有必要将刘韵琴的作品放入女性小说史的脉络中加以观照。自晚清起,部分女作者已经在创作中初步显示出了启蒙者的主体意识。诸如王妙如以《女狱花》为“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进行女界“革命”之事[18](P760);邵振华感于“女界之黑暗”,故“托鸣于《侠义佳人》”,以期“吾女子睹黑暗而思文明,观强暴而思自振”[18](P85)。 进入民元之后,尽管多数女作者随俗趋时、立意消闲;但仍有少数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写作小说,如曾兰的《孽缘》、畏尘的《丹枫庄》以及黄翠凝的《离雏记》,等等。然而,上述小说主要还是宣讲兴女学、倡女权,抨击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对政治问题鲜有阐发,更少有像刘韵琴这般不遗余力地抨击专制政府,热切呼唤保卫共和,鼓吹暴力革命。不仅如此,她还常常以谐趣之手段,导民以政见,同时不避游戏文章与滑稽语体。可以说,刘韵琴的这批作品,将自晚清开启的、具有启蒙倾向的女性小说,推到一个可以称之为极端的向度,不仅在近代女性小说创作中自成一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五四”女作家关注时事民生的思想倾向。
四、才女与市场的“合谋”
在近代中国,不少文人或知识分子均以职业小说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由于个体境遇不同,其生活状态亦有清贫和优裕之分,但仰赖小说著述以维持生计则无不同。特别是在民初之后,小说的商品化倾向进一步增强,作家有时甚至会刻意俯身低就,以迎合市民阶级的审美与趣味。在这批职业作家中间,有一位女作者高剑华。她的小说不仅产量高、速度快,而且,由于创作主体的女性身份,还表现出一种携带着极强“商业基因”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特质,从而在近代文坛上别具一格。
高剑华,生于1890年前后,浙江杭州人。她的祖父是清末名儒高学治,为章太炎的老师。伯父高保康是当世名流,尤精书法。父亲高保徵善于经商,章太炎曾在《高先生传》中回忆,高学治“好金石,财略尽”,倚赖二子保徵才“得取给”,“故得寿考”[19](P210)。更有趣的是,高氏一门似乎有着类似的家族基因,商才辈出,其家产之富,在杭州有“高半城”之誉。以高剑华后来在出版市场上的表现观之,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来自父亲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商业天赋。
出身高门大族的高剑华原本可以过着优游闲适的闺中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早亡,家境败落。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到宁波某女子小学任教,高剑华也前去助教。1910年,她曾短暂地离乡北上,求学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夏返回杭州,与夫婿许啸天完婚。婚后,夫妻二人并无固定职业,基本以撰述小说、出版杂志为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诞生于1914年的《眉语》杂志。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小说理念——“闺秀说部”,将“女作者”商业化、符码化,充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理与猎奇心态。虽然《眉语》的出版时间不到两年,却大获成功,屡次再版;即使被禁停刊之后,影响也没有真正消歇⑥关于《眉语》的运营策略与影响,参见马勤勤:《作为商业符码的女作者——民初〈眉语〉杂志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在笔者看来,《眉语》的成功不仅奠定了许啸天和高剑华在文学界、出版界的地位,同时也建立了二人的信心,成为他们一生从事出版业的重要契机。
高剑华投身于小说创作,便始于《眉语》杂志时期。据笔者目前统计,她发表的小说作品总计11篇⑦篇目为:《处士魂》《春去儿家》《裸体美人语》《刘郎胜阮郎》《绣鞋埋愁录》《蝶影》《裙带封诰》《梅雪争春记》《卖解女儿》(载《眉语》第2-18号),另有《簾影钗光录》《笳声蝶影录》(载《闺声》第1号)。,尽管从篇目来看并非最多,但若以字数计算,文字量当为最大,并尝试写过3部长篇。与刘韵琴期待以小说揭露现实、抨击专制政府相比,高剑华没有居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反而将自己降于“娱人”的位置。在小说《卖解女儿》的开篇,高剑华明确告诉读者“不必深求原理”;而自己写作该篇的初衷,也不过是“梅窗无事,拾得破笔一枝,败墨一盒,记出这件故事给大家取笑”[20]。可以说,高剑华的小说观念,基本符合民初小说界面向市民阶层、立意消闲的主导倾向;而她的作品大抵为言情之作,也符合当时文坛主流。在言情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地位不言而喻,这也恰好是“商品化”小说不可或缺的核心质素,是谓“天下之小说,有有妇人之凡本,然必无无妇人之佳本”[21],“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22](P2)。换句话说,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是小说能否受到欢迎的关键。高剑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十分独到,而且还渗透着极强的女性意识。
首先,高剑华擅于使用第一人称——特别是女性第一人称来讲述爱情故事。《春去儿家》即为一例。全篇除了以女性口吻来述说悲欢离合,最吸引人的是女主人公在讲述中不断穿插的内心剖白。鬒儿无意读到父亲藏起的《会真记》《红楼梦》《牡丹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等句使她越看越有味道;这一幕,几乎可以看作女主人公情欲开启的关键。随后,小说对鬒儿情爱心理的揭示也相当大胆——“抬起头来一看,只见那人轻裘缓带,神彩飞扬,却飘飘逸逸的站在我面前。呀!这不是我镇日相思梦中牵挂的那怡哥吗?我当时又惊又喜,却又羞晕满面”[23]。诸如此类的女性第一人称叙事能够增强小说的主观色彩,让女性的情感与欲望一览无遗。而身为女性的高剑华,对女性心理的把握格外精准,使鬒儿的形象韵味十足。试想,假如这篇小说改用第三人称来讲述故事,将会失色不少。
其次,高剑华笔下的女主人公,基本都是爱情的宠儿。小说模式大抵为两位甚至多位男子共爱一女。例如《绣鞋埋愁录》中三男一女的情感纠葛,《刘郎胜阮郎》中斐立、康纳士围绕古伦娜的争夺,以及《蝶影》里巴理士、波拉治对茱莉的追逐。更有趣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有移情别恋的经历,甚至背叛有恩之人;可是,旧情人却不离不弃,或不惜为之苦守,或甘心代之受刑,虽间有一时之怨气,却最终释怀。世俗之眼常谓“淫奔”女子为失节;可是,高剑华不仅没有在道德上否定她们,而且还赋予这类女主人公美好的形象,读来很容易让人生出伤感、怜惜之意。不得不说,这种倾向与创作主体的女性身份关系颇大。
同时,高剑华的小说也描写过一男一女的故事,但女性仍是浪漫爱情的中心。例如,《裙带封诰》和《卖解女儿》皆塑造了对女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男子形象。如果说高剑华对女性心理的精准把握、大胆表露,满足了男性读者的窥探欲望;那么,以女性为中心的情爱世界的建立,则又能调动女性读者的兴致,使她们将自我投射到小说的想象空间中,进而获取现实中无法得到的心理补偿。可以说,这种基于创作主体的女性身份而创造出的具有“商业性”的女性特质,在民初文坛弥足珍贵,也是其作品畅销的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高剑华的小说还有一些“市场化”的典型特征,大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叙述曲折、富有趣味。例如《卖解女儿》,高剑华将两代人穿越于不同时空的爱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又如《春去儿家》,本来只是一个情节平淡的故事,但作者却通过不断地制造悬念来调动读者的阅读热情;而《裙带封诰》不仅情节跌宕,且将武侠与情爱因素做了融合,于传统形式中翻出新意。其二,语体香艳。例如《绣鞋埋愁录》,在男女主人公的押解途中,“我”买通了官差,得以与蘅芬共处同一囚车。在一番互诉衷肠之后,作者写道:“我告看官,自从初见了蘅娘,直到如今,虽说是凄凉困苦、哭哭啼啼,我却得着了美人的真情。一般的也和他亲了几个吻,舐干了他的泪珠儿,也算是人生在世第一件苦中的乐事了……将蘅娘轻轻放下,又和他亲了几个吻。”[24]这类香艳、露骨的男女情话,在高剑华的小说中常常可见。
总体来看,在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期,高剑华的小说是“商品化”程度最高的表征,她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女小说家的代表。事实上,出身高门大户的高剑华原本应该过着春花秋月的闺中生活;但父亲早亡,家境败落,后又嫁给一介贫寒书生许啸天。这一切,都让她早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当高剑华写作小说之时,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市场效益,因为她需要生存。如此,也就不可能有陈翠娜那样坚守闺秀身段的底气,更无暇像刘韵琴一样以小说来启蒙和救国。然而,幸运的是,高剑华生活在一个文学高度商品化的时代,这使得她有条件从文字中讨生活,叱咤于出版市场,并在小说文坛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中,以独特的女性心理与女性特质胜出。可以说,无论将之置于女性文学史还是中国小说史,高剑华在女性自我主体欲望书写方面均堪称先声。“五四”以后,伴随新文学的发展,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真美善》等杂志还专门推出过“女作家专号”,引起了文坛和商界的注意。这种以女作家的身份构造畅销卖点的营销,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市场再度上演,并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所谓“美女写作”和“身体写作”。然而,不能遗忘的是,利用女作家的身份营造一种“性”文化想象的尝试,则肇始于创办《眉语》并担当主笔的高剑华。
五、“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女学生小说
综见上文,在“五四”女作家正式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传统才女在时代冲击与观念变革之际,对于自我的调适与选择呈现出了非常个人化的过程——她们面临的生活境遇不同,所做的选择也各异。那么,回到本文的开篇之问:“五四”女小说家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是否可以因“晚清民初”与“五四”在时间序列上的前后相接,就将前者整齐划一,统统视为后者的“前史”?事实上,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抒发闺情的陈翠娜、倾向启蒙的刘韵琴,还是投身市场的高剑华,都难以与“五四”一代女作家建立起直接的承续关系。那么,下面将要讨论的出自《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下文简称《会报》)上7位女学生的9篇小说⑧篇目为张誉扬的《梦感》《贤孙复业录》《贫女泪》、刘锺慧的《二郭》、高珍的《华胥国》、郑寿禄的《杏花村侯氏记》、金庆畴的《黄女士》、史德华的《爱国血》、苏异尘的《教育梦》(载《会报》第1-4期)。,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五四”新文学女作家如何“浮出历史地表”。
从时间上来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小说创作集中于1916年至1918年,早于“五四”女作家的集体登场;然而事实上,《会报》上的7位小说女作者基本生于1900年前后[25],与苏雪林(1897)、庐隐(1898)、冰心(1900)、冯沅君(1900)、凌叔华(1900)、石评梅(1902)等年龄相仿。其中,苏异尘、高珍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第六学级生,郑寿禄、金庆畴等为第八学级,而凌叔华则是该校的第七学级生⑨关于凌叔华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习和文学活动,参见马勤勤:《凌叔华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事迹和佚作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后来,与郑寿禄年龄相同的刘韵琴也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苏雪林、庐隐、冯沅君等都是文艺研究会的成员。
可以说,《会报》上的小说女作者与“五四”女作家实质是同一代女学生,个中差别不过是她们处于不同的学习阶段——前者为中等教育,而后者是高等教育。下面,笔者将逐一分析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7位女学生的小说特征,并与“五四”现代女作家的作品相互验证,试图在“晚清民初”与“五四”之间建立起更加通透的通道。
事实上,“五四”一代女作家的出现,与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甚至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代女作家就是女学生[26];对此,前人已论之甚详。其实,早在1916年至1918年的《会报》上,7位女作者的小说作品就凸显出了非常鲜明的“女学生性”。首先,是注重彰显女学生的创作主体。其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以女学生为第一人称叙事,如郑寿禄的《杏花村侯氏记》和史德华的《爱国血》。《黄女士》等还非常注重刻画美好的女学生形象。其次,是格外标榜学习的力量。如张誉扬的《贤孙复业录》,孤儿阿汉能够夺回家产、振兴家声,靠的就是努力学习。而苏异尘《教育梦》中的女主人公“铸群”,更是将女学生的主体想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立志将学校建为“冠绝东亚”“开辟教育新世界”的模范教育机构。可以说,正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多年的学习与生活,为苏异尘提供了小说最基本的素材、知识、经验以及理念。事实上,女学生一直是近代小说反复描写的对象,从晚清到民初,她们的形象也有一个从“溢美”到“溢恶”的变化过程。如果在这样的理路之中反观《会报》所载小说,则可发现,这些出自女学生之手建构起来的自身主体与形象,显得格外珍贵。
此外,倘若引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日常课堂的国文训练,则更能凸显女学生小说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非常注重学生古文能力的培养,对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大家尤为推崇⑩关于古文与小说文体的关系,可参见康韵梅:《唐代古文与小说的交涉:以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为考察中心》,《台大文史哲学报》2008年第68期。。教员在课业评点中,时常出现“丰神酷似昌黎”“如读柳子厚诸山水记”“凝重简括逼近柳州”“剖义精审似子厚”等奖掖之语,以此作为对学生国文作业的最高褒赞。仔细读来,史德华的《爱国血》与刘锺慧的《二郭》,皆与“杂传体”古文有一脉相承之处:小说的主体部分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其生平事迹,亦在为人物立传的同时寄寓作者的褒贬。然而,这两篇小说却都没有在细节方面过多着笔:《爱国血》大体相当在游记中嵌套一篇“申兴国传”,小说中本该浓墨重彩描绘的勇士驰骋疆场、捐躯国难的场景,却一笔带过;《二郭》在描述兄弟二人败家的经过时,也不过寥寥数语。这样的叙事笔法,显然与小说应有风致不相合。实际上,它们更近似于由“杂传”扩写而成的小说;反之,若视之为小说化的“杂传”,亦无不可。
在“杂传体”古文之外,作为小说另一源头的寓言,也在女学生的小说中有所立意。张誉扬的《梦感》记录了“予”所目睹的狮子吃人的噩梦,它接近于柳宗元《黔之驴》《谪龙说》一类的寓言散文。与此“国文”的小说相对照,《会报》上也载有一些“小说”的国文。例如,刘崚渤的《养花记》(第1期)写了一位少年劝勉族人击退强邻、重建园圃的故事。其中,花园、主人、园丁、族人、强邻等皆有喻意;倘稍加敷衍,即可成一篇与《梦感》相似的寓言体小说。而高珍的小说《华胥国》,模仿了唐传奇《枕中记》及《南柯太守传》,更加直接地体现了女学生对古文体小说自然而又自觉的转换和运用。
上文着重分析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7位作者小说的“女学生性”,指出其小说创作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至此,有必要抛出一个大胆的追问,既然《会报》上的小说女作者与“五四”新文学女作家只是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同一代女学生,具有观察“五四”之“前史”的功能;那么,假如冰心、庐隐等人在“五四”之前也写了小说,其作品大概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是否与《会报》上的作品相差无几?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冰心曾自述于1913年写过几篇没有结局的文言长篇小说,“一篇《女侦探》,一篇《自由花》,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27](P7)。 庐隐的首部小说是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隐娘小传》,记录了她初恋的经过[28](PP305-307)。 尽管她们最初的小说作品都未能保存,但可推知她们与《会报》上的女学生一样,小说同样使用文言语体,具有“写自己”的倾向。
幸运的是,苏雪林1920年发表于北京女高师《文艺会刊》第2期的小说《童养媳》存留了下来。据作者自述,这篇小说是其17岁时的作品[29](P114);从时间上推断,大约成于1914年。尽管苏雪林宣称这篇小说是修改后刊出的,但仔细揣摩,它依然与《会报》小说存在诸多一致性。首先,《童养媳》也以女学生第一人称叙事,且以听故事的方式结撰小说,主人公充当的仍是一个旁观者的记录角色,与《杏花村侯氏记》《爱国血》等如出一辙。其次,《童养媳》以古色古香的文言写出,同样是“韩柳体”的小说,令喜欢骈四俪六的六朝美文的冯沅君很不以为然[29](PP114-115)。 再者,小说的开篇也使用了“暮霭”“斜阳”“炊烟”“衰草”之类的意象描写景物,与《会报》小说程式化的开篇不谋而合。
然而,同是隶属于新文学阵营的陈衡哲,其早年的小说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无论是1917年的《一日》,还是1918年的《老夫妻》,不仅在语体上运用白话写作,布局谋篇也完全符合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Short Story)。这种生活横切面的写照,与民初文坛那些虽被目为“短篇小说”实则只是“笔记杂纂”或“不成长篇的小说”[30]区隔开来。而在留美之前,陈衡哲与普通女校学生一样嗜读林译小说,或为写不幸夫妻的《不如归》流泪,或在客栈中读《茶花女》而自得其乐[31](PP91-92)。 可以说,正是留美经历让陈衡哲获得了域外新体验,使她有机会、有能力将西方常识运用到“新”文学的生产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两篇早年作品,堪称近代中国女学生小说呈现新风貌的历史转捩点。
可以说,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文化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文学内部观察现代女作家如何“浮出”历史地表的维度。事实上,对于这些在民初接受新教育的女学生们来说,正是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为她们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与底色;然而最终触动她们文学写作发生变革的那个节点,则是与“西风”的相遇——在一种全新的思想与理念的指导之下,她们随时能够将传统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而生产出新型的文学形式。
六、结语
长期以来,“五四”一代女作家的“浮出”,一直被当作女性小说的研究起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历史事实。然而,经过细致的史料钩沉,可以判定清末民初才是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起点”;不仅如此,其“内核”还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图景。事实上,中国女性小说创作之兴起,是政治环境、出版市场、商业行为、报刊媒介、学堂教育、家庭出身等诸多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而且,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各种要素所占比例不同,也直接影响到女作者小说的内容和特质。这从本文精心设置的4个微缩景观中可窥见一斑——无论是陈翠娜的生活方式还是小说创作,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的闺秀传统;而刘韵琴则将小说作为启蒙工具,旗帜鲜明地为反袁斗争服务,她的作品和小说观念,无一不指向晚清的“小说界革命”;另一位女作者高剑华却与丈夫许啸天一起,在民初的小说市场上几经浮沉,作品中蕴含着十足的商业气息,与当时的通俗文坛相当合拍;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7位女学生,是中国历史上首批写作小说的女学生,由她们的教育背景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来解释“五四”新文学女作家的“浮出”最为恰切。可以说,从3位女作者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群,再到“五四”现代女作家,在女性小说史内部是3个即绵延承袭又具差异的历史环节。因此,笔者以为,无论是近代文学还是女性史的研究,都必须突破“清末民初”与“五四”这种时间轴上“取代”与“被取代”的线性解释逻辑,同时避免“转折/前史”说或“冲击”模式背后整齐划一的研究话语,重新认识“近代”自身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精彩纷呈。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3]天虚我生自传[N].申报,1940-05-19.
[4]栩园丛稿·翠楼吟草[M].家庭工业社香雪楼藏版,1927.
[5]陈小翠.半生之回顾[J].宇宙风,1938,(62).
[6]徐枕亚.序四[A].吴双热.孽冤镜[M].上海:民权出版部,1915.
[7]小翠初稿,天虚我生润文.粉垣埋恨记[J].小说丛报,1918,(7).
[8]郑振铎.文学论争集·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9]梁启超.告小说家(一)[J].中华小说界,1915,(1).
[10]十四龄女子陈翠娜.劫后花(三)[N].申报,1915-05-02.
[11]王钝根.本旬刊作者诸大名家小史[J].社会之花,1924,(5).
[12]栩园居士.苔岑录[J].文苑导游录,1917,(1).
[13]韵琴杂著·序[M].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
[14]韵琴杂著·诗词[M].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
[15]韵琴杂著·小说[M].上海:泰东图书局,1916.
[16]组织小学校[N].申报,1916-08-07.
[17]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8]中国近代小说大系(64)[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19]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0]高剑华女士.卖解女儿[J].眉语,1916,(14).
[21]曼殊.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5,(13).
[22]《月界旅行》辨言[A].美国培伦原著,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月界旅行[M].东京:翔鸾社,1903.
[23]高剑华.春去儿家[J].眉语,1915,(3).
[24]高剑华.绣鞋埋愁录[J].眉语,1915,(9).
[25]毕业生及现在学生一览表[J].直隶第一女师范校友会会报,1916,(1).
[26]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27]《冰心全集》自序[A].徐沉泗、叶忘忧编选.冰心选集[M].上海:万象书屋,1936.
[28]程俊英.回忆庐隐二三事[A].朱杰人、戴从喜编.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9]沈晖编.苏雪林文集(二)[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30]胡适.论短篇小说[J].新青年,1918,(5).
[31]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含章
Female Novelists'Multidimensional Writing 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A Qin⁃q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female novelists'works;multidimensional wri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Chen Cuina,Liu Yunqin,Gao Jianhua and seven other female students at the First Women's Normal School in Tianjin from four perspective of their experience at home,their education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their experience with mar⁃kets and schooling to reveal female novelists'multidimensional writing before modern female novelists were on stage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The paper suggests that chaos zones between modern female novelists and the“May Fourth”female novelists,and they occu⁃pied a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D442.7
A
1004-2563(2017)02-0056-10
马勤勤(198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晚清民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