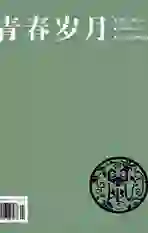从“图—底”关系理论解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2017-04-15肖静
肖静
【摘要】格式塔心理学成功的突破了传统心理学把对象分为若干部分的心理学理论,建立了完整的关于“形”的理论学说。格式塔心理学从视觉和知觉的统一关系出发,探讨了有关“形”的规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图-底”关系规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过各种“形”来展现尼采的精神世界,表达一个用理性和真理都无法穷尽的世界的真相。
【关键词】图-底;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的写作,大多是无系统的,格言体写作方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不例外,这本书主要提及查拉图斯特拉作为异教人,从山上下来,开始了自己的宣讲。尼采是作为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哲学著作。與传统哲学著作的抽象不同,这本书中尼采用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解读哲学问题。《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每一个小的篇章,在接受心理学的角度都可以构成独立的画面,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谓的“形”。
尼采的哲学思想“权力意志”是继承叔本华的思想,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性,每个人都受到意志的控制。欲望、私利、功利的用心操纵着我们无法摆脱。叔本华认为意志是生存和种族延续的意志,它是我们人生的推动力,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无穷的痛苦之中。“尼采的强力意志说到底是人敢于同痛苦灾难相对抗的生气勃勃的生命力、创造力。只要人在征服痛苦的过程之中发扬生命的强力,就会赢得人生最大的成果和欢乐”(颠覆叔本华悲观意志的尝试)这样的精神表现在他早期的著作《悲剧的诞生之中》同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表达了如此的思想倾向。在每一篇章的论述中尼采用他思维中最直观的形象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格式塔,很多学者都认为尼采是用生命写作的人,他不是在隐喻的方式,将哲思隐藏在形象的背后,赋予形象以意象和符号的意味,而是让视知觉呈现出来的东西以及淳朴和本真的方式出现。以解构《圣经》当中隐喻的作用,揭示神秘性的虚假和传统信仰大厦的倾颓。尼采反对表象背后的大的道理。在他的格言式写作中,都有着特殊的图式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上,是呼之欲出的直观的形象。
图式化的背景可以看作是由康德奠定的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传统,而形象是非理性、意志、欲望的化身。而这样的形象在尼采看来是符合人本性的生命力的彰显。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非理性的意志、欲望从理性的樊笼里呼之欲出,我们难以抵挡的是他对试图突破背景而彰显图像的力量。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语言中,有三种形象的变换,第一种是骆驼,他在沙漠中负重前行,代表了人类的理性阶段。沙漠,干涸,一望无际,却了无生机。是广阔无边的背景,骆驼承担着责任与义务,承担着人类理性的传统,承载着上帝生存的最后一丝希望。在不堪重负下,骆驼变身了,变成了狮子,它向天长啸,奔跑怒吼,这是生命力的释放。忍辱负重的骆驼和肆意狂放的狮子构成了同一背景之下相互矛盾冲突的画面。“许多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便是经常利用这种手法创造出谜语,将两种互相排斥的东西展现在同一背景之下,阿恩海姆认为”他们设计这样一种构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观看着对现实所具有的那种盲目信任的感觉完全解体。《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两个形象的转换很好的解构了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理性,解构了是与非、错与对、内敛与狂妄。而这些判断恰恰是人所构建出的观念的之网对人生命力的束缚。尼采用图式的方式突破了它,打破了传统的理论系统。这种方式能使我们感受到某事物的物质存在,然后在你烧一恍惚的情况之下,它又变成了形状完完全全不同的另一件事物,而且同样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物。
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人类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建构了非常完备的知识体系的同时。很多理论学者开始思考。18世纪以来德国古典主义“理性”传统所带来的危机。甚至有些理论家认为传统的理性是混乱的理性。科学、技术、理性、体系带给我们很多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之间的互相戕伐。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尤其是晚年的学说,得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理由:是因为科学的技术的高度发达,使现代生活极为便利。但技术导致了人类生存之根的缺失。就像庄子在《养生主》中提到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我们可以看到让文惠君叹为观止的并不是,刀的锋利。而是庖丁了然于胸的解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对工具用途的突破达到的。所以如何才能打破工具对人的束缚,个体的经验非常重要,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他提倡搁置了历史和偏见的纯粹的意识。意识以及个体经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被认为是解救世界的途径。
在这一点上尼采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对于尼采,尤其是他的《权力意志》很多人认为是纳粹思想的根源。这其实是对尼采的一种误读。他将自己的惶惑、困顿、本能力量赋予了众多的形象,表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中》。这是一种宣告或者是回归,回归到人类最本质的东西,从人类的本源力量探寻个体生命、人类群体存在的意义。尼采所要表达的语言和图像是所寄托意义的两翼。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科学的,而言语作为个人言说方式,是经验的。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恰恰是通过个人言说的方式,使背景虚化,图像显现。这恰恰也是萨特在寻找存在时所使用的方法,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论述到“虚无只有在存在的基质中才可能虚无化;如果一些虚无能被给出,它就既不存在之前也不在它之后,按照一般说法,也不在存在之外,而是像蛔虫一样在存在的内部,在它的核心中。”只有背景被虚无化,存在的意义才能从虚无中显示出来。(存在与虚无)哲学或者文学的论说是可以用图像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的,这是古而有之的命题。“文学图像论并不是在概念上玩花样,也不是在可以追逐什么学术时尚,而是一个背靠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学,它在传统文学意象论和文学形象论之外确定了图像这一新的参照物,以便在文学语言和文学图像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我,发现新我。”(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
在第二章的开篇《持镜子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如此鲜明的形象被衬托了出来。查拉图斯特拉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他洞穴的寂寞里避开人群……为什么我在梦中惊醒?不是有一个持一面镜子的孩子朝我走来吗……当我朝镜子看是,我尖叫了起来,我的心,大为震惊:因为在镜子里看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魔鬼的怪脸和冷笑。在这段描述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极为突出,而且和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背景是纯真的拿着镜子的孩童,而查拉图斯特拉从镜子当中看到的我沉香出了魔鬼的怪脸和冷笑。在魔鬼的怪脸与冷漠之中,孩子的天真与镜子的光洁被虚无化了,显现出来的是阴森可怖的形象。这令查拉图斯特拉也感到极大的震惊,但他迅速意识到了,这是我生命中的敌人在与我的较量。他说道“我的敌人变得强大。”在这样的图底关系的对比之中,查拉图斯特拉确切的认识到,我不是坚定的反传统的布道者,在我的身上也有着社会历史经验的存在。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冲突,但我的目标是明确的,他要下山去,用自己的宣讲,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尽管“我”是孤独的精神个体,查拉图斯特拉正是在这种恐惧、厌烦、忧郁、绝望的状态之中,找到了信仰之于我存在的意义。要使信徒相信,首先必须在内心之中战胜自己,确立信仰的存在。这正是个图像化的片段揭示出来的自我认识的意义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具有明显的文学图像性,这也拉近了尼采与文学图像时代的距离。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具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