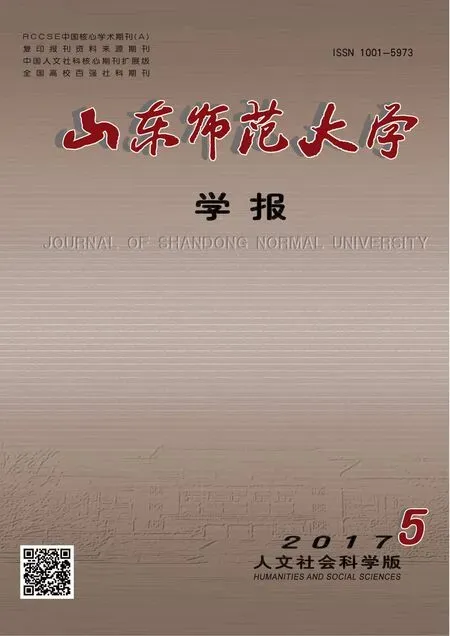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2017-04-14俞武松
俞武松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
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俞武松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
在诸多对于《水浒传》文本的阐释中,由于受到其创作素材丰富、版本情况复杂和衍生文本多样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情况值得关注,其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用素材阐释文本;用异质文化阐释文本;用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通过对于《水浒传》忠义观的考察可以发现,文本强制阐释文本不但导致忠义观阐释与《水浒传》文本的偏离,还导致人物形象及性格的变异以及对于《水浒传》结构、内容的不同认识和选择。或者可以说,讨论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本的强制阐释,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回到文本;而讨论文本强制阐释文本,则希望解决回到什么文本的问题。
《水浒传》;创作素材;异质文化;衍生文本;强制阐释
当前的文学研究除了存在理论上的强制阐释*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外,在中国传统文学诸如《水浒传》等创作历程复杂、创作素材丰富、流传版本多样的文本中,还存在着以文本阐释文本的强制阐释,具体表现为:用素材阐释文本、用异质文化阐释文本、用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等。以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在文本阐释时突破诗史互证的边界,采取诗史互等的方式,将创作的历史素材与文本进行直接比对,或者将作为创作素材的其他文学文本、民间传说等作为阐释文本的依据;二是利用异质文化对文本进行解读乃至批判,得出具备一定理论深度、具有相当视觉冲击力的结论,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与原文本的关联;三是利用“后传”、“续”以及改编作品等衍生文本,对原文本进行解读,将不同文本中的“同一”人物混杂在一起,从而形成接受层面的混杂状态。
纵观《水浒传》的研究,对于忠义观的解读,关系到对于《水浒传》人物的评价和主旨的理解,也关系到对于《水浒传》结构的判断,其中突出地体现了以文本强制阐释文本的问题。
一、素材阐释文本与《水浒传》忠义观的内涵
据考证,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的时间较为接近,史籍记载中以方腊起义较为详细,故事传说中则以宋江起义较为盛行。事实上,“宋江起义作为农民起义并不典型,与其说它是一支革命的农民队伍,毋宁说它是一支流动的侠盗武装”*张锦池:《〈水浒传〉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这就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历史上的“梁山好汉”并没有小说《水浒传》中的强大力量,也未必做出了像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事业。而在宋元的民间传说或者戏曲中,《水浒传》中的人物数量不尽相同、人物性格也差别较大。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后来的民间传说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小说《水浒传》创作的素材。因此,从历史考证和其他文学文本出发,研究《水浒传》人物形象、性格和忠义观的形成,或者采用对比方式凸显《水浒传》人物性格,是中国诗史互证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前者如史学家邓广铭等就宋江是否为投降派、宋江起义开始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探讨*邓广铭、李培浩:《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关于宋江起义开始年代问题的再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刘知渐对历史上的宋江和《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进行对比*刘知渐:《从宋江的历史说到〈水浒〉对宋江历史的夸张》,《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冒志祥从官文书的角度研究《水浒传》中宋江征辽的故事*冒志祥:《从官文书看〈水浒传〉》的宋江征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等;后者如徐海宁从《大宋宣和遗事》、元杂剧和小说《水浒传》来考察水浒故事的主题演变*徐海宁:《古代水浒故事的主题演变探析》,《东岳论丛》1998年第4期。,王晓霞等从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出发研究两个李逵的形象*王晓霞、张振谦:《两种“水浒”,两个李逵——从元杂剧“水浒戏”到明清小说〈水浒传〉》,《四川戏剧》2008年第6期。,等等。这方面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极大推进了《水浒传》的研究工作。
其中,对于《水浒传》主题研究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如果从1950年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发表在《人民戏剧》第一卷第五期算起,到2014年还有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根据知网搜索结果),这60多年来的研究已经基本明确地指出了农民起义说的根源、时代意义和自身缺陷。综合来看,梁山起义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推翻大宋皇帝夺取政权,更没有上升到创造一种新社会制度的高度。因为“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思想所追求的目标起点是解决饥饿问题。农民起义取得一定进展后,代表农民要求的平均主义思想被提出来,北宋以后尤其如此。……农民起义发展后期,农民领袖无不把最后方向指向王权主义的政权”*许并生、宋大琦:《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东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而梁山起义除了明显具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目标外,完全不具备后面的愿景(更为重要的是,梁山起义还有着以忠摄义的特点,下文详述)。这与方腊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许这就是大宋皇帝愿意接受梁山好汉们“报效朝廷”,而对方腊起义却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学者认为,“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视为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念,完全是《水浒》影响的结果。而当我们的文学史家在研究《水浒》的时候,又反过来把那种由《水浒》造成的历史模式套到了《水浒》的头上。于是乎,历史上的宋江是农民,《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自然不言而喻是农民起义了”*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诗史互证突破边界走向诗史互等,而终于用史来阐释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在正史中的记载较少,比如《宋会要辑稿》中没有关于宋江起义的直接记载,而《东都事略·侯蒙传》和《宋史·张叔夜传》中仅有零星记载。从这些为数不多的记载来看,基本可以判定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规模不大,甚至有可能没有占据梁山泊为“根据地”。而随着水浒故事的广为流传,尤其是小说《水浒传》的巨大影响,不但导致民间对水浒故事的认知发生了“正史化”的倾向——认为《水浒传》所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甚至将之等同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更导致了部分史学研究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将《水浒传》故事写进史学著作中。*如部分“中国通史”类著作就认为,《水浒传》中所述之人物和故事“基本上应有所依据”,也将梁山泊作为宋江起义的根据地,并将之与方腊起义一起列为北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由此,导致了《水浒传》创作的素材最终成为阐释《水浒传》文本的依据,诗史互证的传统也演变为诗史互等的强制阐释。对此,需要认识到“文、史毕竟有别。题材和主题也毕竟不能混同。《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不相同的两码事。它的性质如何,只有从对《水浒》的具体剖析中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新议》,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5页。
从素材的数量及其与忠义观的关系来看,《水浒传》作者更多地是从民间水浒故事以及相关的作品出发,完成《水浒传》文本的创作。*宋子俊、范建刚:《〈水浒全传〉主题辨析——与传统的农民起义说商榷》,《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3年。从《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赞》《醉翁谈录》(其中有《石头孙立》《花和尚》和《武行者》等话本名录),到元人杂剧水浒戏,再到小说《水浒传》,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但包含人物性格、形象的变化,也包括故事情节和主题的变化。但是,有学者却认为,“《宣和遗事》和《癸辛杂识》所记已为大部分主要梁山好汉的性格定好了基调。元杂剧有关梁山英雄的剧本留传下来的不多,但也不外乎叱奸骂谗,除暴安良,行侠仗义,逞其血气之勇”*郭振勤:《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汕头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但从这段话来看,《宣和遗事》等已经为大部分主要梁山好汉奠定了性格的基调,后来的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无非更为生动、形象。换句话说,用《宣和遗事》和水浒戏中的人物性格来理解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性格也是基本可行的。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多少带有可以用《宣和遗事》和水浒戏来“强制阐释”《水浒传》文本的意味。在研究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的关系时,有学者认为,“在元人艺术舞台上,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的正义性被大大强化,他们是扶弱锄强、替天行道的社会正义的化身,是敢于反抗、誓死复仇的……敌人害怕这样的英豪,衰弱的民族需要这样的英豪。所以,改造水浒故事,歌颂梁山英雄,是宋元人民的时代心声”。而到了《水浒传》中,不但“同宋元时期反抗……侵略的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发泄对……侵凌压迫的强烈不满”,以至于认为《水浒》是“一部民族心灵史”*王前程:《从“盗匪”到“救国英雄”——水浒故事的嬗变与〈水浒〉主题的变化》,武汉: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很明显,这种对于《水浒》主题的理解受到了《争报恩》《李逵负荆》《还牢末》《双献功》等文本对于梁山好汉的形象塑造和精神寄托的影响。*《争报恩》中说道“替天行道宋公明”,《李逵负荆》中说道“替天行道救民生”,《还牢末》中说道“要替天行道公平”,《双献功》中说道“宋公明替天行道”,等等。这种替天行道的行为与梁山好汉有胆有识、勇武过人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成为人们对于现实不公的反抗和对于民族英豪的呼唤。毫无疑问,这里以元代水浒故事的文本为依据,来“强制阐释”小说《水浒传》,由此得出的结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非小说《水浒传》的核心。
从《水浒传》的内容来看,忠义观无疑是其主题,对于忠义观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对于《水浒传》主题的不同解读。最早出场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人,以及史进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柴进,表现的都是处友之义;当林冲被逼上梁山寻找“投名状”遇到杨志的时候,事君之忠才开始以人生理想的面貌出现。*本文借用袁无涯对忠义的理解(“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参见《忠义水浒全书》,明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刻本。之后,处友之义从形式上占据着故事的主要篇幅。但是,处友之义并没有离开事君之忠而发展,它在展开的过程中逐渐被事君之忠笼罩。虽然有的英雄好汉对事君之忠产生了疑问甚至抵制,但是他们又因为处友之义而屈从于事君之忠,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最终的悲剧。
《水浒传》中“处友”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朋友之间往往从个人情感出发,将朋友之间的义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之中。具体来说,可以从处友之义的三种不同形式来进行分析。
一是基于相互认可或欣赏的义气相投。梁山好汉们初次相遇的时候,经常在互通姓名后为对方声名所吸引,或者在冲突后为对方的本领所折服。由此,双方互相认可或欣赏对方的本领、声名,并在此基础上显得义气相投。在这种关系中,很多人会发展成一种稳定、长久的生死之交。比如鲁智深和林冲虽属偶遇,但二人互为对方的本领所折服,并成为生死之交,以至于鲁智深在野猪林仗义救林冲,最后被迫离开大相国寺,落草二龙山;武松和张青夫妇的相识源于一场冲突,之后大家为对方的本领和声名所折服、吸引,最后结拜为兄弟,甚至在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张青夫妇还帮助武松改扮成头陀避难。不过,并非所有一开始显得义气相投的朋友都会成为生死之交。在接触的过程中,如果一方或双方觉得对方并非是自己真正认可或欣赏的人,这种朋友关系便显得极不稳定且很容易结束。比如鲁智深在痛打了要强娶刘太公女儿的周通之后遇到李忠,大家欢欢喜喜地见面叙旧。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鲁智深发现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悭吝,只要下山”(第五回)*从目前流传的情况来看,《水浒传》的版本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繁本即文繁事简本,主要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简本即文简事繁本,主要有一百十五回本、一百零二回本、一百十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水浒传》为一百回本,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水浒全传》为一百二十回本。本文所引内容均出自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后文只注明回次。,以至于最后卷了桌上的金银酒器,离开了桃花山。
二是基于义气相投的机遇和礼遇。在义气相投的基础上,有时候会遇到能够展现本领或者实现人生理想的机遇,知己和伯乐在这里集于一身。得遇知己,一身的本领有人欣赏、一世的理想有人认可;有了机遇,一身的本领能够展现、一世的理想可能实现。这种关系往往最为稳固和长久,可以说,梁山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在这种关系中,梁山好汉们对此付出的一切都是肯定、积极和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把对知己的认可和欣赏、对伯乐的感激与自我展现、自我理想(价值)的实现融于一体。以至于那些沉沦社会底层的好汉们,几乎将此看成了唯一能够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途径。比如靠打鱼为生的阮氏三雄在吴用的动员下,为晁盖的声名所吸引,并认为晁盖和吴用这样的知己为他们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机遇,因而不顾身家性命地参与劫取生辰纲的行动。在智败搜捕的官军之后,和晁盖、吴用一起走上梁山。
在这样的机遇中,双方会以礼相见、以礼相待,尤其是提供机遇的一方,更会主动地礼遇对方,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让对方为自己所用。换句话说,他们既为别人提供了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也为自己提供了借助他人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机遇。并且随着宋江在梁山领导权的确立,这种被礼遇的机遇逐渐转向报效君王的目的,即将处友之义归之于事君之忠,好汉们的理想和行动最终被“束缚”到一个方向。宋江在数次战斗中收服被捉的武将,大都是从义气相投入手,先取得他们对于处友之义的认可,再向他们表明忠君为国的志向和可能性,从而使之觉得能够获得展现本领和报效君王的机会,并由此说服这些武将加入自己的行列。
三是非于义气相投基础上的机遇。梁山好汉们还遇到一些并非义气相投、也无多少礼遇的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提供机遇的人多是在位的权贵或官吏。尽管如此,好汉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人看成是“知己”,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把握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获得暂时的成功,赢得一时的风光;不过,他们的最终结局都极为类似:或者由于主动决裂,或者由于被逼无奈而分道扬镳。武松在景阳冈打虎之后受到知县的赏识,作了县里的都头,后来又帮助知县把一担金银送到东京。但是,武松在查出武大被毒杀而举报无门的时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这就让武松与这种“知己”主动决裂了。杨志则不一样,他花了许多金银却仍被高太尉弃之不用,流落东京街头卖刀,出于义愤杀了牛二之后被发配大名府,得到了梁中书的赏识,通过校场比武被提升为提辖。原本以为可以一心报效“知己”、实现个人理想的杨志,在生辰纲被劫之后一声叹息,怅然离开。
综合《水浒传》文本来看,处友之义经历了如下的生发过程:
首先是怀才未遇的悲懑。当好汉们怀才未遇、英雄暂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对自己一身本领无处施展、个人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叹,也有对空有一身本领却无人赏识的愤懑。吴用在说服阮氏三雄参加智取生辰纲一事的时候,阮氏三雄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第十五回)这个时候,好汉们的生活状况比较糟糕,或生活困苦、衣食存忧,或孤身在外、辗转飘零,或被逼无奈、杀人放火。比如阮氏三雄生活的困顿,武松在江湖上的漂泊,林冲在草料场快意恩仇,等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放弃自己的一身本领和人生理想,他们经常在发泄式的怨叹中等待着“伯乐”的出现,等待着展现自己本领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遇。可以说,他们的悲懑中激荡着对于未来的期望。
其次是得遇知己的欣喜。当本领、声名或理想被人认可、欣赏的时候,好汉们就遇到了义气相投的知己,他们会表现得非常兴奋、激动;尤其当被礼遇后又面临着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时,他们更会奋不顾身地去为之行动。当宋江和李逵初见的时候,李逵因宋江的声名而倒身下拜,在酒席桌上他更是感叹:“真个好个宋哥哥,人说不差了!便知我兄弟的性格!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第三十八回)在这种兴奋、激动中,李逵听说宋江想要新鲜的鱼做汤吃的时候,便自告奋勇地去讨两尾活鱼,并因自己不懂规矩而和张顺大打出手。这种欣喜既是对被认可、被欣赏的表现,也是对遇到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并受到礼遇——对自己能够有机会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赞颂。
最后是以身报答的行动。面对知己和机遇时,好汉们会以自己的行动、甚至是生命来报答和把握。他们会因为义气相投,而为对方设身处地地处理问题,比如石秀之于杨雄的结义之情而甘愿操刀作屠夫,以至于在被杨雄误解的情况下智杀裴如海,最后与杨雄、时迁一起投奔梁山。他们会因为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而积极主动、甚至不惜生命地去报答知己、实现自我。比如李逵之于宋江这位知己,不但在历次危险中冲锋陷阵甘当马前卒,甚至在被宋江以“忠义”之名下毒之后,也只是无奈地顺从。至于武松之于阳谷知县、杨志之于梁中书、朱仝之于沧州知府等,也无一不是以身报答的行动,只是这样的“知己”和机遇没有义气相投的基础,而更像是居高临下的施予、甚至是嗟来之食的施舍罢了。
从对处友之义的态度和行动来看,好汉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正如武松在醉打蒋门神之后说的一番话:“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第三十回)正是这种死也不怕的豪情,让英雄们在报答知己和实现理想的行动中不计得失,以至于为常人所不敢为,为常人所不能为。当这种豪情融入处友之义中,就使得报答知己和实现理想的行动闪耀着男性雄壮的气息;当这种豪情在现实中遭遇磨难,甚或引致在报答知己和实现理想的行动中身残命丧的时候,就形成了具有内在张力的悲壮之情。
相比较处友之义而言,《水浒传》中将事君之忠视为具有终极意义的目标。尽管有的梁山好汉对此提出了疑问,但是,这些人最终在事君之忠的笼罩下完成了处友之义的行动。
一方面,事君之忠成为人生理想的落点。在《水浒传》诸人中,第一次明确以事君之忠作为人生理想出现的是三代将门之后杨志,“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第十二回)。尽管他后来与鲁智深、武松一起在二龙山占山为王,但他终究走进梁山并接受朝廷招安,在死后被封为“忠武郎”,子孙可赴京“照名承袭官爵”(第九十九回),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不过,并不是《水浒传》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杨志这样始终明确地把事君之忠作为人生理想。像武松、鲁智深等人,在经历了报答知己和实现人生理想的行动遭到挫败后,对事君之忠产生了不满和怀疑,可惜他们没有提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当一百零八人在忠义堂重新排定座次,乐和唱到宋江所作《满江红》中“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鲁智深也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第七十一回)不过,他们最终在处友之义下妥协了。
这里的妥协不能看成是对事君之忠的主动接受,而是他们在宋江以处友之义的名义实施事君之忠的行为下,对于处友之义的坚守和对于事君之忠的无奈。需要明确的是,对事君之忠的质疑主要是对朝廷中蒙蔽圣聪的奸邪们的不满,这些奸邪们阻碍了事君之忠的理想实现。对事君之忠的无奈并非是与之彻底决裂,而是对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面对蒙蔽圣聪的奸邪们的忧虑,并由此导致了对于实现理想的悲观。但是,从《水浒传》的故事来看,这种人生理想最终在忧虑与悲观中付诸行动。
可以说,事君之忠从一开始就作为人生理想的面貌出现,一些人始终积极主动地付诸行动;一些人在对处友之义的坚守下,带着些许无奈走到最后。或许,只有当“酷吏赃官都杀尽”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忠心报答赵官家”(第十九回)。
另一方面,事君之忠也是现实秩序的约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现实统治秩序的约束,一是以现实统治秩序的名义进行的约束。前者是对于以君权为中心的权力、法律规范的遵从,后者是蒙蔽圣聪的奸邪们借以控制和打击的手段。
从《水浒传》故事开始,现实统治秩序的约束就一直在发挥作用。尽管梁山好汉们聚义山林、打家劫舍甚或攻城克地,但他们基本上是为了夺取不义之财、为山寨谋取钱粮、救人性命或者是“替天行道”教训贪官污吏(不能排除一些人滥杀无辜)——智取生辰纲是为了夺取十万贯不义之财,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目今山寨钱粮缺少”(第六十九回),攻打北京城是为了救卢俊义和石秀的性命,而攻打高唐州的原因除了救柴进之外,还因为新任知府高廉“倚仗他哥哥(高俅),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其妻舅殷天锡“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第五十二回)。
但是,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梁山的好汉们并没有想拿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制度)来取代已有的社会秩序(制度),而是对他们认为不属于忠君爱国贤良的所作所为进行替天行道式的处理。究其根本,还是为了报效朝廷(君权),在“赵官家”的清平世界中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流芳百世。因此,智取生辰纲之后,挑担子的军士们没有被杀;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取得钱粮、收服猛将之后,“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第六十九回),“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第七十回);攻打了北京城和高唐州之后,也是“教休杀害良民”、“出榜安民,秋毫无犯”(第六十六回、五十四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蔽圣聪的奸邪们借以君权为中心的权力、法律规范实施的控制和打击行为,其目的在于削弱甚至毁灭梁山好汉(包括朝廷中其他忠君且阻碍他们之人)的势力,以达到其混淆视听、把持朝政、独揽大权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披上了君权的外衣——以圣旨或者其他行政命令的形式来下达,所以这种行为就带有相当强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强制性。如果直接抵制或者反抗这种行为,就落下了抗旨不忠的把柄;如果想要保全自身而又不至于被害,就要巧妙地应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及时应对的例子:面对克扣皇帝赏赐和肆意凌辱梁山好汉的局面,壮士一怒杀厢官。为了避免被高太尉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宋江和吴用商议后杀了杀厢官的军汉,然后申复省院并告知宿太尉,这才避免了中书省院的谗害。
正是因为有了事君之忠的约束和对事君之忠的遵从,替天行道的口号和行动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且被大众和朝廷接受,最终实现“封妻荫子”的人生理想。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与现实统治秩序的冲突,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对于好汉个人而言,宋江和梁山是其知己,为其提供了机遇;对于梁山这个群体而言,君王或者君王权力的代表(宿太尉等)是其知己,为其提供了机遇。所以,梁山好汉们最后走上了招安的道路,并为君王四处征讨,立下赫赫战功,而大部分好汉都在这个过程中战死沙场或者伤病而亡。
二、异质文化阐释文本与《水浒传》忠义观的文化溯源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水浒传》是一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品,故对忠义观或者其他思想进行文化溯源,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使用所谓现代眼光来看,也应就其时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而不应出现用后30年否认前30年的情况。但是,在当前流行的中西比较研究中,却出现了用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批判”《水浒传》的情况,从而使其对《水浒传》的阐释带有相当的强制性。
《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是“七星聚义”所做的一件夺取不义之财的大事,较为突出地展现了处友之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整部作品中真正聚义的开始。有人认为,“智取生辰纲”背后的“为富不仁”和“劫富济贫”等理由是值得质疑的,并由此对“劫富济贫”背后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分析。其分析以基督教为依据,认为“基督教把‘嫉妒’视为七大原罪之一,教导信徒努力排斥这种心中的恶魔。但是,中国人绝对平均主义的背后则是病态性的极端嫉妒心理。《水浒传》时代就有这种心理……‘智取生辰纲’的行为所以会让中国人(包括现代中国人)感到痛快,就是它迎合了中国自古皆然的嫉妒心理……中国人为什么非常欣赏‘智取生辰纲’,这就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充满嫉妒、充满绝对平均幻想的心理”*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35—36页。。这里提出的问题有:“劫富济贫”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背后是对于“富”的仇视和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有比较严重的嫉妒心理,“智取生辰纲”是“劫富济贫”的行为,所以也是充满对“富”的仇视和嫉妒的心理,人们对于“智取生辰纲”的欣赏也是由于“中国人的心理充满嫉妒、充满绝对平均幻想的心理”,究其原因则在于“中国还没有完成以新教伦理取代旧教伦理那种根本性的价值观的转变”。*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37页。
暂且不论“中国人的心理是充满嫉妒、充满绝对平均幻想的心理”是如何得出的,单就其对于“智取生辰纲”的理解而言,无疑存在着知识性问题和用异质文化强制阐释《水浒传》文本的倾向。首先,《水浒传》中明确说过“智取生辰纲”的目的:刘唐在和晁盖相认后说到,“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倘蒙哥哥不弃时,献此一套富贵”(第十四回);吴用劝说三阮兄弟入伙时明确说到,“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公孙胜见到晁盖时明确表示,“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第十五回)。可见,“智取生辰纲”是为了取不义之财、图一世快活。从这件事情的结果来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白胜也将一包金银埋到床下地里(第十八回),也没有接济什么“贫”。不知从这些文本中如何得出“劫富济贫”的结论?再有,对于不义之财的获得,在《水浒传》中也并非梁山好汉们的“特权”,因为“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第十四回)。还需注意的是,晁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并且当他准备救刘唐的时候还送了十两银子给雷横(第十四回),不知他如何“仇富”?作为同乡的教书先生吴用、道士公孙胜、石碣村的三阮兄弟以及刘唐、白胜,或者与晁盖交好,或者仰慕其名而欲结交,也看不出如何“仇富”。况且,《水浒传》中的柴进既富且“贵”,卢俊义、李应等人富甲一方,即使是鲁智深、武松在落草二龙山前也看不出因为贫穷而“仇富”,而林冲、徐宁、呼延灼、宋江等军官或者官吏更看不出什么“仇富”心理。
基于文本事实,可见其立论已无基础。至于其认为基督教教导信徒排斥嫉妒,以及开出的所谓“新教伦理”的药方,无非是用基督教思想和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教精神,来进行的强制批判。从逻辑上说,起点都错了或者根本不存在,如何保证结论的正确呢?从文本上说,《水浒传》中既未涉及基督教,也未涉及宗教改革,更未涉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即使描绘了资本主义萌芽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新教伦理”如何才能发挥作用呢?换句话说,韦伯所论证的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作用*[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在《水浒传》文本中根本无从谈起,即使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又从何而论呢?这种以异质文化阐释的结果,不但形成了对于《水浒传》文本的强制阐释,同时遮蔽了文本和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
事实上,处友之义和事君之忠的观念并非是梁山好汉的独创,也不是作者的灵感迸发。它们在先秦两汉的儒家思想中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尤其到了两汉以后,事君之忠更明确了其主导地位。
对于处友之义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论语》。《子罕》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按照杨伯峻的理解,孔子在这里的意思是等待识货的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不妨将此理解成是在等待一个能够认可和欣赏自己的人,在等待一个能够展现本领、实现理想的机遇。对于孔子而言,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在诸侯国中寻找一个能识货的人、一个能实现理想的机遇。这在《论语·阳货》中有着直接的例证,公山弗扰在费邑图谋造反,请孔子去他那里,而孔子真的准备前往。当子路不高兴地发问时,孔子作了自己的解释,并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实现的理想也明白地表述出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对于十分推崇周礼的孔子而言,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礼的秩序,所以他对于“八佾舞于庭”的季氏非常愤怒,在见了名声不好的南子之后为避免误会而指天发誓。由此不难推断,孔子对于与识货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突破礼的秩序,换句话说,他也会用礼来衡量和评判这种关系。这一点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有着更为明确的理解和表述,“士之待礼,犹玉之待贾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这里将士比作玉,明确将礼与识货的人(贾)并举。事实上,当季桓子收了很多齐国送来的歌姬舞女而三天没有过问政事,孔子就离开了。朱熹赞同这是因为“简贤弃礼,不足与有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页。的原因导致的。换句话说,当孔子意识到自己不再被礼遇且不再拥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可能,就选择了主动离开,结束这种关系。
在“我待贾者”这个问题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迁似乎比孔子说得更明白,他在《史记》中更是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思想——士为知己者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的“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广为人知,这两句话在《战国策·赵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豫让的故事中均有出现。豫让为了报答对其“甚尊宠”的智伯,不惜毁容毁声潜伏为奴,数次刺杀赵襄子来为智伯报仇,后“伏剑自杀”。这是受到知己的礼遇而不惜一切报答知己的行为。这种报答知己的行为受到知己对自己的认可程度和礼遇程度的直接影响,“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聂政、荆轲也是如此,《水浒传》中好汉们报答知己的情况亦与此同。
对于司马迁而言,他笔下的诸人物“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司马迁在经历继承父志编修史书到遭受李陵之祸、身陷囹圄的惨变后,其心理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正如《太史公自序》中说的那样:“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因此,他后来撰写《史记》“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在司马迁看来,导致这种抑郁和不平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在李陵之祸中,“明主不深晓”,“拳拳之忠,终不为列”(《报任安书》),自己的一片忠心没有得到皇帝的理解和认可,反而受刑遭辱,隐忍苟活。这就让司马迁再难以像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一样,去不顾一切地践行“士为知己者用”的人生信条。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人,其《史记》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更是“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不但“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9-220页。对于《水浒传》而言,其作者“受李贽、金圣叹等在野文人赏识,多有共鸣,当属同类,应该是一个极富才情却得不到任用,不满现实又无处呼告,很有思想却不能不缄口,生活于元明之际或更晚的民间文化人。他的倾吐欲望与‘水浒故事’产生了契合,于是加工撰作出洋洋一部《水浒》”*王鸿卿:《〈水浒〉主题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至于事君之忠,也可以在孔孟那里找到相关论述。孔子和孟子“肯定的‘父慈子孝’、‘事亲从兄’,显然就是强调一个人应该在与其他某些人(即那些与自己保持着血缘关联的人)的特殊性关系中履行血缘亲情的原则规范,从而实现自己的血亲团体性存在。当然,在人的存在中,除了这种父母子女(血缘)的团体性因素外,还包含着其他建立在特殊性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团体性因素,诸如丈夫妻子(姻缘)、朋友熟人(友缘)、同乡邻人(地缘)、领导下属(治缘)、同事同行(业缘)、师生同窗(学缘)等种种团体性的因素”*刘清平:《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越敦华:《哲学门》第1卷(2000年)第1册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由此可见,事亲从兄指向的是血缘或类血缘的团体性存在,并且这种团体性存在被推广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
在父权主导和嫡长子继承的环境中,事亲从兄无疑意味着以血亲团体性存在的人们对于这个团体中男性领导权力(等级)及其继承者的遵从。当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时候,重点在于强调礼的重要性,而非像汉代那样突出君王的绝对权力和地位。孔子对此说得很明白:“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夫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尽管孔子也谈到了事君,但却并非突出其绝对主导的地位。孟子虽然更加明确地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并列,但他主要也是为了强调血亲的重要地位。
在孔子和孟子那里,事亲从兄主要着眼于实现血亲团体性存在。不过,当大一统的汉代将这种血亲团体性存在与君权、神权结合之后,所产生的忠君理念则让后人在忠孝之间的关系中“理所应当”地将天平偏向忠。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背后是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是各种思想的融合。“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讲的仁义等等)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完成了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36—137页。事实上,构建这种思想体系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时代政治社会的要求,为了维护君王统治,并且为这种统治进行合理化和正当性的辩护。因此,忠君思想在树立绝对君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确立了重要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孔孟主张的血亲团体性在相当程度上被泛化和强化了,事亲从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纲五常’更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忠’与‘孝’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了不可违背的伦理和政治法则”*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通览》,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第126页。。正是这样的思想才得到了君王统治的认可和发展,而那些提出和发挥这些思想的人更容易得到赏识和重用。与之相对的是,孔孟在当时的社会中并没有居于高位、掌握重权,这便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当时君王统治想要的东西,也难怪孔子说出“我待贾者”,甚至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了。
可以说,在血亲团体性存在中,事君之忠以“三纲五常”的形式统摄着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由此出发,《水浒传》中事君之忠与处友之义的关系及其文化渊源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衍生文本阐释原文本与《水浒传》忠义观的评价
前文所述对于“智取生辰纲”的评价,已经涉及对于《水浒传》忠义观的评价。无论喜爱还是憎恶,都不应成为评价《水浒传》的先决条件,甚至陷入“我喜欢就是好,你不能说不好;我不喜欢就是不好,你不能说好”的非学术状态。即使做不到绝对意义上不受情绪影响,至少也应该以文本为依据来进行评价,尽量减少个人情绪的左右。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文评的形式具有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产生了许多个性化的批评。对于《水浒传》而言,金圣叹的点评和对《水浒传》文本的处理可谓脍炙人口,但这不等于他的点评和处理就是千古不易之定则。虽然今天有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以百二十回本即“袁本”《忠义水浒全书》为底本),但从对于忠义观的评价来看,这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存在着以“腰斩”后的文本“强制阐释”原文本的倾向。
据研究,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前,繁本和简本系统的《水浒传》均为通行本,其特点都是以“忠义”为中心,在梁山大聚义后接受朝廷招安,随后奉旨平辽并讨伐不替天行道的其他强盗,虽功成遇害而仍执“忠义”之心于泉下。但在金圣叹宣称得到“贯华堂古本”后,“竟然成为此后近三百年中《水浒传》的定本,以致世人不知《水浒传》还有其他的‘繁本’、‘简本’”。*张锦池:《〈水浒传〉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面对如此情况,学界已有不同看法,但很多观点是从农民起义的角度来进行论证的。如张国光发展了胡适的观点(金本把《忠义水浒传》变成了“纯粹草泽英雄的《水浒传》”),认为宣扬“忠义”的《水浒传》是投降主义的,而金本《水浒》则是鼓吹农民起义的。*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濮阳:中州书画社,1981年。罗尔纲虽然不赞同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说法而认为施耐庵的《水浒》原本就是七十回,但是他与张国光对于金本《水浒》的认识有着相近之处,同样认为金本《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毋庸置疑,金本《水浒传》的故事更加集中,人物个性所表现的反抗性也比较突出。但是,从忠义观的角度来看则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
从《水浒传》的文本来看,对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在前七十回已经基本完成。梁山大聚义之后的征辽和讨伐,更多地偏向于在处友之义的约束下,践行事君之忠的“夙愿”,虽然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反抗或者逃离(公孙胜奉师命离开是个特例)。或者可以说,梁山大聚义之后的事君之忠对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存在着一定的约束和削弱。金圣叹对《水浒传》人物的描写大加赞赏,其中的主要人物,诸如武松、鲁智深、林冲、李逵、石秀、阮氏三雄等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不过,这些人物到了招安以后就变得不再出众,一幅幅鲜活的英雄画卷变成了一幅南征北战图。究其原因,就像在孔孟那里对于血亲团体性的理解一样,“由于赋予了血亲团体性以至高无上的根本地位,就进一步要求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必须从属于血亲团体性,允许凭借血亲团体性来约束限制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从而最终在本质上呈现出血亲团体性的特征”*刘清平:《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赵敦华:《哲学门》第1卷(2000年)第1册(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决定了梁山好汉们在招安之后的命运,他们之前的个性必然被慢慢打磨成一个标准的忠义模型。这不但与实现“封妻荫子”的理想一致,也与君王和朝廷的企望相符。只要君王这个最大的“知己”能够认可他们、为他们提供机遇并加以礼遇,他们一样会不顾一切地为之行动,并越来越忠。因此,可以说梁山好汉们的奋起之争主要是在忠君之下,对于现实中不公平命运的奋争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其反抗性是鲜明的。不难发现,招安之后的人物性格远不如招安之前鲜活、突出,招安之后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人物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或补充。梁山好汉们的个性在招安之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展示,也许从这个角度看,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反倒更加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对于那些不赞同招安的人而言,招安只是他们在处友之义下的妥协,也是他们个性受到约束的开始。在这种约束之下,其个性中的闪光部分受到了削弱,以至于淹没在了事君之忠下。
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的做法实际上突出了处友之义,而削弱了事君之忠,正因为此,他才将平辽和征讨的内容删去。这一点通过文本的对比即可发现。在金本中,宋江得到九天玄女传授三卷天书的时候,并没有“遇宿重重喜,遇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这四句偈语,而容与堂的百回本中则存在。结合之后的故事发展来看,这不但是对宋江一生命运的预示,也是对此后故事情节的预示。偈语中的“宿”和“高”分别指的是太尉宿元景和太尉高俅,前者反对对梁山用兵而力主招安,并最终促成此事;后者虽然领兵欲平梁山,但终究没能如愿,反而被俘上山。而“北幽”和“南睦”则是南北两个地名,前者指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而有宋一代始终未能收回的“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即预示着后来征辽的故事;后者指南方的“睦州”,当年被方腊攻陷并在方腊起义失败后被改为“严州”,即预示着后来讨伐方腊的故事。这就是百回本《水浒传》在梁山大聚义之后的内容。而在百二十回本中,这四句偈语为“遇宿重重喜,遇高不是凶。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宿”、“高”二人二事没有变化,“外夷”和“内寇”取代了“北幽”和“南睦”,加上“几处”取代了“两处”,则预示着除了征辽和平方腊外,还有征讨田虎和王庆的故事。这种不同并不像金本那样完全删除了梁山大聚义之后的内容,而只是量上的不同。况且,有研究者指出,宋江破辽后出现的诏书所署时间为“宣和四年冬”,而破方腊后上给朝廷的表文署“宣和五年九月”,并由此推断征讨田虎和王庆的时间有了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明代万历年间《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的本子可以看出征讨田虎和王庆的故事是后人“插增”进去的。*朱一玄:《〈水浒传〉前言》,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2页。即使暂时抛开田虎和王庆两部分内容不论,征辽和平方腊也足以显示事君之忠以及遮蔽在其中的处友之义。
有鉴于此,可以说金圣叹通过对于《水浒传》的“腰斩”,实现了以金本《水浒传》阐释原本《水浒传》的目的,既使得处友之义被凸显,也使得事君之忠被遮蔽甚至消解,进而使得二者之间的张力消失;虽然集中了人物形象和个性,但是削弱了忠义观,以至于后人还经常用金本《水浒传》来阐释其他版本的《水浒传》。
如果说金本《水浒传》是最早、最有代表性的衍生文本的话,那么《金瓶梅》《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扬州评话《武松》《独臂武松》以及诸多“水浒”影视作品等,则是后来逐渐出现的衍生文本。其中,《金瓶梅》更多的是借用《水浒传》的部分内容来说出一个全新的故事,其主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等则是对于《水浒传》故事的延续和发展,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原作的精神;扬州评话《武松》《独臂武松》等则是对《水浒传》中的个别受人们喜爱的人物进行演绎和丰富,其精神往往续接《水浒传》而故事情节则有所发挥或创造,比如对于“武松独臂擒方腊”的认同;至于《荡寇志》则是在形式上续接金本《水浒传》,从宋江的噩梦写起,其意在阐明:“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俞万春:《荡寇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这里不但将忠义与强盗对立,而且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忠义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更进一步的是,该书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如下的做法:“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俞万春:《荡寇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这就不但出现了前文所述的诗史互等、以素材强制阐释文本的情况,也出现了用衍生文本《荡寇志》强制阐释原文本《水浒传》的情况。
究其原因,恐怕与标榜忠义的梁山好汉们实现忠义的方式不无关系。从处友之义方面看,梁山好汉们对于知己的报答是坚决和豪迈的。不过,这种坚决和豪迈在血亲团体性的约束限制下,并没有充分发展社会性的方面。换句话说,梁山好汉们在报答知己所采取的行动中,并没有考虑到行动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当阳谷知县想让武松将一担金银送到东京的时候,武松认为这是“得蒙恩相抬举”(第二十四回),欣然领命。身为都头的武松未必不知道这些金银是哪里得来的,也许当他觉得自己受到重用的时候已经默认了这种官场的游戏规则,而没有去考虑这样做的社会危害和负面影响,甚至选择拒绝。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之后,张都监设计将武松调遣过去,声称要武松作自己的“亲随梯己人”,武松也非常感激,“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坠蹬,伏侍恩相”(第三十回)。武松像大多数梁山好汉一样,在判定知己的时候,缺乏对于知己的评判,也缺乏对于这种关系的反思,从而显得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更有甚者,有些报答知己的行动,出现了随意杀戮的情况。比如董平在归降宋江以后,除了“赚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之外,还“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而这样做的原因竟是“程太守有个女儿,十分大有颜色。董平无妻,累累使人去求为亲,程万里不允。因此,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和”(第六十九回)。这样来看,董平在报答知己的行动中夹杂了自己的私欲,甚至可以说他用忠义观掩盖了自己的私欲。再比如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和戴宗的时候,“火杂杂地轮着大斧,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第四十回);在三打祝家庄的时候,他竟然无视盟约,杀了扈三娘一家老小。如果按照江湖上公认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标准,对于那些无辜枉死的人,李逵是不是该以命抵命呢?如果从一诺千金去看李逵的行为,岂不是言而无信的表现?
从事君之忠方面看,梁山好汉们同样是坚决和豪迈的,甚而在招安之后似乎带有一种优越感:既有得偿所愿的快意,又有能够报效君王、封妻荫子的欣慰。于是,他们主动请命,前去征讨方腊这样的“江南草寇”。在他们的心里,尽管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赏和封赐,但自己是代表君王征剿,是尽忠报国。因此,他们不惜兄弟战死沙场,不惧被骂为“打家劫舍的草寇”。可见,他们只是从报效君王的角度来进行征剿,而没有或者是没能对这种“以寇制寇”的行为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更难以提出解决方法。在这个层面上,事君之忠具有相当的狭隘性。这种掩藏在忠义观之下的狭隘性和随意性,将梁山好汉们的另一面展示了出来。而展示出来的这些内容,既没有和他们公认的一些做人、做事标准相一致,也没有进一步发挥忠义观中积极、健康的部分。后人对梁山好汉们的批评也涉及这个问题,兹不赘述。
至于由《水浒传》衍生的影视作品,不但借鉴了《水浒传》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将现代人的价值标准融入到剧本的再创作中,从而出现了所谓的“翻案”,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影视作品对于潘金莲形象的塑造。在《水浒传》中,潘金莲由于被清河县一个大户纠缠而去大户的夫人那里告状,导致“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之后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骚扰,而潘金莲也嫌“武大身材矮短,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第二十四回),这就为《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形象奠定了基调。当武大和武松兄弟相认后回到武大的家里,潘金莲以嫂子的身份见到武松,却有了这样的想法:“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第二十四回)这里透露了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武大的个人条件不好、形象特别差;二是潘金莲对于和武大婚配是不满的;三是武松的形象好、本领大且没有婚娶;四是潘金莲由此想和武松有一段姻缘。从一般的角度来理解,觅得佳偶是理想的选择,对于佳偶的追求也具有正当性。但是,当一个人已经有了婚姻而又没有解除婚姻的时候,再去追求所谓佳偶就要受到婚姻制度和相关伦理规则乃至法律的约束。换句话说,潘金莲被迫嫁给武大是不得已,武大的实际情况让她对于婚姻产生了不满,并有了另觅佳偶的想法。从今天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甚或女权的角度来看,潘金莲的想法和行为自然具有反抗意义。但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面对的深层问题却是:其追求佳偶的想法和行为与现实中的血亲伦理、好汉标准、婚姻制度、法律制度等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武松而言,其想法和行为与血亲伦理和好汉标准的矛盾更为尖锐。如果承认潘金莲在与武大的婚姻中遭受了不幸,那么就不能否认或者忽视其想法和行为所要面对的深层问题。如此,或许可以将问题归结为:是否可以因为婚姻中的不幸而置血亲伦理、婚姻制度和法律制度于不顾?甚至因为婚姻中的不幸而毒杀配偶?看来答案至少不是肯定的。
可以看到的是,《水浒传》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潘金莲不同意大户纠缠的具体原因,但因此认为她“反叛了当时男子三妻四妾的社会规则”,而没有综合考虑其动机和实际效果,恐怕是把她的形象和所做事情的意义拔得太高了。至于个别演员认为“潘金莲不仅不是淫妇,而且是‘不甘命运被人摆布,敢于追寻爱情’的烈女”,而对于其出轨,甚至表示“尊重通过各种规则上位的人,这就是很现实的生活”*《颠覆原著角色 盘点为潘金莲翻案影视剧》,http://www.anhuinews.com/zhuyeguanli/system/2013/08/09/005976920.shtml。,则不得不让人深思。如果抛开其中混乱的价值观和对于《水浒传》原著的无知外,这些认识折射了一个共同的倾向:用衍生文本来强制阐释《水浒传》原文本。需要声明的是,此处并非反对对经典著作的改编和再创造,而是认为这种改编和再创造不能置原文本于不顾;即使没有能力回答原文本中的复杂问题,也应该慎重将之简单化、娱乐化,不应该罔顾世道人心。正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潘金莲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改编应当从社会历史角度写出淫妇的悲剧,不应当牺牲人物形象,片面凸显抽象人性无处安放而至毁灭的‘崇高’。应当指出的是,名著改编要剔除那些于今有害的思想成分,并不足以构成对原著基本精神的迁移”*郑伟:《名著改编不应误读现代意识与大众审美情趣——由新版〈水浒〉剧改编说起》,《人民日报》2011年8月9日。。
四、结语
对于文本强制阐释文本问题的分析和批评,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不等于否认中西比较的可能,也不等于对经典文本的改编和再创作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除了前文所述要“剔除那些于今有害的思想成分,并不足以构成对原著基本精神的迁移”外,还要注意文本的选择,如研究小说《水浒传》忠义观就要以其文本为核心,不同版本之间可以互证互校且要注意区别改变基本思想而增删文本内容的情况,其他诸如创作素材、衍生文本以及异质文化等都不足以构成对其文本基本思想的否定。当然,这并不妨碍通过以上途径对文本提出批评以及对文本基本思想进行反思。因此,在讨论回到文本时,选择什么样的文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文学外部研究不断挤压文本研究空间的时候,提倡回到文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水浒传》的研究情况来看,解决好回到文本的问题就必须重视且处理好素材与文本、异质文化与文本、衍生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怎样回到文本上,避免理论的强制阐释;在回到什么文本上,避免文本的强制阐释。
CompulsionandDeviation:QuestionsofandReflectionsontheTextualInterpretationofWaterMargin
Yu Wuso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Beijing,100026)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of Water Margin,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extual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requent collis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due to the richness of their creative materials, the complicated versions of the text and the influence of derivative texts. They are: using the materials to interpret the text, using heterogeneous culture to interpret the text, and using derivative texts to interpret the original tex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extual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not only leads to the devi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oyalty and the deviation from the text of Water Margin, but also results in the variation of the imag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characters an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choices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Water Margin. It may be argued that on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Western theory in the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is how to return to the text, while in discussing the textual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the way is hopeful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turning to what text.
Water Margin; material for creation;heterogeneous culture;derivative text;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I207.41
A
1001-5973(2017)05-0031-15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5.004
2017-08-13
俞武松(1981— ),男,安徽滁州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博士。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