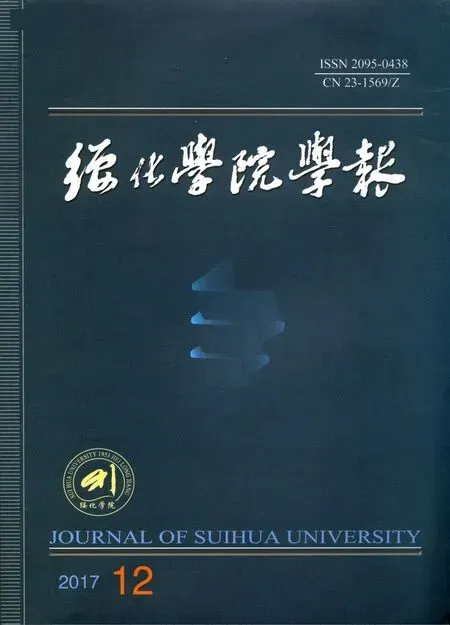《致科学》与《拉弥亚》的互文解读
2017-04-14何微微魏德蛟
尹 青 何微微 魏德蛟
(昭通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昭通 657000)
《致科学》与《拉弥亚》的互文解读
尹 青 何微微 魏德蛟
(昭通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昭通 657000)
爱伦·坡和约翰·济慈以理性与感性的对立为母题,分别以十四行诗及叙事诗的形式创作了《致科学》和《拉弥亚》两篇佳作,对两作品的互文解读有助于彰显它们在人物意象、整体构思、创作旨趣上的异同。
理性;感性;秃鹰;拉弥亚;希腊神话
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诗歌创作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自足性,不可受到科学实用性的影响,很多诗人反对科学而提倡唯美的创作思想,因而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常见的创作主题就是科学对艺术的破坏和侵蚀,鉴于此,本文拟对爱伦·坡《致科学》和约翰·济慈《拉弥亚》进行互文解读。
一、科学的诗意意象——忠贞少女与秃鹰
科学尊崇理性,崇尚严谨而清晰的逻辑思维,追求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法则,总是给人刻板的印象,对此坡和济慈皆进行了拟人化的诗意处理,赋予了科学以独特的象征意象。《致科学》采用了传统的十四行诗的形式,由三组四行诗(quatrains)和一个总结对句(couplet)组成。诗中诗人同时采用顿呼、拟人、暗喻、修辞疑问句等多种修辞格方式来揭示了科学对诗意的敌意。在诗歌的第一个四行中诗歌的叙述者用“顿呼”的方式直呼科学为“时间老人的忠贞少女”和“啄食诗人心灵的兀鹰”。
“时间老人的忠贞少女”这一暗喻契合并暗示了科学追求历经时间考验的真理这一刻板的形象,同时科学被比作一只“翅膀由沉闷的现实构成的秃鹰”。秃鹰是一种专吃动物死尸的食腐鸟类,在西方文化中以其“丑陋”而著称,秃鹰会让人产生“腐烂”“死亡”“厌恶”等诸多联想。在此科学被比作“秃鹰”,它不让诗人飞到星光灿烂的天空去摘取珍宝,还粗暴地扼杀了诗人心中优美的神话,并最终使他失去在绿荫下做美梦的难得享受。
在第二个四行中诗人用修辞疑问句反问诗人如何能够喜欢、尊敬并融入科学:“他何以爱你?何以认为你深奥,/你总是不愿任凭他去漂泊流浪,/不愿他去镶满钻石的天空觅宝,/不愿他展开无畏的翅翼去翱翔?”[1](P65)在第三个四行和最后的一组对句中,诗人再次用修辞疑问句指责科学破坏了美丽的神话:“你不是已把狄安娜拖下了马车?/不是已把山林仙子逐离了森林,/让她去某颗幸运的星躲灾避祸?/你不是已从水中撵走水泽女神,/把小精灵赶出绿茵,然后又从/凤眼果树下驱散我夏日的美梦?”[1](P65)诗中“拖拽”(drag)、“驱赶”(drive)、“撵走”(tear)等词无一例外给人以粗暴、冷酷的暗示,强力地刻画了科学令人生厌的一面——科学妨碍了艺术家在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世界里的自由创作。在此,坡从一个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青年的视角表现了他对神话和感性的艺术世界被科学所扼杀的悲叹。坡不把科发展视为进步,相反他觉得科学用它凝视的眼睛破坏了诗意,把科学比作“秃鹰”,形象地揭示了科学呆板、丑陋、暴虐、冷酷的破坏者形象。
无独有偶,济慈叙事诗《拉弥亚》中里休斯的老师——智者阿波罗尼的形象与秃鹰在形神两个方面皆极为相似。在外表上,阿波罗尼形似秃鹰,他“头顶光秃,穿着道袍”,典型的学究模样;在内在品质上与秃鹰及其相似,他敌视一切虚幻的东西,总是试图去揭示那些他自认为有悖真理的幻觉和假象。里休斯充满了对他的畏惧,故事中当里休斯暂时抛开对拉弥亚身份的疑惑与她前往哥林斯的住所时,他们刚过城门,里休斯就掩着自己的脸孔,这时“一个白须鬈曲,目光锐利,头顶光秃,脚步缓慢,穿着道袍的人走近”,就在他们相遇擦身而过时,里休斯异常紧张,脚步飞快,而拉弥亚吓得浑身发抖,她问:“里休斯!你为何蒙住/自己不让他敏捷的眼光看见?”。里休斯答道:“那是哲人阿波罗尼,/我的可靠导者和良师,但今夜/他像萦绕我美梦的‘愚蠢’之鬼灵。”[2](P193)
对里休斯来说阿波罗尼如同秃鹰,是他的噩梦,象征了他和拉弥亚美好爱情的死亡。在他们的婚礼上,他不请自来,以保护里休斯的名义宣称要保护他免遭人生的厄运和一条蛇的作弄,不顾两人的苦苦哀求,揭穿了拉弥亚蛇的真实身份。然而,最具讽刺性的是里休斯突然意识到他的导师才是真正的毒蛇,他所擅长的只是一种傲慢的诡辩,非法的妖术和谎言:“哥林斯人!看那个白须的恶徒!/注意他没有睫毛的眼皮怎样围住/他恶鬼似的眼睛!”[2](P207)然而,阿波罗尼却称里休斯为“蠢才”,并随之用他那诡辩家的眼光,如利刃一般,猛烈、无情、敏锐、急剧地直贯拉弥亚的全身,并无情地道出拉弥亚蛇的真相,随之她烟消云散,里休斯脉息尽失,婚礼变成葬礼。
阿波罗尼的行为如同“秃鹰食腐”,体现了科学的冷酷和高傲,他傲慢地认为揭穿拉弥亚的身份是在拯救里休斯,这是作为哲人的理性天性使然,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然而他的行为与秃鹰食腐并无二致,枯燥的真相、真理就是其固执追求的腐肉,然而他却乐此不疲,这揭示了西方父权制社会中理性主义对感性主义的压制,排斥和异化,理性企图消除一切幻想和感性的东西,其结果就如坡所言:“科学用凝视的眼睛改变一切!”[1](P65)结果剩下的只有干瘪的现实与枯燥的真理。
对比两个作品,坡和济慈都把科学拟人化、人格化,并赋予了科学以“秃鹰”这一形象生动的意象,突出表现了科学或理性主义对艺术、感性的凝视,控诉冰冷的、机械的理性主义消灭了感性、幻想、及所有美的事物,体现了两者相似的审美取向,他们都追求一个不受理性束缚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
二、艺术的诗意形象——女神与蛇妖
浪漫主义时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美学追求就是感性主义和想象力,认为感性和想象力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感性、想象力与和理性、现实等相对,与科学的理性,冷酷,机械性不同,艺术创作强调感性,想象力,因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一直被艺术家们看作是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坡和济慈也不例外。
在坡的审美哲学中女性的美是最富有诗意的,《致科学》中提及的各位希腊女神,包括森林女神哈玛德律阿得斯(Hamadryad),河泽女神那伊阿德斯(Naiad),狩猎女神狄安娜(Diana)都是诗人所崇尚的想象力和美的象征。森林女神是树之精灵,与树合为一体,与其长存,是森林的庇护神,然而由于科学的入侵,神秘庇护被代之以“光合作用”“新陈代谢”等冰冷的科学解释,随之一切美好的想象都消失殆尽;河泽女神是江、湖、泉水、小溪的守护神,现在科学用令人乏味的科学术语解释天气的变化使大自然的神秘荡然无存;狄安娜是狩猎女神和忠贞的象征,诗中所提到的战车是她所驾驶的狩猎战车,她和她的战车是一体的,然而科学已然把她拽了下来,破坏了美丽的神话和事物的和谐统一。神话的世界遭到了科学粗暴的破坏。
济慈和坡一样热爱希腊神话,被认为是“英国诗人中最爱希腊的”[3](P323),他的颂诗《怠惰颂》《赛克颂》《希腊古瓮颂》《阿波罗赞歌》皆与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或故事有关,其叙事诗《恩狄弥翁》《许佩里翁:片段》《拉弥亚》也都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拉弥亚》取材于罗伯特·伯顿的《悲哀的解剖》的第三部第二节中所叙述的青年里修斯与蛇妖拉弥亚的爱情悲剧,而故事本身可回溯到希腊作家费洛崔托的《阿波罗涅》。济慈对该故事进行了改写,加入了拉弥亚与希腊天神赫尔墨斯的交易这一情节。故事讲述蛇妖拉弥亚暗恋科青年学者里休斯,不得亲近,借赫尔墨斯遍寻所恋林泉仙女不得之机,与之协议,她为之破解小仙隐身之术,而赫尔墨斯则应允将其幻化成美女之身,双方随各成其愿,拉弥亚得以亲近里休斯。两人遂前往哥林斯居于其中一虚幻住所,两情相悦,然好景不长,因里休斯执意举办婚礼以炫耀于亲友与邻里,婚礼上他的导师阿波罗尼不请自到冷酷揭穿拉弥亚的身份,顿时拉弥亚香消玉殒,华丽而辉煌的住所连同铺张的陈设与装饰随之化为乌有,里休斯也悲骇而死。
与坡诗中各位女神泾渭分明的象征意义不同,拉弥亚亦神亦妖的形象具有更为复杂而含混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和各位女神一样,它是感性、想象力的象征。在赫尔墨斯帮助她变成美女蛇之前,她拥有神力,能号令自然精灵,她用魔力将赫尔墨斯苦苦寻求的仙女隐身,随之又用魔力使之现身以满足他的欲望。另一方面,它似乎又是妖女、妖精和恶魔的化身。在外形上她形如奇幻的彩虹,是一个充满由各种光、色、魔力构成的炫目复合体。
不仅如此,拉弥亚神秘而含混的身份又是与里修斯紧密相关的,她是以女神还是蛇妖的形象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里休斯。当感性占上风之时,他的内心就能享受相对的平静,安然接受拉弥亚的存在。然而他却不能完全沉溺于感官的世界,理性悄然抬头,给她带来极度的不安,继而威胁她的存在:“自从他躲在那座金碧辉煌的/甜蜜的罪恶之宫以来,他的精灵/第一次与越过它的黄金境界,/进入了那几乎被放弃了的大千世界。/那个始终警惕的,聪明透彻的贵妇,/痛苦地见到这点,他透露需要/比她欢乐的统治更多,更多的东西;/她就开始悲恸叹息,因为他想到/她力所不及的东西,深知瞬息的思想就是热情的丧钟。”[2](P196)
里休斯不满足于独享幻想和魔法所带来的愉悦,同时想把它们暴露在现世的众目睽睽之下,向世人炫耀他的宝贝,他过度的自负已然超越了极限,因此他被惩罚了。他的傲慢与阿波罗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由于他执意要举行世俗的婚礼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一悲剧表面上看似阿波罗尼造成的,但其真正的根源是里修斯分裂的自我,而拉弥亚亦神亦妖的双重身份恰好说明了里休斯人格中不平衡的感性和理性,并间接揭示了济慈在其创作过程中对理性与感性之关系的更加暧昧的审美取向。科学本身是冰冷而具有破坏性的,然对感性的追求又是不令人满足的,“济慈一方面渴求诗歌和想象力能给人带来慰藉,同时他对于诗歌与想象力是否足以回应人类痛苦又充满怀疑”。[4](Pix-xiv)
对比两个作品可见《致科学》与《拉弥亚》中感性、想象力的象征意象皆以女性形象出现,前者是各位女神,后者是亦神亦妖的美女蛇,然而拉弥亚这一人物显然在叙事诗中得到了更细致、更丰富的刻画和表现。相应地,《致科学》的叙述者是一个充满热情,耽于天马行空的幻想的镜清水明的少年,他直接明了地表达对科学破坏幻想、想象力和美的世界的不满,他热爱艺术,向往一个富有诗意的、充满想象力的美的世界。而《拉弥亚》中的主人公青年里休斯则个性复杂多变,他既沉溺于感性和感官享受,然而又不能完全抛开理性,其结果就是幻想在理性的凝视下消失殆尽。他多变的性情充分体现在拉弥亚被异化的、含混的、双重身份上,她不仅是感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象征同时又是情欲、破坏力和邪恶的象征。该故事寓意在生活或是艺术创作中任何企图把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截然分开的尝试只能招致致命的悲剧,理想和感性既不是全然对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三、结语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诗人的才能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他认为一个诗人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利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5](P117)从以上对《致科学》、《拉弥亚》的互文分析中我们不仅在坡和济慈的诗歌中看到了古希腊神话传统的不朽,同时从坡的诗歌中似乎又看到了济慈的不朽,然而正如艾略特所说传统是一个前无起始、后无终结的整体,相信后来的诗人或是任何个别文本都是这个传统链条中的一个部分。
[1]爱伦·坡.爱伦·坡诗选[M].曹明伦,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2]约翰·济慈.济慈诗选[M].朱维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弗雷德里克·塞夫顿·德尔墨.英国文学史[M].林惠元,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323.
[4]John Keats.John Keats:Selected Poems [M].Ed.John Barnard.PenguinBooks,1988.
[5]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I106
A
2095-0438(2017)12-0060-03
2017-06-22
尹青(1979-),女,云南镇雄人,昭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约翰·济慈叙事诗研究”(YN-0013-A)。
[责任编辑 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