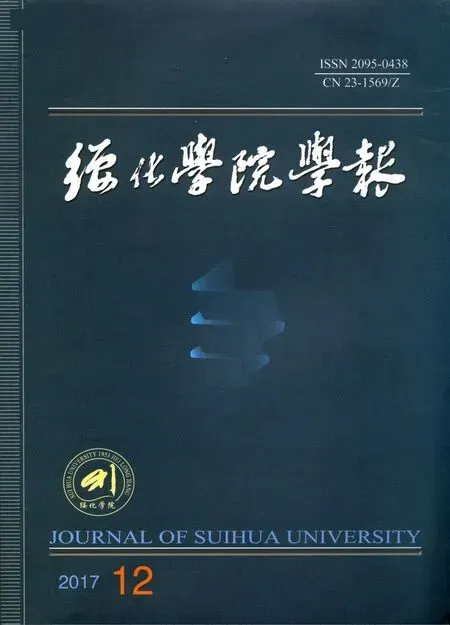《西游记》白骨精故事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
2017-04-14刘佳
刘 佳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1)
《西游记》白骨精故事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
刘 佳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1)
白骨精是《西游记》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女妖怪,其原型是“尸魔”,白骨精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白虎精渊源颇深。白骨精故事围绕“三戏”“三打”“三逐”层层展开,蕴含了道教文化中的“斩三尸”之意,体现了《西游记》成书经历了“全真化”环节的特点。作为《西游记》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白骨精故事在小说结构中承担了发展取经团队人物性格、强化团队意识的叙事功能,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西游记》;白骨精;文化内涵
唐僧师徒在取经途中最早碰到的女妖怪是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中的主角——白骨精。作为“第一个”出现的“女妖怪”,它不同于想和唐僧交欢的杏仙等女妖,也不同于欲和唐僧做百年道伴的蝎子精,白骨精形象包含了特殊的文化内涵。而白骨精三戏唐僧的故事也在小说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本文将通过对“三打白骨精”故事的解读,深入探讨白骨精故事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白骨精故事及其渊源
(一)白骨精故事的基本情节要素。小说中的白骨夫人没有什么背景,法力有限但是诡计多端,尤其是通晓人类的弱点,演技也很精湛,是一个智慧型的女妖。第二十七回以白骨精故事为重心,较为详细地上演了一出“三戏”“三打”“三逐”的好戏。
白骨精的智慧表现在她深谙家庭亲情对人的巨大影响,唐僧取经可以说是为了普渡众生,为了大家,而小家是大家的组成元素,所以当一家老小都被自己的“劣徒”棍棒打死在面前时,他的慈悲之心就不停驱使他念紧箍咒教训孙悟空。她幻化作女子、老母、老父,深深抓住了唐僧肉眼凡胎的局限,成功离间了师徒关系,使孙悟空被第一次驱逐出取经团队。
(二)白骨精与白虎精。白骨精在妖怪中也是占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小说中却没有完整介绍它的来龙去脉,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惑,似乎白骨精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没有靠山的小妖。作为世代累积型长篇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广泛汇集了关于西游故事的种种材料,宋元话本,戏曲及民间传说,其中成书于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中讲到一个居住于“火类坳”的白虎精,和白骨精故事有密切的关系。该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又过火类坳,坳下下望,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十余里……猴行者曰:“我师曾知此岭有白虎精否?常作妖魅鬼怪,以至吃人。”师曰:“不知。”良久,只见岭后云愁雾惨,雨细交霏;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罗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如白莲,十指如玉……妇人闻言,张口大叫一声,忽然面皮裂皱,露爪张牙,摆尾摇头,身长五丈。定醒之中,满山都是白虎……猴行者化作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1](P44)
首先,白虎精的出场和白骨精类似,都处于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一个是“四门陡黑,雷声喊喊”,一个是“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果然这山上有一个妖精。当孙大圣去化斋时,惊动了他,他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见长老坐在地下,就不胜欢喜。”[2](P301)其次,它们都通过变幻成年轻貌美、步履婀娜的少妇来接近取经人,后均被孙行者识破。一个“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2](P309)一个是现出原形,化作满山白虎,终被猴行者降服,肚皮裂破七窍流血而死。再次,地点的暗示。在《西游记》里提到了“蛇回兽怕的白虎岭”以及“我丈夫在山北凹里。”[2](P303)这里,“凹”同“坳”。最后,猛虎变为美妇的传说历来有之。《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虎八中,宋薛用弱《集异记》有《崔韬》一则,叙蒲州人崔韬旅途宿馆,见一虎自门而入,于中庭脱去兽皮,变成一奇丽严饰女子,就韬衾而寝,韬问女子缘由后道“诚意如此,愿奉欢好。”[3](P2071)并弃虎皮衣于枯井,携女而去。擢第赴任时复宿于仁义馆,二人言及旧事,韬依妻之言从井中取出虎皮,才穿上便化为恶虎,食韬及所生一子而去。通过对比阅读文本,可见白虎精与白骨精有着一定的渊源。
二、白骨精故事的文化内涵
(一)与众不同的“尸魔”。首先,她战斗力很弱,与其它妖怪如金角银角大王等相比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在第三十二回中,日值功曹化作樵夫来向师徒四人报信说,二妖神通广大还拥有五件宝贝,而白骨精肯定不会被功曹放在眼里。当孙悟空化斋不在唐僧身边时,她也不敢公开和猪八戒、沙僧一决高下,只敢先“戏他戏”。并且“三打白骨精”的打斗极为简单,只孙悟空一人与之作战,猪八戒和沙僧都没参与,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每每一眼就能辨识真相,然后果断地手持金箍棒追打,白骨精也只能用“解尸法”逃脱,由此可见她的法力有限,而且也只变幻了三次。
其次,她实力不强但聪慧,有头脑,是情商很高的演技派。三次变幻,巧妙地抓住了取经团队成立时间短、磨合不够、沟通不畅等缺陷,先后利用了伪装计、反间计、将计就计等计谋,造成团队内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此外她没有武器,原文只是重复着“踏着阴风”幻化做人形,如一缕轻烟,无形无迹。白骨夫人也没有朋友、亲戚甚至小喽啰等帮凶,只孤军战斗,她前两次通过“解尸法”预先逃脱了孙悟空的铁棒,最后还是被悟空一棒打死,“断绝了灵光”。她的领地很小,不成气候,在第二次吃唐僧肉计划失败后她自言自语道:“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过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2](P307)由此可见与占山为王、有家室和兄弟的牛魔王等妖怪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再次,她和与神仙有牵系的妖怪更没有可比性。例如和托塔李天王、哪吒攀了亲戚的金鼻白毛鼠精,虽然吃了人,两次捉住唐僧,最终被押往天庭发落,保留了性命;冒充佛祖的黄眉怪给师徒四人造成极大危难,最后还是弥勒佛出现,化解了危机,他最后依然回到弥勒佛身边,变回了黄眉童子;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偷走老君的宝贝金钢琢下界到金兜山金兜洞当起独角兕大王,用天界的宝物将孙悟空等人的武器收走,除妖过程险象环生,最终也是随老君回到天宫。凡此种种与天界有关联的妖怪,不一而足,白骨精与之相比,简直相形见绌。
最后,白骨精的目的是“吃唐僧肉”,它是西天路上第一个要吃唐僧肉以求长生的女妖怪。但与后文中欲和唐僧结合的女妖怪不同,白骨精并非想要通过“毁他戒体盗元阳”来增强法力和求得长生不老,而是直接把魔抓伸向唐僧,抓来吃掉。在这一难中,围绕白骨精展开了“三戏”“三打”“三逐”的好戏,尸魔白骨精暗指人的皮相,“心猿”孙悟空暗指人的内心,白骨精用不同的皮相去欺骗唐僧,却骗不过“心猿”。由此可见此妖的别开生面与在小说中的重要性。
(二)“斩三尸”的道教文化内涵。白骨精接二连三的欺骗给唐僧师徒带来巨大的考验,甚至使取经队伍四分五裂。在唐僧眼里,孙悟空野性未改,连伤三命,罪不可恕,竟不顾师徒情份,写了一纸贬书欲要与之一刀两断;在猪八戒眼里,自己可以更加自在,不再处于大师兄的光环之下。取经人之间缺少必要的信任和强大的凝聚力,而这两者是取经成功的重要保障,否则必将产生矛盾与分歧,乃至招来意想不到的祸端。
在“三戏”的过程中,白骨精屡屡使唐僧和猪八戒放松警惕,甚至离间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情分,由此给取经团队内部造成极大的挑战。结合前文,如此一个法力有限的孤魂野鬼,为什么还要劳烦齐天大圣连打三遍呢?这是因为西游故事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展丰富起来的,宗教象征化是这个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西游记》中驳杂的融入佛、道、儒三家之言,虽有扬佛抑道的倾向,但其成书经过了“全真化”环节[4](P114)。
俗话说有一有二,没有再三再四,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们对“三”是有一种独特的情结的。关于“尸魔三戏唐三藏”中的“三戏”有的学者认为它指佛教所说的人心之三毒,即贪(爱着)、嗔(怒气)、痴(无知),三者在《西游记》中正好与孙悟空的暴戾、猪八戒的贪色、沙和尚的痴呆相对应。陈洪先生指出:“《西游记》成书的过程中有教门中人物染指颇深,百回本成书之前,西游故事已在多种民间宗教中流传,而其情节及人物都与教义特别是内丹术产生了关联。”[4](P118)具体来说,“三戏”蕴蓄了道教常说的“斩三尸”之意。
道教认为,人身有三尸,嫉人成道。三尸又叫三毒,是阴浊之气。三尸变化多端,隐显莫测。能化美色使人梦遗阳精,能化幻景使人睡生烦恼,使大道难成。只有斩除三尸,才能得道[5](P106)。这里“尸”是存在、停留的意思,具体指三种虫子,分别代表了人体内部的三种欲望。“三尸虫”包括上尸三虫,中尸三虫和下尸三虫,它们分别象征着让人蠢笨无智慧,让人烦恼、妄想、无清静及让人贪图男女饮食之欲。白骨精故事中的“三戏”即象征着取经团队必须铲除和消灭这“三尸之根”,才可能修成正果,但俗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斩三尸”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次到位,所以才设置了“三戏”的情节,表明唐僧师徒必须经历艰难的历练。白骨精的三次幻化,做到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要传达的寓意就是“斩三尸”,即要西天取经成功,必须进行“斩三尸”的修行,必须清除各种凡俗欲望产生的干扰。原著中孙悟空第三次终于把白骨精打死了,但唐僧却在猪八戒的挑唆煽动下把孙悟空赶走了,这反复的“三戏”“三打”“三逐”正象征“斩三尸”的艰难,它历练着取经团队成员的内心,拷问着团队的凝聚力。可见故事里主要的“尸虫”,就是暗指取经团队的内部凝聚力问题。
经过“斩三尸”这一劫,唐僧和孙悟空之间才真正建立了师徒关系,细读文本可知,此前紧箍咒仅控制了孙悟空的身体,并未真正收服他的本性;三打白骨精后,孙悟空在唐僧屡次教诲不要滥杀无辜下,他视人命如草芥的野性发生转变,进一步去了戾气,更好地定心、修心,他的二次出山,代表师徒关系真正的稳固。这一劫难后取经团队内部更加团结,师徒四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重新踏上西天取经的大道。
三打白骨精隐喻着明心见性必须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洗礼,在降妖除魔的过程中,作者既歌颂了事在人为、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也影射讽刺了明代社会的黑暗与矛盾,正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说:“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还象征着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给下界百姓带来无限的祸害与灾难。”[6](P97)由此可见白骨精故事的文化内涵以及它在八十一难中与众不同的地位。
三、白骨精故事的叙事作用及意义
(一)人物性格得到发展。李卓吾、黄周星评《西游记》二十七回时说道:
美色之于人甚矣哉!前者既有四圣之试,而至此复有尸魔之戏。四圣之试,扰以圣而化凡;尸魔之戏,则以魔而害道矣。卒之一戏、再戏,必至于放逐心猿而后已。事虽出于三藏,而祸实由于八戒;三藏但怪其行凶作恶,而八戒实痛其月貌花容也。究竟此一月貌花容者,肉眼视之则月貌花容,而道眼观之则骷髅白骨……行者之逐,至再至三,可见吾心之放,亦非俄顷之失,必由渐积而成。[7](P328)
猪八戒在“四圣试禅心”后再次面对美色的考验,进一步去除凡心,扫除爱欲。美色之于猪八戒可谓一大软肋,所以说白骨精的第一次变幻,祸实出于八戒。并且此时他对大师兄怀有嫉妒和不满之心,一方面孙悟空总是在唐僧面前戏耍取笑他,明知二十三回出现的几位女子是菩萨变幻却故意隐瞒,拿他逗乐,看他出丑,还“呆子呆子”地随意取笑,丝毫不顾及他引以为豪的“天蓬大元帅”的尊显身份;另一方面他想要的自由和心里的小算盘常被孙悟空看破和限制,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团队凝聚力的重要性,所以常常教唆唐僧,花言巧语,总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猪八戒贪恋食色的性格描写,沟通了前后故事的内在联系,八戒形象也得以丰满和发展。
唐僧耳根子软,缺乏主见,有些迂腐,善恶不辨,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回开头写孙悟空和镇元子结为情投意合的兄弟,而唐僧似乎对高徒有点拈酸吃醋,在高山的嵯峨之处让孙悟空去化缘,行者赔笑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三藏就责备他不肯尽心服侍自己,怪他“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2](P301),并再次重申自己当年把孙悟空从五行山解救出来的大恩。在白骨精的“三戏”下,他固执地只见女子、老妇、老头,质疑孙悟空的判断,轻信猪八戒,造成师徒情分的疏离,从多个侧面展现了真实的唐僧形象。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总能看到事物的真相,他慧眼识妖,面对师父、师弟的误会与阻挠,表现出除恶必尽、不胜不止的战斗精神。但历经此劫难重回取经团队后的孙悟空在后期遇到伪装本来面目的妖怪时,就不再像对待白骨精那样简单粗暴了,他在西行路上逐渐定心、修心,不再认为一棒子将妖怪打得魂飞魄散是大本事,是为正义锄奸了,他选择在尽量不伤害唐僧的情况下,让师傅自己认知善恶,避免了很多类似因误会而造成的不信任。如第三十三回“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中,银角大王变作受伤的道者,预谋接近唐僧,孙悟空识破了妖怪的伎俩,却不再明枪实刀地和妖怪正面冲突,他依了唐僧的要求乖乖背着银角大王上路,自己默默在口中叨念:“你这般鬼话儿,只好瞒唐僧,又好来瞒我?我认得你是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师父哩。”[2](P376)不敢再当着唐僧的面一棒打死他。又如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中,红孩儿看到唐僧师徒的阵仗,思忖到:“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得到手。但哄得他心迷惑,且下去戏他一戏。”[2](P460)把自己伪装成失家失亲的小儿,孙悟空知道红孩儿使诈,便使个“移山缩地之法”,第一次成功避免了唐僧遇见红孩儿被他蛊惑而大发慈悲心,第二次计谋失败后孙悟空只好任由红孩儿骑在自己脖子上。第八十回“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中,金鼻白毛鼠精变化为遇险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呼救,孙悟空在半空中发现黑气浓重知有妖精,他对唐僧一番说解,第一次阻止了师父救人,但第二次唐僧又被迷惑,将之救下并带着妖精上路。三打白骨精之后孙悟空在降妖伏魔的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他会在金箍棒落下之前说清楚事实,如果唐僧依旧不信,便不再使用暴力了,变得更加随机应变。
由此可见,经过尸魔这一难,取经人的形象在“重复、积聚、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以及转变”[8](P148)中逐渐丰满且性格得到发展。
(二)团队意识得到强化。米克·巴尔论述从行为者到人物时说过:“由于某一事件的存在,人物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不同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能会改变。反过来,人物性格的变更可能也会影响事件,并决定素材的结果。”[8](P152)白骨精抓住取经团队成员各自的弱点以及前期磨合不足的局限,不断地动摇着团队内部的关系,使之发生内讧,甚至土崩瓦解。先以女色诱惑,继而利用人类的同情心加以道德性批判,凭着精湛的演技让唐僧和孙悟空闹得不可开交,以至决裂,赶其回花果山;猪八戒意志不坚定,六根未尽,懒惰贪色,没有将西天取经作为至高目标,更没有意识到大师兄在此行中是不可或缺的,因而白骨精的出现造成西天取经途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分裂,其独特之处显而易见。
李卓吾、黄周星评《西游记》时指出:“试观其未遇三美之前,黄风岭上,流沙河边,是何等同心戮力,乃至此竟似两截人乎?”[7](P328)经历了两次色劫后,“行者之逐,至再至三,可见吾心之放,亦非俄顷之失,必由渐积而成。”亦印证了前文“斩三尸”不易之说。孙悟空被逐后,唐僧受难变成猛虎,“意马忆心猿”,沙僧积极建议,八戒义激猴王,危难时刻大家更加意识到大师兄的重要性,团结迎敌的意识爆发,心猿秉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念又回到取经队伍中,降黄袍怪、解救百花羞公主、破除唐僧的虎气,师徒重修旧好,自此以后团队凝聚力更加强大,一心同体,共诣西方。
要之,白骨精故事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及意义,从其世代累积的成书过程可追溯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找寻到白骨精形象的渊源;从其“全真化”的过程可以发现“三戏”“三打”“三逐”中蕴含道教中的“斩三尸”之意。做为《西游记》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白骨精故事将唐僧的迂腐善软、孙悟空的果敢无畏、白骨精的鬼蜮伎俩、猪八戒的私心欲望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使人过目难忘。《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神魔小说,更有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因此才经久不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中熠熠发光。
[1]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2]吴承恩.西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李昉.太平广记[M].华飞,点校.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4]陈洪,陈宏.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J].文学遗产,2003(6).
[5]陈士斌.西游真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6]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吴承恩.西游记[M].李卓吾,黄周星,评.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
[8][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I207.4
A
2095-0438(2017)12-0041-04
2017-08-29
刘佳(1992-),女,山西太原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LGYCX1711)。
[责任编辑 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