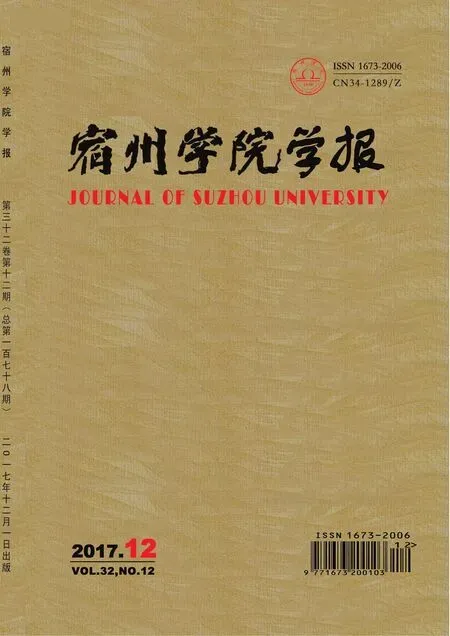家庭治疗视角下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矫正
——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
2017-04-13姚峰
姚 峰
1.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2.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合肥,230031
家庭治疗视角下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矫正
——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
姚 峰1,2
1.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2.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合肥,230031
为了了解家庭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运用家庭治疗相关理论,对一个青少年犯罪个案家庭的家庭结构、家庭沟通模式、家庭功能等因素进行研究,在对该个案家庭进行分析的同时并进行干预。干预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家庭新的规则和互动模式,解决家庭功能不良等问题,进而有效改善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从而达到预防和矫正犯罪行为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治疗对预防和矫正青少年犯罪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注意家庭治疗在中国家庭应用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家庭治疗;青少年犯罪;犯罪矫正
青少年犯罪问题始终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故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正也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从预防的角度看,除了个性因素外,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犯罪也有重要的影响,而从矫正的角度来说,家庭因素的影响也显得尤为重要。西方的家庭治疗主张用整体的视角看待个体和家庭问题,注重通过家庭系统的改变,来处理和消除个体所出现的症状[1]。笔者作为合肥市社会调查员,参与了对一些犯罪青少年家庭的调查,本文力图通过对一个青少年犯罪个案的解析,结合家庭治疗的相关思想,对该个案的犯罪预防与矫正提出观点。
1 个案基本情况
赵某某,初中文化,因为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缓刑,被判刑时17岁。赵某某有一个姐姐,比他大7岁,父母均为某县农民,父亲为初中文化,母亲为小学文化,在赵某某一岁时,父母到省会城市打工,在该市城郊结合部开了一个小百货店,并租住在附近,赵某某两岁便跟随父母一起来该市。赵某某小学成绩尚可,但是,由于父母忙于生意,疏于管理,到了小学高年级后常和小朋友玩耍,不爱学习,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小学毕业后,父母当时感觉孩子有一些管不住了,加上忙于生意,便送其去离家15千米左右的一所民办寄宿制学校读初中。
上了初中以后,成绩一直不好,还因谈恋爱受过一次处分。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后自费上了该市某中职学校的三年制高铁乘务专业,在该中职学校只读了一个学期,由于经常旷课被学校记过处分。从学校正式辍学后,先后在火锅店、网吧、汽配城等店面打工,但每个工作均不超过两个月,且都是他主动提出辞职,辞职的理由都是太苦太累、工作环境不好、工资不高等。
之后,一直在家呆着,期间多次和他人在自己家中以及宾馆吸食冰毒直到被捕。
2 理论背景
家庭治疗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此前处于支配地位的是针对个体的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受到系统论和控制论等认识论的影响,主张用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眼光看待问题个体,主张在系统中考察个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
2.1 家庭治疗的相关理论
回溯近年的相关研究,对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研究已从包括家庭完整性和经济地位的家庭结构变量转向了包括家庭气氛、家庭教养方式等的家庭功能变量,认为后者对青少年的行为才有更加直接且重要的影响[2]。而家庭功能和行为变量的内容恰恰是家庭治疗所关注的领域,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是基于一种系统理论而发展起来的。根据这种理论,家庭系统、父母养育和家庭关系在个人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了解决个人表现出来的问题,就需要把整个家庭作为治疗对象来开展工作。如果某个家庭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成员出现了越轨行为或者其他严重的问题行为,那么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该家庭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产生的一些症状[3]。因此,在分析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或者矫正问题时,仅仅了解这个青少年个体心理和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他的家庭进行了解和分析,按照家庭治疗的理论分析,重点在于系统思想、循环因果以及相应的家庭结构和功能。
2.2 系统思想
家庭治疗的真正发展得益于1940年代以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兴起。Bateson将系统理论引入家庭的分析,他认为家庭不仅是家庭成员的相加,更重要的是一个关系网络,如果要理解某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必须要将其放在整个家庭系统进行理解。控制论是由数学家Wiener首创,其核心是反馈圈。反馈主要是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传递,包括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负向的反馈是为了不让系统的整体性改变,而调整个体以维持系统的状态,正向的反馈是要改变这个系统。从家庭的角度来看,正向反馈和负向反馈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根据情况不同而作出相应调整。系统论主要强调的是家庭的结构和等级(如系统和子系统),而控制论则强调家庭内在的规则、自我调整和控制等[4]。
2.3 循环因果
在家庭治疗出现之前,心理治疗的因果关系大都建立在线性模式上,认为是既往所发生的事件,造成了现在的症状。Bateson运用循环的概念,改变旧有的个体心理治疗思维方式,认为现在的症状主要是由于个体目前所处于的系统所形成的循环反馈圈造成的。Bateson认为线性因果尽管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但是它有明显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人与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关系。相互或循环因果的想法对于诊断家庭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如果不对家庭系统整体进行观察,只是单纯地寻找个体原因往往是无效的,循环因果表明家庭问题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现有的互动的行为之中[5]。
2.4 家庭结构
Minuchin.S所创立的家庭结构疗法认为,心理问题都是家庭组织结构问题的副产品。在阐述家庭结构的内涵时,他引入了“界限”的概念,适当的结构必须要有适当的界限,所谓“界限”是指家庭结构中子系统或成员彼此的“间隔”[6]。
有两种家庭结构模式容易导致家庭的功能失调,一是界限模糊的家庭结构,即家庭成员的关系彼此缺乏明晰的间隔、角色混淆不清。二是界限僵死的家庭结构,即家庭成员关系过分阻隔,比如父母疏于关心孩子、和孩子缺少沟通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往往比较刻板,缺少弹性,彼此之间有较大的心理距离[7]。
清晰的界限是指界限既不僵化也不疏离,既保持分明的界限又有灵活性,家庭成员既能独立自主也能相互支持。而界限模糊的母子关系和界限疏离的父子关系的模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家庭结构[5]。
2.5 家庭功能
Olson的家庭功能理论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理论。Olson认为家庭功能包括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8]。家庭治疗临床实践表明,家庭功能不良更容易导致子女出现问题。大部分实证研究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家庭功能和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存在负相关。有关临床研究证明,那些表现极端的家庭,例如亲密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无稳定规则的家庭,特别容易引起家庭成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越轨行为。Shek用家庭功能评价量表(FAI)考察1 519个家庭的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违法犯罪和物质滥用)存在显著的相关,那些报告家庭功能不良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问题行为[9]。郑希付在《行为与家庭》一书中也提到,家庭中子女行为异常程度与家庭功能的得分成正比关系[10]。家庭功能与儿童青少年的学习不良也有关系[9]。
2.6 资源取向
资源取向就是努力从劣势中寻找优势,将“问题”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并努力在现有条件下发掘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在实际治疗中,治疗师要帮助家庭关注和放大其自身所拥有的正向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摆脱目前的困境。通过对资源的探讨和扩大,还可以增加家庭成员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增强他们改变的动机和动力,这也是为家庭赋权的过程:包括探讨和扩大家庭已取得的进步,探讨家庭对未来的设想,探讨和放大例外情境,增加效能感和自信等。
3 家庭治疗理论视角下个案的家庭问题
从家庭治疗的视角来反思该个案家庭,可以对该家庭系统存在的互动关系和家庭功能作一个分析,从而找出系统对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进而进行干预。
3.1 家庭界限僵死
该案中赵某某小的时候和妈妈沟通较多,但是上初中之后和父母几乎没有交流和沟通,由于父亲性格等因素,和父亲的关系更是处于疏离的状态。赵某某数年之后才和母亲说,他在初中阶段一直被人欺负,还被人勒索过东西,但是一直都没有告诉父母。家庭关系的疏离和界限的僵死,是导致赵某某没有和父母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的重要原因。
Hollin通过研究发现感受到爱、认同父母、尊重父母的孩子最不可能犯罪,相反,缺乏与父亲的支持性关系的青少年比较容易出现危险行为,因此与父母良好的关系可以有效地遏制青少年反社会行为。Berger等人则强调依恋关系的重要性,亲子依恋比较良好的青少年在可能从事犯罪活动时会先联想到该行为会导致父母的失望和不安,于是可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2]。
3.2 不良的循环因果
赵某某的母亲是家中老大,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对家庭的责任感强,早早和丈夫外出打工,很想事业成功。但是她们一家均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一个弟弟曾被家庭引以为豪,研究生毕业后,事业正在上升期,突患肝癌去世。在弟弟去世后,赵某某的母亲有五六年的时间都处于抑郁状态,甚至有想死的念头,当时生意也受到影响,经常埋怨自己的丈夫没有文化,没有能力挣钱,夫妻关系当时也出现了危机。最近几年家庭经济才有所起色,家庭氛围比以前也稍好一些,赵某某的母亲也开始信仰基督教,以此缓解内心的痛苦和压力。
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赵某某的母亲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和使命感,但由于弟弟的去世,而让她的家庭责任感受挫,加上对丈夫的不满,导致丈夫对家庭更加疏离,孩子当时正处于叛逆期,父母的冷淡和疏离更加剧了孩子在家庭以外寻求支持,而孩子的反叛和一系列越轨行为也加剧了父母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循环式的因果关系。
Bandura和Walter发现罪犯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和非罪犯的父母相比有更多的拒绝和更少的关爱。Anderlee对监狱中80名违法犯罪少年与80名12~15岁的正常少年的面谈调查发现,违法少年从双亲(特别是父亲)那里得不到爱,与父母亲(特别是父亲)缺乏情感交流。Langner等人发现家庭中父母冷漠,缺乏情感交流以及母亲拒绝,往往会导致儿童的攻击行为[2]。这些研究更加证明了由于和父母沟通交流问题或者情感拒绝等的不良互动模式,形成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不良的互动因果,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越发会远离家庭,甚至出现犯罪行为,进而导致父母和孩子互动关系出现更大的问题。
3.3 家庭功能失调
初中以前赵某某和母亲的关系比较融洽,在一张床上睡到初中毕业,平时也是母亲管得较多,母亲嫌他丈夫文化低,不会说话,也不会管教孩子。而父亲在家庭中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只顾忙自己的小店生意,偶然教训赵某某也是粗暴地打骂,造成父子感情疏离,父亲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夫妻俩对孩子的学习几乎不过问,平时生活监管也不够,在案发前几年,赵某某一个人长期住在出租房内,父母则住在店里,在客观条件上也给赵某某容留他人吸毒制造了条件。由于家庭氛围不好,缺乏关爱,赵某某的姐姐性格也较为内向,上学期间发生早恋现象,早早便辍学嫁到外地离开了家。
Shek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不良的家庭,青少年的学业适应也不良,而且有产生更多问题行为的可能[11]。 Shek在对家庭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作进一步考察后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的一般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家庭功能不良的青少年可能有更多的问题行为[12]。还有研究者指出,对青少年犯罪行为有直接影响的是家庭功能的缺陷而不是家庭结构的问题,所以优化家庭功能才是预防犯罪的关键[13]。中国学者李莉萍以30位犯罪青少年和20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与普通大学生相比,犯罪青少年的家庭成员间缺乏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家庭功能也不良。
赵某某的辍学,工作半途而废,早恋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都显示出他所在的家庭系统存在问题,而最终的越轨犯罪更是显示出家庭功能的失调。Rosenberg简要地概括了结构主义家庭治疗的立场,他总结道:“当一个家庭陷入困境时,我们可以假定它正在一个功能失调的结构中运做。”[14]
3.4 系统反馈的失效
所有的家庭都有反馈过程,这些过程可以维持整个家庭组织的稳定,一个持久的家庭系统是能够“自我校正的”。当前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激活了这种校正反应,因此,控制论认为,所有的不变都是靠变化来维持的[15]。
赵某某初中阶段上了离家较远的封闭式的寄宿制初中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回忆:当时因为不适应学校环境,很恨其父母。在初中期间,赵某某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初三时由于谈恋爱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初中毕业后在中职学校第一学期就受到一次处分,并结交了一些不良朋友,赵某某的第一个女“毒友”就是当时认识的;他们一家居住的地方是处于城市边缘地带,流动人口多,是一个老工业区,该区域的经济萧条,容易产生一些治安问题。以上问题赵某某的父母都是知道的,但是由于家庭边界僵死,导致家庭沟通不良,家庭无法完成对不良反馈的自身调节功能,多是听之任之,继续忙于生意,或者是毫无效果地训斥,导致夫妻意见不一致而更加疏远的恶性循环。由于反馈调节系统不灵,在孩子受到处分甚至辍学的一系列事件中,家庭不能通过改变策略以维持平衡,最终导致孩子进一步越轨而犯罪的恶果。
Minuchin.S为以下家庭贴上病理的标签:当家庭面临应激情境时,家庭互动模式和界限的僵化程度增加,从而阻止对任何其他选择的进一步探索。正常的家庭恰恰相反,通过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和足够的灵活性以允许家庭重建,来适应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应激[14]。
4 家庭治疗对个案家庭的干预过程
从家庭治疗的系统性视角看,问题家庭的互动方式、僵化的家庭结构等导致家庭功能不良,而出现家庭成员个体的心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家庭成员改变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重建家庭功能。
4.1 探索家庭新格局
4.1.1 挖掘家庭内部的有利资源
赵某某家庭结构健全,从小一直是父母带大,几乎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并不缺少父母的关照,也没有明显的人格缺陷。目前,他父母关系较为稳定,能意见一致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并且认识到了家庭教养方式存在的问题,愿意以后多抽时间陪孩子。按照家庭治疗的资源取向,这些有利因素都可以成为家庭成员打破已有的沟通模式和循环格局而建立新的家庭格局的资源。心理学工作者通过对问题的分析,一方面帮助赵某某父母增加战胜目前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调整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增强家庭凝聚力。
4.1.2 认识不良的循环
在帮助家庭认识到过去的不良沟通模式的弊端后,心理学工作者进一步融入到赵某某家庭中,同家庭成员一起探索新的家庭互动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赵某某的父母主动认识到了原有家庭模式中系统和边界存在很多问题。赵某某母亲也发现自己和儿子过于紧密的关系,可能冷落了丈夫;赵某某父亲也意识到由于自己过分关注生意,而游离在家庭之外,导致妻子对其埋怨;而孩子在父亲的游离和母亲的粘滞中也会选择从家庭的矛盾中逃避,从而导致越轨和犯罪行为。
4.2 建立新的反馈循环系统
家庭系统中的不良反馈也会受到更高层次反馈过程的重新调整。心理学工作者可能会以某种方式重新建构家庭组织,为达到互动的稳定性而创设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该案例中,心理学工作者加入到家庭循环中,通过让父母反思,把焦点集中在调整父母双方的互动关系,以免这种关系由于孩子的越轨问题互相埋怨而导致失控;并进一步通过促使父亲和母亲形成一个自我校正系统,打破以前家庭通过孩子的症状行为而维持家庭平衡的病理性的调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更高层次的反馈过程把心理学工作者、父母和孩子都包括在内,这样更高层次的反馈就会对较低层次的反馈过程进行重新调整。换一种说法,这个“心理学工作者—父母—孩子的系统”改变了那个“父母—孩子的系统”[15]。
4.1.3 安全套的推广使用 使用安全套是减少暴露危险的最直接方法之一,是阻断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重要手段。早在泰国推行“100%使用安全套”行动后,安全套使用率大幅上升,大大降低了泰国HIV感染人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此后该项目计划在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和中国等国家推广实施[29]。但配偶间安全套的使用目前仍处于降低水平,据国内一项对妊娠妇女的调查显示非常愿意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55.00%~58.80%[30],在配偶间推广使用安全套仍需加强健康教育和引导。
4.3 重新恢复家庭功能
4.3.1 发挥次系统的功能
结构派家庭治疗理论认为,在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之间还可划分成较小的系统,叫作次系统,如夫妻、父子、母子等。在本案例中,心理学工作者注意修复了夫妻次系统和父子次系统的关系,发挥夫妻了联盟的作用,同时注意到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提高父亲在教育孩子中的作用。
4.3.2 重新界定边界
家庭次系统存在边界,边界的存在决定次系统成员之间和次系统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角色分工和沟通方式。本案例中,母子之间的边界模糊,母亲在家里管得过多,因此,在干预过程中,心理学工作者有意强化了母子之间的边界。同时鼓励父母之间多交流,并让父亲认识到自己的沟通方式存在的问题,加强了父子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弱化了他们之间疏离的边界。
4.3.3 角色任务合理明确
每一个功能健康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中都承担着合理的角色和任务,角色任务应该恰当,否则影响家庭结构的合理运转。在本案例中,父亲在家庭中承担的任务不足,心理学工作者在干预中强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同时,也让母亲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并积极支持丈夫发挥父亲的作用。
4.3.4 促进沟通
Alexander和Parsons提出的功能性家庭治疗是通过促进母子间的沟通来减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遏制犯罪动机,并提出了具体的干预措施,包括建立家庭规则和系统地对家庭成员进行沟通的辅助训练等。本案例中心理学工作者通过提高父母对孩子的支持以及减少对孩子的负面评价,并让母亲意识到母子沟通的重要性,有效地改善了母子交流的模式,对矫正赵某某的不良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16]。
5 相关反思
家庭治疗的主要思想来自于西方,因此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对个案的影响,考虑文化适应现象。
5.1 循环因果的逻辑可能会造成对权力处于弱势的家庭成员不公
循环因果逻辑认为家庭中每位家庭成员都要对家庭系统功能失调负责,在这种逻辑下,父母不需要对事件负全责,孩子却要肩负部分责任,容易造成父母对责任的逃避。女性主义家庭治疗师也对这种家庭系统论进行了批判,她们认为这种系统论隐含着对男女地位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的认可,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不公平。
中国传统家庭一般是男权主义下的家庭,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才能使家庭系统维持平衡。这样可能会忽视女性和孩子在家庭中可能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主义家庭治疗师认为当家庭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或者暴力行为时,治疗师还保持中立就是对男女不平等地位的默认和宽恕[17]。因此,家庭治疗师在对权力失衡家庭进行治疗时,就要考虑来自社会文化中不对等的性别结构的影响,或者家庭特殊经历或者结构的影响,这样有助于理解家庭问题并不是个人或是夫妻互动出了问题,还有来自大环境社会文化的问题,能够减少对个人的责备,而朝着思考如何能够产生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改变家庭中的权力不平等,为弱势一方赋权和争取平等。
当代中国家庭模式具有复杂性,很多家庭未必是传统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往往会有另外一种权力表现,比如本案例中的女性在家庭权力可能更大,男性反而处于弱势地位。该案例中,尽管赵某某家庭形成了不良的循环因果,但是分析起来是由于母亲强势,父亲退缩,所以母亲在家庭不良循环中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要合理地给孩子父亲分配权力,让他重新回归父亲的位置,重新恢复家庭平衡。
5.2 不能忽视解决个体问题
近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很大,加上社会文化的变迁,家庭伦理和价值体系出现了很多混乱和失范现象,从而导致一些个体出现心理偏差和人格缺陷。因此,如果仅仅对家庭系统格局理解和改变,而忽视某个特殊个体的问题的解决,也可能导致家庭系统问题的循环格局难以被打破[18]。
该案例中,孩子尽管人格基本健全,但由于长期处于缺失功能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在解决家庭基本问题、恢复家庭功能之后,还需要进一步针对孩子的问题进行个别化访谈,维持家庭治疗的效果。
5.3 家庭功能具有文化特性
对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判断,需要结合家庭所处的文化环境来进行,否则会将一个不熟悉的家庭模式贴上功能失调的标签,而这个被贴上功能异常标签的家庭可能与该家庭所属的文化是相适应的。因此,要从家庭所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结构背景的角度,了解家庭,在看到家庭内在成员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的影响[19]。
例如,在案例中与恢复家庭功能相关的家庭关系因素、家庭边界因素、家庭规则和沟通方式上,中国家庭都有着和西方家庭不同的标准,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家庭功能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家庭。
[1]Minuchin S,Lee WY,Simon GM.Mastering Family Therapy:Journeysof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M].New York:Wiley,1986:22-27
[2]蒋索,何姗姗,邹泓.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3):394-400
[3]裴建寿.家庭治疗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J].综合论坛,2014(9):352-352
[4]胡赤怡,李维榕,王爱玲.试论家庭治疗的理论基础[J].医学与哲学,2005,26(8):64-64
[5]胡赤怡,李维榕,王爱玲.浅论家庭治疗的工作概念[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4):487-488
[6]Minuchin S.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M].Cambridge,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57-58
[7]汪新建.关系的探究与调整:西方家庭治疗的新视角[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0-91
[8]Walsh F.Normal family processes[M].3rd Edition.New York:Guilford,2003:514-547
[9]方晓义,徐洁,孙莉,等.家庭功能: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4):549-549
[10]郑希付.行为与家庭[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5-116
[11]Shek Daniel T L.The Relation of Family Functioning to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chool Adjustment,and Problem Behavior[J].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97,158(4):467-479
[12]Shek Daniel T L.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chool Adjustment,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J].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2002,163(4):497-500
[13]刘芹.优化家庭功能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键[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5):16-20
[14]Irene Goldenberg,Herbert Goldenberg.家庭治疗概论[M].6版.李正云,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4-166
[15]Bradford P Keeney.变的美学:临床心理学家的控制论手册[M].杨韶刚,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74-92
[16]邹泓,张秋凌,王英春.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的研究进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3):123-123
[17]尚晓丽.西方女权主义家庭心理治疗发展概况[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3):28-30
[18]郁之虹.家庭系统理论视域下的家庭暴力:互动因果的矛盾循环格局[J].社会工作,2014(6):87-88
[19]赵芳.家庭治疗的发展:回顾与展望[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96-97
10.3969/j.issn.1673-2006.2017.12.002
D917.6;C913.5
A
1673-2006(2017)12-0005-06
2017-08-15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合作的社区矫正心理服务体系构建的研究”(12219rwsk2015B05);安徽省2017年度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目(gxbjZD37)。
姚峰(1973-),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家庭治疗、犯罪心理学。
刘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