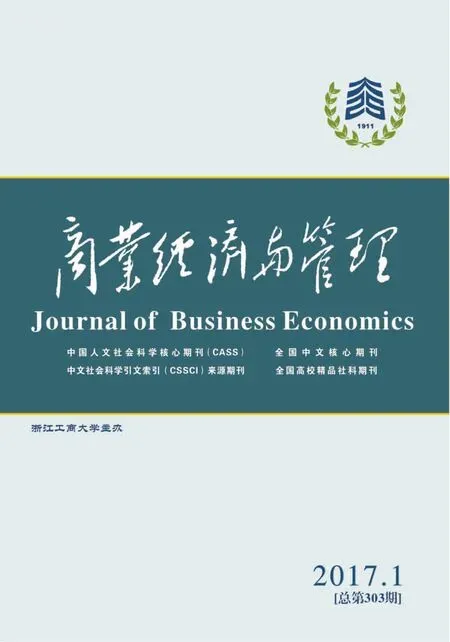美国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
2017-04-12丁涛
丁 涛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美国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
丁 涛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美国制度学派尽管属于非正统经济学,但对西方营销学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制度学派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美国学派和老制度学派,前者在流通与营销的课程开设、分析方法及其初步的理论构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后者对流通与营销理论体系的综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代表营销理论体系构建的巅峰之作明显体现了制度主义思想的充分运用和发挥。可以说,美国早期流通与营销理论扎根于美国制度学派,尤其是老制度经济学。这一研究发现为学界更全面的认识流通与营销理论提供了新视野,对我国营销学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流通;营销;老制度学派;美国学派
营销学起初是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产生的,但今天学界关于经济学与营销学之间的对话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营销管理范式主导着美国营销学的发展,致使主流学界对营销的理解局限于管理学的视野内,并认为营销学属于管理学的分支[1]。我国营销学主要引进和跟随美国主流思想,在教学与研究中严格遵循着营销管理范式,但忽视了对思想史的考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与营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营销学在从经济学独立出来之前,其前身是作为一门研究商品流通的经济学而存在的。“营销”这个术语也是从“流通”中诞生的。美国商品流通领域的研究课题主要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学派完成的。但美国制度学派作为一个非正统经济学①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属于西方正统经济学,而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美国制度学派和今天的演化经济学等都属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Unorthodox Economics),也被称为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其对营销学的影响就更容易被忽视。本文将从思想史的视角解读美国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以期更全面的认识营销学,进而推进经济学与营销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一、 美国制度学派的思想源流
美国制度学派是非正统经济学谱系中的重要代表,发端于19世纪的美国学派并与德国历史学派结缘,后由老制度学派继承和发展。19世纪美国的经济思想首先是美国特殊经济背景下的产物,最早体现在1787年美国宪法中,后由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正式提出,经过马修·凯里(Mathew Carey)、亨利·克莱(Henry Clay)、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西蒙·帕滕(Simon Patten)、理查德·伊莱(Richard T. Ely)等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一个与古典经济学对立的美国经济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支持者被称为“美国学派”。美国学派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主导了美国官方的政策制定,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民经济学说[2]112。然而,美国翻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后,转而宣传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hard)等古典经济学,甚至篡改了历史,将美国学派从经济思想史中删除,导致学界对这个学派的普遍陌生[3]319。
我们注意到,美国学派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学者,即来自德国的李斯特。他在流亡美国的六年(1825-1830)时间里与美国学派的核心人物凯里等结交,并成为该学派重要成员之一。李斯特的突出贡献是对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发挥,被誉为“第一代保护主义的整理者”[3]74,尤其是1927年完成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成为其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雏形。李斯特回到德国后,于1841年发表了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此书不仅标志着李斯特成为美国学派的集大成者,而且被视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开端[4]68。德国历史学派发展迅速,19世纪中期以后,施莫(穆)勒(Gustav Schmoller)领导的新历史学派曾统治着德国经济学。与此同时,德国成为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研究中心,德语成为学习经济学的必备工具,赴德国留学并从师于德国历史学派是众多美国学者所神往的[4]158,如帕滕和伊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由此,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条脉络从以马修·凯里和丹尼尔·雷蒙德为中心的保护主义者开始,经过李斯特传到德国,再通过罗雪尔的圈子传承给诸如帕滕和伊莱等在德国大学求学的美国学生”[3]80。帕滕、伊莱等师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美国留学生被称为第三代美国学派,同时也是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先驱。
德国历史学派实际上是对德国非正统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概括,被西方学者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克尼斯和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以施莫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以桑巴特和韦伯为代表的“新新”历史学派。李斯特则被视为“原始历史学派”的代表[5]233。与此类似,美国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可以概括为美国制度学派,划分为美国学派和老制度学派两个发展阶段。本文将按照这两个阶段探讨美国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
二、 美国学派的“重流通”思想
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主要意图是对抗古典经济学,使美国摆脱世界主义经济学的误导。按照斯密、李嘉图等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美国适合发展农业,向英国提供原材料并从英国进口工业品。美国学派认为这一思想将会把美国锁定在“劈柴担水”的地位上,并破坏美国的经济平衡,因而提出要优先发展工业,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美国的民族工业显然无法与英国抗衡,因而美国必须采取高额关税等保护主义路线,使民族工业避开国际竞争。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放弃国际市场,转向培育国内市场,即为工业品和农产品建立一个健康而稳定的国内需求市场。美国恰恰在这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如美国学派的代表亚历山大·埃弗雷特所言:“美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大量的人口以及用之不竭且多样化的自然资源,这些优势足以使美国‘成为一个在世界上自给自足并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3]106。美国学派深谙这一优势的巨大潜力,并提出“国内市场(内需)”说[2]117,即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使国内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形成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循环的经济系统。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关键在于开展国内自由贸易和降低国内流通成本,为此美国学派提出了“内部改善”纲领。*1824年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发明了“美国制度(体系)(American System)”一词,用来描述他的三部分纲领:保护性关税、国内(内部)改善和国家银行[3]34。在这方面,美国突出表现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引领了美国的“交通革命”。*最为突出的是铁路建设,1860-1890年间,全国铁路线从31246英里增加至166703英里,比1890年整个欧洲的铁路线(139000英里)还要长[8]185。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公共事业或公共投资持有的理念是“公共投资所获得的回报不能通过它产生的收益来测量,而是应该按照它在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体成本上的作用来衡量”[6]。这种理念促使美国的交通革命演变为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的革命,如1870-1910年间,铁路货运每吨每英里的运费由22美分降至0.75美分[7]。因此,美国崛起的背后是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国内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进而以迅速发展国内贸易来带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
据估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国内贸易大约等于对外贸易的二十倍,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8]189。就连主流经济学阵营的伟大导师马歇尔都不得不承认“美国不需要对外贸易……它的国内贸易额比整个西方世界的贸易额还大”[9]224。美国在19世纪的成功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启示是注重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诚如李斯特所言:“向海外追求财富虽然重要,还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对国内市场的培养和保卫”[10]162。
可见,美国学派体现了一种“重流通”的思想,这一思想有效推动了美国国内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但他们只是基于美国经济现状而进行的经验分析,注重政策和实际应用,并没有开展系统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19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专门研究商品流通的著述,如爱德华·埃克森(Edward Atkinson)1885年发表的《产品流通》(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11]。19世纪末以后,美国商品流通领域发生的变革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备受关注,相关研究文献随之大量出现。而该时期正是伊莱等第三代美国学派主导美国经济学的时代。
三、 美国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
(一) 流通与营销理论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
美国商品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与当时美国的经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其中两个突出的社会热点是农民问题和流通渠道变革。其一,农产品的流通与营销备受关注。宅地法的颁布、铁路的修筑、机械化的普及、地域的分工与专业化等因素推动美国农业生产力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得到迅速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生产过剩”[12]38-39。农产品缺少销路且价格日益下跌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农民问题随之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话题。显然,此时农民的困境不在农业生产,而在农产品流通。因此,美国早期的流通与营销著述中往往注重对农产品流通的讨论。
其二,美国商品流通渠道发生了深刻变革。19世纪美国商品流通渠道呈现出高度的分工与专业化特点。生产者通过专业的销售代理(selling agent)将商品销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将商品转售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将商品转售给最终消费者。由此形成了19世纪美国商品流通渠道的正统模式(orthodox type),即生产者—销售代理—批发商—消费者[13]69-71。但19世纪末以后,这种正统模式趋于解体,主要表现为生产者绕过中间环节并独立承担各种商品流通活动,从而由生产者(producer)演变为生产商(merchant-producer)。具体而言,生产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销售人员和广告直接与批发商或零售商接触,从而绕过销售代理,还可以通过广告和品牌策略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从而绕过所有的中间商[13]73。减少中间环节成为20世纪初美国流通渠道变革的主旋律。流通渠道的变革引发了美国社会对相关问题的激烈讨论,例如商业组织的社会功能、生产商与中间商的利益冲突、广告和品牌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等。
(二) 流通课程的出现与营销学的产生
在上述经济社会背景下,美国高校产生了开设一门被称为“流通产业或部门(Distributive Industries)”相关课程的冲动,而且很多高校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中[14]21-22。例如,密歇根大学1902年开设了美国第一门流通课程,被称为“美国的流通与调控产业(Distributive and Regulative Indust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俄亥俄州立大学1905年专门开设了“产品流通(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课程。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流通课程中都出现了“methods of marketing goods”,此处“marketing”尽管还只是个动名词,但已经预示了“营销学”的诞生。
“Marketing”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产生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巴特勒(Ralph S.Butler)[15]7。巴特勒于1910年起在威斯康辛大学工作,并从事销售领域(field of selling)的教学。在备课过程中,巴特勒发现,还没有一门课程能够涵盖整个销售领域的内容,因此,他自己设计一门称为“营销方法(Marketing Methods)”的课程,后来改称为“营销(Marketing)”。巴特勒将这门课程描述为:“简言之,我意在关注一个产品的发起者(生产者或制造商)在实际开展人员促销和广告之前所需要做的所有工作”[14]24。也就是说,巴特勒站在一个生产者或制造商的角度看如何将产品推向市场。显然,巴特勒所设计的营销课程实际上是对上述流通课程中的“methods of marketing goods”的系统总结,使“Marketing”作为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来。就此而论,“营销”是脱胎于“流通(distribution)”*“distribution”在国内营销学文献中多被译为“分销”,而在国内流通经济学文献和日本流通与营销学界被译为“(商品)流通”,本文采用后者。而产生的,前者显然在后者的范畴之内。为什么会在“流通”中产生“营销”这个新的术语呢?
日本学者已经间接回答了这一问题,即市场营销首先是作为现代生产者的流通活动而出现的[16]83[17]142。结合上述美国流通渠道变革的背景不难发现,生产者打破传统的流通渠道模式,踏足流通领域并承担了原来由中间商从事的商品流通功能。生产者(producer)由此演变为既负责生产功能又承担流通功能的生产商(merchant-producer)。一言蔽之,市场营销起初被用来专指一种特殊的流通,即生产者承担的流通功能;而营销学就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或以微观的企业管理视角来研究商品流通,即夏春玉教授所谓的“流通管理理论”[18],也与田村正纪教授所谓的“微观流通流”[17]7相近。
营销这个概念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同时,其含义从上述微观视角的营销管理演变为宏观视角的商品流通,或者说,营销的含义已经包括了商品流通的全部内容。因此,在一些经典的营销著述中,营销与流通这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替换。例如,梅纳德(Harold H.Maynard)等在他们的名著《营销原理》*此名著在民国时期曾被引入我国,即由丁馨伯1933年编译的《市场学原理》,是国内最早的营销学著述,当时“marketing”被译为“市场学”。开篇之语就指出:“用‘营销’这个术语来指代与商品所有权和实体转移的商业活动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而流通又被当做营销的同义词使用”[19]3。尽管承认流通与营销之间的对等关系,但美国学者在相关著述的正文中普遍使用了“营销”这个概念,而“流通”逐渐被遗忘了,即流通领域的研究文献多被冠之以“营销”。*笔者在整理文献时发现,上个世纪20年代的营销学文献中,流通与营销这两个术语经常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而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以后,营销学文献中就极少提到流通了。但这并不是说,流通不重要了,而是因为该时期营销的含义已经包含了流通的全部内容。不幸的是,今天的主流营销学又把原有的流通含义剔除了。因此,为避免因营销被理解为微观营销而引起的不必要争论,本文没有将流通与营销分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营销管理范式致使主流学界对营销的理解又从宏观或整体的含义退回到其最初的微观的企业管理含义。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门流通课程的开设和营销学的诞生正值伊莱等第三代美国学派活跃在美国学术舞台的时代。上述两门流通课程的开设者Edward D.Jones和James Hagerty都是伊莱的学生。为营销学的诞生做出重要贡献的巴特勒来自威斯康辛大学,这所大学正是伊莱经济思想的集中地。下文将紧接着这一问题介绍伊莱在威斯康辛大学培养的流通与营销理论的早期贡献者。
(三) 伊莱等第三代美国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
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都曾赴德国留学并师从德国历史学派,其中,最著名是亨利·亚当斯(Henry C. Adams)、约翰·卡拉克(John B. Clark)、*卡拉克尽管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批判过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但由于崇尚边际分析,最终成为一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4]159。理查德·T·伊莱(Richard T.Ely)和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前三位倡导成立了美国经济学会(AEA),也因受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而被美国经济学界昵称为“德国人”[4]159。就职于威斯康辛大学的伊莱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引领着年轻一代的美国学者对正统经济学发起了猛烈攻击,并宣称:“新一代美国人正在接受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而彻底抛弃英国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干瘪骨架”[20]103。正统经济学看似以复杂而深奥的理论自居,但实际上是与现实脱节的干瘪骨架,伊莱则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因此,伊莱在为他的学生建议毕业论文的选题时,着眼于当时美国的现实国情,切中商品流通与营销领域诸多热点,诸如流通渠道冲突问题,农产品流通问题,零售、批发等商业组织的历史演变,广告、商标等的社会福利影响等。
正是在伊莱的培养和熏陶下,威斯康辛大学出现了美国早期流通与营销理论的重要贡献者,该大学也由此成为美国流通与营销思想发展的领导者[15]5。这些学者包括Edward D.Jones,Samuel Sparling,James Hagerty,Henry C.Taylor,Benjamin H.Hibbard,Paul Nystrom,Theodore Macklin等。Jones和Hagerty在上文已提及,其中,Jones不仅是流通课程的最早开拓者,也是最早提出建设流通或营销科学(a philosophy or science of distribution or marketing)的学者之一。Sparling(1906)的《商业组织入门》可能是最早开展流通机构分析和流通功能分类研究的流通著作。*此书分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流通部门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distributive industries)”,包含市场的演化、交换、直接销售、批发和零售、旅行人员销售(traveling salesmanship)、邮购、广告、信贷(credits and collection)六章,内容丰富,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该书还对商业活动进行了分类,尤其注重对流通和营销活动的分析。Nystrom(1915)的《零售经济学》不仅是开展专门的零售机构分析的奠基之作,也被认为营销学最早的著作之一。Taylor早在1900年左右就开展农产品流通的相关教学和研究,*Taylor是伊莱的杰出门生之一,在德国留学时还亲身感受到了施穆勒的熏陶,回国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讲授经济史和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是针对正统经济学缺少空间概念而产生的。Taylor本人将经济地理学描述为:“经济地理学这门课程要用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间描述每种重要的农产品在哪里生长,在哪里消费,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运输、销售和处理(transportation,merchandising and processing)”[20]105。显然,农产品流通在这门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Taylor的领导下所做的大量农产品流通研究中,首先是将整个流通过程清晰的展现出来。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最早认识到,农产品的中间商之所以索取价格根源于他们承担不可或缺的流通功能。此观点为农产品流通与营销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随之,威斯康辛大学产生了大量的农产品流通与营销著述。其中,Hibbard和Macklin在1921年分别发表的《农产品营销》和《高效的农业营销》成为农产品流通与营销研究领域的经典力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学者对渠道冲突和商业组织的研究过程中酝酿了美国机构分析(institutional approach)的产生[20]104,这是美国制度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
除了机构分析,美国学者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还形成了另外两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式,即商品分析和功能分析。此时,美国学者开始探讨这三种分析方式的综合,试图为营销学构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表现为“营销学原理”等相关著述的出现。其中,颇有影响的的三本力作是康沃斯(Paul D.Converse)1921年出版的《营销方法与政策》、卡拉克(Fred E.Clark)1922年出版的《营销学原理》和梅纳德(Harold H.Maynard)等1927年出版的《营销学原理》。上述学者无疑都受到了威斯康辛大学流通与营销学者的熏陶,其中,克拉克还强调了亚当斯对他的影响和激励;康沃斯(Paul D.Converse)则受到了伊莱和康芒斯等的直接影响[14]251-252。他们尝试将商品分析、功能分析和机构分析综合到一起,力求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他们的分析思路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认为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功能,因而可以通过功能分析推演出各种机构和组织的产生和演化过程,由此可能实现对流通或营销系统的整体分析。然而,他们的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各类流通与营销机构未能有机结合到一起。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开始探讨新的营销理论整合思路,即回到了源自美国学派的机构分析。而此时的机构分析已经演变为老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
四、 老制度学派对构建流通与营销理论体系的深远影响
(一) 制度主义广泛渗透在重要的流通与营销著述中
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老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些最重要的流通与营销专著直接以“制度(institution)”命名,例如《营销制度》(The Marketing Institution)和《营销学:制度分析》(Marketing: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前者的作者布莱耶(R.F.Breyer)非常崇尚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是康芒斯;后者的作者杜迪(Edward A.Duddy)和莱夫赞(David A.Revzan)则直接采用了康芒斯对制度的定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institution”在上文中被译为“机构”,但在此处被译为“制度”。不难发现,前者是国内营销学文献中常见的译法,而后者则是经济学文献中的一般译法。同一时代和地域条件下,同一个术语在经济学与营销学中的不同译法,表明了两门学科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是不必要的,下文对此作出解释。
如上所述,institutional approach源自威斯康辛大学对各种生产或流通机构的分析,因而被理解为“机构分析”。在国内的营销学文献中,这个短语至今还被译为机构分析,这种译法完全符合西方主流营销学界的一贯认识。也就是说,institution被理解为从事生产或流通活动的主体,如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等。机构分析主要运用归纳、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这些主体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并没有得到主流营销学界的认可,认为它侧重统计数据的堆积和对现象的描述,缺乏理论高度。显然,这根源于正统经济学对历史分析和归纳方法的批判。诚然,早期的流通机构分析被认为停留在对机构进行历史和现状的描述层面上,但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的机构分析著述已经发生重要的转变。
这一转变主要受益于老制度学派康芒斯的影响,康芒斯是伊莱的得意门生,也是老制度学派的集大成者。康芒斯对institution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对各种生产或流通机构的描述,而是将其理解为“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或“集体行动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人行动”[21]87-92。康芒斯说:“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甚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公会、联邦准备银行、‘联合事业的集团’以及国家”[21]87。可见,在康芒斯的理论体系中,通常所理解的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机构”,而属于“运行中的机构(going concern)”。
在康芒斯看来,运行中的机构是一个反应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体现人的意志和目的性,这既不同于正统经济学中类比于物理学的机械结构,也不能看作类比于生物学的有机结构。运行中的机构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运行中的工厂”,体现人类意志对自然的控制,强调生产能力并遵循效率原则;另一个是“运行中的营业”,体现人类意志对交易的控制,或对人的控制,强调议价能力并遵循稀少性原则。正统经济学多局限于效率原则的应用,重视投入产出率的研究,因而被康芒斯称为工程经济学。而制度经济学更加重视人的目的性,强调所有权转移的研究,因而被康芒斯称为所有权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康芒斯揭示了“营销”*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的中译本是由著名学者于树生翻译完成的,出版于1962年,其中,marketing被译为销售,因为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正式使用营销一词。一词的双重含义,即遵循效率原则的实体转移过程和遵循稀少性原则的所有权转移过程[22]287-291,这类似于国内流通学界所谓的物流和商流。
可见,institution的这个术语,从发端于威斯康辛大学的institutional approach 到康芒斯的巨著institutional economics,词的形态本身看似别来无恙,但含义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中文从“机构”到“制度”的两种不同译法更是清楚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不曾被学界所注意。也就是说,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受制度学派的影响,institution的含义已经由简单的“机构”演变为复杂的“制度”,因而上文中的institution和institutional approach应分别译为制度和制度分析。当然,康芒斯对institution的定义引起了不少误解和批评,为此他区分了institution 和institute,目的是提醒学界不要把前者简单地理解为后者[23]。与production和product之间的关系类似,institute是institution创造和执行的产物,如规则、权力、义务、债务等。但这一区分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在多数学者看来,康芒斯的理论体系总是晦涩难懂的,尤其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康芒斯对上个世纪30-50年代营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上述提到的两本重要著作就是例证。布莱耶对营销制度的研究不再是通常所谓的机构分析,而是倾向于一种动态的系统分析,尽管没有确凿的把握说布莱耶受到了康芒斯的直接影响,但二者对institution的认识是相通的。 杜迪和莱夫赞直接采纳了康芒斯对institution的定义,强调了人类行动是集体性质,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以团体行动为特征[24]。他们认为通常的流通机构应该是指“marketing agency”,因此,institutional approach是一种系统而总体的分析方法,即“将市场结构理解为由各个相关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受经济和社会力量调节的商品流通过程中,成长和变化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25]vi。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制度分析将传统商品分析、机构分析和功能分析整合到一起,但他们的研究似乎并未达到这一目的[26]。实际上,他们所采用的制度分析与阿尔德森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后者做出的成就远远高出前者,并被誉为营销学之父,其思想源泉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康芒斯。
(二) 老制度学派集大成者康芒斯与营销学之父阿尔德森
关于阿尔德森的营销学理论,西方学者一般会首先提及两篇著名的论文,即1948年与库克斯合作的《营销理论的构建》(Towards a Theory of Marketing)和1958年的《营销学的分析框架》(The Analytical Framwork for Marketing)。《营销理论的构建》是阿尔德森构建营销理论体系的开山之作,其中可以明显看出康芒斯的深刻影响。文中指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一个基本的分析思路是从社会学中团体行为(group behavior)的概念入手或奉行团体行为主义(group behaviorism),“专注于研究团体行为一般模式的营销学者会发现这种研究思路前景广阔”[27]。团体行为成为后来阿尔德森构建营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28]13。阿尔德森所谓的制度主义者主要是指康芒斯,他对团体行为主义的认识源自康芒斯的“集体行动”,并在1957年的名著《营销行为与经理行动》中明确指出:“他(康芒斯)所惯用的‘集体行动’,大体上相当于本书中采用的‘团体行为’”[28]21。*上文已经指出,杜迪和莱夫赞两位学者也采用了康芒斯“集体行动”这一概念,而这两位学者也是阿尔德森所非常熟悉的,并引用过他们的《营销学:一种制度分析》,因此,阿尔德森也可能受这两位学者的影响。但通读阿尔德森的著述会发现,他一定多次翻阅并熟读了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在1950年发表的《组织行为系统的生存与调整》一文中,阿尔德森在团体行为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主义分析中的最基本概念,即“组织行为系统(organized behavior system)”,这一概念也是源自康芒斯的“集体行动”,或者说是直接从康芒斯的“运行中的机构”延伸而来。他说:“组织行为系统这个概念与康芒斯的‘运行中的机构’相似……总体的交换行为更类似于康芒斯的‘集体行动’这一个概念”[29]77。阿尔德森在1958年那篇著名的论文《营销学的分析框架》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尽管“组织行为系统”与“运行中的机构”两个概念稍有差异[30]66。基于此,就不难理解阿尔德森对institution的认识和对传统机构分析的批评。
如上文所述,在康芒斯看来,制度或集体行动实质上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阿尔德森认为对各种零售、批发或其他流通机构的分类、描述和运行分析,都是停留在对现象描述的水平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分析[28]22。阿尔德森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制度分析应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机构分析容易忽视这一问题。有趣的是,这类似于康芒斯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只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关注效率,而忽视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机构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对比类似于工程经济学与所有权经济学之间的对比。上文已经指出,康芒斯揭示了营销的双重含义,这直接影响了阿尔德森。阿尔德森曾指出:“他(康芒斯)对营销过程提出了一种新观念,他对其二重性质的认识是有趣的”[28]21。其实,康芒斯对营销的这一认识未见其他学者提到过,唯独阿尔德森注意到了,足见他对康芒斯经济思想的熟悉和认同。
康芒斯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有所不同的一点是,后者一般认为制度分析应该遵循与牛顿主义对立的达尔文主义研究范式,将社会类比为一个有机体,而康芒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21]118-146。采用达尔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老制度学派奠基人凡勃伦。康芒斯认为,基于有机体的类比以及达尔文式进化的考虑,凡勃伦的理论属于“自然的淘汰”,这依然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忽视了人的意志和目的,而制度经济学应该是“人为的淘汰”[22]313-317。康芒斯认为自己的理论避免了这种错误,是因为“把个人的交易和集体行动的运行中的机构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22]316。康芒斯明确区分了机械结构、有机体和运行中的机构[22]272-283。其中,后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运行中的机构包含着人类的目的性和意志,而生物有机体显然没有这样的特点。当然,对于康芒斯的这一观点,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但阿尔德森基本上站在了康芒斯的一边。他认为,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的联系“不能像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跟随者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将达尔文的理论扩展为一门进化社会学”[28]18。因此,阿尔德森所谓的“组织行为系统”不同于生物有机体,前者将团体的目标以及个体的身份(status)、期望(expectation)等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人类社会有目的的选择,而非自然选择或达尔文主义的盲目选择。
康芒斯研究集体行动和运行中的机构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康芒斯的所有贡献中,似乎唯有这一洞见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尤其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兴起的科斯、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或交易费用经济学所青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称自己的理论以“交易”为分析单位[31]64,但阅读此书时发现名不符实。究其原因,新制度经济学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与集体行动的制度主义决裂了。阿尔德森真正洞悟了“交易”内涵,多次强调康芒斯的这一贡献。他在《营销学的分析框架》一文中说:“在所有经济学家中,康芒斯对交易这个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给予最多的关注”[30]64。他在名著《营销行为与经理行动》中指出:“对交易的分析是非常少见的……康芒斯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比任何别的经济学家都多”[28]320。交易这个基本单位在阿尔德森致力于构建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在上述提到的著述中都提到了“交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康芒斯提出的“战略交易(strategic transaction)”和“惯例交易(routine transaction)”这两个概念,并将前者修正为“全谈判交易(fully negotiated transaction)”,这是为了凸显交易中谈判费用的重要性。基于此,阿尔德森也沿用了康芒斯在分析交易时所采用的议价权力(bargaining power)、等待权力(waiting power)等概念。在《营销行为与经理行动》一书中,阿尔德森专门用了两章内容(第5、10章)论述了议价或谈判、全谈判交易、惯例交易等相关问题。谈判或议价实际上是围绕着交易的本质开展,即所有权的转移,主要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商流。因此,阿尔德森主要依据中间商在所有权转移过程承担的功能对其进行明确的分类,如服务批发商、佣金商、经纪人等[28]304-306。
在1965年的名著《动态营销行为》中,阿尔德森将“备货(assortment)”这个概念融入到“交易”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交易分析公式。阿尔德森指出:“读者肯定会发现个体与‘团体’的概念的对应关系可以类推至商品与‘备货物’的概念之间”[28]196。可见,备货是一个商品集合的概念,似乎也是受到康芒斯“集体行动”的启发而提出的。正是商品集合的这一概念使其交易公式表现出独特性,被交换的商品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而是与其他商品组合起来形成备货的整体效能(potency)。以两种商品的x、y直接交换为例,二者对应的备货分别为A1和A2,则两个备货所有者发生交易的基本条件是交易后的备货效能提高了,即P(A1-x+y)>P(A1),P(A2-y+x)>P(A2)。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每个商品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商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而改变了原有备货的价值,这可能是打破“贸易乃零和游戏”这一固有观念的最有力解释。另外,在这个交易公式中,阿尔德森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避免了正统经济学的均衡和效用最大化假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都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和选择[32],并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最大化。对于这个问题,阿尔德森也受到了康芒斯的影响,康芒斯称正统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为“无限选择对象的谬论”[21]377。
备货(物)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最终的消费者而言。在阿尔德森看来,流通或营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备货物。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营销或流通的功能就是将不适合消费者的聚合物(conglomeration)转变成适合消费者的备货物,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匹配。阿尔德森将匹配过程归结为四个环节,即分类(sorting-out)、集中(accumulation)、分散(allocation)和备齐(assorting)。此过程中,除了要完成各种关于所有权转移的交易活动外,还要完成各种关于形态、时间和空间的转换(transformation)活动。基于此,阿尔德森提出了“交变链(Transvection)”这个自己首创的分析单位。*关于Transvection的中文译法参见吴小丁和张舒的讨论[34]。交变链包含了某一商品从原材料经过中间备货和变换后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国内外流通学者经常讨论的商流和物流功能显然包含在交变链之中。但阿尔德森似乎将生产过程也纳入到交变链和流通过程中,因为在他看来,生产过程或形式效用(form utility)的创造取决于营销决策。而且,他将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allocation)也纳入到流通过程中研究。
显然,备货是一个横向的商品集合概念,而交变链是一个纵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描绘了一个宏观的营销或商品流通图景。但遗憾的是,阿尔德森在为建立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而绞尽脑汁的同时,也倾向于接受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自己陷入了学术分裂症之中。他将自己定位为“微观功能主义者(microfunctionalism)”,专注于家庭和企业组织的营销管理研究,为营销管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营销管理主要遵循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奉行微观经济学范式的营销管理的兴起,阿尔德森的功能主义分析就被抛弃了。如上所言,功能主义分析实际上是宏观导向的,因此,备货和交变链这两个概念早已被主流学界遗忘。日本著名流通学者石原武政深谙阿尔德森对流通理论的贡献,尤其将“备货”视为理解流通或商业的极其重要的概念。他在名作《商业组织的内部构成》中指出:“毋庸置疑,如果理论关心的是个别企业的营销活动,就根本不可能关心备货形成的概念;而当理论关心的是流通或商业整体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涉及备货形成的概念”[33]31。诚哉斯言,今日营销学将阿尔德森之备货等核心概念弃之不顾。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营销思想史与经济思想史并于一起考察,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属于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尝试。从营销思想史的角度看,本文考察了上个世纪初至50年代末营销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上述时间段正是美国学派和老制度学派活跃于美国学术舞台的时代。本文将这两个学派理解为美国制度学派的两个发展阶段,进而分别探讨了他们对美国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影响。
美国学派不仅对美国流通课程的开设和营销学的诞生发挥了积极意义,而且直接影响了流通与营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以伊莱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提出并充分发挥了机构分析的研究思路。老制度学派对流通与营销理论的综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康芒斯的制度主义思想广泛渗透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的相关著述中。其中,代表营销学理论体系的巅峰之作是由阿尔德森完成的,这位营销学之父的力作中处处可见康芒斯的影子。
康芒斯提出的核心概念,如“集体行动”、“运行中机构”,以及“交易”这个基本分析单位,在阿尔德森构建其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他说:“在所有经济学家中,康芒斯最出色的表述了我所谓的‘功能主义分析’”[28]21。由此而论,阿尔德森所要构建的营销学理论框架扎根于制度主义中,他曾在1950年指出:“任何理论视角的营销制度研究必须依赖于那些采用制度主义分析的经济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如康芒斯、韦伯、克拉克”[29]76。但不幸的是,制度主义分析和阿尔德森的功能主义分析似乎已经被学界遗忘。
制度学派在推进营销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首先着眼于商品流通问题的领域。“营销”在诞生之初是从流通课程中分离出来的,即生产商从事的流通活动,或理解为企业管理视角的微观流通。但营销这一概念普及以后,其含义不再局限于微观流通,而更加强调宏观流通的含义。因此,美国学者上个世纪30-50年代开展流通与营销理论的综合时,基本上采用了营销这个概念。营销与流通在营销思想史中的亲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这对今日营销学的启示是,对于营销概念的解释不能局限于微观管理的视野,对宏观营销或流通的排斥无异于对营销思想史的忽视或无知。
对我国营销学界而言,全面而系统的把握营销的上述含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营销学不应再局限于引进甚至直接照搬美国的微观营销范式,而应在立足我国国情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宏观流通与营销理论。
[1]夏春玉,丁涛.营销学的学科渊源与发展:基于思想史视角的探讨[J].当代经济科学,2013(1):103-109.
[2]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11-125.
[3]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贾根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4-319.
[4]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高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68-158.
[5]埃里克·S·赖纳特.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C]//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王中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8-245.
[6]贾根良.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2(2):83-90.
[7]王旭.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历史作用[J].世界历史,1986(6):11-18.
[8]何顺果.关于美国国内市场的形成问题[J].历史研究,1986(6):174-189.
[9]马歇尔.货币、信仰与商业[M].叶元龙,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4.
[10]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2.
[11]GOEHLE D G. A Historical Approach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saling Thought[C]// NEVETT T, HOLLANDER S C. Marketing in Three Era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Marketing History Conference. Landing: MSU,1987:225-241.
[12]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8-39.
[13]SHAW A W.Some Problems in Market Distribu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69-73.
[14]BARTELS R.The History of Marketing Thought[M].Columbus,OH:Grid,1976:21-252.
[15]BARTELS R.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ng Thought,1900-1923[J].Journal of Marketing, 1951,16(1):1-17.
[16]石原武政,加藤司.商品流通[M].吴小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3.
[17]田村正纪.流通原理[M].吴小丁,王丽,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7-142.
[18]夏春玉.流通、流通理论与流通经济学——关于流通经济理论(学)的研究方法与体系框架的构想[J].财贸经济,2006(6):32-37.
[19]MAYNARD H H,WEIDLER W C, BECKMAN T N. Principles of Marketing[M].New York:Ronald Press Co,1927:3.
[20]JONES D G B, MONIESON D 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Marketing Thought[J].Journal of Marketing,1990,54(1):102-113.
[21]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87-377.
[22]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72-317.
[23]COMMONS J B.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36,26(3):237-249.
[24]SAVITT R. Pre-Aldersonian Antecedents to Macromarketing:Insights from the Textual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1990,8(4):293-301.
[25]DUDDY E A, REVZAN D A. Marketing: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M].New York: McGraw-Hill, 1947:vi.
[26]ARNDT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ing Systems:Reviving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J].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1981,1(2):36-47.
[27]ALDERSON W, COX R.Towards a Theory of Marketing[J].Journal of Marketing,1948, 13(2): 137-152.
[28]ALDERSON W. Marketing Behavior and Executive Action[M].Homewood,IL:Richard D.Irwin,1957:13-320.
[29]ALDERSON W. Survival and Adjustment in Organization Behavior Systems[C]//WOOLISCROF B, TAMILIA R D, SHAPIRO S J.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to Aldersonian Marketing Thought.New York:Springer, 2006:75-94.
[30]ALDERSON W. The Ayalytical Framwork for Marketing[C]//WOOLISCROF B, TAMILIA R D, SHAPIRO S J.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to Aldersonian Marketing Thought.New York:Springer, 2006:61-73.
[31]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4.
[32]ALDERSON W. Transactions and Transvection[C]//WOOLISCROF B, TAMILIA R D, SHAPIRO S J.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to Aldersonian Marketing Thought.New York:Springer, 2006:229-249.
[33]石原武政.商业组织的内部构成[M].吴小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1.
[34]吴小丁,张舒.商品流通研究的市场营销学理论渊源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3):35-42.
(责任编辑 郑英龙)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School on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Theory
DING Tao
(SchoolofEconom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school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western marketing science, though it is under the unorthodox economics.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school experienced two developing stages that can be called the American school and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respectively. The American school had active influence on curriculum design, analysis method and preliminary theory foundation of distribution or marketing.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circulation and marketing theory system. The most outstanding academic work on marketing theory had fully assimilated the ideology of America institution school.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early American marketing science deeply rooted in institutionalist thoughts. The findings in this article expose marketing research to a new perspective, which has practical meanings to marketing science in China.
distribution; marketing;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the American school
2016-09-30
丁涛,男,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与营销思想史研究。
F710
A
1000-2154(2017)01-0005-10
10.14134/j.cnki.cn33-1336/f.2017.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