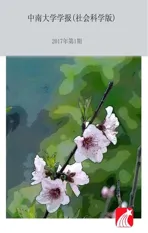个体网络借贷规制进路分析
2017-04-12刘骏
刘骏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个体网络借贷规制进路分析
刘骏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严守信息中介之定位,即否定了自身担保型平台、资产证券化的债权转让型平台的合法性,以此构成与学者们主张的学理进路之最大分歧。然而,严守信息中介的定性与司法案例中所呈现的风险是不相称的,足以证明这种规制进路的不合理,本质上就是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学者们所主张的学理进路则多将网络借贷不同模式的异质风险同质化处理,偏离了司法案例中的风险实际,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此,基于风险的差异化规制应该是个体网络借贷规制的最佳完善进路。
网络借贷;《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平台业务模式;司法案例;差异化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Mishkin的观点,金融中介具有可以降低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巨大优势。[1]传统上,金融中介可以分为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两种模式,但借助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兴金融模式是与传统模式迥然不同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2],而个体网络借贷就是其中的一种[3],同时也是“小微企业融资模式的创新”[4]。
自2007年以来,以P2P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个体网络借贷开始在我国落地生根,伴随着2013年互联网金融的爆发而“异军突起”,成为了互联网金融中的佼佼者,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众多问题,如“跑路”“非法集资”等案件频发。对此,政府监管部门也在积极探寻监管之策,自2015年《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互联网金融意见》)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定调以来,随后获得监管授权的银监会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紧接着2016年年初从中央到地方有大量的监管准备工作已经展开[5],号称“监管元年”的到来。2016年8月24日,中国银监会联合工信部、公安部等四部委正式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网络借贷暂行办法》),监管的“靴子”终于落地。相较于《征求意见稿》,《网络借贷暂行办法》除了具体监管细则有部分调整以外,整体上并无重大变化,继续沿用了限制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思路,即将网络借贷平台限定为一个中介服务机构。这与个体网络借贷的发展实际有着较大差异,预示着洗牌期的到来。
《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出台后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好评,其中不乏专业研究者,比如李爱君教授[6]、杨东教授[7]。这两位教授曾发表过相关个体网络借贷的规制观点[8,9],其观点与《网络借贷暂行办法》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那么,两位资深教授的观点为何前后存在较大差别?当然,也可以说《网络借贷暂行办法》的监管思路与多数学者的观点存在差异,这也表明学术界和监管层的规制进路并不一致。何以至此呢?诚然,个体网络借贷是现实中存在的产物,是优是劣需要现实来检验。换言之,关于个体网络借贷的规制进路选择应该从其发展实际出发。就法学研究而言,司法裁判案例是绝佳的现实研究样本。但是,相关研究只有一篇刑法规制的论文。[10]这足以说明此类基于实际的研究在个体网络借贷规制中被忽视。鉴于此,笔者借助北大法宝司法案例、裁判文书网、无诉案例三大权威裁判文书库,通过关键字检索获得了初步的裁判文书案例,排查了与个体网络借贷风险不直接相关的案例,最后获得150份裁判文书,构成研究个体网络借贷风险与规制的现实样本,以此来探索当前学术界与监管层的观点差异。
二、个体网络借贷规制的监管走向与学理进路之现实考察
我国监管层和学者们所主张的规制进路存在较大的差别,但是差别到底有多大,还需要展开进一步分析。对此,笔者进行了如下梳理。
(一) 个体网络借贷规制的监管走向之基调
在《互联网金融意见》出台以前,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就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等文件,但是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个体网络借贷也一直处于“野蛮生长”状态。而去年《互联网金融意见》的出台预示着“事情正在起变化”。
1. 我国的网络借贷平台规制的监管定调
《互联网金融意见》对个体网络借贷定了调,对其概念、服务范畴、法律性质、监管部门都进行了规定,自此,监管层拟将个体网络借贷平台限定为信息服务中介的意向已经十分明确。2016年8月底,《网络借贷暂行办法》正式出台,除了部分条款进行了小调整,基本上与《征求意见稿》保持了一致,对于网络借贷的规制具体如下:第一,明确网络借贷平台只能是信息中介,不能成为真正从事金融业务的信用平台,平台本身需要进行备案管理;其业务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划定了网络界定平台的行为权限。第二,确定了网络借贷行业监管的责任和分工,形成了银监会为主导,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门相协调的监管体制。第三,采用资金第三方存管、限制借款集中度风险、实名注册以及信息披露等方法来充分保障出借人利益。
综上,我国关于个体网络借贷的规制思路已经逐步清晰,明确了各类主体的义务与责任,当然其核心内容就是网络借贷平台严守信息服务中介的定位。
2.个体网络借贷规制的监管定调之实质影响
《互联网金融意见》出台后,有人认为这种定调否定了当前的非完全中介模式,网络借贷行业将面临大洗牌。[11]也有人认为这种定调并未否定其他类型模式,并集中讨论了当前几种模式“是否一定不具合法地位”。[12]然而,随着《网络借贷暂行办法》的出台,行业洗牌的担忧成为了共识。这种办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据称,《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出台后,在美国上市的知名网络借贷平台“宜人贷”股价狂跌22%,这表明了市场对于这一办法的预期并不看好。但是实际来看,这一反应有点过于激烈,因为《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只会影响部分平台的业务模式和大额借款。
通常,个体网络借贷模式被分为中介服务型、担保型、债权转让型三个大类[9],这种划分与《网络借贷暂行办法》的划分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根据这一监管规则就否定担保型、债权转让型的合法性是存在理解偏差的。根据网络借贷平台的“负面清单”规定,“直接或变相向出借人提供担保或者承诺保本保息”和“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是被禁止的,这两类行为就与担保型与债权转让型直接相关。但是细看,其规定并非“一刀切”。担保型平台分为平台自身担保型和第三方担保型,平台担保常用的就是平台垫付(主要是自有资金或风险保障金)和平台收购坏账债权,而第三方担保则以融资担保公司(如陆金所)、小额贷款公司(如有利网)等主体进行担保;而规定只是否定了平台担保模式,并不否定第三方担保,即平台本身不能成为“担保人”。债权转让型具体可以分为不改变性质的债权直接转让和改变性质的证券化形式两种,其中,是否改变债权本质是判断是否涉嫌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节点[12],而规定中只是禁止了类资产证券化的行为。我国债权转让的主流模式——宜信模式并不改变债权性质,其平台仍然只是一个信息中介[13],所以这里仅仅否定了实行资产证券化的债权转让型平台。是故,《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否定了自身担保型平台、资产证券化的债权转让型平台的合法性。
(二) 网络借贷规制的学理进路之梳理
学者们对于个体网络借贷的规制关注度较高,并形成了一定的学理进路。这种分析多以风险规制为核心,进而形成了风险归类—规制对策的学理进路。
鉴于网络借贷规制中的核心就是风险防控,所以相关学理进路都是建立在个体网络借贷的风险认知基础上的。不同学者对于个体网络借贷风险认知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切入点上:较多研究者从网络借贷所涉及的四类主体出发[9],或者从风险的外部和内部切入[14],也有自成体系的风险归类[15]或者罗列式呈现[16],甚至还有专门的法律风险讨论[17,18]。但这种切入点上的差异并没有出现大的认知分歧,具体风险内容上殊途同归,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平台合法性风险(主要是网络借贷平台运营模式的合法性问题),洗钱风险(出借人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洗钱的风险),平台欺诈及非法集资风险(当平台控制人利用平台进行不规范操作来欺骗投资者投资或者资金被平台所控制时极容易出现此类风险,具体可分为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种),借款人信用风险(借款人提供信用信息不真实容易诱发借款人骗贷、借款违约的风险),网络技术风险(低成本开发的网络借贷系统在信息保护、信息管理上可能存在较大风险),平台经营风险(平台业务模式不被大众认可或者不能进行可持续性经营的相关风险)。
前述风险归类实际是为规制找到病根,随后方可对症下药。风险归类已经在内容上殊途同归,其风险规制或监管对策也就难免大同小异。通常采用如下几大法宝:网络借贷的平台定性(承认其合法性)与准入监管(事先预防欺诈平台),资金第三方托管(为了防控“资金池”的形成而坐实“非法集资”),信息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欺诈风险),风险保障金(降低借款违约风险),配套措施(信用体系和个人信息保护)。概言之,学理进路普遍认同个体网络借贷的金融创新之本质,对此持一种鼓励发展的开放态度,形成了以资金托管、信息披露为核心的风险防控模式,尤其是对于出借人的利益保护。
(三) 两种进路的比较
通过前文梳理,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进路的区别所在,监管者侧重于严守信息中介的定位,而学者们主张以保护出借人利益为核心。当然,监管者的信息中介的定位也有着保护出借人利益的考虑,但两者差别在于学理进路并没有像监管者那样对于部分业务模式进行否定性评价。换言之,监管部门对于网络借贷的态度更为保守,而学者则十分开放。当然,学理进路与监管走向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有很多学者的观点被监管层所接受,比如李爱君教授主张的借款额度限制、杨东教授倡导的多部门协作监管,但是两者对于业务模式合法化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三、个体网络借贷规制的监管走向与学理进路之实证评析
区分两种进路只是第一步,辨识哪种进路与网络借贷的发展实际相契合才是本文的主题。笔者下文将对两种进路进行具体评析。
(一) 个体网络借贷规制的监管走向评析:信息中介定性抑制了金融创新
监管层为何要将网络借贷平台限定在“信息中介”的范围内?相关规制文件出台时都伴随有主导部门的解答,从其解答制定文件的动机来看,监管层出手监管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换言之,监管层规制网络借贷的目的在于保持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那么,网络借贷平台严守信息服务中介之定位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么?根据监管层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答记者问》,严守信息中介之定位主要是因为“业务创新偏离轨道”和“风险乱象时有发生”。被否定的平台模式都属于个体网络借贷的“异化”模式,的确出现了业务偏离和风险发生。业务偏离的异化是否需要采取取缔的方式呢?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偏离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9],两类被取缔的异化模式毫无疑问都是一种金融创新,现实中也大量存在,意味着这些模式都是市场的自发结果。即使异化成为了信用中介,只要是金融创新,难道不应该被鼓励和引导?监管层进一步指出了风险乱象需要监管,这暗含着被取缔的平台模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而监管层所指向的风险主要是违约风险及其经营风险、违规从事金融业务风险、非法集资风险。笔者在梳理司法案例时验证了这两大主流风险的现实存在。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两类风险是前述两类平台占主导呢?笔者用150份裁判文书(其中刑事判决书34份、民事判决书71份、裁定书45份)所呈现的风险来验证风险乱象是否是业务模式偏离的必然结果。根据前文模式划分,我们也按照这种分类进行统计,相关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个体网络借贷司法案例涉及的平台类型①
1. 异化模式是否增加了违约风险以及经营风险?
150份裁判文书中有114份是关涉网络借贷违约的案例。由此可见,违约风险是当前最为主要的风险,但这并不能确定不同网络借贷平台模式的违约风险差异。对此,我们将根据不同模式进行区分(详见表2),担保型平台的违约案件是最多的,其他平台的区别相差并不大,这可以表明担保平台以外的违约风险是不存在较大差别的。那么,平台担保的违约案件较多是否意味着这一类模式就增加了违约风险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仔细研究这些案件就发现,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都无一例外要求网络借贷平台承担连带责任,这实质上是有利于出借人的利益保障的。而中介服务型虽然只有6个案例,但有2例出现了借款人无法送达被法院驳回的情形,这正好证明了该种模式对于出借人的利益保障是较为不利的。
为了进一步区分,笔者对于网络借贷违约案件中的违约风险防控进行了统计(详见表3)。平台担保、第三方担保、第三人担保是最为常见的防控方式,法院也都支持了这些连带责任的请求,所以从司法实务来看,担保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违约风险防控方式。

表2 不同网络借贷平台的违约风险案例统计

表3 违约风险防控方式统计
根据笔者对于相关司法案例的统计发现,债权转让型平台和自身担保型平台并没有显著增加违约风险,相反自身担保型平台还是违约风险防控比较有效的,基于此,否定其合法性的立论不能成立。当然,自身担保型平台在网络借贷中既扮演了“居间人”,又担任了“担保人”的双重角色,此时借贷平台“具有了资性担保公司的实质”[19],这是需要获得相应资质的。并且,“在不建立‘资金池’和进行资金银行托管的情形下网络借贷平台‘自身担保’行为并不会带来风险的集聚与扩散。”[12]所以,针对自身担保型网络借贷平台的规制,是需要其获得相应担保公司的资质,而并不是否定其合法性。
2. 业务偏离是否必然导致非法集资的发生?
笔者发现共有56份裁判文书涉及网络借贷平台的非法集资风险,其中24件关于借款违约的民事纠纷被法院以涉嫌非法集资而驳回。这是网络借贷乱象的一个集中反应。但是否与平台模式直接相关呢?根据表4可知,担保型平台同样也是重灾区,而中介服务型则尚未有相关司法案例,但是这里的重灾区并非平台自身担保,也是第三方担保,所以不能据此认为信用中介平台就会增加非法集资的风险。

表4 不同网络借贷平台的非法集资风险案例统计
为了进一步厘清,笔者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相关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探索非法集资风险的具体手段(详见表5)。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信息披露不真实(虚标和虚拟担保等)和平台掌控资金账户才是非法集资的成因,这并非平台的原本生态,只是部分不规范平台利用了当前的市场混乱和投资者的不理性。从理论上讲,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没有掌控资金账户的可能,现实是相应资金托管业务还不成熟。但是必须承认担保型平台、债权转让平台在现实中更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以非法集资为目的的平台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网络借贷平台,不能因为其存在被利用的可能性就否定其合法性。

表5 非法集资平台常用手段统计
所以,非法集资风险并不是业务偏离的必然结果,而是部分人假借平台模式之名开展了非法集资行为,因此,非法集资风险不是限制网络借贷平台发展的理由。
当然,上述案例中并没有资产证券化的债权转让型平台的相关案例,这类平台以PPmoney和联金所为代表,[20]目前尚未有相关案例进入司法程序,在这里并不能验证其风险问题。其他国家也尚未对此采取取缔的态度。比如美国最大的网络借贷平台Lending Club就是这类平台,美国将其纳入了证券监管,虽然这种模式被人诟病,[21]但是其导致的市场主体自动退出要远远好于来自监管部门的直接取缔。同样,自身担保型平台(如英国的Rate Setter)在国外也是被法律所认可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对于网络借贷的担保模式进行了肯定,此与监管层的定调是矛盾的。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意见》作为管理型规定并不影响司法认定[12],这种分析虽然正确,但也反映了不同国家机关对于网络借贷的态度差异。为何独独中国的监管者要反其道而行之?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式监管过度抑制金融创新的思维作怪,监管者粗暴地宣布了很多网络借贷平台的“死刑”,只是为了其监管的便利。换言之,《监管办法》要求网络借贷平台严守信息中介的定位就是我国历来对于金融创新持抑制态度的思想的一种体现。[22]
此外,笔者对于《网络借贷暂行办法》部分规定也存有疑问,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银监会主导监管是否合适?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之规定,银监会的监管范围是“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而网络借贷本质上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这一点也被监管层所认可,所以它明显不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监会监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且《监管办法》是授权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备案,这也意味着网络借贷平台并非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因此,银监会主导网络借贷的监管是超越其监管职权的,即使《互联网金融意见》有授权,这也不能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一上位法相抵触。
二是网络借贷规模限制的合理性何在?《网络借贷暂行办法》第一条所列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其依据是民商事法律制度,这与网络借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的界定是一致的。但是,《网络借贷暂行办法》第十七条又要求网络借贷以小额为主,并限制借款规模,由此被认为是《网络借贷暂行办法》中新增加的亮点,彰显了普惠金融与风险分散的监管理念。笔者认为这里存在四个问题:其一,既然网络借贷属于民商法调整的民间借贷,借贷规模限制难道不与民商法的合同自由原则相违背吗?其二,网络借贷是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难道不应该秉承风险自担原则么?监管不应该是提示大额借贷风险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只允许小额借贷存在么?其三,投资额度限制中有总的借款额度限制,鉴于当前借贷平台之间并无信息共享的机制,这在现实中又如何落实?其四,普惠金融是国家义务,监管层可以通过其监管权强制市场主体去完成这一使命么?采用激励性引导不是更好的路径么?可见,第十七条之规定虽然有着分散风险的良好初衷,但是并不是十分合理的。
《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可圈可点的地方虽然不少,但是利用其监管权来取缔金融创新的做法实为不妥,并且这种干预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支撑。所以说,《网络借贷暂行办法》作为国家对于网络借贷的干预是一种不恰当的规制方式。
(二) 网络借贷规制的学理进路之评价:异质风险同质化处理的倾向普遍
网络借贷规制的学理进路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网络借贷的风险归类基础上的。但是网络借贷模式由传统的中介服务型已经“异化”出了多种模式,异化即意味着模式差别,模式差别难道不会导致风险存在差别吗?风险差别是否需要有差别的规制呢?如前所述,现有的相关研究将这种风险归类时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多半被采用了同质化处理。这是否能适应现实情况呢?
根据前述的司法案例实际来看,不同平台模式的风险是有较大差异的,无论是非法集资风险还是借款违约风险都是如此。虽然担保型平台是司法裁判中风险比较聚集的平台,但是其在保护出借人的利益上更有优势。基于“担保人”的角色定位,平台对于借款人的审核会更加严格,相对于出借人利益保护更具有优势,所以这类模式的规制重点在于其“担保人”角色的适当性。因此,不同平台在其风险分布和出借人利益保护上都是有区别的,规制监管也应该区别对待。然而,关于网络借贷规制的学理进路中大多都没有严格区分,而是笼统讨论,出现了异质风险的同质化处理,这使得相关理论观点与实践脱节,所以这种进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模式的风险差异。比如叶湘榕[23]比较了不同模式的风险,他侧重于寻找不同模式间的共性风险和特性风险,并没有将共性风险进行细分,比如借贷的违约风险是各类平台普遍存在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不同模式对于这一风险的承受能力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的。
综合来看,无论是监管走向还是学理进路,对于网络借贷的风险没有进行区分处理,这是两者共同的不足之处。然而监管层走得更远,已经明显地抑制了金融创新。一言概之,网络借贷的两种规制进路都存在不合理成分。
四、网络借贷规制进路的未来选择:基于风险的差异化规制
金融创新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功能提升和效率改善[24],所以个体网络借贷这一类金融创新应该被激励,而不是粗暴地直接取缔创新模式,在金融抑制严重的我国尤其如此。基于此,在网络借贷的规制进路中,笔者认为学理进路更为合理,但是网络借贷的未来规制应该根据风险差异进行区别对待。具体而言,应侧重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 事前的差别化准入
《网络借贷暂行办法》所认可的中介平台的备案管理模式是较为恰当的。笔者认为这一设计将来可以继续沿用,即中介服务型平台、第三方担保的担保型平台、不改变债权转让性质的债权转让型平台采用登记备案制度。鉴于三类平台有所差别,备案登记也需要进行具体的区分,比如第三方担保的担保型平台需要提供相应的第三方担保机构的资质信息。
自身担保的担保型平台以及实行资产证券化的债权转让型平台具有金融机构的实质,必须采用注册制,但是必须达到其他规定的合规性要求,比如自身担保的担保型平台必须取得担保机构的资格,注册时仅仅进行形式审查。当然,此处的债权转让型平台已经与国外的债权式众筹相等同,似乎在众筹立法中专门进行规制更为妥当。
(二) 事中的有区别监管
平台的相关风险多产生于运营之中,所以事中的监管是最为关键的。但是,各种模式的风险有差异,具体监管措施也需要适度调整,但主要是防控平台控制资金以及信息欺诈。
1. 所有平台的“洁身自好”之路:资金托管制度
多数非法集资的出现都是因为平台掌控了投资人的资金形成了“资金池”,所以只要是提供资金交付业务的平台都需要实行资金托管,这里的托管需要在具有托管资质的机构开设专门的托管账户进行,尤其是债权转让模式,相关的托管业务需要对外公示。并且,应该禁止平台或员工代理资金行为,相关资金应该由借贷双方直接汇入托管账户。从司法实践来看,有借担保模式或债权转让模式行委托代理之实的情况,这是众多非法资金诞生的根源,所以其防控重点是建立资金托管。资金托管是防控非法集资风险的主要路径。
2. 信息不对称的矫正:基于风险的差别化信息披露分级
借款人的信息不真实产生的“虚标”和合同诈骗都是源于信息不对称,所以信息披露是防控这类风险的重要制度,这主要是防控借款人带来的信用风险以及平台欺诈风险。无论哪种平台都需要提供一个完善的信息披露平台,同时可以引入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模板,并根据模式差别有所区别。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平台业务模式披露:各类平台进行准入登记或备案之后需要将相关信息进行公示,标明自身的相应资质和业务范围,比如担保模式需要披露担保的相应资质、担保能力等信用信息。同时各自需要对于自身模式的风险进行披露,对于投资者起到风险提示的作用。上述信息披露必须在平台显要位置标明。
借款人信息披露:鉴于模式与风险的不同,借款人信息披露可以差异化处理。对于中介服务型和债权转让型(仅仅指不改变债权性质的转让平台)要求相对较高,担保型可以适当降低,这是因为后者有一定担保功能,平台或者第三方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去主动审核借款人信息。
投资者信息:鉴于不同模式下的风险防控能力的差别以及信息披露的成本问题,可以借鉴信息披露豁免制度,但主要限于债权转让模式。因为该模式下投资者并不直接与借款人发生借贷关系,而其他模式尚需要进行适度披露,为借款人和投资者搭建一个交易信息对接平台。
第三方机构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第三方资金托管业务披露和第三方担保机构的信息披露。首先,各类平台都需要披露自身的托管业务情况,其内容包括托管业务的合作方资质、资金托管协议副本等内容。其次,第三方担保机构需要披露其担保资质、担保能力等信用信息。
当然,笔者的主张只是对于网络借贷规制学理进路的一个补充和完善,其中很多合理的规制对策在此不再赘述,譬如信用制度建设。《网络借贷暂行办法》中对于借款人和出借人的相关义务规定也是一大亮点,这在将来的制度设计中也可以继续保留。
五、结语:个体网络借贷规制需要更加尊重市场
《网络借贷暂行办法》对于网络借贷的规制虽有亮点,但仍然没有摆脱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的桎梏,在金融创新时代其监管应该“由简单粗暴的行政取缔向规范性行政规制转换”[25],这样才能真正担负起监管者的职责。换言之,对于金融市场的规制应该尊重市场,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以风险防控之名打压金融创新。诚然,关于网络借贷的规制研究也应该更加契合市场现实,方能提出“接地气”的具体方案。个体网络借贷原本是一种市场内生的金融创新,其规制进路应该按照市场逻辑展开,此乃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倡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真谛。尊重市场,才是保持市场活力之道。
注释:
① 文中表1~5根据北大法宝、裁判文书网、无诉案例三大数据库的检索案例整理。
参考文献:
[1] Mishkin, Frederic S.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9 edition) [M]. Boston: Addison-Wesley, 2009: 29.
[2] 谢平, 邹传伟. 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12): 11−22.
[3] 谢平, 邹传伟, 刘海二. 互联网金融手册[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徐细雄, 林丁健.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14(6): 144−148.
[5] 张韶华. P2P的地方监管[J]. 中国金融, 2016(7): 69−71.
[6] 网贷管理暂行办法落地 李爱君教授逐条解读网贷细则[EB/OL].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60825/3876324. shtml, 2016−08−25/2016−08−27.
[7] 杨东教授第一时间解读银监会P2P监管办法: 金融监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规[EB/OL]. http://mt.sohu.com/201608 26/n466163120.shtml,2016−08−25/2016−08−27.
[8] 李爱君. 民间借贷网络平台的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研究[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2(2): 24−36.
[9] 杨东.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异化及其规制[J]. 社会科学, 2015(8): 88−96.
[10] 李永升, 胡冬阳. P2P网络借贷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以我国近三年的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J]. 政治与法律, 2016(5): 38−47.
[11] 刘素宏. P2P行业告别野蛮生长三大困局待解[N]. 新京报, 2015−07−20(A13).
[12] 刘志伟. 论P2P网络借贷平台业务发展的合法模式选择——从《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谈起[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27−33.
[13] 刘然. 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性质[J]. 法学杂志, 2015(4): 133−140.
[14] 王会娟. P2P的风险与监管[J]. 中国金融, 2015(1): 45−46.
[15] 冯果, 蒋莎莎. 论我国P2P网络贷款平台的异化及其监管[J].法商研究, 2013(5): 29−37.
[16] 卢馨, 李慧敏. P2P网络借贷的运行模式与风险管控[J]. 改革, 2015(2): 60−68.
[17] 刘晶明. 网络借贷平台视角下我国网络金融的法律风险与规制[J]. 法学杂志, 2015(9): 125−132.
[18] 章惠萍. 网络借贷(P2P)平台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J].理论月刊, 2015(11): 73−75.
[19] 李钧. P2P借贷: 性质、风险与监管[J]. 金融发展评论, 2013(3): 35−50.
[20] 林小虎. 网络借贷与资产证券化[J]. 时代金融, 2015(27): 113−114.
[21] 张永亮, 张蕴萍. P2P网贷平台法律监管困局及破解: 基于美国经验[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5(5): 88−97.
[22] 刘乃梁.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思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923−928.
[23] 叶湘榕. P2P借贷的模式风险与监管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4(3): 71−82.
[24] 兹维·博迪, 罗伯特·莫顿. 金融学[M]. 北京: 中国人大学出版社, 2000.
[25] 刘志伟. 非法集资行为的法律规制: 理念检视与路径转换[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1): 110−117.
Analysis of regulatory approach of online P2P lending
LIU Jun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The Temporary Management Methods of Online Lending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Business Activities requires lending platform to be an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 namely negates the legitimacy of self-secured platform and asset securitization credit assignment platform, and it is the maximum difference with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advocated by scholars. However, the requirement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risk presented by judicial case, which is enough to prove that this regulatory approach is unreasonable. In nature, it means that financial regulation suppresses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advocated by scholars heavily dealt with the heterogeneous risk of different online lnding modes in homogenization process, which is deviated from the actual risk of justice case, and lacks operability. In view of this,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risk should be the best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P2P Lending.
online lending; The Temporary Management Methods of Online Lending; platform’s business models; judicial case; differentiation regulation
D922.28
A
1672-3104(2017)01−0034−07
[编辑: 苏慧]
2016−09−09;
2016−1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虚拟经济运行安全法律保障研究”(14ZDB148)
刘骏(1990−),男,土家族,湖北鹤峰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和金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