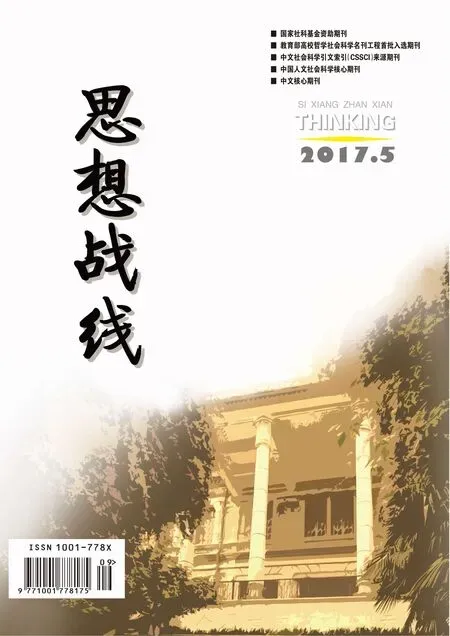民族问题的现代治理:概念与特征
2017-04-11,
,
民族问题的现代治理:概念与特征
高永久,郝龙
民族问题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子系统,在共享社会治理基本内核的同时,其治理范围被明确限定在民族事务领域。与此同时,民族社会运行与民族问题的自有逻辑与特点,又使得民族问题治理有着不同于一般社会治理的若干独特属性。因此,需要在明确民族问题治理基本概念的同时,应从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出发,探讨民族问题治理的独特性,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以求明确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基本属性。
治理;民族问题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基本属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概念接连出现在各大国际组织的年度报告和部分国家的政治纲领之中,逐渐成为西方学界与政界话语中的热门词汇。进入新世纪之后,“治理”概念在我国学术与政治话语中也日益活跃起来,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议》,更是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项总目标和总要求。这一社会改革反映在民族问题领域中的基本要求,便是推动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于怎样理解民族问题治理,怎样认识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等问题,目前的许多相关研究都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的阐释。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就民族问题治理的概念、对象以及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基本特征做简要说明,期望为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一、民族问题治理
“治理”是不同于“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处理模式,它在将政府之外的诸多社会行动主体纳入治理体系的同时,更通过对合作行动的强调,关注治理能力发挥的持续过程。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治理的子系统,在共享治理理念基本内核的同时,其治理范围被明确限定在民族事务领域。
(一)社会治理与民族问题治理
围绕社会治理的概念、内容与特征等问题,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一种常见做法,是从“治理”与“管理”的关系入手。对于二者间关系的最初理解,是将“治理”视为“管理”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新的表现。*[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编译,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页。换句话说,治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全新事物,它意味着“管理”的条件和方法有了新的变化。*[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漆芜编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5页。因此,优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权力行使方式,就成为由“管理”向“治理”转型的核心要义。好的治理即“善治”(good governance),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的强调,即政府的角色在于“设立能够让市场有效运行的规则”“纠正市场的失灵”以及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提供基本保障。*The World Bank,“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1992,p.1.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团主义、社群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兴起,社会治理逐渐被认为是应对市场机制失灵、等级制管理体制局限和社群普遍发展的一种新的秩序调节方式,并由此呈现出与“管理”的明显差异。*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在部分学者看来,二者的核心焦点尽管均落在公共事务和社会秩序之上,但至少在权威来源、权威基础与性质、权力运行向度、管理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由于它将政府机制与各种非正式、非政府机制同时囊括其中,“治理”已成为一种比“管理”更为宽泛的概念。*[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页。具体而言,治理所依赖的权威并不局限于政府的强制性权威,更包含着基于社会成员共识的各类非政府公共权威;这些共识性权威的存在,改变了原先等级制下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行使模式,不但构建起一种多主体协作的自组织网络,更带来了管理范围的扩展。
除围绕“治理”与“管理”之间关系的观点分歧外,社会治理本身的复杂性也是阻碍其共识性认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涉及到社会内部多种组织力量间权力分配与协作配合的实践难度,另一方面更是源于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社会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拥有自身独特的运行逻辑,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与各个子系统的特点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治理实际上是对诸多具体社会领域治理模式的总称,其中民族问题治理便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子系统之一。
作为社会治理系统的一部分,民族问题治理同样指向社会的整合、问题的化解,也就是与秩序问题直接相关联,只不过其治理范围被限定在民族事务领域。需要强调的是,民族问题治理子系统与其他治理子系统之间可能存在治理对象与范围以及部分具体制度上的区别,但并不涉及在治理主体、元规则与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绝对分割。参与民族问题治理的各行为主体,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同样也参与各领域的社会治理之中。以少数民族民众为例,他们的治理权利同时来源于国民身份和民族身份。作为国民的一分子,他们享有与多数民族的民众同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等;作为民族成员,他们也拥有依法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
(二)民族问题治理的内涵
基于时下主流的社会治理理念,本文将民族问题治理界定为基于目标一致和利益共识结合起来的,由国家各级政府、民族地区的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作为社群的民族和地方群体及其民众广泛参与,针对民族公共事务和民族问题展开的持续性协同治理过程。具体而言,民族问题治理的内涵中包含着三个基本内核:
第一,民族问题治理的对象是民族公共事务,简单而言也就是所谓“民族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种特殊类型,民族问题不但不是对发生在民族群体或民族地区中的所有社会问题的概称,其自身更存在着独特的基本特点和面向。当一类社会问题被称为民族问题时,意味着在这类问题的形成、认知和解决中均有民族因素介入,三个方面缺一不可:首先,在民族问题形成上,必须有民族身份和民族关系因素直接或间接的明确介入;其次,在民族问题的认知上,能够清晰辨认出存在着历史或现实中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等沿民族身份边界展开的社会区隔现象;最后,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需要民族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尽管在这种参与中存在着主导与辅助地位的差别,但脱离相关民族的帮助,这些民族问题都无法得到最终的妥善解决;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无论其人数多少,所关涉民族的合理意愿都应当被尊重和考虑,各个民族间的利益关系应当被尽量协调一致和合理维护,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问题的消解,更是民族关系的和谐和民族社会的进步。
第二,民族问题治理包含着一定的结构性逻辑,即民族问题治理体系的建构。除各项正式的法律政策与非正式的章程条例的拟定外,治理体系构建的一项重要议程便是确定治理主体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在民族问题的治理主体中,不仅是各级政府,各族社会成员和非政府的公共与私人机构也被囊括进来;另一方面,主体间协作关系的建立,也使得“共识”成为多主体合作的出发点与联系纽带,某项事务或问题只有当其事关各主体的利益时,才得以成为治理的对象。
第三,民族问题治理同时还呈现出一种过程化面向,即民族问题治理能力的发挥。民族问题治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联合行动”。社会的持续运行和不断变迁,决定了治理并不单纯只是一种制度或规则——治理体系的设定,它同时还是一个为实现和推动社会系统各领域良性运行的不间断过程——治理能力的持续发挥。能力发挥的实际效果,既取决于治理体系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水平,也取决于各主体间的共同利益与目标认知状况:利益分歧越小,对治理目标的认识越接近,治理能力的效用也就越大;反之,巨大的利益与认知分歧必然会造成联合行动的瓦解,最终导致治理机制的失效。
二、民族问题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对民族问题治理体系特征的讨论,涉及三个紧密关联的问题,即民族问题的治理主体有哪些?这些主体间将建立怎样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治理将产生怎样的后果?针对上述三个方面,本文分别总结出多中心性、关系协作性与层次性和权责模糊性三大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多中心性
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或者说“多中心性”(polycentric governance),构成了民族问题治理体系的根本特征。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一方面,它由众多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协作,任何子系统的局部变化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系统的整体变化;另一方面,每个子系统又均有自身独特的运行逻辑和结构形式,以及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与实际内容。在这种社会复杂性背景下,“任何一个社会治理主体,都无法具备解决上述复杂社会问题所需的全部知识、工具、资源和能力”。*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正因如此,以多元主体参与的多中心结构取代管理或统治模式下的“中心-边缘”结构,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发展趋势。*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在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各级民族地方政府,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与市场法人,作为社群的民族/族群、宗教团体、地方团体,以及享有自治权利的各族民众等类型。
治理范畴中的社会组织通常是指相对独立*之所以说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许多社会组织会接受甚至依赖于政府的合法审批和财物支持,但即便如此,在人员安排与目标设定上这些组织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于政府机构的专业性服务团体,因此又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这些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作用。*马长山:《NGO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期的法治秩序》,《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与社会组织相类似,以地域、文化等联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群,同样发挥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黏合作用。然而,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依靠程序化的规则规范和志愿性结合起来,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职能;而后者则在组织关系上较为松散,通常也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说职能较为泛化),其成员的选择同时兼具强制性与自愿性双重色彩。在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那里,无论是桑德尔(Michael J.Sandel)提出的情感性社区与构成性社群,*[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还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划分的地区社群、记忆社群和心理社群,*[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6页、第124页、第176页。都在强调道德、归属、意义等非制度化要素在社群形成中的结合作用,特别是民族社群、血缘社群等的形成更是有着社会意义上的先赋性——强制性的表现。至于享有自治权利的各族民众,其在参与社会治理、管理自身事务当中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二)关系协作性与层次性
在明确治理主体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形式与关系状态。除国家以外的各主体之所以能够参与到治理中来,是因为这些主体拥有或能够拥有宽泛意义上的权力(权威),从而具备在一定范围或领域内调节秩序、化解问题的能力。*吴 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第12页。因此,国家对各类非政府主体权威合法性给予一定程度的承认,成为建构协作关系的初始步骤。然而,除了权威的合法性问题外,各主体之间系统逻辑与利益分歧的存在同样也会给良好合作的达成增加困难。*Cynthia, Hewitt De Alcántara,“Uses and abuses of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p.50,p.155.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建立协作关系的有效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建立共识,即通过共同的目标将各治理主体有机结合起来,各方出于对特定公共事务的共同关心或受到特定社会问题的共同影响而主动加入到治理结构中,实现资源与知识上的优势互补;第二种模式则是利益协商,即通过谈判、协商、说服等非强制方式,尽量缩小各方的利益分歧,以求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认知。然而,建构良好的协调关系只不过是第一步,由于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将这种协调关系巩固和维持下去则是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面向。例如,保证合作的规范性——依据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展开合作,就是“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之一。
几乎所有的治理文献,都将自组织网络视为现代治理的一种基本结构,认为这是主体多元性和关系协作性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一般来说,社会组织化存在着两种模式,即被组织与自组织。前者是依靠外界干预与预先设计而实现的社会组织化过程,常见于管理和统治模式;后者则是一种秩序的自发形成过程,其中“自发”意味着“组织力来自事物内部”。*吴 彤:《自组织方法论论纲》,《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年第4期。哈耶克认为,“人为秩序”(artificial order或exogenous order)作为人类知识建构的产物必然存在着片面与缺陷,“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奥]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 湛,文跃然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74页。知识的“片面与缺陷”的碎片化分散,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自发秩序”(natural order或endogenous order)——以市场秩序为最主要代表——的尊重必须要优于“人为秩序”。*[奥]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61~62页。具体到治理范畴中,即意味着以具有运作自主性的自我管理网络,取代等级制的社会控制体系。这里的“网络”一词,指向一种特别的社会组织与协作方式,其特别之处在于对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互惠、相互协作和权力依赖*[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编译,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页。的强调。
对多中心之间的“共识性”或“协商性”合作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治理体系的平面化,各主体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仍会呈现出一定的层次区分。一般来说,国家及其最高代理机构——中央政府处于元治理地位,*[英]鲍勃·杰索普:《治理与元治理:必要的反思性、必要的多样性和必要的反讽性》,程 浩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5期。负责对治理合作的设计与管理。*Meuleman 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Metagovernance: Why Governance Doctrines May Fail”, 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no.10(1),2010,pp.49~70.具体到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各级地方政府虽然也拥有着部分的元治理职能,然而,多数情况下仍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结成一个自组织的社会治理网络。由于牵涉到治理范围与治理能力的差异,这个网络绝非能以一个平面图形标示,而是呈现为一个左右交织、上下连接的三维几何图形。自主网络的层次性不同于政府层级的等级性,较高层级的治理主体与较低层级的治理主体之间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或隶属关系。
(三)权责模糊性
多元治理主体间层次有序、关系协调的合作模式的确立,在政治实践中将引发这样一种后果,即权责的模糊性。通常人们听到的大多是“明确职能分工”“确定权责归属”的提法,那应该如何理解治理的这一属性呢?实际上,这种权责模糊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现代治理的权责分配中出现了公私部门之间界限的模糊:一方面,不断发育成熟的现代社会,要求限制政府强制性权力的干预范围,将一些非必要的职能性责任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社会组织和自治的社会成员之上;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与社会成员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又在某种程度上制造出了一个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社会。这是因为,抛开“现代”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范式,*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政治社会”在洛克、卢梭等古典理论家看来就是意味着由自然法状态向社会法状态的转变;*王 涛.:《洛克的政治社会概念与自然法学说》,《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而且,“政治”一词并非是与国家政治一样的词汇,它往往是指“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做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美]戴维·米勒:《布莱克威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邓正来编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9~440页。只要具备上述特性的行动都可称之为政治实践。二是治理合作的实质在于对散布社会中的知识与资源的调动与运用,过分地强调权责区分,难免会将部分重要甚至必要的知识资源排除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之外,使治理能力的发挥大打折扣。当然,这种权责模糊性只是相对的,目的在于扩大可调用的治理资源。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职权范围的确定和责任的归属,都是保证治理能力有效发挥的必要依据。
三、民族问题治理能力的基本特征
民族问题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决定了社会治理能力的基本属性同样也是民族问题治理能力的基本属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运行与民族问题的自有逻辑与特点,又使得民族问题治理有着不同于一般社会治理的若干独特属性。前者表现为共识或协商基础上形成的结果指向性特征,问题特殊性要求的机制灵活性特征,“防患胜于未然”理念带来的风险预估性特征;后者则着重体现在民族群体的文化关涉性和民族差异的地方情境性两大基本特征之上。
(一)结果指向性
目标导向性,是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管理主体的政府一方面会基于自身的认知状况和利益立场设定一个总的政策目标和若干衍生出的具体目标,另一方面也会运用各种强制权力保障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理想目标的达成。在英国研究者罗茨看来,这种对脱离了具体时空和情景考量的目标的过度强调,犹如“迷宫里的老鼠”,活力无限却又效用低下且备受限制。尽管需要依靠共同的目标将各个治理主体联系在一起,然而他又认为,治理不应当“沉迷在目标之中”。*R.A W.Rhodes,“The New G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Political Studies,no.44(4),1996,pp.652~667.作为联系纽带的共同目标不意味着要像管理主义那般迷恋于理想的状态,它必须指向治理的预期结果,即对公共事务和民族社会问题的及时有效处理。既然治理是结果指向的,那么所设定的共同目标必须具备两大基本特征,其一是明确性,即对治理的结果预期——针对的民族问题、解决的时效、意欲达成的效果——必须明确;其二是现实性,治理需要从民族社会现实出发,切实尊重各种事实状况,而所要实现的预期也应该符合现实逻辑——也就是说,对现实的调整重于对理想的追求。
(二)机制灵活性
与管理相比,治理机制表现出更为灵活多变的特点,使其能够有效适应各类问题的特殊逻辑与应对策略以及治理过程中不同的主体组合与协作方式。具体来说,机制灵活性要求的产生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从元治理到跨系统治理再到子系统治理,系统层次之间和各子系统之间在运行逻辑与结构特点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性。其次,源于治理对象的空间差异性与时间变动性,当治理的结构层次不断下降时,作为治理对象的民族社会问题会逐渐具体化、情境化,并伴随着民族社会变迁和权力格局变化(与民族社会问题的识别有关)的影响而处于一种持续变化状态中。最后,治理主体间的目标一致性和利益共识性也会随着民族问题治理层次和治理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对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不仅参与治理的主体数量与关系形式会不同,在协作行动中化解利益分歧、建立目标共识的方式也会不同。
(三)风险预估性
现代治理既是一个问题治理过程,又是一种风险治理活动。前者基于现实也指向现实,侧重于问题发生后的应对与调整;后者基于现实但指向未来,关注在问题发生前的预判与提前消解。风险(risk)与实际发生的危险(danger)不同,它主要是指一种风险意识,“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的现代化手段”。*[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然而要注意的是,贝克的“风险”概念立足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控制能力上,他认为风险“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且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在此使用风险一词,主要是借鉴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反思性(reflexive)观念,强调的却是反思基础上的风险预警和提前化解。任何民族社会问题的形成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积累与变异,如果能通过反思性的监控与预警机制,在民族社会不利因素的累积尚未出现问题化质变或仍处于可控范围内时即能发现和应对,不但能够增强民族问题治理能力的效果,更能有效减少社会成本的消耗。
(四)文化关涉性
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概念,既被人类学者描述为一种以血统和文化为联系纽带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英]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强调文化内的认同与文化间的区分/边界;又被政治学者们视为“民族-国家”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单位,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页。关于在民族矛盾与冲突中文化因素与政治因素究竟孰占主导的问题,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两种理论分野:一种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为代表,强调依据语言、习俗、宗教等差异划分的文明分界线构成了冷战后族群冲突的结点;*[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 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页。另一种则以“文化的政治化”理论为代表,它反对亨廷顿式的文化本质论调,认为所有的文化不可能封闭起来,并且“冲突不是有文化本身所酿成的,文化只是起了参与的作用”*[德]迪特·森格哈斯:《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将有号召力的文化因素粉饰成政治口号只是用于唤起大众的共鸣与支持,真正引发冲突的,归根结底还是未能(或无法)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本文无意卷入上述争论,只是想要强调,无论作为矛盾的源泉还是旗号,文化都始终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面向。这决定了与一般社会治理相比,民族问题治理有着更强的文化关涉性;而相对于专门的文化问题治理来说,它又带有着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民族理论上看,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多元一体”结构,在本质上归属于一种平等多元主义的民族关系模式。不同于苏联强权式的依附关系和美国熔炉式的同化关系,它奉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和结构上的一元主义,*[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第六版)》,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即追求文化上的族员身份与政治上的国民身份的统一。正因如此,民族问题治理的文化关涉性所强调的,不是对民族间文化差异的“绝对”消解,而是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差异的负面破坏性力量,尽量降低民族群体冲突的频率和烈度。*[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五)地方情境性
情境(situation)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提出,*W.I. Thomas,“ The Behavior Pattern and the Situation”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no.22,1927,pp.1~14.用于分析微观符号互动中情境定义(the definition of situation)对个体行动的影响。*[美]托马斯等:《不适应的少女:行为分析的案例和观点》,钱 军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页。本文在使用情境一词时,主要是借鉴其对意义在一般规则与具体行动中的差异性的强调这一观点,实际上则是指向环境/语境(context)和地方性(locality)两个维度而言的。Context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由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构成的社会环境,一是由一种具体文化形塑出的社会语境。*[英]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肖文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已说明,不同民族/族群*本文主要在民族的地域与文化分支意义上使用族群这一概念,不涉及“去政治化”的相关争论。受自然环境、交往交流、历史传承等影响,在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上均会表现出或大或小的差异性,差异越大则关于社会运行逻辑与意义认知方面的分歧甚至矛盾也就越大。Locality通常与local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相关联,例如,格尔茨在一篇关于地方性知识与法律的文章中写道,法律作为一种抽象的一般规则区别于各种具体的地方规则,当多元文化的存在制造出一般与具体之间的矛盾时,不同的地方逻辑会“在法律的逻辑方面和实践方面打着一个楔子,因而破坏了整个法律工作的效用”。*[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为了避免这一状况的出现,人们需要了解其中的意义结构差异,并将地方性知识纳入法律分析之中。推及到民族问题治理而言,也就是要求治理的部分规则与具体的治理行动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地方社会环境与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性,尽量消解其中的分歧、矛盾甚至对抗成分。
民族问题治理的地方情境性不仅有着差异/分歧面向,更有其一致面向,即如何在“多元”基础上塑造“一体”的问题。在“国家-社会”的二元范式下,国家被理解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实体,它垄断着一切合法的暴力手段,将自身打造成“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5页。与市民社会处于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之中。然而,关于国家与社会间零和博弈的观念也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这种二元范式由于过度关注了韦伯关于“国家”定义*[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中的支配(强制)一面,而忽略了对支配的合法性建构一面。*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正如艾伯拉姆斯(Philip Abrams)指出的那样,国家不是躲在面具之后的政治实践,它同样也是阻止我们窥探其实践的面具。他认为,面具和实践分别对应着国家的两个不同侧面,即由一致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想象构成的国家观念(state-idea)和表现为国家权力的代理机构及其实践的国家体系(state-idea)。*Philip Abrams,“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 (1977)”,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no.1(1),1988,pp.58~89.就像米格代尔用自己的著作所诉说的,“国家观念”打破了二分对立范式的枷锁,使我们在看到国家干预与社会抵抗的同时,也能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20世纪80年代,米格代尔出版了《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然而10多年后,他又出版了《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 杨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强调国家与社会在观念与实践两个维度上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如此,在民族问题治理中,我们在关注地方环境与知识影响治理实践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在不同的民族社会中形构一致的国家观念的问题。
四、结 语
对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基本特征的说明,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阐述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对这些要求的满足,是推进治理现代化和实现治理能力有效发挥的必要保障。否则,从治理机制的激活,到主体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再到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整个过程中的任一环节,都有遭受失败的可能。
例如,治理对象的认识分歧,很可能会阻碍治理机制的有效、及时激活。在认定什么是民族问题方面,存在着事实论与认知论两种分野。*王思斌:《社会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事实论强调民族问题对社会秩序和生活的破坏性事实。由于社会权力通常被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很多时候一种社会现象尽管会损害部分人口的生活或民族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尚未被权力群体察觉或该现象并未与权力群体的期望相左,就很难被认定为民族问题。然而,无论社会权力部门是否将其视为问题,这种破坏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认知论则偏重人们对民族问题的发现、认知和判断,认为一种负面现象只有当其被社会认识到并致力于以社会力量进行解决时,才能称为民族问题。在认知论者看来,对民族问题的认定虽然有其客观依据,但将其作为问题对待则更有赖于人的认知。一种负面社会现象的确会产生出破坏或阻碍作用,但只有在引起人们的重视之后才能将其认定为一项民族问题,因为人们关于这一现象的认知决定着社会对该问题下一步的反应。民族问题认定标准的分野,很可能会在治理过程中引发不同主体在治理对象认识上的分歧。当某一民族问题只被部分治理主体觉察到之时,实现问题治理机制的及时、有效激活,势必要面临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当这种认识分歧发生在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时,将会对协作关系的维系和治理能力的发挥造成严重损害。实际上,主体间协作关系的潜在威胁,不但可能会出现在治理对象的认定方面,同样也可能出现在治理目标的预设方面。所谓治理目标预设,是指治理主体对治理所要达成的目标结果的基本预期。各治理主体之间由于存在着性质、位置、利益关切等方面的固有差异,对治理目标的预期设定(包括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难免会产生分歧。与对象分歧相类似,如何将目标分歧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压缩至治理各主体可接受的范围内,对民族问题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 张 健)
Modern Governance of Ethnic Issues: Concepts and Features
GAO Yongjiu, HAO Long
As a sub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of ethnic issues shares the basic core with social governance, but its scope is explicitly restricted to the field of ethnic affairs. With ethnic society operation and ethnic having their own logic and characteristics, ethnic issues has a number of attribute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ommon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fine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governance of ethnic issues and explore the peculiarities of ethnic issues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authors wish to specify the attribute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of ethnic issues by combining generality with particular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of ethnic issues,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asic attribute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阶段性成果(14ZDA07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北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14JJD850011)
高永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 龙,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C95-0
:A
:1001-778X(2017)05-008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