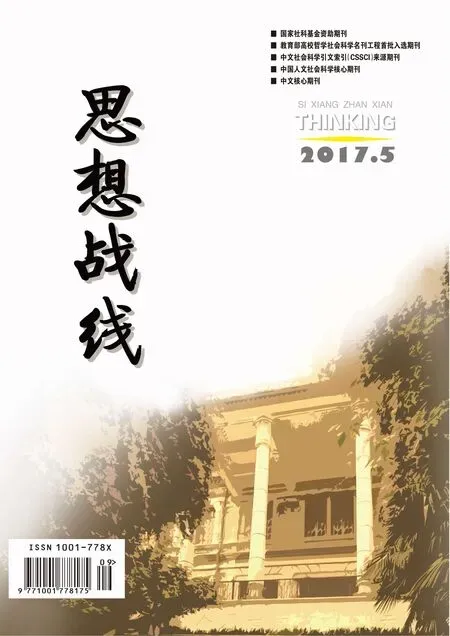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内源性动力研究
——以迪庆藏民族发展演变为分析视角
2017-04-11,
,
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内源性动力研究
——以迪庆藏民族发展演变为分析视角
李志农,顿云
当前云南藏区共时性研究中缺乏一种历史纬度的思考,云南藏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及其文化特征说明,一个民族内部在族群演变进程中嵌入交融、多元汇聚的内部关系结构,就能实现交融、开放和多民族文化的共享。这些构性因素的基础性、限定性作用,是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内源性动力,实现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的相互聚合并一致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稳定。
云南藏区;民族关系;内源性动力;藏民族;发展演变
云南藏区是云南省唯一以藏民族为主体民族、包括26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除藏传佛教外,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一些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尽管民族问题的宗教性、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特征突出,但是云南藏区长期以来保持了“模范藏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良好局面,在五大藏区中以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而著称。对此,以往大多数研究多从民族、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经验性总结和概括,*相关研究见郭家骥《云南藏区稳定发展的基本经验》,《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王德强 《云南藏区维护社会稳定经验述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王德强,史冰清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而往往忽视其社会内部关系结构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基本前提。我们认为,云南藏区各民族的“和谐共处”,必定有在其区域范围内自然和人为生成并长久维系的有益于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与包容,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以及境内跨宗教、跨族群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内部结构性因素,即所谓的内源性动力。而充分认识及分析其内源性动力的意义在于,期冀学界及各级政府在分析和制定民族地区各项政策时,还需进一步加强对民族社会本身的认识和重视,还需充分认识到“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社会基础以及社会文化总体对政策实施成效的规范性意义。事实证明,“多民族国家建设必须有与其目标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只重视民族政策本身而忽视政策运行的社会结构,将往往导致事倍功半或事与愿违”。*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014年5月起,中共中央多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29日。“嵌入”(embedment)概念源自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意指“市场经济是附属在社会体系之中的”*[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 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第53页。概念的引入,无疑将对当代中国民族社会的政治实践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它首次把民族关系视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的结构性问题,认识到社会结构对制约、协调和整合民族关系的限定性意义,及夯实社会基础对我国民族团结的基础性作用。它突破了以往忽视社会结构的整体意义,在民族政策的制定上脱离社会实体的国家主义的单一性实践路径,和在民族关系的研究上“从上而下,从外而内”的研究窠臼,充分强调了社会结构对民族关系的整体规范性意义和基础性作用。
有鉴于此,已有学者从中观层面对中华民族嵌入式的多元一体社会结构进行了个案的研究与分析。如有学者从迪庆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基础”的角度,分析了云南藏区这种超越并包容族群与宗教“地域共同体”的构建内生性因素;*刘 琪:《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也有学者运用历史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分析明清以来汉族移民进入后的汉藏互动、文化交融,认为汉藏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是云南迪庆藏区民族关系构建的一个重要变量。*李志农,邓云斐:《明清时期的汉族移民与云南藏区文化生态分析》,《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延续以上社会结构内部分析的视角,从历时性维度分析云南藏区藏民族形成与演变,揭示在藏民族内部所蕴含的关系结构及文化特质与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以期通过论从史出,由里及表地对云南藏区藏民族内部关系结构和人文形态特质的认识和把握,对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深入的讨论,并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理论以中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补充。
一、嵌入交融:云南藏区藏民族发展演变历史追溯
(一)吐蕃以前迪庆高原藏族先民
迪庆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据考古发现推测,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与周围各地区的文化密切相关。1958年在迪庆维西县发现了戈登村遗址,1959年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发现新石器遗址,这些遗址分别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迪庆的石器文化和川青、西藏有关,并与云南地区的文化保持着联系。1974年以来,在德钦县永芝、纳古、石底和中甸县尼西乡等地相继发现了石棺墓、古墓葬群。*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迪庆藏族自治州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2003年,第217页。从这些墓群中的遗物和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也可以看到在青铜时代迪庆高原与四川、甘青草原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同性。*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另据《迪庆概况》记载,在秦王朝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后,其触角已达迪庆这一地区。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置郡县,这里属于越郡之姑复地,东汉为牦牛羌地。自此,金沙江称作牦牛川,藏区叫“直曲”沿用到今。可见,藏族,至少是操藏语的部族当时已在此居住。*王晓松:《迪庆藏族历史文化简述》,《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
(二)吐蕃时期迪庆藏族逐渐形成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建立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推广其宗教与文化,势力范围至青海、川西和迪庆高原。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占领了迪庆大部,在此屯兵万余。*潘建生:《浅析迪庆藏区的政教关系》,《迪庆方志》1992年第2期。唐为阻止吐蕃势力的南下,在西南修筑了边防要塞安戎城。680年,吐蕃在当地羌人引导下夺取了安戎城,挥戈南下占领了西洱海地区。同年,吐蕃在今维西塔城一带设立神川都督府,并架16座铁桥控制当地。神川都督府成为吐蕃军队的重要集散地,将大批由吐蕃本土部落组成的军队调遣至此驻守、留居当地。这些来自吐蕃的军队和康区土著的白狼、槃木、姐羌共同生活,相互影响并融合。唐末,吐蕃逐渐同化了诸羌和外来的汉裳蛮、施蛮、长裤蛮,成为迪庆境内藏族的先民。*相关研究参见曹 相《云南藏族源流考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王恒杰《迪庆历史传统与自然因素》,《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王晓松《迪庆藏族文化简述》,《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
这一时期里,宗教对迪庆藏族的真正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先是苯教在迪庆地区的传入,使当地土著的诸羌与留居于此的吐蕃先民在信仰上靠近。而后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使得各部落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上逐渐趋于一致,而最终使迪庆与吐蕃本土的文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吐蕃时期是藏族逐渐形成的阶段,吐蕃王朝的向外扩张和征服,完成了对整个青藏高原的统一,为藏族在迪庆区域内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宋元时期迪庆民族融合
宋代,迪庆属于善巨郡。在宋王朝积极倡导的“茶马互市”影响下,这一地区与内地经济的交往日益频繁。这一时期,普洱的茶叶经南涧下关、中甸、德钦运往藏区,藏区的马匹、牲畜及皮毛运往内地,建塘“茶马市场”兴旺起来。*王晓松:《迪庆藏族文化简述》,《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率领下,分三路南征大理。大将兀良合台率西路兵经迪庆“革囊”渡江,在临西(今维西)、旦当(今香格里拉建塘)留下一部分将士。宋元时期,云南藏族的分布与南诏时大致相同。元朝统一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迪庆与内地的交往也更密切,在迪庆地区有了驿路,设立了马站。*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这一时期,迪庆作为藏区与内地交通和枢纽地带,经济呈现繁荣景象,蒙、回等一些民族的军民和小手工业者,先后定居于当地,并融入了藏族。
(四)明朝木府土司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有关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论著很多,杨福泉、赵心愚等学者分别对藏族和纳西族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关于这一时期纳西族融入藏族的研究主要有:冯 智《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及成因》,《西藏研究》1994年第1期;周智生《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区——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周 琼《明清时期中甸民族迁徙与融合初探》,《学术探索》2005年第2期等。
明代,中央政府继承了元朝对藏区的管辖。面对退居蒙古草原的蒙古势力南下和藏族势力联手的威胁,明朝政府在加强北部边防的同时,对滇西北地区实行了“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木氏土司成为其抑制滇西北地区的扶持势力。*杨福泉:《略论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实力变得更为雄厚,对周边地区和民族进行武力征服,在迪庆进行了长达两百年的统治。木府土司大量移民屯垦,大批纳西族进入迪庆藏区,深入迪庆各地。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也带来其他民族的融入,除纳西族外,也有白、汉等其他民族融入当地民族。他们在生活习俗上相互学习,文化上相互影响。木增土司统治期间,迪庆社会比较安定,安定的社会使藏族同纳西族、汉族还有其他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历史资料记载,纳西族和藏族在族源、语言、宗教等多方面有着深刻的渊源与关系。自公元7世纪开始,两个民族之间开始形成密切的联系,而明朝是两者交往空前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藏族、纳西族逐渐成为迪庆的主要聚居民族,虽然当地藏族在政治上被纳西族统治,但是纳西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陈 燕:《浅析历史上纳西族与云南藏族的政治关系》,《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如纳西族学会了种青稞、吃糌粑、喝酥油茶、穿藏装、说藏话,在宗教信仰上,其中一些人也开始信仰藏传佛教。与此同时,纳西族将一些先进的种植技术带给了藏族,藏族也受到了纳西族的影响。总体而言,这个时期进入迪庆藏区的纳西族,大多都被藏化成为藏族的一员,或与藏族杂居或保留其特性,成为藏区的纳西村寨。
(五)清朝至民国时期迪庆藏族社会民族交往
清康熙年间,西藏内乱,为稳定西藏政局,清政府派遣了大批远征军,其中一部分汉族士兵和纳西、白等民族的土兵流落于中甸、德钦,与土著藏民杂居。并在迪庆地区设市通商贸易。雍正年间,清朝派绿营兵镇守维西、中甸,同时,随着对中甸的经营垦殖,一批经商开矿的汉族、回族人口相继进入迪庆;乾隆、咸丰年间,滇西回民起义失败,一部分回族人群转而进入迪庆避难。继后,苗、彝、独龙、怒等民族人口陆续迁入迪庆。这一阶段,蒙古人中的全部,纳西族、汉族、回族中的一部分,渐渐融合于藏族之中,成为今天的迪庆藏族的一部分。*相关研究见周 琼《明清时期中甸民族迁徙与融合初探》,《学术探索》2005年第2期;曹 相《云南藏族源流考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周智生,陈 静《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多民族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封建制度下的迪庆经济萧条,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加上自然条件恶劣,迪庆各民族人口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这一阶段里,人口流动高峰主要体现在辛亥革命后,亦即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后,迪庆社会相对安定,内地人民不断流入,使得迪庆藏区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从《维西县志》和《云南德钦调查报告》的记载来看,这一时期中甸和德钦的藏族仍占绝大多数,但从总体来看,流入的汉族、纳西族等人口比过去增多。从内地迁入的其他民族和当地的藏族杂居相处,并根据自己的特点从事不同的行业,如汉族、纳西族、白族、回族就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对促进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随着经济的恢复,作为滇川藏交汇点,中甸的建塘镇、德钦的升平镇、奔子栏、维西的保和镇成为商贸交易中心,大量商人聚集于此。除了本地的藏商外,还有许多来自丽江、鹤庆、剑川、大理和四川、江西等地的内地商人,包括有纳西族、白族、回族和汉族等民族。*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286~288页。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以上理论,从宏观层面“为我们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关系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结构图”。*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遵循以上“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多层次多元格局”结构图景,上文从中观层面的族群演变视角,对1950年以前云南藏区藏民族的演变发展进行了历史追溯,在深层次上阐释了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内源性动力及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在下文中,将延续以上分析视角和历史脉络对云南藏区藏民族的演变与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多元汇聚:1950年以来云南藏区藏民族进一步演变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藏区先后经历了和平解放、建州、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区域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藏民族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变。
(一)1950年以来迪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与藏民族进一步演变
1.20世纪50年代迪庆经济的初步发展和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进一步交错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和平解放我国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迪庆作为从南部进藏的必经之地,对支援和平解放西藏具有重要意义。1950年3月,解放军云南军区命令14军12师126团、125团3营为南路军,以中甸、德钦、维西为基地进藏。为确保进藏任务的完成,中央又下达了由中甸、德钦的茶马古道,向西藏运输240万斤粮食的任务。为确保运粮工作的顺利完成,迪庆3县及丽江地区都组建了援藏委员会。截止1953年,援藏委员会先后完成了3次运粮工程,总共动用了人力60 224人,骡马12 500匹以上。*当代云南藏族简史编辑委员会:《当代云南藏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5页。在这些大规模的运粮、修路工人中,除来自迪庆本地区外,还有来自周边鹤庆、剑川等地的民众,部分人员在任务结束后便留在了迪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进藏人口。
迪庆和平解放后,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发展生产,成为迪庆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1953年,中央从内地抽调了大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到迪庆藏区工作,同时还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来帮助当地群众发展农业、指导生产技术等,*参见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研究室《见证迪庆——从政府工作报告看迪庆发展(1957~2015)》,内部资料,第87页。这批最早的援藏干部大都留在了迪庆。
1958年后,迪庆掀起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大修水利、大修公路、大办钢铁、大开荒地......抽调了3 000余人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当代云南藏族简史编辑委员会:《当代云南藏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2页。大规模地发展生产,需要大量劳动者,而迪庆本地人口并不多,劳动力更是有限,因此招收了大批外来务工者进入,不少便住在藏族社区,并与藏族通婚,这些外来务工者在这一时期成了注入迪庆藏族社会的重要力量。*经查阅文献后发现,对其他民族融入藏族社会的情况,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但田野调查提供了丰富的口述史材料。
20世纪60年代初期,迪庆的社会经济重新步入了正轨。1961年,迪庆藏族自治州全州商业机构发展到200个,从业人员554人。农村商贸市场得到恢复,农村家庭副业得到发展。*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迪庆藏族自治州志·综合经济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2003年,第552页。1965年,迪庆建成了香格里拉思伟水电站,派遣了水电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到迪庆。1966年,云南省林业厅投资修筑州内公路。同年,中甸、德钦、维西的农机厂都恢复生产。随后,印刷厂、煤炭厂、水泥厂等工厂相继成立。1975年,“州革委”组织修建电站……*当代云南藏族简史编辑委员会:《当代云南藏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99页。国营工商业、林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当地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另一方面,一批批来自内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到迪庆,并成为当地的常住人口。
总之,随着迪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人口进入迪庆,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通婚逐步融入藏族社会。族际通婚不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是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联结,族际通婚不仅模糊了民族间的边界,增强了不同文化间的互鉴,也消除了民族间文化的隔阂,为迪庆藏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2.20世纪80年代后民族政策导向下“政治性民族”(Political nation)*“政治民族”是与“文化民族”相对应的概念,周平教授把二者解释为:“前者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力量是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因而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后一类民族,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力量是国家政权,因而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参见周 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产生族群认同的连续统理论认为,历史是流变的,族群也在流变之中。
“认同”并非一个单向度的自变量或因变量,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和认同体系。族群成员或族群内部各部分对于族群整体的认同,实际是一段由许多代表不同认同状态的点构成的线段,它以“完全认同”和“宣布脱离”(放弃认同)作为线段的两个端点。在现实社会中,某一族群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认同状况,就处于这个“连续统”链条的不同位置上,并可能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而左右游移。*李志农,廖惟春:《连续统:云南维西玛丽玛萨人的族群认同》,《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升学就业、录用提拔等方面以民族优惠政策为重要手段的民族政策,使资源分配与民族身份捆绑在一起。民族身份由原有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具有越来越多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政治共同体。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一批“政治性藏族”也应运而生。*“政治性民族”概念出自周平教授《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延引此概念,笔者用了“政治性藏族”一词。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常发现父母均为其他民族,子女的民族身份却是藏族的案例。在迪庆藏区,由于藏汉、藏纳、藏傈等族际通婚的普遍性,一个家庭中有多个民族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在这样的家庭中,历史记忆、文化身份似乎并不是最主要考量,随父或随母或者随祖父母选择藏族身份,或者想办法成其他在当地处于明显政策优势的政治身份,*如在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孩子参加高考普遍有20分的民族加分;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傈僳族在升学、就业、职务提拔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惠和照顾。往往是他们不二的选择。
当然,拥有了藏族的“法律-政治共同体”身份,并不意味着拥有了相应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然而,文化并非静态的,它会随着人们的交往而流动,交流交往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互动过程,也是民族构建的互动性社会实践过程。“政治性藏族”的社会身份,能够使他们便于以一种新的文化策略主动调整融入主流文化,在与当地的主体民族藏族交往时有更多的“共同话语”“共同情感”,也让他们对藏族及藏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同,而他们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情感,又不可抗拒地被杂糅进藏民族的“共同话语”“共同文化”“共同情感”中,成为了拥有藏族政治身份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中间人”,这种被构建起来的藏族身份,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可能由完全不认同流变为完全认同,当然,也可能由完全认同流变为完全不认同。
三、云南藏区藏民族文化特征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内源性动力分析
(一)交融、开放与多民族共享藏民族文化特征
作为地方史的迪庆藏族社会发展史,既是迪庆藏族社会发展变化历程的书写,也是一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迪庆藏民族文化多元交融性特征的历时性表现。如前所述,来自西北高原的古羌文化,是迪庆藏民族的母体文化。在吐蕃时期,吐蕃对康区诸羌部落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统治,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吐蕃文化的同化。吐蕃王朝灭亡后,那些无法返回故里的吐蕃后裔,与诸羌部落逐渐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彼此渗透,血统上彼此通婚的局面。从10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出现和藏传佛教文化不断由吐蕃本土向云南藏区的广泛传播和渗透,使这一地区的诸部落文化终与吐蕃本土的文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藏传佛教文化成为其最核心的文化。宋元时期,随着蒙古军队的南下和元朝在这一地区设立驿路、马站、站户等设施,蒙、回等文化融入了当地文化。明清以降,纳西、白、汉、回等其他民族的迁入与融合,使迪庆藏族内部的文化中又融入了纳西、汉等其他民族的文化。195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迪庆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带来的一系列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相互流动,进一步助推迪庆藏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纳与采借。纵观云南藏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看出,该过程是一个民族不断累加、文化不断互动的过程,但其以藏民族为主体民族、藏传佛教信仰为主体文化的格局却始终未曾动摇。
文化间的相互吸纳与采借,必然导致文化间的边界模糊、相互混杂,体现出共享性特征。在迪庆藏区,无论是藏民族文化还是其他民族文化,并不存在一种文化与一个民族一一对应关系的独享性特征,而突出表现为交融、开放、多民族文化共享性。以岁时性节日为例,在迪庆,最隆重的节日不是藏历新年而是春节,而在其春节仪式体系中,既有汉族的祭祖、祭灶、贴春联等,也有藏族的点酥油灯、到喇嘛寺烧香、祭神山等。而在祭祀神山的转山活动中,“转山是不分民族的,藏族也有、汉族也有,其他民族想来的都可以来,这不只是我们藏族的神山,也是佛教的神山”。*2016年11月5日,德钦县西当村村民访谈。
(二)云南藏区藏民族文化特征与和谐民族关系
诚然,迪庆藏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迪庆藏区也并不是从来就如此和谐。新的民族、新的文化进入时也出现过隔离、斗殴、抢劫等情况。本文仅从族群演变发展的视角,梳理了迪庆藏族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及藏民族社会内部血缘混杂的复杂关系结构,进而分析了其民族内部文化的变化及其文化特征。事实上,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藏民族社会内部血缘混杂,文化交融,其族群内部的多元一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迪庆多民族社会的缩影。由于地缘、政治和人口等原因,藏文化成为了当地主体文化,它与区域内其他民族的文化一道,共同构筑了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云南藏区区域民族文化生态,是云南藏区民族关系构建的内源性动力,其内源性动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是迪庆藏区各民族相互包容的心理基础和化解民族矛盾的天然和谐机制。
在文化人类学学者看来,“文化不是无边界的‘奢谈’,而是有确定的地域、有边界范畴、有族群认同、有实践价值的系统”。*彭兆荣:《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在各民族杂居互动、交流交融的族群人文环境中,各民族间从谙熟彼此间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到接受差异、和平共处,再到相互吸收,彼此采借,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间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包容和接纳吸收,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对话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这种自身内部结构所具有的张力,使生活在这个文化区域的人们,理所当然对其他民族没有跨文化感和距离感。这种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心理基础,既是各个族群历史互动的结果,也是化解民族矛盾的天然机制,是迪庆藏区和谐民族关系形成并持久维系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其二,它是迪庆地方社会和谐民族关系得以形成的文化生态基础。
如有学者所言,“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形塑了当地的文化生态,而且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文化价值与文化理念的共享”,“本身就暗含着这一区域某种稳定的深层结构”。*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基于共享某种自然地理基础、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和情感,或物质利益和互补的经济生活而结成为有机整体的迪庆地方社会,由于地缘、政治、生态环境、人口数量等因素,藏民族成为了当地主体民族,其民族文化是当地主体性文化,对当地区域性民族文化生态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然而,作为云南藏区的藏民族文化,其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在其整个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对周边民族文化的采借、吸收和整合,体现了其文化构成的多元性特点。同样,不仅在藏民族社会内部,在其他民族社会内部,也同样是既有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保留,又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纳。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交叉所形成的多元、多重文化的互动交织关系,及其由此形成的各民族内部文化及各民族共享的区域民族文化,是一种超越了典型的藏族文化或典型的汉族、纳西族、白族等单一文化类型分类的多元一体民族文化,是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文化生态基础。
其三,在中国民族多元一体认同的前提下,对云南藏区区域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认同的同义表述。
费孝通先生在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提出了民族认同的多层次理论,他认为,“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和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层次,区域认同又是国家认同的另一个层次,二者是同心圆的结构,共同嵌入国家认同之中,其关系可理解为“所属关系”和“包容关系”。如“迪庆区域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包容于“云南省多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云南省多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又包容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认同”。“这种上位包容下位的分类体系,不会让我们停留在某个层面上,也不会仅仅突出其中一个层面,而是让我们的分类形成一个连续统,层层递进,互不取代。”*纳日碧力戈,哈建军:《守望尊严的必由之路及民族经验的认同理性》,《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由此,对云南藏区多民族共同体区域文化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
四、结 语
迪庆既是一个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文化空间,它并非一个个单一民族居住区域的简单复合或叠加,而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地区,在多元互动的民族关系中,各民族相互借鉴、彼此吸收,无论是在区域民族社会内部还是各民族内部,都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本文在探讨“云南藏区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问题,构建藏区和谐民族关系的共时性研究中,加入了历史的维度,通过对明清以来云南藏区藏民族嵌入交融、多元聚合的历史演变进程的梳理,以及对其文化特征的分析,运用社会内部分析视角,重新审视该区域的历史和文化,展现了一个民族内部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多民族共享性和文化边界的模糊性特征,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嵌入式”社会结构。它既是迪庆藏民族及藏文化的特征、也是云南藏区其他民族及区域文化的缩影。*相关研究参见李志农,邓云斐《明清时期的汉族移民与云南藏区的文化生态分析》,《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嵌入式”社会结构,是迪庆藏区和谐民族关系得以形成的生生不息的内源性动力。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种由各个互相依赖的部分构成的单位”。*[美]马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3页。从藏民族演变的视角,通过对云南藏区区域社会结构、民族文化生态、社会文化价值等“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强调,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从文化根基的解释探讨社会现象的方法,从深层次上阐述云南藏区社会历史的诸种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过程,应该是一个由内生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互相聚合并一致作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助推藏区的跨越式发展,而充分认识民族社会的结构性、基础性因素,能有效地避免外源性动力与地方民族社会的脱嵌,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稳定。
(责任编辑 陈 斌)
Endogenous Power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ibetan Region in Yunnan——A Case Study of Tibetans in Diqing
LI Zhinong,DUN Yun
Mostly synchronic, current studies on Yunnan Tibetan area lack a historical dimension.By examining how the Tibetans came into being and developed in Yunnan and analyzing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e can discover tha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an ethnic group has developed into what it is by embedding and blending different element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ulture——blended, open and multicultural sharing. The basic and restrictive effects of these constitutive elements are the endogenous power for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in Yunnan Tibetan area. Therefore, by combining endogenous power and exogenous power, we may promote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for the lasting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Yunnan Tibetan area,ethnic relations,endogenous power,Tibetan nationality,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重点委托项目“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内生性动力研究”和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云南藏区多民族共同构建的历史与现实研究”阶段性成果
李志农,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顿 云,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K28
:A
:1001-778X(2017)05-0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