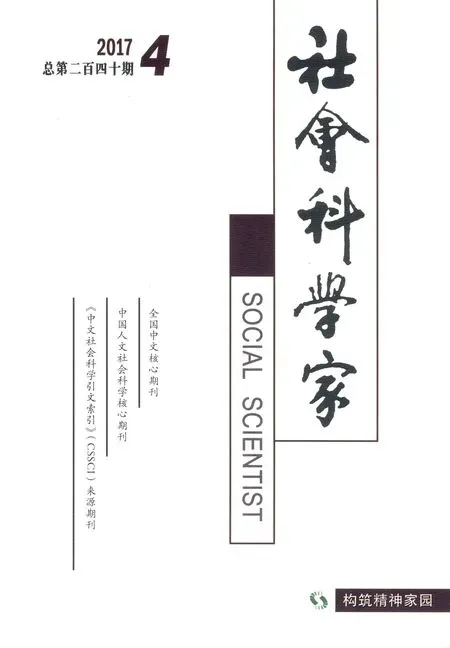“十七年”儿童文学对现代儿童教育的启示
2017-04-11申景梅
申景梅
(黄淮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十七年”儿童文学对现代儿童教育的启示
申景梅
(黄淮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带有浓厚的教育色彩,即便是今天反思那段特殊年代的儿童文学,也依然能总结出对当今儿童教育具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十七年期间”,新中国的英雄儿童、学校生活中的新儿童、乡村生活中的儿童等各类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也存在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压倒一切、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泛滥、儿童文学的“童心”不在等教育层面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加强对生命的认识和还原事物的本意、用信仰培养转化英雄和理想教育、把教育的权势交还给儿童,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儿童教育。
“十七年”;儿童文学;儿童教育
马克思曾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一个文学作家都会受所处年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尤其是在“十七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在讴歌儿童的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虽然这种创作思路对于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会对儿童的成长带来诸多的不利后果。为此,文章主要探讨了“十七年”儿童文学对儿童教育的利弊,进而总结了当前我国儿童教育的未来发展思路。
一、“十七年”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塑造
具体来看,作家根据题材选取不同,“十七年”现实生活题材儿童小说中儿童形象叙事有三个不同的侧重点:
(一)新中国的英雄儿童——英雄与传奇的倡导
“十七年”是一个狂热追求英雄的年代,英雄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浑身洋溢着崇高浓郁的英雄主义情怀。这一类典型不断涌现在作家笔端,不但是被反复歌咏的对象,亦是对新中国儿童进行阶级教育的良好素材。《刘文学》是老作家贺宜塑造的“新中国第一个少年英雄”形象。1959年11月18日晚,小小刘文学不顾个人安危,为了半背包海椒,与地主王荣学展开搏斗,牺牲时年仅14岁。从情节设置分析,虽然刘文学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代,面对集体利益财产受到破坏时,他与地主展开的是“生与死”的搏斗。从审美取向来看,无论是跟地主坏分子做斗争,还是跟内心落后因子做斗争,小主人公毅然一副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面孔。从结局安排来论,小英雄最终在其自身道德意志严格内化的过程中牺牲生命。1959年,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举国上下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夜,在这极为癫狂的政治话语背后,死亡并不是小英雄们唯一的选择[1]。在《刘文学》中,贺宜对新中国英雄儿童书写的主旨是高度宣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力推崇个人牺牲精神的。
(二)学校生活中的新儿童——“共产主义新人”理想的构建
1964年,毛泽东告诫全党:“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2]“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帮助我们新的一代形成他们共产主义的意识、性格和理想”[3],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语境中,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担负起时代启蒙和塑造民族性格的任务,教育他们“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作家艺术思维集体内敛,作品思想艺术高度集中,在同一种叙事模式下用相同的话语意义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新中国校园生活中“新儿童”形象。
《罗文应的故事》是张天翼这一时期儿童短篇小说的代表,被誉为50年代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老作家显然想通过罗文应来教育那些贪玩好动,自己管不住自己孩子。“有些小同学(特别是男同学),也想用功学习,但往往看见好玩的就忘了学习,自己也管不住自己。老师为他着急,他自己也很苦恼,很矛盾——把时间玩掉了,也很后悔,但到时候又克制不了自己。”[4]六年级学生罗文应先是“自己管不住自己”,在解放军叔叔和同学们集体的帮助下,罗文应“管住了”自己,最后加入了少先队。他的思想转变得益于集体的力量和少先队的帮助,在广大少年儿童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功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儿童文学作者到学校里去,到儿童中去,写新一代的实际生活,塑造出新一代的典型形象,这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迫切任务”。老作家马烽在儿童小说《韩梅梅》中塑造的韩梅梅也是具有此种意义的典型人物,这个热爱劳动、坚毅顽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少年形象,使当时的广大青少年读者受到有益的启发和鼓舞。综观以上作品,它们无一例外紧紧跟随时代的步子,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活,塑造了许多具有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爱护公物、拾金不昧等具有“共产主义”高尚品质的儿童形象。
(三)乡村生活中的儿童——党和“成人”引领下的乡村叙事
乡村是儿童活动成长更为广阔的天地。“十七年”侧重展现乡村儿童风貌的儿童小说因其独特的叙事意蕴而自成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这类乡村儿童形象与“十七年”儿童文学中新、旧时代的英雄儿童以及学校生活中的新儿童,是有交叉的,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个划分有些主观。“十七年”儿童小说文本解读的用意不是进行截然分类,而是试图把握一些主题相对统一,具有时代共性的典型作品所传达的历史的回声。
儿童文学作家兼编辑任大星的《双筒猎枪》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上,不久便被译成外文。它既是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书,也是对富有斗争精神的乡村少年儿童所唱的一首赞歌。新作家胡奇在1959年儿童小说举步维艰时,发表了《五彩路》,他用心书写了四个藏族儿童曲拉、桑顿、丹珠、娜木“经过艰苦的斗争,他们终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在党的关怀下锻炼成坚强的红色少年”的过程。最擅长“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乡村题材儿童小说《蟋蟀》(任大霖),它选择孩子们斗蟋蟀这样极为普通极为细微的题材,来反映农村少年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在党的教育下健康成长的大主题。小驹子、二牛和丫头是《微山湖上》(邱勋)中三个乡村儿童主角,作品表现的是他们到微山湖上去放了半个月的牛,在这平凡的劳动中,展示小驹子和他的伙伴们的优秀品德:勇敢团结,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热爱微山湖的革命传统。这些也正是每个新中国的优秀少年所共同具有的品质。这类儿童小说着重叙述的是乡村的孩子们从自私到无私,从怯懦到勇敢、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往往都是党的教育、成人帮助的结果,“成人并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配角’,应该把儿童的教育者和鼓舞者的形象写得鲜明、丰满,真正能成为儿童在成长中的榜样,成为儿童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二、“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教育观分析
(一)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压倒一切
儿童文学自二十世纪初出现以来,就一直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使命。到了“十七年”的中国社会,儿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政治意识形态需要俨然已经成为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儿童文学必须无条件地服务政治安排才有生存的空间,通过文学作品对儿童进行政治“教育”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不可否认,儿童文学的确需要承担起一定的政治启蒙和思想教育的功能,儿童文学内容需要符合国家的教育政策,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并且通过儿童文学的艺术手段,来进一步提升对儿童的教育效果。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就曾评价道:“有的作家只注重到了(儿童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却忽视了作品的教育一一,光有艺术性和趣味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和当前的政治意义(教育一一)相结合。”[5]因此,“十七年时期”的绝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都是从社会主义教育的角度来对其价值进行评价的。
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过于强调政治第一和意识形态的正确,严重束缚了作家们创作的自由想象空间和艺术表现空间。那些遵从儿童文学创作规律,提倡作品要突出趣味性和艺术性的作家们,纷纷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的作品在那个反右的大背景下被统统否定,并且被冠以“反对当的儿童教育政策”、“污蔑党的政治运动”的罪名被严厉批判。其实这些被“扫进历史尘埃”的右派作家们大多数只是反对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反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标准,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成反对党的文学和教育政策。
(二)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泛滥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塑造了华夏子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是一代有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加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了一个个为国家为民族勇于牺牲的英雄人物,并且中国人所尊崇的英雄人物和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崇尚的英雄,绝大多数都是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表现出一种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尤其是刚建国时期,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五星红旗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的”。因此,“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都在反复歌颂哪些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战士,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也就自然就成为儿童文学作品教育儿童最好的题材。如《刘胡兰》中不畏惧敌人,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红岩》中在监狱长大,最后死在监狱的小萝卜头,还有《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小兵张嘎》中的张嘎,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对孩子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希望唤醒孩子们的坚强意志,使学生更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同时,政权阶级也不希望全国人民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停止奋斗的脚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人们尤其是儿童进行英雄主义教育和理想主义熏陶,以激励人们万众一心走向共产主义的明天,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用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来激励和教育孩子,就成为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有其特殊的作用,它能够让人们更加关心他人和集体的力量,并且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但是文学作品过度的提倡儿童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长此下去就造成了人丧失了自主性,尤其是那种由国家意志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道德意志形成了某种强制性的规范。到了“文革”时期,这种理想主义更是被“四人帮”利用成为压制人性、肆意剥夺人权的借口。
(三)儿童文学的“童心”不在
如果回顾“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历程,“教育工具论”和“童心论”是两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品的“童心”可以理解为“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文学评论家在1962年创作的《小百花园丁杂说》中就曾对“童心”做过这样的阐述:“与其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有童心,不如说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心里应该跟儿童更贴近些。”[6]“十七年”间,包括贺宜、陈伯吹都是主张“童心论”的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陈伯吹更是“童心论”的代表人物。陈伯吹在1956年发表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儿童文学绝不能忽视童心的特殊性,儿童文学创作首先要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他曾举例道:“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这样才能写出儿童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但是陈伯吹的这一“童心论”主张却被当时的文化节扣上了资本主义错误思想的帽子,陈伯达的“童心论”思想也被当时称作是杜威“儿童中心论”的翻版,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像当时的《人民文学》、《文汇报》、《儿童文学研究》等刊物都针对“童心论”发表了批评文章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批评的声音,可以说他们都是站在阶级的立场进行了政治性批判,并没有涉及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的本质问题。
当时文化界大部分人都是在特定政治社会环境背景下,只能用阶级斗争思维来看待儿童文学的创作思路,一切与阶级斗争相悖的观点和思想都必须予以排斥或消灭。当时的社会背景要求儿童文学必须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即特别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教育工具论”,这是“十七年时期”最主流或者叫唯一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其中,鲁兵在1962年他写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一书中说:“儿童文学历来是一定阶级的教育工具。可以说,有儿童,有儿童教育,就有儿童文学,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儿童文学都需要对儿童进行教育,并且毫无例外的儿童文学就是最好的教育儿童的工具。”“教育工具论”是当时唯一政治正确的儿童文学教育主张,当时的《少年文艺》重新修改了方针,要求所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满足“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启发儿童智慧,增进儿童知识,培养儿童活泼、勇敢和乐观主义的精神”,由于这一重修的方针中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内容删去了,导致《少年文艺》在当时被猛烈批评是走上了邪路。
三、“十七年”儿童文学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加强对生命的认识,还原事物的本意
“十七年”时期的政治挂帅不仅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带来了很多束缚,同时也给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儿童造成了不小的压抑。思想政治教育不等于说教,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人人追求个性化的时代,政治说教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让对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加强儿童对生命的认知以及还原事物自身的本意是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加强对生命的认识方面,现在很多的儿童青少年表现出对生命的漠视。比如在听到某某学生跳楼情圣的新闻,不少人表现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态度,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极度不尊重的表现。只有加强儿童对生命的认知与尊重,让他们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爱惜生命的有价值的人。还原事物自身的本意方面,我们以文学教育为例,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都含有丰富的内涵,这些作品能够向人们讲述人生、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揭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是我们在对儿童的文学教育中掺杂了太多了政治解读。例如,一篇课文讲到了乌鸦啼叫,下面的注解写着:“乌鸦啼叫是在痛斥资本主义的黑暗。”讲到了小朋友摔倒,注解写道:“反映了旧社会的人民生活的艰辛。”类似这样的解释在我国的课本里比比皆是,但很多却可能并非文章作者的真实本意。因此,我们在引导儿童去欣赏阅读文学作品时,应当尽量引导学生去还原作品的本意,不能对文章进行弯曲解读,一味地往政治方向上靠拢。
(二)用信仰培养转化英雄和理想教育
“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过于强调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造成了孩子文化性格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以及理想的空洞型。并且,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让孩子们的表现欲过于强烈,只知道献身精神,但是独立思考能力严重不足。甚至有些孩子在这种教育氛围下,对政治过于热衷,对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强,却丧失了自己的信仰。而且在和平年代,我们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英雄。英雄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如果遍地都是英雄,那么英雄就失去了它的崇高性。因此,当下我们对儿童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应当着重培养的是儿童的一种信仰。我们在给儿童讲一个个英雄的故事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让人人都成为英雄,而是为了让学生懂得面对义和利时如何做出抉择,并且愿意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而负责。何为信仰?信仰就是明知难为而为之,坚持自己心中的人生追求,并且愿意用一生的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念。只有让儿童从英雄和理想中总结出属于自己的坚守信念,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所看所想是有价值的,并非时别人强行灌输而来的。
(三)把教育的权势交还给儿童
“十七年期间”的儿童文学过于重视“教育工具论”,使得儿童文学的创作偏离了儿童自身学习和兴趣成长的规律。儿童的在教育方面的一大特性就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双重身份——学习者和教育,儿童既是自我学习的主体,也是自我教育的主体。叶圣陶先生也曾用“种子”来比喻儿童的这一特性,他说儿童就像种子一样,有要求自己省长的内部动力,也需要教师给予及时供给养料的外部条件,以让他们更好地发展自我。因此,教师要意识到儿童就是一个个不同的种子,要允许种子结出不同的果实。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学会把教育的权势交还给儿童,而不是想着去教化儿童,但这不等于成人就可以对孩子自由放任。理想的儿童教育,应当是让儿童在宁静的大自然中自由的游历,任由他们的内心世界徐徐伸展。而成人就好比远处飘来的悠扬的钟声,让儿童对大自然事物产生更加强烈的感知。在儿童教育中,教师应该让自己成为懂得领路的向导,而不是在儿童身后不断催促的绳鞭。
[1]曹松.“十七年”儿童文学中“成长”的品质塑造[J].文教资料,2015(32):11-12.
[2]刘成勇.“化”儿童与“儿童”化——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扫描[J].创作与评论,2014(8).
[3]王家勇.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的儿童形象嬗变[J].齐鲁学刊,2016(1):156-160.
[4]钱淑英.“十七年”童话: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艺术新变[J].文艺争鸣,2013(11):40-45.
[5]耿羽.“小顽童、小大人与小标兵”:中国经典动画中的儿童形象研究——以建国后十七年繁荣发展期作品为例[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6(1):29-35.
[6]云翔宇.对“儿童是梦想家”的一点思考——读刘晓东《解放儿童》[J].科技展望,2015,(03):234.
G610
A
1002-3240(2017)04-0118-04
2017-02-12
申景梅(1973-),女,河南平舆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校:粟红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