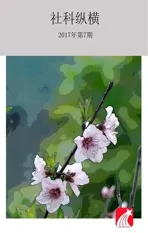民族文化的互融共生与跨域传承
——丝路文明视角下的砖雕文化变迁史
2017-04-11牛乐
牛 乐
(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民族文化的互融共生与跨域传承
——丝路文明视角下的砖雕文化变迁史
牛 乐
(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艺术文化的共享特质可以穿越文化间的壁垒,使多元的文化传统在地域和族际间交流,成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砖雕文化在地域、族群间漂移和传承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的西部地区是以丝路文明的传播为线索,由多元的文明形态、文化关系构成的文化共生场域,其持续的文化变迁和突出的多元文化特质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内涵。
河湟 丝绸之路 砖雕 文化变迁
导言
河湟民族走廊①是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也是历史上陆路丝绸之路的要冲和多民族历史文化的交汇点。自明初设茶马司于河州卫②以来,临夏地区由于繁荣的汉藏茶马贸易成为河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元代以降,随着多次大范围的移民活动,临夏及周边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开始形成,除汉藏民族之外,来源广泛的穆斯林族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和渗透能力,成为河湟多民族文化圈中最活跃的文化因子[1](P27-30)。从历史情况看,穆斯林民族传承的域外文化基因使河湟地区诸民族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均渗透了丝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痕迹。
明清时期临夏的繁荣兴旺直接建立在藏区与内地商贸经济的基础之上,回族商人们经常不辞艰险劳苦的来往于汉藏地域之间,清代史籍《河州采访事迹》中描述,“商则汉民贸易不出乡关,回民负贩远及新疆、川、陕。”[2](P42)由此,穆斯林商业文化不仅活化了经济贸易和商品交换,也为多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搭建了桥梁。
公元17-18世纪是河湟文化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几种源流不同,差异明显的文化传统相互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宗教的壁垒,而各民族文化习俗与不相称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也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赖,各民族间的文化共享以及价值观的趋同性却日益显著,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特质。
一、丝路文化传播与砖雕艺术的跨域传承
砖雕是以建筑为载体的艺术形式,相对而言,公共建筑更能体现其宏大的体量感和坚韧低调的质感。此外,明代的建筑等级制度③从实质上推进了砖雕艺术的发展,使砖雕摆脱了作为墓室装饰的形态而走进了地上的民居和公共建筑。
临夏砖雕的第一次辉煌始于清中期至清末,临夏地区相对发达的工商业以及应运而生的市民阶层成为砖雕文化发展的基础,商业文化的发展催生了诸多民间性质的公共建筑,充实的民间资本成为这种新兴审美需求的经济后盾。
从建筑风格以及砖雕构件的形制上判断,盛行于山陕、徽州、苏杭一带的砖雕无疑是临夏砖雕的主要渊源。明清时期,砖雕文化随着移民和贸易传入河湟地区,相对于河湟地区原生态文化的粗糙,内地砖雕文质与儒雅的气息和低调奢华的外观备受青睐,故很快盛行于民间,砖雕作为一种技艺、行业甚至文化符号自此在河湟地区生根。
早期的临夏砖雕曾有“回族砖雕”之称,这一称呼有其深刻的原因,临夏砖雕不雕刻人物形象的习俗以及特定的传承族群(回族)可以证明其与伊斯兰文化之间密切的关联。
临夏地区的穆斯林民族来源广泛,慕寿祺《甘宁青史略》载:“甘肃回族,以河州为总汇之区”[3](P23)。蒙元征服时期,大量的中亚穆斯林军人和手工艺人被安置在临夏周边地区[4](P4-5),成为临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的重要来源。④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迁入民族,这些穆斯林族群保留了丝绸之路全盛时期大量中亚,西亚文化传统,尤其以丰富的手工艺文化传承著称。自公元17世纪起,伊斯兰教苏菲主义⑤(Suf i yyah)文化自中亚沿丝绸之路传入河湟地区,临夏地区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格局随之发生了转变。不同于传统穆斯林社区的教坊制度⑥,苏菲派是以“门宦”⑦为单位,以“拱北”⑧为活动中心的新兴基层组织形式,同时,苏菲派相对多元的宗教生活形式显然契合了普通穆斯林群众的情感诉求以及生活需求,由此,一些大门宦建立的道堂⑨和拱北逐渐成为穆斯林社区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
自公元18世纪起,临夏地区的伊斯兰教苏菲派门宦先后开始了规模性的营建活动,基于苏菲派的宗教习俗,这些建筑主要是各门宦教主和传承人的拱北(墓园),虽然域外伊斯兰教先贤墓祠的形制较为简单,但是临夏苏菲派门宦修建的拱北则趋向于宏伟和华丽,凸显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征。
尽管砖雕被广泛的应用于民居建筑,但是拱北建筑显然与砖雕有更好的默契,因为拱北的核心建筑八卦亭(墓塔,亦称金顶)是以中国传统的亭式建筑为基础,结合多边形砖塔的形制而设计的特殊建筑体,其平坦宽阔的立面、层叠的飞檐、丰富的转折楞线刚好适合砖雕堂心以及砖仿木结构、抽象纹饰的表现。当然,这仅仅是就建筑结构和装饰手法而言,从文化层面考虑,不管苏菲派的做法如何标新立异,作为陵墓建筑的拱北使用大量的装饰既合乎中国文化的习俗,亦能体现一个宗教团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从诸多宗教文献和口述史里描述的情况来看,在藏传佛教文化和繁杂的民间信仰基础深厚的河湟地区,清初的苏菲派采取的是相当开放的文化策略。作为一种嵌入的文化,苏菲派门宦无疑在多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了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空间,而这种空间的包容性成功的削弱了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
同时,苏菲派开放性的、善于变通的多元文化特质很快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种特质决定了其发展并没有停留在宣教的形式上,而是以一系列文化实践切入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并生动的体现在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中。在毕家场门宦的内部文献中,毕家场清真寺的场地来自于汉族乡民的慷慨馈赠,至少说明了这一时期相对融洽的民族和宗教关系。
华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1681—1766)曾经多年在甘青交界的多民族地区传教,其事迹至今在黄河两岸流传[5](P163-164)。而“华寺”这一名称在民间与“花寺”的相通则来源于另外一个传说,即马来迟主持用汉藏风格的彩绘装饰了本门宦的清真寺,这种作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堪称大胆与豁达,表现出真切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感,并为临夏地区伊斯兰教建筑独特的地域风格奠定了基础。与华寺门宦几乎同时代形成的大拱北门宦则采取了另外的策略,创始人祁静一(1656—1719)精深的汉学修养和儒道气质⑩得到了汉族群众的广泛认同[6](P24),也造就了大拱北门宦伊儒交融的文化传统。
从实际情况来看,清代苏菲派门宦表现出的文化开放性超乎想象,而拱北则成为集合了多民族文化精华于一体的文化建筑群。笔者曾经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韩则岭拱北考察时见到一些清代建筑上拆下的古砖雕,其中狮子、虎、鸟类等动物形象极为丰富,而临夏地区现存的汉文化气息浓厚的砖雕精品均出自清代的各苏菲派拱北。
不论文化的变迁如何主导了砖雕文化的发展,工匠群体仍然是所有文化精神得以物质化的最终媒介。直至20世纪末,回族人仍然是从事砖雕行业的主体人群,但是一些汉族艺人认为,早期临夏砖雕的工匠群体是汉族人,清代临夏苏菲派门宦大规模营造清真寺和拱北的时期,各门宦的子弟通常担任监工,在此期间,许多有手工艺天赋的回族人士投身于砖雕制作,逐渐使回族人成为此行业的主流。(11)
尽管争议尚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临夏回族至少在文化层面发展了砖雕技艺。由于临夏地区穆斯林民族明显的中亚血统,回族匠师对于砖作技艺的擅长以及独特的审美趣味显然与中亚、西亚地区盛行的伊斯兰建筑装饰手法有微妙的传承关系。
在临夏地区,虽然私人宅邸同样盛行砖雕装饰,但是其规模和工艺却很难与伊斯兰教建筑相提并论。苏菲派的清真寺和拱北至少带动了整个河湟地区包括建筑、彩绘、雕刻在内的手工艺行业的复兴,种种被物化的精神形式在这些宗教建筑上得到了增殖的条件和机遇。当然,河湟建筑装饰业的繁荣并不只来自于伊斯兰教建筑,因为至少在清代,各民族的建筑装饰都没有刻意的突出民族身份。也可以说,是各民族共同的审美倾向、相互认同的习俗、多民族手工艺团体的参与和协作共同奠定了临夏砖雕文化繁荣的基础。
二、文化互融与多元内涵的形成绽学仁口述史(12)
我们祖上第一辈是从陕西西安来的,我父亲是第八辈。我们家里做砖雕已经四辈人了,太爷活了59岁,爷爷活了61岁,父亲活了80岁,我已经84岁了。
传统的临夏砖雕,回族的清真寺、拱北刻的花子不一样。藏族有藏族的风格,汉族有又汉族的风格,道教、佛教的砖雕花子又不一样,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名词(名字,意指文化规范、内涵)上的区别。名词关键的很,名词就是在私人家要怎么做、在公共场所需要怎么做,寺院庙道需要怎么做,一个系统(场所、教派)和一个系统不一样,有图纸(专用的图像)呢。
回族的砖雕都是用东西代替人物的,比如道教的要用暗八仙图案,佛教的用琵琶三弦等乐器,回族拱北多用食品(瓜果)表现出来(代替形象),比如什么石兽图、石狮子图都是用柿子、石榴等水果代替出来的(取谐音)。清真寺是礼拜的地点,各种各样的花,飞鸟、人物清真寺里都不放,主要是以花卉代表出来的。有些拱北里有飞鸟、人物,但人物不雕五官(嘎的忍耶学派的拱北常出现龙、凤、狮、鹿等鸟兽及少量人物形象)。
拱北里现在雕刻的花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以前都是梅、兰、竹、菊这些老花卉,都有各自的说法(寓意)。比如说莲花代表清、牡丹代表富贵。花草、山水、树林都是可以随意雕刻,像红园、国拱北里有五棵松树的、两颗松树的图案,这个很普遍。一般四季常青这个题材拱北和寺庙道观都可以做,吉祥富贵之类的题材私人家里做的比较多。
但是这些名词都有专门的说法和做法,比如拱北里五颗松树的图案叫做五老观太极,上面云彩里有一半个月牙,这个月牙不能做的很圆,始终是有缺口的(象征伊斯兰教的新月)。
东公馆也有好几处门洞上雕有牡丹,当初这些作品的名词都改过了(与原意不符的意思),后来是请我去定的名字。比如双瓶富贵,其实代表的意思是伊斯兰教的两世富贵。还有所谓山河图,其实山河图不是山河图,是江山图,意思是我的江山,是按马步青意思创作的。现在做砖雕的,这些名词(指原来的说法和文化含义)都不知道了,都被改了(混淆),不按规矩做了,按照自己的个性做呢,有时候把木活的名词和砖雕的名词都混淆了。
你现在到砖雕厂里看一下,好多东西做的不对,隶家(外行)看起来花(花哨好看)的很,行家看起来都不对。
就一种文化而言,显性的传承关系较容易被理解,而隐含的内容则较难甄别。从现象上看,临夏砖雕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儒道文化的融合特质,但是深入分析则不难看出其特有的价值观以及隐含的宗教文化内涵。
直至清末,临夏砖雕图案仍然带有浓厚的文人画意境和民俗特征,这些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混合的图像主题显然具有更为内在的阐释余地。如苏菲派拱北装饰中常见“二龙戏珠”的图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龙珠是龙的精华,二者是生命体与其元神的关系。在藏传佛教中,龙珠象征佛法,而龙则象征护法神。穆斯林学者的解释是,“在伊斯兰教中,龙珠象征真主的‘真一’性,而龙则象征极其虔诚、喜爱真主的人”[7](P433)。再如拱北中常见的“百鸟朝凤”图像,虽然是汉族常见的吉祥图案,但是有学者认为其来自于古波斯传说中的善鸟“西摩革”(Si m urgh)。[8](P101-103)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这种波斯神鸟的形象多出现于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诗歌传统中,后亦随苏菲主义文化向东方传播,逐渐与中国凤凰神鸟的形象碰撞并融合。
此外,拱北中一些常见的汉族民俗图案,如一品青莲、松鹤延年、龙凤呈祥、海水朝阳等均被赋予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而基于儒家文化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一些儒家文化气息浓厚的叙事性图像也被普遍应用。尽管伊斯兰教禁忌偶像,但是各拱北的装饰图案中龙、凤、鹿、狮子、蝙蝠、仙鹤、喜鹊等吉祥瑞兽比较常见,人物形象虽然罕见,但是仍不乏一些实例,尽管这些以文人绘画为粉本,偶尔出现的人物形象均处于图像的边角位置并通常不雕琢眼睛,但是在国内的伊斯兰建筑中已属绝无仅有。
在所有的砖雕图案中,牡丹、葡萄和博古图案最具代表性,如果对临夏地域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则不难发现,临夏地区广泛而悠久的牡丹种植传统,伊斯兰文化的本原精神、集体记忆以及浓厚的商业传统无疑强化了这些图像的文化内涵。以葡萄和博古图案为例,葡萄在汉族民俗图案中常象征“多子”,但是在伊斯兰教建筑上的运用则归因于中亚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宗教文化中的天堂意象。而回族人雕刻的博古图案则已超越了汉族博古图案所内涵的古雅趣味,其庞杂的内容与宏大的规模体现出更为浓厚的商业文化韵味,明显属于对穆斯林民族本原文化的借题发挥。
此外,藏文化对临夏砖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十分显著的证据是藏族传统装饰中瓣玛(13)纹的大量使用,这种丰满的半圆线装饰来自于藏式建筑,甚至可以说,富丽堂皇的藏族装饰风格为临夏砖雕注入了活力,并且中和了汉族装饰文化中枯淡的文人趣味。
在这种文化交融的语境中,山陕、京津、徽派建筑砖雕文质与世俗交织,内敛与夸张兼备的文化气息渐次明晰;南方古建轻盈的飞檐翘角,多层次的镂空雕刻技艺逐渐冲淡了中原建筑砖雕的平板和滞重;来自藏式建筑的华丽的瓣玛线被广泛使用;伊斯兰文化禁忌偶像的习俗以及审美情趣去除了人物形象,代之以绚丽的锦地图案和充满儒商情趣的博古图案。
值得关注的是,临夏砖雕的纹样通常没有固定的名称和内涵,回族匠师与汉族匠师对同一种图案的理解和名称亦不相同,例如回族人会将汉族的蟠螭纹理解为回字纹或者云纹,而将卷草纹一类图案统称为香草。因此,作为一种符号体系,临夏砖雕的图像显然具有多重的所指和意义,并常与建筑体以及整个建筑群共同构成一个不可拆分的意义整体。
三、工匠群体、技术、符号以及民族身份的变迁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河湟地区近代多元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时期,临夏在河湟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显著,与西南方向的青藏高原牧区以及东南方向的洮岷农业区相比,临夏的工商业社会形态无疑表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同时,与关陇文化区的连接赋予了河州交通枢纽的地位,并与周边的地域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的影响范围至今可以通过方言、生活习俗、信仰体系、商业结构得到确证。这一时期,河湟各民族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拮抗逐渐趋于稳态,一幅分布有致的文化地图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穆斯林民族逐渐成为河湟地区商贸、饮食服务业、手工制造业的中坚力量,其商业活动在族际互动中的作用愈益显著。这一时期,河湟各民族丰富的艺术文化凭借商业流通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而这些艺术文化形式常常在同一个传承场域中融合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在各民族艺人们丰富的口述史中,当时的临夏呈现出一幅世俗而活跃的文化场景。
在临夏城郊,半商半农、有条不紊的教坊生活培养了精通雕刻,但是不创作偶像的回族砖雕匠人;临夏东乡山区,土地干旱贫瘠,东乡族穆斯林仍然保留了多种源于中亚、西亚的手工技艺;永靖县的汉族工匠有营造古建的传统,精巧的木雕、木作技艺和瓦工技艺是其谋生的手段;一百公里外的藏区,来自卫藏,尼泊尔的藏传佛教艺术使得青藏高原边缘的藏传佛教艺术趋于成熟,掌握了严格造像规则、色彩感觉诡谲的热贡画师游走于甘青各地,以塑像、唐卡彩绘为生;常年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彩绘艺人引进了热贡艺术富丽堂皇的色彩,多元杂糅的彩绘图案仍然夹杂着清代官式彩绘的影子。
在这种历史场景中,穆斯林工匠、汉族工匠、藏族画师常常为了同一座建筑工作。对民间工匠而言,族群身份和宗教并非一种天然的屏障。简而言之,尽管藏族寺庙、汉族道观、回族清真寺、拱北有完全不同的宗教内涵,但是却往往由同一群人承建。在此过程中,回族、汉族、藏族艺人们相互磨合,这种合作方式使封闭的工匠群体和技术体系被瓦解,种种非物质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族群间漂移。在此,习俗、民间智慧、审美、被优化的技术、矛盾但是相互认同的观念共同塑造了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景观。自此,回族的砖雕、汉族的木雕、藏族的彩绘成了河湟民间对于工匠群体最普遍的认知。
值得关注的是,不论建筑形制、技术,还是图案、习俗,河湟地区的建筑装饰文化均表现出重装饰、轻结构的特质,这种倾向从中原地区开始向西部推进并产生渐变,至临夏地区产生了突变。究其原因,远离政治中心的自由造就了河湟民族建筑装饰的随意性以及僭越规格的习惯。基于缺乏秩序的攀比、创新,清代官式建筑端庄的斗拱形制被改进,横拱逐渐演化为多层次、富丽堂皇的花牵板。[9](P69-71)木构平坊被大量的镂空雕刻装饰,而藏式、和玺、素式、旋子彩绘乃至各种吉祥图案被不尽协调的应用于同一座建筑上,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河湟建筑装饰风格。
就临夏砖雕而言,完善的雕刻技巧、创新的风格以及不断涌现的优秀匠师共同使临夏砖雕摆脱了内地砖雕的影子,发展成一种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成熟的、体系化的民间工艺形式,正是这些特点最终使临夏砖雕闻名遐迩。
与清代砖雕相比,民国时期的临夏砖雕则呈现出更多的生活气息,姿态万千的花卉与琳琅满目的博古图像渐成砖雕题材的主流,尽管其民俗主题依旧,但是生动与成熟的造型艺术风貌已经远非清代砖雕可比。同时,日渐频繁的地域文化交流使沿海发达地区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装饰元素渗透到临夏砖雕之中,这些西方文化元素不仅带来了创新的纹饰和构图,也带来了造型技巧上的写实化倾向,这种写实技巧与民间造型体系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艺术效果,反映在砖雕风格上,呼之欲出的高浮雕逐渐成为主流。
此外,族际交流的加深使文化符号的共用和交互影响更加显著,自19世纪末起,伊斯兰教拱北的金顶(八卦亭)造型日趋高耸,顶部由传统汉式建筑的攒尖顶逐渐蜕变为高拔圆润的盔式攒尖顶,阿拉伯式建筑高耸的比例特征愈益显著,而这种高拔圆润的顶部造型甚至影响了汉族的佛寺庙建筑,客观上造就了河湟多民族建筑装饰文化多元杂糅的特征。同时,这种具有文化地标含义的建筑符号甚至借助商业贸易和建筑行业的活动将河湟民族文化输出到青海、四川、云南乃至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从现象上看,建筑装饰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共享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行业制度、文化传播形态所决定的,而其深层的意义则揭示了一种文化的共生形态,这种形态是多元的文化基因在多层面互动与重构的结果。
穆永禄口述史(14)
从前临夏砖雕最有名的师傅是绽成元、周声普,一个是绽派,另一个是周派,绽成元做的是临夏的东公馆,周派做的是临夏的大拱北。我的师傅是绽成元,他的师傅是马伊努斯,大约是清朝时期的人,民国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马伊努斯也叫“马们神匠”,临夏那个时候都叫他“周周(临夏方言,意为蜘蛛)马师傅”,也叫“周周马”。听师傅说,以前的西道堂(15),临洮的那个拱北(指穆扶提东拱北)都是他做的,在这里很有名。每年开春的时候就干活去了,回来的时候把面粉放在木车上拉回家去吃,过完冬天后就又回来干活了。
绽成元民国的时候做了东公馆,名声大振,还有马永昌和马双喜这两位匠人,他们是和绽成元一起雕刻水平最好的师傅,他们两个比绽成元都小一些,都是回族。还有一个是王志前(音),修建东宫馆的时候是记账的,和绽成元他们是同辈的人。他刚开始不会刻砖雕,后来这个人秉性好,给匠人们记账记工分,自己喜爱砖雕,就央求匠人们说,我也要跟你们学习。以前学习砖雕的人都给管一碗饭,他这个人有文化会算账,这样以后就跟着学刻砖雕,学的很快,那个锤头上的花,临摹的特别的好,边上的树木植物都临摹的很好,还很会雕那个“蝙蝠”。这么一来,这位账房就跑去和匠人们一起刻砖雕去了,一直刻砖雕大概到一九八几年去世的。
1937年,时任柴达木屯垦督办的马步青(1901—1977)开始修建豪华宅邸(东公馆),这一工程首次将京津地区流行的西洋巴洛克风格带进了河湟民居的规制之中,景观和图案的营造处处用心。《双瓶富贵》门代表了主人的穆斯林身份,《江山图》借助宋人山水画的构图暗喻了其政治处境,而随处可见的葡萄、梧桐、牡丹、松柏图案则显示了穆斯林士族阶层的文人风雅。
东公馆工程几乎汇集了当时临夏地区各工种的顶级高手,使其成为民国时期河湟建筑装饰的巅峰之作。在砖雕行业的口述史中,东公馆砖雕的创作者绽成元是个极为聪慧的回族艺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酷爱汉族书画,甚至还有对景写生的习惯。虽然无从考证更多的细节,但是这种传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河湟民间浓厚的文化氛围。凭借清雅的文人气息和生动的现实感,绽成元和东公馆建筑一并成就了近代临夏砖雕的盛名。
自此,葡萄,牡丹与博古成为临夏砖雕的三绝,而在多子、富贵、文雅、财富等等主题背后,浓郁的中阿合璧的建筑装饰就如盛行于河湟地区的河州花儿一样,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形式,也成为一种蕴含了丰富精神意象的文化符号。
1958年的时候,临夏各个拱北和清真寺的砖雕移到了现在的红园的清晖轩里。当时毕家场拱北、华寺拱北是比较大、比较有名的拱北,红园里的砖雕全都是从毕家场和华寺那两个地方拆来的,这些活都是绽成元、周声普这些老匠人们做的,其中“五老观太极”是绽成元刻的,还有个“一品富贵”是马永昌雕的,还有些是周声普雕的。
绽成元是临夏乡间上的人,他是临夏城郊镇的,那个时间他是工程队的人,就是后来临夏工程队的古建一队,那个时候我年纪轻,就在这个工程队里当学徒。
开放以后,各个有名的匠人都陆续去世了,后来就剩下马永昌和马双喜这两位匠人了,再就没有老匠人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徒弟叫马三虎,现在已经早就去世了。刚开始,马三虎在乡上当书记,后来从人大退休的,他是有文化的,不是专门刻砖雕的。
最早以前,木匠有木匠的行规,砖雕有砖雕的行规,木匠是汉族做,砖雕是回族做,行规都不一样。那时候的人们都很守行规,你的图案我不能照着学,相互不掺行,现在的不一样了,只要是能挣钱,木匠、画匠给钱都做。以前刻砖雕的人跟随师傅学习,人数很有限,现在刻砖雕的人就多起来了,木匠也学刻砖雕,木匠的特长是会刻花,和砖雕的刻法差不多,这么一来汉族也刻砖雕了,后来就比回族刻的多了。
1958年,临夏各拱北比较精美的砖雕堂心被迁移到临夏人民红园清晖轩的八字照壁两侧。事实上,从1958年到1978年的这一段时间,尽管砖雕随着古建修复队的工作进行,但是临夏砖雕基本上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1980年,绽成元去世。1983年,周声普去世。同一时期,临夏的各清真寺和拱北开始陆续恢复重建,而此时健在的砖雕艺人已经屈指可数,高水平的砖雕技师一时难求。绽学仁、穆永禄、马三虎、马永昌、马双喜等几位老艺人带领一些学徒开始了改革开放后临夏砖雕的第一批创作,其中不乏上乘的作品,但是也有不少由建筑艺人代工急就,扁平、粗糙的雕刻难称临夏砖雕之名,于近年被陆续拆除更新。
20世纪80年代末,位于临夏市的毕家场拱北、大拱北和榆巴巴拱北复建工程对于临夏砖雕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一批富有才华的砖雕新秀在这些工程中崭露头角。绽成元之子绽学仁主持设计了国拱北宏伟的建筑群,经过几次扩建,目前已经成为临夏市重要的人文景观。同一时期,学彩绘出身的沈占伟(1969-)转行从事砖雕创作并很快显露出过人的才华,木雕和玉雕丰富玲珑的多层次透雕工艺被其完美的运用到砖雕工艺中,大拱北和榆巴巴拱北留下了其早期的佳作。作为汉族人,沈占伟的成名也体现了砖雕从业群体民族属性的变迁。但是,尽管“回族砖雕”的称呼逐渐远去,临夏砖雕仍旧保持了不雕刻人像的穆斯林习俗。2015年,沈占伟和穆永禄同时被评定为临夏砖雕第一批国家级传承人。
2006年,临夏砖雕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广交会上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使临夏砖雕名声鹊起。与21世纪之前的风格相比,显著的变化仍然从拱北砖雕开始,拱北砖雕的图案日益繁密,趋向于不留空白的阿拉伯装饰风格。同时,以磨砖对缝技术营造的简朴的影壁不再流行,传统砖雕用耐心堆积而成的技艺被代之以触手可及的奢华与充实感。
这种显著变化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从业者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些技师认为这种复杂的装饰趣味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榆巴巴拱北重建期的工程承包人,其同时也是一位波斯地毯的经营者,是他对于地毯图案和构图的趣味引导了这种风格的产生。也有人认为,砖雕行业的“日工制”(按日支付工资)导致了这种风格的产生,理由是经济实力较好,虔诚而考究的拱北业主总是希望借此提升砖雕的精致程度,而砖雕师也认为唯有在一日之内、方寸之间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才能体现自己的手艺,对得起这份报酬。
就工匠群体而言,行业间的渗透和角色转换比以往更为频繁,按照传统的行业习惯,彩绘、建筑、砖雕、木雕等工种之间有比较严格的业务范围和技术壁垒,这种做法间接的保证了在有限的资源下合理的分配各个行业的利益,交叉学习或者施工的情况并不多见。
随着内地木雕装饰机械化生产的普及,手工木雕的市场日渐低迷,许多木雕艺人转行从事砖雕(砖雕因材质的特殊性目前尚无法使用机械雕刻),相对于砖雕技师,木雕技师更擅长雕琢细致的花色图案,无形中调适了传统砖雕相对质朴和平实的趣味。此外,不能忽视模具翻制技术对于手工雕刻的影响,用精细的、富于曲面变化的石膏模型翻制的砖雕会产生更为丰富和细腻的艺术感受,而这种精致感显然对整个行业具有示范作用。更不可低估的是,对于民间艺人来说,精致的工艺永远比内涵更具有诱导和示范作用。
从文化视角来看,不论这种精工细作的砖雕风格究竟源于何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风格、图案的变化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外在的演进特征,作为文化精神的物化,艺术风格的改变始终映射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文化整体格局的变迁。
结语
基于多元的文化传统,河湟地区的民间艺术文化高度繁荣,丰富的艺术遗存和活态的艺术形式共同营造出特殊的地域文化景观,成为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成果。
由此可见,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子系统,艺术文化的生产、传播是粘结复杂的社会关系,对社会文化结构起到活化作用的重要介质。在现实社会中,艺术文化的多元性、传播性、共享性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互动和沟通作用,即使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知识背景下,艺术形式和符号的共享也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础,这一特性同样使多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跨民族、跨地域传承并保持活态的发展。
注释:
①“河湟”作为地理概念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原指黄河上游以及湟水、大通河流域,故亦被称为“三河间”。当代文化视角下的河湟地区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关系构成的地理文化概念,范围包括以黄河为界,甘肃、青海两省境内的多民族聚居区域。“河湟民族走廊”基于费孝通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后由国内多位民族学学者共同发展成型。
②临夏回族自治州历史上先后有枹罕、河州、导河等多个地名。
③《明史·舆服志四》中载:“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
④关于中亚穆斯林工匠随军迁徙的原始资料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元史》等中外古文献。
⑤苏菲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教派,而是民间对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修行者或组织的总称,起源于公元8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禁欲主义思想和修行团体,并于公元10世纪被纳入正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学术界对苏菲(Sufiyyah)一词的词源解释不一,但是普遍认为其在发展过程中承袭了古希腊末期“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部分哲学思想。
⑥教坊指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穆斯林居民居住区,每个教坊之间互不隶属,是传统穆斯林社区宗教、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中心。
⑦“门宦”是伊斯兰教苏菲派修道团体在中国内地的称呼,新疆地区称作“依禅”,波斯语称“塔立格”(Tariqah)。由于其本身具有“学派”的含义,在现实中又具有一定的宗族特征,
故国内学术界尚未对其取得一致的定义。如果从学派和传承体系划分,以临夏地区为中心的门宦组织由虎夫耶(Khuflyyah)、 哲 赫 忍 耶 、(Jahriyyah)、 噶 德 忍 耶 、(Qadiriyyah)、库布林耶(Kubrawiyyah)四个苏菲学派构成。
⑧学术界一般认为“拱北”是阿拉伯语(Qubbat),或者波斯语(Gumbez)的音译,中亚、波斯及中国新疆地区称“麻札”(Mazar),意为“先贤陵墓”或者“圣徒陵墓”。
⑨苏菲派的宗教文化传习场所,有时设置于拱北内,亦可单独营建。
⑩苏菲派讲求修道的教法三乘(礼乘、道乘、真乘),大拱北门宦在四大苏菲学派中最讲求对“道乘”的追求,这种用中国文化词语对伊斯兰神学理论进行的互译始于明清时期金陵学派的“以儒诠经”运动,代表人物为王岱舆、刘智等中国伊斯兰教学者。
(11)此说见于唐栩《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工艺特色初探》第140页,对于临夏建筑艺人胥恒通先生的采访录。
(12)绽学仁(1935-),回族,砖雕大师绽成元之子,国拱北寺管会主任。曾主持设计、修建临夏市国拱北、红园广场等当代砖雕建筑群,本段口述史根据笔者2008年采访绽学仁先生的录音整理。
(13)“瓣玛”一词来源于藏语“莲花”的音译。
(12)穆永禄(1952-),回族,临夏砖雕国家级传承人。曾师从绽成元等砖雕大师学习砖雕技艺,参与了大部分临夏近代伊斯兰教拱北建筑的复建工作。本段口述史根据笔者2015年采访穆永禄先生的录音整理。
(15)中国伊斯兰教派别之一,创始人为甘肃临潭伊斯兰教学者马启西(1857-1914)。
[1]张俊明,刘有安.多民族杂居地区文化共生与制衡现象探析——以河湟地区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马磊.清代民国时期甘青藏区回商、市场与族际互动[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4]李维建,马景.甘肃临夏门宦调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马通.西北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6](清)祁道和.清真根源[M].临夏大拱北门宦内部资料.
[7]杨文炯.二龙戏珠的文化象征——河湟民族走廊多元文化整合的隐喻[A].西部民族走廊研究——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8]周传斌.回族砖雕中凤凰图案的宗教意蕴[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9]唐栩.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工艺特色初探[D].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J209;G127
A
1007-9106(2017)07-0006-07
* 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临夏砖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项目号:15YJE760001)相关成果,并受到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资助([2016]57号)。
牛乐(1971—),男,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