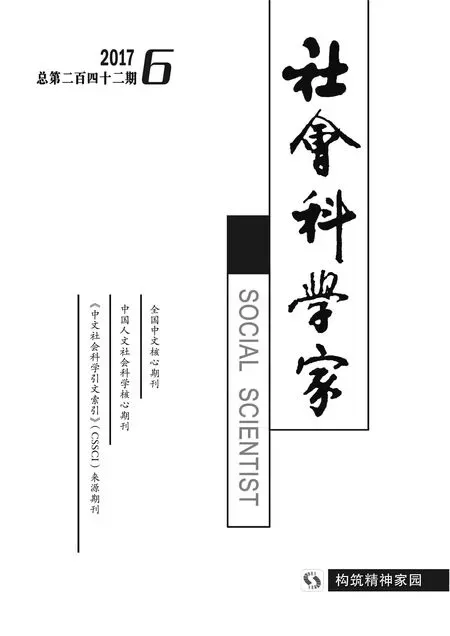《红字》的情感理论维度
——贝兰特读霍桑
2017-04-11陆扬
陆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当代西方前沿文论专题研究
《红字》的情感理论维度
——贝兰特读霍桑
陆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主持人:陆 扬
主持人语:西方当代文化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理论死了”一类格言警句,呼吁回归审美。如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 (1994)。9年以后,特里·伊格尔顿也写了一本《理论之后》。这个潮流的前提是,文学理论高高在上、天马行空,什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理论、意识形态政治学,什么都谈,就是不谈文学作品本身。是以殊有必要拨乱反正,回归文本。这个重申审美和叙事的人本主义立场,初衷当然是好的。可是理论从来就是实践的先导和概括,它同实践一样生命之树常青,哪能说死就死了呢。是以所谓理论寿终正寝的说法,不过是昙花一现。理论跌了一个跟斗,马上抖擞精神,重振雄风,照样成就为文学研究的主导话语。本专题的三篇文章,正是在这一视野中完成的。我本人的《〈红字〉的情感理论维度》结合霍桑《红字》和贝特兰《国家幻想的解剖》来谈近年风起云涌的情感理论;赵靓的《拉康与法国精神分析批评》有意梳理拉康理论的文学批评谱系;王曦与西蒙·克里奇利的《西蒙·克里奇利谈“他律理论”:悲剧剧场、爱与哀悼》,则是以悲剧意识和伦理情感为题,对克里奇利的一个直接采访。综合来看,应无疑问可以增强我们的理论信心。
劳伦·贝兰特分析霍桑《红字》的《国家幻想的解剖》是20世纪末叶以来“情感理论”的扛鼎之作。她认为霍桑是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将《红字》写成了一部国家认同的幻想型作品。而她则有意探讨作为国家主体的芸芸众生,为什么不光是先已分享了国家的历史或政治忠诚,同样也分享了一系列地方的和个人的情感形式。斯宾诺莎《伦理学》将情感(affect)定义为身体的感触。从身体的角度,特别是小说女主人公海斯特身体的角度来看《红字》,则不光可以读出性别压迫的先声,在贝兰特看来,霍桑的公民观念和性别观念,也在官方和大众、国家和地方、集体和个人,以及乌托邦和历史的交集中,呼之欲出。
贝兰特;霍桑;海斯特;斯宾诺莎;情感
一、国家幻想与国家符号
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康内尔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84年开始,执教芝加哥大学英语系至今,为该校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批评探索》等著名杂志的编委,并以“国家伤感性”主题的三部曲蜚声。第一部是《国家幻想的解剖:霍桑、乌托邦与日常生活》(1991)、第二部是《美国女王去华盛顿城:论性与公民》(1993)、第三部是《女性抱怨:论美国文化中伤感性的未竟事业》(2008)。三部论作中,尤以第一部《国家幻想的解剖》,公认是情感理论作品分析的扛鼎之作。
该书题为《我是别处的公民》的导言中,贝兰特开篇第一句话是“国家激发幻想”。她注意到1849年霍桑丢掉了他在海关的联邦稽查员饭碗,诚如《红字》题为“海关”的前言所交代的那样,霍桑的想象力开始跑起了野马,感觉自己就像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在断头台上身首分离,落得一个“政治死人”的应有下场。由此又联想到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睡谷传奇》里面那个无头骑士来,感觉那真是美国革命的幽灵,洋洋得意策马过来,手里抓着自己的脑袋——那真是堂吉诃德的长矛,谁要挡路,就一枪过去。所以不奇怪,霍桑甚至考虑过给《红字》起名《一个断头稽查官的遗稿》,并告白读者,就当它是一个从坟墓那里写出来的东西,给予原谅吧。
霍桑以上交代《红字》写作序曲的前言里,贝兰特读到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给已经不复有脑袋来顶戴它的霍桑,赐下一顶殉道桂冠。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他的写作、他的知识、他的情感,以及他本人的身体。“断头台”的比喻尤其吸引贝兰特,霍桑当时说的是,假如断头台不光是个比喻,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落到公职人员身上,那他绝对相信,获胜党派必会激动不已,不惜把他们的脑袋统统砍掉。霍桑又说,在他给免职落难之际,有一两个星期新闻界还频频在报纸上出他洋相,让他觉得阴森森就像欧文笔下的无头骑士,恨不得给活埋了,落得个政治死人的应有下场。不过好在真实情况是,自己的脑袋还好好长在肩膀上呢,而且凡事有利有弊,如今他有了闲暇,买来笔墨纸张,收拾干净久被冷落的书桌,又可以开张写作啦。
贝兰特读《红字》的上述前言,感受是小说的作者为他的公职而自豪,因丢了工作沮丧不已,气不过自己如此依赖着这个象征意义和真实意义上的国家,如是情不自禁,要来冷嘲热讽一番。霍桑这部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令名声鹊起的《红字》,由是观之,用贝兰特的话来说,就是一部国家认同的幻想型作品。就在这部作品的前言里面,霍桑完成了从官员到作家的身份转换:
不仅如此,在“海关”里,霍桑总是独辟蹊径地走在身份转换的边缘之上: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本土”故事作家、一个历史国家的无头牺牲者、一部丢了脑袋的国家小说、一个得意洋洋的美国无头作家,以及,更进一步,一个美国古老轶事的“编辑”,这些轶事后来变成了《红字》。[1]
贝兰特指出,在她这本《国家幻想的解剖》里,“美国”是一种假定的关系,是一系列集体实践的展示,也意在探讨作为国家主体的芸芸众生,为什么不光是先已经分享了历史或政治忠诚,同样也分享了一系列的情感形式。就好像霍桑在他的小说前言里口口声声在说“我们”——这是指作者和消费他作品的读者,清楚显示读者未及翻开他的《红字》,就已经在美国名下同他绑定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继承了国家的“政治”空间,这里政治指的不光是法律、领土、遗传基因和语言经验,同样也指以上一切因素错综复杂的综合空间,对此贝兰特命名为“国家符号”(NationalSymbolic)。在这个特殊空间里,法律主导着公民领域,主导着他们的权利、责任、义务自不待言。但是贝兰特强调说,“国家符号”还有其他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国家幻想”,来规范欲望、控制情感。国家意味着什么,上文已有交代,那么幻想又当何论?贝兰特解释说:
至于“幻想”,我是指国家文化如何变成本土文化——通过形象、叙述、纪念碑,以及藉个人/集体意识得以流通的诸多场地。它无关国家形式的逻辑,反之是许多同时发生的“字面义”和“隐喻义”,直白的或未有言说的。[1]
所以不奇怪,在贝兰特看来,批评家纷纷将霍桑的断头比喻,释为作者公民权阉割的一个喜剧性象征,由此强调霍桑如何将国家比作一只凶悍的母秃鹰,担心他对“她”依赖过渡,会丢失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由此,身体/国家的阅读模式得以确立。根据这一阅读,霍桑这部立足于身体/国家两分的《红字》,便是一方面深入了集体幻想的设置,一方面又探究了国家符号实践如何将貌似一盘散沙的素材组织起来。在贝兰特看来,霍桑把握美国的方式,是俨如法官,来逐一评判盘根错节、纠葛一体的不同立场:国家的和地方的,法律的和人道的,集体的与个人的,抽象的公民和具体、不同性别的公民,以及乌托邦与历史、记忆与失忆、理论与实践等等,不一而足。贝兰特指出,这不仅是《红字》的风格,也是霍桑19世纪50年代“美国”小说的一贯意识形态实践,包括他的《带七个尖角的房子》、《福谷传奇》等。
二、《红字》的情感维度
《红字》开篇写两个世纪之前,清教小城波士顿某夏日早上的一个场景。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霍桑来说,这的确就是“古老轶事”: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教区里,高挑美貌的海斯特·白兰怀抱婴儿,胸挂代表通奸(adulteress)的红色A字,在更为古老的绞刑台上罚站三小时示众。海斯特举目望去,人群中看到了一个双肩不平的博学学者,那是她多年渺无音讯的丈夫。海斯特回监狱后神情亢奋,狱卒带来了自称罗杰·齐林沃斯医生的陌生来客。海斯特一如既往拒绝说出谁是女儿父亲,但是答应帮决意复仇的齐林沃斯隐瞒身份。拘留期满后,海斯特带着女儿栖居城郊一处荒弃茅屋,靠一手好针线活度日。我们知道一直在尽力庇护海斯特的丁梅斯代尔,就是孩子父亲。眼看闺女珠儿日渐长大,久受罪责折磨却无以吐露,加上一旁齐林沃斯步步紧逼,牧师健康每况愈下。齐林沃斯假自己的医生身份,像狼狗一般追踪牧师,终于确认丁梅斯代尔就是珠儿的父亲。数日后,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树林相会,海斯特提议两人私奔欧洲,丁梅斯代尔也一时心动。选举日,牧师汹涌澎湃布道完毕,随游行队伍来到绞刑台上,当众忏悔罪业,随即咽气,倒在海斯特怀里。多日后,大多数在场人都说,他们亲眼看到牧师胸口有个清晰的红字烙印。同年,失却复仇对象的齐林沃斯,弥留之际留下遗嘱,留给珠儿大笔遗产。海斯特回到她的茅屋,胸前又挂上红字。海斯特死后葬在丁梅斯代尔近旁。两座坟墓合用一块墓碑,上有铭文:郁黑的土地上,红字A。
以上轶事假如薄伽丘来写,那是牧师巧言令色诱骗良家妇女的故事。假如福楼拜写,那又是一个清教主义名义下的包法利夫人。假如司汤达来写,恐怕是红颜祸水可怜两条男人性命。换了托尔斯泰,估计会是安娜忏悔重生的故事。但是霍桑把这则当地流传的“古老”逸闻写得如此悲怆肃穆、回肠荡气。《红字》之所以成为近年情感理论情有独钟的经典对象文本,自有它的缘由。除了贝兰特以“国家幻想”的批评展开叙述,即就情感本身的鞭辟入里解析,小说中也多有精彩段落。如“尾声”部分霍桑写到丁梅斯代尔死去后,以复仇为余生唯一目的的齐林沃斯,顿时蔫了下来。这个不幸的人眼看他复仇一步步走向成功,可是一旦复仇取得全面胜利,邪恶的目的失去物质的支持,这个没有人性的人本身突然变成了可怜虫。由此引出一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爱与恨从根本上说是不是同一种东西?霍桑说,这个问题真是叫人情不自禁要来深究下去,他对此的解答是:
这两种情感发展到极点,每一种都变得亲密无间、心心相通;每一种都会让一个个体依赖另一个个体来获求情感和精神生活的食粮;每一种都会让那个激情澎湃的情人,或者那个同样充满激情的仇人,一旦情感对象消失之后,倍感失落、孤单凄凉。因而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两种激情本质上似乎是同为一物,只是其一碰巧是在圣洁的光辉里为人所见,其二偏偏是在昏暗阴森的光线里被人目睹。在精神世界里,老医生和牧师——两人都成了对方的牺牲品——也许不知不觉之间,会发现他们的世俗和憎恶心结,已经转化成了金色的爱。[2]
霍桑以“爱”作为一切情感的本原,即便对于小说本身来说,似乎也是过于乐观了一些。是以齐林沃斯没有被写成大奸巨恶,即便他被赐予又老又丑的相貌,而且给复仇扭曲了心神。他最后留给珠儿巨额遗产,使这小姑娘一夜成为新大陆最富有的继承人,可见他心底里终而是存有温情。但丁的《神曲》中,叙事人也是在遍历地狱、净界、天堂三界后,最终体悟到世界本是由“爱”编织而成,基本同《红字》一样,用“爱”来归纳作品的主旨,即便多少也还是一样显得言不由衷。
但是霍桑上面这段话使我们“从哲学角度来看”,由此看到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伦理学》作为近年“情感转向”的哲学基础,给情感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
我把情感(affect)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
所以无论对这些感触中的任何一个感触,如果我们能为它的正确原因,那么我便认为它是一个主动的情感,反之,便是一个被动的情感。[3]
这可见,情感与身体、与观念密切联系。它改变身体的情状,使之亢奋、痛苦、嫉恨,直至疯狂。身体如此,观念亦然。一如霍桑写丁梅斯代尔遭受肉体和灵魂的双重煎熬,同时却又美名远扬,特别因了他超乎常人的情感传布及沟通能力,被视为道德化身。虽然,霍桑终而是用“爱”和“恨”来概括丁梅斯代尔和齐林沃斯的情感,但诚如上文所示,这两种情感按照斯宾诺莎的定义,都算不上对情感际会有恰当正确动因的“主动的情感”,反之是不恰当、不正确触发情感的“主动的情感”,即霍桑上文所说的激情(passion)。《红字》由是观之,便也同样可以读作一个由红字A书写出原罪和拯救的亚当夏娃的故事,失乐园之后如何情感泛滥,复归平静的故事。
要之,委实是霍桑不遗余力,光顾着写这两位主人公的美好外貌了。像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那样美好的身体,怎么可能成为邪恶的渊薮呢?反之齐林沃斯的畸形身体可以看作扭曲内心的外显。霍桑写他岁数其实不是很大,可是又处处称他为那个老头、老医生。可见霍桑自己心里也有矛盾。假如认可婚姻是神圣的,齐林沃斯九死一生来到妻子身边,猛然发觉妻子胸口挂着通奸红字,赫然站在眼前示众,他的愤怒可想而知。即便愤怒是基督教的七宗原罪之一,思想起来也该是情有可原。假如认可婚姻不过是一纸文书,践约毁约悉听尊便,那么齐林沃斯与海斯特最多不过有点露水情分,要来挑战海斯特与英俊牧师的伟大私情,是不自量力也是自取其辱。所以这两个男人都是给激情冲昏了头。用霍桑本人的话说,一个是“激情澎湃的情人”(thepassionatelover),另一个是“同样充满激情的仇人”(thenolesspassionatehater),终究是要耗尽心力,同归于尽。《伦理学》中,斯宾诺莎以快乐、痛苦、欲望为人类的三种最基本情感,在此基础上,尽可以构筑起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情感。而以丁梅斯代尔为代表的爱,和以齐林沃斯为代表的恨,亦最终可还原为快乐和痛苦着两种原始情感。诚如斯宾诺莎所言:
爱不是别的,乃是为一个外在的原因的观念所伴随的快乐。恨不是别的,乃是为一个外在的原因的观念所伴随的痛苦。我们又可以看出,凡爱一切的人,必然努力使那物能在他的面前,并努力保持那物,反之,凡恨一物的人,必然努力设法去排斥那物,消灭那物。[4]
小说家很少会关心哲学。但是霍桑有意提醒读者,《红字》里这两个男人代表的两种激情,从本质上看也许是同一种东西。快乐、痛苦、欲望三种原始情感固然都是“被动的情感”,但是一旦观念正确,即是说,由上帝引领出心中的正确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终究能够被动变身主动、否定变身肯定。而这样一种神圣的情感,我们发现,最终是在小说结尾处由海斯特领略到了。
三、贝兰特的分析策略
贝兰特的分析又有不同,它的核心之一是“国家符号”。《国家幻想的解剖》第一章《美国、后乌托邦:霍桑家乡的身体、景观与国家幻想》里,作者一开头就引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以为题记:“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4]贝兰特认为,马克思这里是揭示了一种革命的美学,它是根据其同符号形式的关系,来解释群众运动的政治内容。故而国家就像女人这样的比喻,主要不是指女人怎样表现出国家民族气质,而是涉及到运动得以形成的技术问题。贝兰特继续引述马克思的话: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4]
贝兰特说,这些语词好看也好听,可是名不副实,其实是在讽刺,它们正当得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本人的一句话,那就是“辞藻胜于内容”。即是说,这些言过其实的漂亮辞藻,恰恰是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缺乏自觉的政治意识。它们要求公众“相信”这些华丽场面是“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体性,而革命的政治内涵又反过来偷梁换柱,被置换成了一种超越时间和地域空间的情感活动。故对于马克思而言,贝兰特认为,这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度兴奋的谵妄症,如影相随紧伴着资产阶级的形象生产。
因此,贝兰特指出,当马克思将民族和国家同一个新的意象,一个妇女的意象结合起来,由此揭示国家羸弱谜底时,并非意在通过妇女的脆弱性来表达民族国家的无意识问题,亦并非意在通过妇女比喻来“解决”国家问题,而是换个形式再次提出问题,进而提炼了问题本身。这一“提炼”没有提供明确答案,而是开拓了新的探索路径:就马克思借用性别比喻来重申国家问题而言,便是表明,殊有必要来估价历史经验的政治形式与主体条件之间的谜一样关系。是以贝兰特开宗明义,声明《国家幻想的解剖》开篇第一章,就是通过分析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特殊条件,诸如主导文化或者说“官方”文化、渐而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公民”的人物等,来重申和拓展马克思所关心的语言与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故此,她提出的“国家符号”这个概念,指的便是国家空间制造的话语实践,以及将特定地理/政治疆域内的个体同集体历史绑定在一起的“法律”。而这个国家符号的传统徽记、它的英雄、它的仪式,以及它的叙事,是提供了国家主体或者说集体意识的入门台阶,它们最终将顺理成章地改写自然法,以使国家符号不仅给公民的主体经验和政治权利打上深刻印记,而且波及他们的私人生活,乃至身体本身的生活,简言之,他们的情感生活。
这一从马克思论资产阶级“辞藻胜于内容”的例子,延伸到《红字》文本本身的“国家符号”分析,在贝兰特看来,首先小说中清教生活的心理学,就是缘起于公民们的国家文化认同,与其词汇、记忆与身体之间的脱节关系。她指出,在马萨诸塞州这块殖民地第一任总督约翰·温斯洛普的政治经济学延伸出来的情感理论里,“爱”不过就是指涉某种社会控制形式的技术词汇。国家需要它的臣民来爱法律,然后爱契约,通过司法景观,将个人转化为民法的“集体主体”。就海斯特、丁梅斯代尔、齐林沃斯这三个核心人物来看,他们有中规中矩的国家记忆,但是与此同时,又有针锋相对,即便是被暂时压抑下去的反记忆。而要来探究反记忆的谱系学,莫过于深入“身体”的语言和空间。身体被认为是个人得以变成为法律主体的物质载体,刻写着历史意义,同当下的政治与制度问题没有关系。但是贝兰特引福柯的话,指出身体的历史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以往欲望、失败、挫折等病态经验的印记所积累造就。这样来看,《红字》中的身体,就不光是心灵的神秘写照,所谓病理症状叙说出主体的无意识来。它同样显示出历史和欲望的踪迹,游走在集体和个人身份认同之间的历史与欲望的踪迹。
上述踪迹也是国家幻想被私人化的历史轨迹。就海斯特·白兰而言,贝兰特指出,这段轨迹首先表现在女主人公不时回到她蒙受羞辱的绞刑台上来。绞刑台是国家幻想的司法象征。贝兰特发现,小说中,至少有三个地方,将它彰显国家符号力量的中心地位。绞刑台由此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展览个人如何终究屈服于他或她所属的国家法、民法和教会法,正所谓杀鸡儆猴,以儆效尤。三个场合中,情势的变化不但影响到法律的主体,而且影响到法律本身,由此展示出一种特殊的语言分裂,而被叙事人概括为疯狂。
第一个场合是海斯特众目睽睽之下,胸挂红字出现在绞刑台上。在这个巨大的清教主义惩罚机器里,贝兰特发现,国家真是不遗余力,连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的学童,都给放了半天假,来观看海斯特的三个钟头惩罚示众。市场里人头攒动,正可见出公众对政治生活的热心参与程度。贝兰特注意到霍桑刻意写了人群中叽叽喳喳妇女们的反应:“人群中的重点是在妇女身上,在这个始初场景里,这一侧重点凸显了‘人民’的表征,这是游离在表面上‘代表’了他们的政府和总督之外的‘人民’,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1]由是观之,马萨诸塞这块所谓民风纯正的殖民地,满城居民趋之若鹜来看热闹,就是显示了其公共权力领域的自身特点。
再看海斯特的出场。贝兰特认为,霍桑这里安排的场景也用意深远,体现出对女主人公不同的评判视角。故第一章《监狱门口》,叙事人是出于历史学家和道德家视角,根据天地良心的自然法逻辑来做出判断。第二章《市场》则回到惩罚场景:波士顿的居民目不转睛,全都紧盯着那扇满是大头铁钉的橡木门。这里的公众凝视行为,在贝兰特看来,是展示了一种集体主体性,即是说,小说用以开场并且结尾的政治和司法集体视角——从众人观看海斯特示众到最后丁梅斯代尔众目睽睽之下死在海斯特怀里,足以说明《红字》中的主体性不是一种个人功能,而是属于历史、属于社会。
第二个场合是围绕红字的超自然氛围。同样是在绞刑台上,贝兰特认为它始于镇上最年长牧师约翰·威尔逊的耸人听闻罪恶论。眼见海斯特紧咬牙关,不发一语,威尔逊滔滔不绝谈起了罪恶,而且疾言厉色大谈红字A,以至于“它在人们的想象中激发出新的恐惧,似乎是用地狱的火焰将它染成了猩红色。”[2]对此贝兰特指出,这里的地狱意象传达的是清教和法律话语的超自然主义,它虽然目不可见,却是惩罚和示众民法景观的词语版式。她又引第二章中最后一句话:“那些目送她的人窃窃私语,说是那个红字放出一道血红色光线,闪烁在监狱里黑漆漆的走道里”,认为这是暗示了小说中清教主义世界观的超自然表现,本身就是法律的化身和延伸。而另一方面,红字在众人心中又最终转化为了上帝的书写,令人肃然起敬。红字作为一种话语的基础,因此并不在于简单指涉上帝法律或者国家法律,同样在于它萦怀在人们心中,成为想象的载体,为日常语言的使用和误用提供了场地。贝兰特强调说,字母A这个能指的灵活性,对于法典的符号力量来说,至为重要。
最后是绞刑台上展示的法律的性别身份。贝兰特指出,从一开始,小说就表明法律的性别是男性,一如围观人众里市民回答不速之客齐林沃斯,他们马萨诸塞的地方长官们一直认为,这女人年轻漂亮,虽然罪当死刑,可是他们怜香惜玉,下不了狠心。而被惩罚的海斯特,则面对全场死死盯住她的冷漠的眼睛,强作镇定,保持着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类似的描述多不胜数,足以说明法律的施与和被施与,都超越个体,给概括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故此,主体也好,女人也好,公民也好,不是被“官方历史”,而是给修辞的历史整合在了一起。就像《红字》题为《海关》的前言所交代的那样,这个政府机关的林林总总,莫不具有隐喻意味。加上文学和圣经的联想,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一切所构成的流行话语,莫不刻写着男尊女卑的性别印记。
关于海斯特,她的动机、见解和欲望,贝兰特发现小说叙事人是反复陈述了她主观“所知”和“客观”真情之间的沟壑。如在绞刑台最初示众过后,小说第五章写到海斯特“这个她自身脆弱和男人无情法律的可怜的牺牲品,还没有彻底堕落”,可同时反复说她自欺欺人,沉溺在半真半假的幻想里。而且因为自以为感觉到了丁梅斯代尔的温暖眼神,又“犯了新的罪过”。总之,海斯特是在清醒和迷糊之间左支右绌,她的主体性在叙事人看来,是极不可靠的。不光是红字A的意义不确定,她的精神和道德信念也风雨飘摇,疑云密布。而这一不确定性诚如小说交代,最终是让她“几近疯狂”——在叙事人看来,她精神失常了。对此贝兰特指出:
简言之,海斯特在挣扎。但是殊有必要记住,她挣扎在两个领域的双重法律之下:清教主义的法律和叙事人的法律。首先,她为清教法律的清洗活动给出了自己的身体,以支持“良心”的开发,对于“大众”的心灵和身体而言,它就是法律义务的觉悟。在市场示众蒙羞三年之后,她“官方的”身体便成为许多互不关联事物,诸如罪过、法律、良心、集体认同、社会等级的鲜活化身。如此定位下来,海斯特实质上便与她的同胞、她的姐妹公民们别无二致。[1]
这是说,海斯特的形象是代表了广大妇女的主体性及身体纠结。不光是海斯特,广大妇女们同样是苦苦徘徊在公共领域的主导话语和国家之外的地方知识之间。在贝兰特看来,这最终也反映了霍桑的态度:霍桑的公民观念和性别观念,就这样在官方和大众、国家和地方、集体和个人,以及乌托邦和历史的交集中,呼之欲出。诚如《国家幻想的解剖》一书副标题《霍桑、乌托邦和日常生活》所示,在贝兰特看来,霍桑是将包括妇女命运在内的地方政治,看作国家政治乌托邦的一个他者镜鉴了。
[1]LAUREN BERLANT.The Anatomy of National Fantasy:Hawthorne,Utopia,and Everyday Lif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2.
[2]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M].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2.260;69.
[3]斯宾诺莎,贺麟.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15.97.
[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2009.475-476;474.
[责任编校:阳玉平]
I207;I3/7
A
1002-3240(2017)06-0021-06
2017-02-25
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度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批准号:15ZDB084
陆扬(1953-),上海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