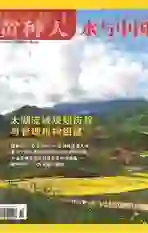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2017-04-06胡晓红
胡晓红
摘要:为了阐述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特色,分析了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文明进程及其文明化理论。分析认为,埃利亚斯文明化理论主张:社会文明不仅是一个过程,还取决于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人格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文化与文明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内涵及其在上述国家的社会起源,反映了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下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结构的产物;个体行为方式的变迁亦经历了日常行为举止的文明化及其隐入私人生活、社会行为的文明化3个阶段。
关键词:文明化;个人与社会;历史社会学;埃利亚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3009106
[GK-2!-2]
埃利亚斯是西方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被称为 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以研究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而著称于世,成为历史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埃利亚斯最突出的贡献,是围绕社会的“文明”过程所做的系统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成“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体系。
一、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
埃利亚斯以《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以下简称《文明的进程》)誉满全球。他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了文明化理论,并且在后来的许多论述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与斯梅尔塞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斯考克波尔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以及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理论家所阐述的思想和理论统称为历史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强调:要对当代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模式提出恰当的追问,就不能脱离历史的视角。无论是经典理论还是现代理论,都一直表现出敏锐的历史意识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仅是停滞不变的过去,不仅仅是由事件、纪念日、朝代和伟人所构成的,它还拥有更多丰富的内容。与自然主义恰好相反,历史的理解能够使个体对特定的具体实践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性有所反思。事物本身的秩序会随时间(历史局势)与场所(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相对社会实践以及所进行的考察选取一种更具反思性的位置。可以说,这种自我反思与历史意识是同步发展的。
历史社会学主张,任何研究社会的理论都必须有能力描述它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也就是说,根据这个社会面对其所主导条件的内部发展历史来阐明它
的出发点。历史社会学认为有必要从更广阔的、更深远的历史视角来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仅从现代国家入手。因为,文明要设想未来的事情会有什么不同,就必须理解文明是如何达到目前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文明程度。因此,历史社会学“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关注过去,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关注未来”[1]。从文明的视角来研究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文化形式,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文明的研究,成为历史社会学黄金时代发展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便是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学术追求的核心思想是要发展出一种以“历史性”为线索的社会学模式,彻底摒弃传统社会学中的許多根本性假设。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特色,就是围绕社会的“文明”过程所作的系统研究,他的策略是从现代西方文明是如何演进的过程作为视角透视西方社会理性化的影响因素和结果。他针对欧洲国家形成与宫廷理性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观念以及各种形式的礼貌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有关欧洲国家形成与西方礼貌文化史的历史社会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埃利亚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社会形态”出发,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去分析个体行动、社会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变动的关系“过程”中理解、解释个体社会行为、心理结构和社会文明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历史并没有什么表明文明的过程是“理性化”的结果,它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计划性的。它是由人类联系网络的自发动力和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方式的特定变化推动着。人们相互依赖以及人类冲动的相互关联,这种社会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过程,构成文明进程的基础。社会形态的基本规则,既不是个人理性“意识”的规律,也不是所谓“自然”的法则,而是人类联系的整体性重组导致了人们行为方式、人格结构的“文明化”。由此,埃利亚斯专注于人格或心理倾向的长期变化,考察人类主体性与权力构型之间的相互交织。他认为,文明的进程既是一个心理事件,也是一个社会事件,它不仅涉及意识内容的变化,也涉及整个人类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他把各种社会形式和人类主体性的转型这两方面融和在一起。这是国家形成与认同形成之间一次非同寻常的联姻”[2]。
因此,为了理解和解释文明的进程,既需要研究人格结构的变迁,又需要研究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微观层次上,心理研究要求把握个体心理能量的整个领域和各种功能的结构和形式;不仅要考虑“意识”或“无意识”单独的功能,而且要考虑各种冲动由一个到另一个的连续性循环过程。在宏观层次上,对文明的进程的揭示,要求对整个结构进行久远视野的社会研究,不仅要研究单个的国家社会,而且要研究在内在依赖社会中特定团体构成的社会领域及其进化的连续性过程,换句话说,要对分化且充斥紧张的社会领域的整个形态进行研究。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从剖析西欧11世纪到18世纪的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人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的影响入手,通过追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的礼仪、习俗、人格、文学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表现,通过历史的展开和历史文献的佐证,集中讨论行为、权力和习性之间相互关联的长期变化的问题,说明行为方式和权力中的变化是如何在人格结构或习性中反映的,以此来分析这种过程与国家形成、国家内部权力的垄断化之间的关系,探讨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历程,从而建构起“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也就是,通过“追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标准与心理特征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国家形成与内部安定过程的彼此关系”[3]。
埃利亚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长期结构演变是与人的社会行为及其习性相联系的。这里所说的“习性”与通常所说的“第二天性”所意指的含义差不多,它指的是我们性格构成中那些非天生固有的但一出生就从社会经验中不断学习从而积习很深的东西,它们习惯成自然,仿佛就是与生俱来的一样。我们的个人习性似乎主宰着我们的行为,但习性是在社会环境中养成和继续形成的,会打上特定的权力差别的烙印,而社会环境则又根植于更大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说,文明化的过程并不是自行完成的,它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这些变迁集中于国家的形成过程,随着国家的形成而逐渐变得正式化,它会日益通过强制与示范,具体指明个人行为的规范。
由此,埃利亚斯得出结论:心理功能的结构,特别是既定时期行为控制的标准,与社会功能的结构以及人际联系的变化是相关联的。人类行为的“文明化”并非仅仅是“理性化”过程的结果,人的内驱力和意识状态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自我驱力变化所推动力来自于人类行为相互作用产生的压力,来自于按特定方向推进并导致联系形式和整个社会网络发生变革的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改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态,从而对人的行为方式、情感以至人格结构提出了改变的要求,并推动着其改变。正是不断增强和扩展的相互依赖导致了人类的‘文明化。”[4]
二、“文明”与“文化”的界定
及其在德法两国的社会起源
(一)对“文明”与“文化”的界定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开篇即指出:“‘文明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5]由此可见,“文明”的概念具有广泛的意涵。但究其本质,埃利亚斯眼中的“文明”,不过是西方社会的一种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它被用于指示一切使得西方社会确信自己优于其他社会的引以为自豪的事物。由此可见,所谓“文明”,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组织有素、可以预期、可以计算的社会。自称“文明”不仅是某种自我肯定,也是间接地对某些他人的否定,其间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文明”的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着不同的涵义。
西欧早期近代化的这种国别差异,导致西欧长期以来存在着“文明”与“文化”这两种观念的矛盾。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开篇即对德国和英法两国的“文明”和“文化”进行了界定,指出它们之间大致有3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文明则是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次一等的价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5]。在德国,人们一般用“文化”来表现自我和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也就是说,“文化”指的是个体性的精神产品,可以不断生成与再生,无终极目标下的“进步”可言。而“文明”则指外在表现出来的物质、行为方式等。德国知识分子力图把“文明”降为第二层次,而通过“文化”来使知識分子独立于“上层”(宫廷社会)和“下层”(劳众)。
其次,在英法两国,“‘文明这一概念既可用于政治,也可用于经济;既可用于宗教,也可用于技术;既可用于道德,也可用于社会现实;而德语中‘文化的概念,就其核心来说,是指思想、艺术、宗教。‘文化这一概念所表达的一种强烈的意向就是把这一类事物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区分开来”[5]。因此,德国“文化”的内涵比英法两国的“文明”要窄,英法两国的“文明”指示着政治、经济、技术、宗教、伦理和价值等多种因素,它既可以指成就,也可以指人的行为、举止而不论其是否有成就;德国的“文化”主要指与这些事实之外的、由人创造的特殊价值与特性,“德国的‘文化则很少指人的行为以及那种不是通过成就而是通过人的存在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5]。
最后,对英法来说,“文明”指过程,而在德国,“文化”指倾向。埃利亚斯进一步解释道:“‘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诸如艺术作品、书籍以及反映民族特性的宗教和哲学体系。”[5]总的来看,“文明”是指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程度减少的过程,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而德国的“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是指这种差异的增大。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表达:“如果‘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5]因而,对于采用“文明”概念的英法两国来说,文化差异的界限早已确立,“文明”是消除这些界限的方法;而对于采用“文化”概念的德国来说,创建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正是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本身要达到的目的。
经过上述的比较,埃利亚斯指出“‘文明和‘文化所体现的民族意识是不同的:德国人自豪地谈论着他们的‘文化,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自豪地联想起他们的‘文明”[5]。由此可见,这些概念产生于各自国家或民族的共同经验,是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同使用它们的群体一起成长、一起演变的,这些群体的状况和历史就反映在这些概念之中。因此,只有深入到不同文化整体中,置于它们各自的社会历史中,才可能理解和把握。具体说来,德国和英法两国对“文明”界定的差异可用这几个国家的宫廷向中产阶级开放的程度和国家身份认同观来解释。
(二)“文明”与“文化”在德国和法国的社会起源
在德国,“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矛盾,“文明”是一种表现自我的行为方式,相对于文化而言,更侧重一种自我意识,强调人的外表和表面现象。而“文化”则指人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直接代表人的行为本身。在德国,“文明”与“文化”的对立与德国当时的社会境况有关。
18世纪的德国,处于分裂、经济欠发达的落后状态,阶级差别明显,阶级壁垒突出。在礼仪上,上流社会盛行法语和法国礼仪,并以此鄙视德国中下层阶级的德国传统。因此,德国市民阶级对德国宫廷独裁政治的冲击并非直接针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特权,而是直接指向上层社会的礼仪。他们以“文化”作为自我想象和德国传统,攻击上流社会所谓的“文明”。在这里,“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是:“文明”是肤浅、礼貌和表面的客套;而“文化”是内向化、情感深化、沉湎于书本和个性人格的形成。当处于德国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作为德国市民阶层的代言人出现的时候,“文明”与“文化”的对立所反映的仅是一种社会内部的矛盾。这便是德国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与宫廷上流社会关于文明教养的争论,这个争论对德国“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境况,反映着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但缺乏强大社会后盾的德国市民阶级与宫廷贵族的斗争。当时,德国知识分子阶层被远远地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全部的合法性存在于他们的思想、科学和艺术的成就之中。与他们对立的是社会的贵族阶层,这些人是靠他们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上流社会的举止行为和宫廷礼仪来证实自我和建立自我意识的。
法国革命后,随着国际竞争的出现和市民阶级的发展,这种社会矛盾却孕育着民族矛盾的萌芽,主要表现在那些讲法语的、按照法国模式“文明化”的宫廷贵族与处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由此,“文化”和“文明”的矛盾,又由国内阶级矛盾的表达转变为针对德法矛盾。也就是说,德国知识分子阶层不仅从反对宫廷贵族的斗争中证实自己,还进一步通过与其他与之竞争的民族划清界线来证实自己。因此“文化”与“文明”这一对立概念的内容、意义与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主要用于表现社会内部的对立发展为主要用于民族对立。由此可见“文明”和“文化”的对立再现了德国的社会历史背景,表达了德国人的自我想象,指示着先是存在于国内各阶级之间,而后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自我确认的差异以及特征和行为的差异。
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在德国的发展历程,埃利亚斯总结到:“‘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命题不论以什么概念来表达,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所表达的是人的某种特性的对立,这种对立最初表现为社会矛盾,以后则主要表现为民族矛盾。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与宫廷贵族在德国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5]
法国“文明”概念也是在18世纪下半叶法国市民反对宫廷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但其形成过程、功能和意义明显不同于德国概念。与德国不同,法国市民阶级发展较早,而且国内阶级壁垒低,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出类拔萃的人物较早被宫廷社会的圈子所容纳,并且与宫廷社会形成密切的联系。而且,早在18世纪,市民阶层的上层人物与宫廷贵族之间在习俗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当市民阶层成为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时,原来为宫廷贵族阶层所特有的社会特征,诸如行为方式和习俗的形成、交际形式及情感方式的形成、重视礼仪、交谈能力和字斟句酌、发音清晰等等,逐渐演变为民族特征。对于法国的社会现实,埃利亚斯总结说:“所有这一切最早都是在法国宫廷内部形成的,然后才通过连续不断的扩展运动逐渐从社会特征演变成了民族的特征。”[5]
除此之外,法国的市民阶层很早就表现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他们参与了统治和管理,甚至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它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持续的、密切的接触;另一方面是市民阶层很早地得到了较强的政治训练,并且学会了在政治范畴内思考。
法国的社会结构使市民阶层慢慢地发展起来,由于法国的中等阶层与德国中等阶层的行为方式和所处的情况不同,他们长期保持在宫廷传统的框架下,对贵族阶层的反对表现温和,他们要求的是改善、修改和调适。他们并没有提出与宫廷全然不同的理想和模型,而只是改革既有联系和模型,他们将宫廷模式视为“虚假的文明”,而试图用一种遵循自然法则和理性的英明统治的“真正的文明”取代它。他们没有像德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那样通过“有教养的人”以及“个性”的思想提出一个与“文明人”截然相反的模式,而是继承了宫廷的传统,使之发展、壮大。因此,法国“文明”概念的作用、意义以及其形成过程也不同于德国的“文化”概念。
法国的“文明”是与“野蛮”状况相对立的概念,直接从“有教养”中衍生出来,“有教养的”一词与法国的“文明”概念非常接近,“有教养”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指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等,它在“礼貌的”、“文明的”等宫廷贵族的用语中得到了体现。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行为特点在法国的古典悲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讲究礼仪,用理性来抑制人的情感;恰如其分的举止,拒绝所有平民式的表达方式等等。
实际上,在这种“文明”的概念中,混杂着两种观念,一种是它构成另一社会阶段“野蛮主义”的一般对应性概念,这在宫廷社会中长期流行;而另一方面,它强调文明不只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必须推进的过程,这就是“文明”概念中新的因素。显而易见,法国“文明”概念与德国“文化”概念一样,也反映着法国市民阶级的社会命运,在形成初期,也是宫廷反对派和中等阶层的工具,特别是中等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社会内部斗争时所运用的工具。隨着市民阶层的崛起,“文明”这一概念便成了民族精神的体现,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表达方式。“文明”这一概念表明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和进化的过程。
总之,“文明”和“文化”概念都有着自身的社会根源,它们在不同国家人们的共同经验中获得其功能、形式和意义,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形态(即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结构的产物。
三、个体的文明化进程
文明是一个过程,“高雅”“有教养”“文明”标志着社会发展过程的3个阶段。对应概念的转换,埃利亚斯眼中的个体文明化进程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文明标准的制订——宫廷礼仪阶段
文明标准的制定并不是社会各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宫廷礼仪的基础上逐步扩展至各阶层的。随着中世纪等级制度的瓦解,正在形成中的宫廷贵族阶层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阶层。在宫廷中,人们用一种新的、完全不同于其他阶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也通过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区别和表征。在这一阶段,“文明”标准的制定是出于一种社会需要,文明的社会起源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二)文明的扩展——礼貌阶段
当文明跨越了宫廷的边境,逐渐成为大众所共同接受的价值准则时,文明就扩展为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貌”。对于文明扩展的过程,埃利亚斯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总会有某个阶层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他们不仅形塑着自己的行为模式,并且这种行为模式有意或者无意地成为其他阶层行为的典范。对应于埃利亚斯所考察的宫廷社会,这个过程表现为首先在宫廷的小圈子内形成了关于“文明”行为的评判标准,然后这些标准又逐渐向其他阶层扩展,并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一个行为准则,于是社会各阶层达成了对“礼貌”的共识。
当然,文明的内容是在宫廷阶层同市民阶层的碰撞中逐步调适而完成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个并行的趋势:宫廷阶层的市民化和市民阶层的宫廷化。一方面,宫廷中的习惯、风尚和行为方式不断渗入中等阶层的上层,并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来自市民阶层的行为方式也影响着宫廷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宫廷阶层同市民阶层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三)自我强制机制的形成——文明化阶段
“文明”不仅成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规范,也内化为人们自我监督的心理机制。人们越来越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置于别人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对此,埃利亚斯考察了擤鼻涕、吐痰、餐桌礼仪、卧室行为、两性关系、攻击行为等方面行为规范的变化。结果发现,在中世纪前,人们随地吐痰、擤鼻涕、赤手进食、共用餐具、当众大小便并很少掩饰性方面的兴趣或活动,而这些行为在中世纪后普遍受到社会的鄙视。
透过这些琐碎的问题,我们发现:“以往曾经给人带来无尽愉快的东西现在不仅仅是被禁止了,而且反倒成了不快的源泉。其原因在于:为社会所不欢迎的本能与愉悦的表现受到某种限制措施的威胁和惩罚,这些措施会使人们对原有的满足快感的方式产生不愉快和焦虑的感觉并不断巩固。攻击性情感与行为方式的逐渐驯化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3]
总的来说,伴随着文明化进程,人体的一切功能越来越严格、完全被隐私化了。人类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分裂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密行为和公共行为。而与这种公共性和私人性行为的区分相关联,人格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冲动、冲动抑制、社会性羞愧和耻辱的冲突在人的心灵内部展开,“自我”“超我”被强化,本能被置于“潜意识”之中。原本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却逐渐成为自发的行为方式;原本是形塑而成的某种自我控制,却被认为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这种做法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达到的程度和它所具有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阶段,也就是反映了文明的进程。由此可见,“纯‘理性化的原因或解释并非‘文明化过程的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正好相反,即‘文明化过程使人们愈益用理性化的方式思考或解释问题”[3]。
由此可见,文明逐渐演变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自我控制的机制,人们不断地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调适着自己的行为。同时,这种机制按照社会的建构也持续不断地调解、改造和压抑人们的情绪,人们越来越压抑自己的本能,以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整个社会的规范。就这样,外来控制正是基于社会结构转化为自我机制。从外在的行为方式到内在的心理结构;从理性的自觉意识到情感生活的内涵与结构;从外在约束到自我控制,埃利亚斯的用心是将人们的思路引到人的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引到人的情感和心理,引到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
沿着概念转换的轨迹,我们发现文明是行进在文明化过程本身的轨道上,行进在西方社会发生的行为变化的轨道上。概念的转换,反映着人们对行为方式的一种重新评价,它伴随着行为规则、行为方式的变化。人们行为方式的历史变迁包含了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日常行为举止的文明化;二是这种行为日渐隐入私人生活中;三是社会行为的文明化。这3个方面构成西方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文明”概念反映的正是这个文明进程的终结。
四、结语
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始终强调:文明进程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这意指在人类历史的任一时段或空间,就文明一词的内在含义而言,都没有文明的“零点”或“终点”,文明永远都在形成之中。
参考文献:
[1][WB]Marcuse HNegations[M]Boston:Beacon Press,1968
[2]布賴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5]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M]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