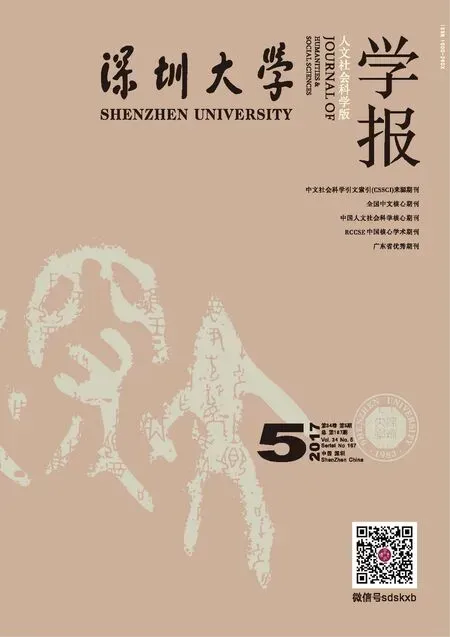从盛行到自持: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的演进
2017-04-03禹竹蕊
禹竹蕊
(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四川 成都 610071)
从盛行到自持: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的演进
禹竹蕊
(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四川 成都 610071)
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得到肯定是源于其预设,即视政府为完全理性,进而可以代替心智不够成熟或是理性不足的当事人做出理性行为判断和选择。但政府的成员本身不可能是完全理性人,因而这一理论从诞生之初就饱受诟病,甚至有专制主义“变身”之嫌。同时,过度滥用和容易导致行政管理效率低下,则是法律父爱主义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于福利国而言,要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公共福祉,要带领国民谋求幸福最大化,国家和政府出于法律父爱主义,难免会干涉和克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应该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对此进行必要限缩,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有效化解法律父爱主义面临的双重困境。
法律父爱主义;法律家长主义;行政效率;限缩;自持
行政管理是门与时俱进的艺术。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行政管理的方式与手段也在进一步嬗变。行政管理模式由传统的压制型逐渐演变为回应型,管理方式由“自上而下”逐步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理手段也从强调刚性手段进化为强调“刚柔相济”。而这一切,源于行政民主的发展,也折射出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的演进。
一、法律父爱主义及其理论基础
(一)法律父爱主义的缘起
父爱主义源于拉丁语pater,是指像有责任心的父亲那样行为,或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有爱心地对待他人[1](P48)。发肇于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也称“法律家长主义”,是指法律为了当事人利益而不管、不顾其意志,进而限制其个人自由,迫使其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一种干预模式[2](P75)。善意的目的、限制的意图、限制的行为、对当事人意志的不管不顾,共同构成法律父爱主义的显著特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学派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和令人怀疑的,社会并不能保证政府总是真正地追求公共利益,反倒是市场经济机制可以把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导向追求公共利益,因而应当完全依靠市场推动社会,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和企业,政府应当消极地充当“守夜人”的角色[3]。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将这一学说奉为真理,人们普遍将自由视为权利的本质属性或构成要素,认为所谓自由就是“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外来干预或胁迫。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或要求,那么,这种主张或放弃本身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4]当时的政府极少干预个人的自由,行政管理过于消极。然而,过分放纵个人自由,必定会导致财富过于集中、经济分配不均。自由竞争加剧,垄断、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人们迫切需要政府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角色,提供市场需求的各种公共服务。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干预经济并解决纯粹市场调节的缺陷,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管理职能不断增强,并开始保护在市场竞争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权利。福利国家的理念相继在各国树立,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个人健康和公共安全方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二)法律父爱主义盛行的理论基础
法律父爱主义的盛行,源于其理论基础。
人存在“三个有限”,即: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这一观点一经行为经济学和行为法律经济学提出,就得到了普遍认同。质言之,人难免会存在诸多认识上的偏见或偏差,尤其是在知识高度碎片化的今天,一个人不可能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个人的理性判断往往囿于知识的短板、认知的缺陷、阅历的有限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而变得非理性。有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明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好、最有利的,但自控力不够强,抵制不住诱惑,并不会做所谓的最优选择。此外,虽然人都有利己思想,但出于对公平、正义、社会认可度等各种因素的权衡,某些时候个人的行为选择并非完全为了自身利益。况且,行政管理的对象,亦即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除了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包括弱势的、需要救助的、行为能力欠缺的人,还包括理智不够健全的、需要管制的人。故而,法律父爱主义认为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公民的自身利益可以忽视其意志而采取限制其自由的举措,当然,这种限制措施旨在增加公民的利益或是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这是一种善意的考量,闪烁着父爱的光芒,关怀透着理性,严苛不乏温情。
问题是以父爱主义为名从法律上限制自由是否正当?
众所周知,在现实社会中,权利主体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或自由,倘若伴随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很可能与其他权利或其他主体的权利、自由发生冲突。如果一个权利主体毫无节制地滥用自由、行使权利,这种冲突就会愈加凸显。经历了自由主义法治国时期,人们对无政府状态的“完全自由”所带来的社会无序有了一种天然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就成为了一种共识。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思想的自由之外,绝大部分自由都是有一定边界的,换言之,自由并非绝对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应受到相应的制约,对自由的限制和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可见,法律父爱主义对自由的干预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而且,有利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对此,戴维·米勒称,即使行为者的行为对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仍然可能“对他人造成远期的后果,因为它削弱了行为者贡献于社会的能力或者制造了需要他人来承担的代价。”[5]米勒认为政府制定开车需要系安全带的法规,旨在避免其他社会成员为行为人的冒失行为买单。换言之,一旦开车者没系安全带而导致交通事故,政府税收就会用于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等费用,安全带立法旨在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避免政府税收不必要的支出。依照这一观点,法律父爱主义有利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
一些行为经济学家还指出:如果某些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公民的行为,但能给那些不理性、容易犯错的人带来极大好处,且只带给那些充分理性、不易犯错的人很小的不利或成本,甚至不产生成本,这样的法律规制对那些为其自身利益做出可靠决定的人来说是无害的,而对那些不能做出最佳选择的人来说是有利的。而且,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能提高社会福利的制度[2](P77)。
可见,法律父爱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法律观念,其理论基础充斥着人本主义的色彩,贯穿着人文关怀的精神,与福利国、社会国的理念相辅相成,符合近代行政的潮流与趋势,成为了各国行政管理中常见的方式和手段。这一理念恰与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仁政与民本理念彼此契合[1](P53-54),故而在我国的行政管理领域中也倍受青睐,一度颇为盛行。
二、法律父爱主义面临的双重困境
时至今日,社会发展要求政府不再单纯地做消极的守夜人,要求政府在主动提供行政给付、公共服务的同时,还要积极对市场失灵等现象进行宏观调控。尽管职能转变的需求使得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愈发主动,但法律父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一)理论上的质疑
1.如何确保政府的理性
其实,法律父爱主义从诞生伊始,来自理论上的质疑就从未停止过。
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之所以得到肯定,源于其预设,即将政府视为完全理性,进而可以代替那些心智不够成熟或是理性不足的当事人做出理性的行为判断和选择。但是,政府毕竟只是个抽象概念,其行政管理从拟定规则到决策制定,再到管理实施,皆要依赖具体的人来实现。但这些政府成员的身上也同样存在人的“三个有限”。既然政府成员本身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人,如何能够确保他们对公民自由的“横加干涉”有着充分理性?这是法律父爱主义在理论上面对的首要质疑。
2.如何化解专制主义之嫌
更大的质疑来自反专制主义者。在反专制主义者看来,法律父爱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变身”,是专制主义披上了“父爱”的伪装,摇身一变,打着关怀和善意的旗号,对公民的自由进行限制,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一般认为,基本权利从本质上反应了公民对国家的防御,是一种对抗权。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立宪主义已经把对基本权利侵害的重心从“过程”的考虑转移到对“结果”的判断上,即只要国家权力的行使增加了人们基本权利实现的困难或致使人们基本权利无法实现时,均可能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害[6]。故而,德沃金指出,“必须认真看待公民权利,特别是‘关怀和尊重’的平等权利,这是指应当尊重每个人独立自主的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应得到生活得更好的机会,但不能强制人作出更好的选择。即使我们确信,如何行动对某某人是有利的,会使他生活得更好,也不能强迫他选择我们判断为正确的行为路线和生活方式。如果他被迫按照我们的判断去行动,在许多情况下,他并不会生活得更好,因为这将侵害独立自主的价值。”[7]
可见,法律父爱主义并非在所有人心目中都是绝对的善,至少它一直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批判的对象[8]。就连康德也认为,“如果一个政府建立的原则是对人们的仁慈,像父亲对他的孩子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它是家长主义式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是能被人想象出来的最坏的政府。”[9](P113)尤其是在行政民主化的浪潮中,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在行政管理中大力增加公众参与的元素,行政管理者必须放低姿态,倾听被管理者的诉求,太过强势的法律父爱主义难免遭受质疑和“嫌弃”。
(二)实践中的困惑
1.限度问题
诚然,即使是支持者,也认为在行政管理中,法律父爱主义的运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只有当风险是不合理的,对当事人行为的直接干预才能被证明为正当。如果无限制地扩大法律父爱主义的范围,就会陷入“超父爱主义”的陷阱[1](P55-56)。 毕竟政府天然处于强势地位,随时可能超越权力应有的边界从而侵犯个人权利,超出必要限度的法律父爱主义可能会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大开方便之门。权力一旦披上了法律父爱主义的外衣,对自由的伤害极可能比赤裸裸的权力带来的伤害更大;一旦政府从“善意”、“善行”出发干预公民权利,此类权力行使更应当保持警惕和审慎,以免侵害自由。
问题是,我们意识到了过度滥用法律父爱主义的危害,却在实践中把握不好一定的度。例如,2009年,鉴于网络视听的内容泛滥失控、网络不良行为日益增长,广电总局大规模关闭视听网站。这一管制手段目的明确,有利于净化网络环境,有利于保护网民身心健康,却遭受了极大的质疑。究其原因,便是反对者认为“强行关闭”这一管理手段超出了必要限度,并非达致管理目标的唯一手段和最优选择,不具备正当性。
2.效率问题
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另一困境便是效率问题。在此,以两个典型事例予以佐证。
众所周知,不系安全带一般情况下更多危害的是司机和乘客自身的安全,安全带规制是一种典型的出于法律父爱主义的强制管理措施。目前的电子监测技术仅能拍摄到司机和副驾驶座上乘客的情况,不便拍摄后排乘客有无系安全带,同时,路面行车的特点、道路交通的拥堵都使得警察不可能拦下每一辆车进行检查,相应的执法只能是随机性执法,并不能真正对所有行使中的车辆进行监管,其管理效率自然低于预期,还会招致执法是否公平的质疑。难怪波斯纳也认为要求系安全带的规制是无效率的[9](P113)。
此外,基于法律父爱主义,美国在行政管理中大力推广“强制披露”这种监管模式,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模仿。“强制披露”制度要求信息披露人向披露对象提供相关信息,以便披露对象能够更明智地做出选择,也使信息披露人不能够滥用其优势地位。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告知人们相关的权利和成本,有的是警告人们危险的产品、不可靠的人,甚至是提醒他们自身可能会出现的不谨慎。例如食品内容标识和香烟外包装上的警示语都被认为可以显著地改进民众的健康和膳食习惯。然而,近年来有美国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强制披露”这种监管模式,在诸多领域也是低效率、失败的。研究表明,尽管在不少核心的强制披露领域中,家长式监管可能是有益的,但更多时候这样的披露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处理披露信息的个人经验以及社会经验使人们确信,忽视、不理会、跳过披露信息并未带来明显的灾难。很多证据表明,人们往往并未注意到披露信息;即使他们注意到这些信息,他们也熟视无睹;当他们阅读这些信息时,他们敷衍了事;他们忘记和误解所阅读过的大量信息,并很少将所了解到的信息融入到自己做出的决定中。而在诸如养老金计划、银行借贷、医疗等领域,复杂的信息披露涉及太多专业知识,不具备相应常识的当事人往往无法读懂被披露的信息,几乎难以从中获益,无法借助长篇累牍的信息做出所谓的正确判断,最终要么放弃阅读直接签字,要么通过和专业人士的交流做出选择。可见,花费了大量成本的强制披露,其效率乃至成效都不尽人意[10]。
三、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的自持
不可否认,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随着行政民主的发展,面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法律父爱主义在运用时应该有所限缩,才能真正赢得尊重,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积极功能。
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与目标选择,乃至利益衡量,这些固然是法律父爱主义运用到行政管理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但相关论述较多,在此无需赘述。本文认为,法律父爱主义要恪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力争做到自持,从而促进行政管理的理性。
(一)恪守法律保留
按照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一个行政行为能否成立,首先需要检视其法律容许性,即这个行为是否为法律规范所允许。任何公民依法对社会、对公共福祉都负有一定的义务,国家机关为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而合法行使公权力,有时难免会对公众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通过实体法来设置公众对合理损害(包括自由和权利的适度限制和克减)的容忍义务是一种必要的法律规范技术。如果这种损害是合理的且在社会义务的范围之内,公众应该容忍合理损害。但这种对合理损害的容忍应该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容忍义务只能由宪法和法律来规定。
同时,从阶段性构造来看,行政过程包括了行政立法、政策制定等行政目标和标准的设定,以及行政行为实施、纠纷解决等三个阶段。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显然是行政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源头上决定了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水平高低,也是预防行政争议的关键。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严格意义上讲,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都需要遵循宪法和法律,更何况,法律父爱主义的贯彻落实旨在阻止相对人的自我伤害或增进其利益,虽然能在客观上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效果,但其措施会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相对人的自由或权利,甚至是基本权利。这便要求在行政管理中,法律父爱主义必须以法律保留原则为界限。一旦其决策触碰基本权利,必须恪守法律保留。
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是指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或者说公权力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11]。根据对于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和方式是否做出规定,基本权利限制可以分作一般性的法律保留、特别的法律保留以及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限制。前两种情况下,立宪者将基本权利的限制交由立法者来做进一步规定或者交由行政机构基于法律针对个案做出行政行为,例如《宪法》第39条①规定的“禁止非法搜查”属于一般性的法律保留,《宪法》第40条②规定的“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特定情况下依照法定程序可以限制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则属于特别的法律保留。倘若立宪者并未将限制某类基本权利的权力交由立法者,行政机构更加无权通过行政行为来限制基本权利,这便是典型的宪法保留。
可见,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是法律保留或宪法保留。行政立法或管理政策的出台绝对不能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擅自对基本权利进行干涉和克减。哪怕目的是保障相对人其他权益,哪怕目的是增进公共福祉、维护公共利益,在行政管理中背离了法律保留原则的法律父爱主义,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甚至有违宪之嫌。
对此,台湾学者指出,法律保留的密度和行政行为对人民权利的干涉强度以及涉及人数的多寡应成正比。吴庚教授认为,“无论奥地利之全面保留理论,或现时德国盛行之重要性理论或国会保留理论,皆允许法律保留之例外,承认有低度保留之存在,但均无法建立完全明确之区分标准,故只能谓对人民权利干涉强度高者,法律保留之密度大,反之亦然。”“涉及人数多寡与是否应由国会立法加以规范,有关联性:影响多数人或以一般国民为适用对象者,通常应由法律加以规范。反之,例如属私经济行政(国库行政)之行为,或签订行政契约,通常系行政主体与个别对象间之行为,而且必须与相对人之意思合致,故法律保留之密度较小。”[12]正因为一般性法律保留、特别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要求呈阶梯性递增趋势,故而,在行政管理中,若是出于法律父爱主义普遍干预人民自由和权利,便必须恪守法律保留甚至是宪法保留。
(二)遵循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涉及威权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按通常说的“三分法”,分为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强调行政行为的实施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私人权益的保障,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私人合法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那么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作为行政法的“帝王条款”,比例原则从理念上源于对正义的需求,着眼于法益的均衡,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为最终归宿。这一原则是对依法行政原则的有力补充,要求行政行为在合法的前提下注重合理。
福利国家的兴起,自然要求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公共福祉,国家和政府可以进行积极的行政管理。但是,姑且不论传统的刚性行政行为方式,即使是新兴的柔性行政行为方式,在对社会进行管控时,都有可能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一定的干涉和克减。这便要求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应当自觉遵循比例原则。除了要考虑对自由和权利的干涉和克减在目的上是否正当,还需要考虑管制方式是否必要,以及管制手段与管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关联。具体而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首先,从适当性原则出发,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应该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公共福祉和促进个人谋求幸福最大化,而不应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加强行政管理、便于执法的工具。美国自1927年撤销反吸烟立法后,法院普遍认为“除非这种限制能合理地提高公共福利,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干涉。”[9](P114)这便是基于适当性原则对法律父爱主义进行的限缩。其次,依据必要性原则,如果采取强制性较弱的管理手段也能达成管理目的、取得同样的社会效果,那么在相应领域,行政机关应采取其他相对更为温和的管理手段而非运用法律父爱主义强制性干涉和限制相对人自由或权利。最后,按照狭义比例原则的要求,法律父爱主义的运用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忽视私人权益,也不能因某类或某几类私人权益而忽视其他的私人权益,以父爱主义为名的法律干预所克减的自由和权利与行政管理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合乎比例,绝不能用大炮打小鸟。例如政府为了民众健康要求香烟在外包装上必须印刷相应警示语,此等法律父爱主义的运用合乎比例,但倘若因此强制要求民众禁止吸烟,那就违反了狭义比例原则,会遭到民众的埋怨和抵制。
四、结 语
自由和权利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稳定、秩序和福祉是国家政府不变的追求。法律在何时为了人的尊严而必须站出来违背当事人的意志、限制其自由和权利,何时应该将一切交由当事人自己做主,这是法律父爱主义在行政管理中随时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审慎和温和是法律父爱主义应当具备的姿态,在对各种利益和价值进行审慎衡量之后,若是必须对自由和权利进行干涉和克减,也应当在必要的限度内采取最温和的方式予以限制,且限制的手段和方式要经得起实质意义上的考量,限制的实施也要经得起程序性规则的审查。唯有懂得自持,唯有合法合理的限缩,行政管理才能减少和杜绝“超法律父爱主义”的出现。
注:
①《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②《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1]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2]郭春镇.论法律父爱主义的正当性[J].浙江社会科学,2013,(6).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2.
[4]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8.
[5](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M].李里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65.
[6]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173.
[7]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449,551-553.
[8]郭春镇.另一个德沃金如是说——《自治的理论与实践》札记[J].河北法学,2007,(10):4.
[9]孙笑侠,郭春镇.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6).
[10](美)欧姆瑞·本·沙哈尔,卡尔·E.施奈德.过犹不及 强制披露的失败[M].陈晓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1]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47.
[12]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8.
【责任编辑:来小乔】
From Prevalence to Self-Restriction:Evolution of Legal Paternalism in Administration
YU Zhu-rui
(Law Department,Party College of Sichuan Province,Chengdu,Sichuan,610071)
Legal paternalism is recognized in administration for its presupposi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tterly rational and can thus make rational judgment and choice for people who are not mature or rational enough.But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completely rational,therefore this theory has been criticized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and is even condemned as the“transformation” of despotism.Meanwhile,in practice,legal paternalism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as it is abused and prone to cause inefficiency in administration.For welfare states,to maintain public order,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promote public welfare,and lead people to pursue maximization of happiness,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out of legal paternalism,may inevitably interfere in and cut dow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ights.But necessary restriction should be made in this regard to ensure administration is legal and reasonable so as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dual dilemma facing legal paternalism.
legal paternalism;Legal paternalism;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limit;self-restriction
D 90
A
1000-260X(2017)05-0060-06
2017-06-20
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17年度重大研究项目“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研究”(ZD2017001)
禹竹蕊,法学博士,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