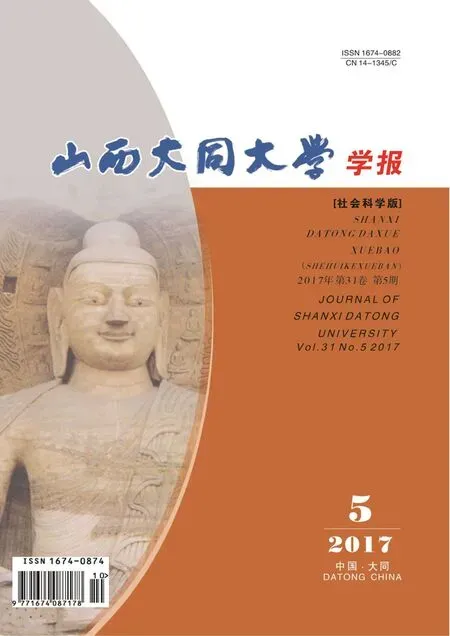近期文坛爱情书写的新趋向
2017-04-02吴玉永
吴玉永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近期文坛爱情书写的新趋向
吴玉永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近期文坛上的爱情书写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趋向,纯情叙事正在悄然归来。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打破爱情禁区到“回到爱情自身”再到“性还原”的发展过程。社会阅读期待也从单一地为性描写的“大尺度”喝彩,转向了对“山楂树”式的纯情叙事的呼唤。当由“情”向“性”的倾斜达到某种极端化的程度之后,其“情还原”的生成也就具有了物极必反式的必然性。这种纯情叙事的再逆转倾向,标志着作家对情与欲的关系乃至对人的认知,都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升华,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前文坛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刻的自我调整。
爱情书写;性还原;情还原;再逆转
这个话题要从2010年的“山楂树现象”说起。一部普通的网络爱情小说《山楂树之恋》,一个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平实的爱情故事,在被搬上电影银幕之后,迅即在全社会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小说”、“史上最纯洁的爱情”之类的称誉不胫而走。平心而论,这部小说的艺术水准很一般,“史上最纯”之类的评价也未免言过其实。如“梁祝”、“王宝钏与薛平贵”、“孔雀东南飞”、“钗头凤”、“宝黛”及琼瑶式的言情、“神雕侠侣”式的铭心恋情等,仅中国文学史上就不可胜数。而这也正是“山楂树现象”的发人深省之处。它表明社会阅读期待在发生变化,读者已不再如当初那般仅仅高调地为性爱书写的“突破”和“大尺度”而喝彩,而转向对“山楂树”式的纯情叙事的呼唤。另一方面,近期文坛创作现状也表明,一种爱情书写的新趋向已然生成,“纯情叙事”正在悄然归来。这首先体现在网络小说和影视剧创作中。如《和空姐一起的日子》(许悦)就被誉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蔡智恒)之后“最干净的爱情小说”,是“干净剔透的纯爱读本”。作为“新生代都市女性情感代言人”的青年女作家唐欣恬,其“都市婚恋系列小说”广受关注和好评,《女金融师的次贷爱情》《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但愿爱情明媚如初》等,既有《山楂树之恋》式的纯情和“干净”,更有对“80后”一代对真纯爱情的执着、坚守态度的弘扬。这批“网络写手”堪称文坛后备力量,是文坛未来的生力军。影视剧中的这种纯情叙事倾向更为明显,如《金婚》(王宛平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郑晓龙导演)、《咱们结婚吧》(孟瑶编剧,刘江导演)、《第二十二条婚规》(周涌编剧,金琛导演)、《嘿,老头!》(刘东岳、俞露编剧,杨亚洲导演)等,就大都因其对纯情的张扬而获得巨大成功。其次,诸多文坛名家在爱情书写方面也相继推出了正面凸显纯朴情感的新作,如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潘向黎《轻触微温》《倾听夜色》《缅桂花》、铁凝《春风夜》、温亚军《下水》、乔叶《取暖》、漠月《湖道》、葛水平《喊山》等。这些作家有的是一直在坚守着其纯情叙事的典雅之风,如潘向黎等;有的是其爱情书写经历了大开大合和鲜明反差,从早期创作中那清纯少女般的唯美和诗情崇尚,到上个世纪末执着于女性欲望及其负面人性的展示,再到近期再度表现出对纯情叙事的青睐,如铁凝等。同样令人欣慰的是,这批实力派作家的近期创作在不约而同地强化着纯情叙事回归倾向的同时,其作品也获得了社会阅读群体的高度评价。
纵向地看,这种纯情叙事的新趋向的生成,其实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新时期之初,面对“爱情荒漠”的文坛及作家谈“爱”色变的不正常现象,刘心武、张洁率先发出“爱情的呼唤”,《爱情的位置》、《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所形成的冲击力,至今让人回味不已。由《男人的风格》(张贤亮)、《离异》(吴若增)、《假释》(陶正)、《金灿灿的落叶》(王安忆)、《山雀儿》(李宽定)等大批作品所合力发起的,则是对既定爱情观念的挑战和“回到爱情自身”的努力,其间那“神女峰的倒掉与挑战者的姿态”[1](P79),尤其令群情振奋。1980年代中期,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三恋”等以对性的正面而诗意的描写、对性心理的细腻而生动的揭示,完成了对“性禁区”的突破。此后《白鹿原》(陈忠实)、《废都》(贾平凹)等“不回避,撕开写”的性爱书写,无疑已成为其轰动效应的一大助推因素。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文坛热点的“私人化写作”中,爱情书写已逐渐突进到“性还原”的地步;借用《此人与彼人》(述平)中的话来说:“在他们这里,性的神秘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消解,加在性之上的许多外在的因素都因此显得轻飘飘的没有了它应有的重量。……性还原为性本身。”这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爱情书写的演进轨迹。这一轨迹或可简化为:爱情禁忌→爱情呼唤→“回到爱情自身”→突破“性禁区”→“性还原”。
“17年”文坛上的“爱情禁区”显然属于一种极端化的偏颇,它对中国文学的消极影响决非仅仅在于题材上的钳制,而且对其艺术水准构成了整体上的损害,也导致了文学对“人”的理解的简化。新时期之初文坛对爱情禁区的突破和爱情书写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进步。强调“回到爱情自身”及其性描写的突破,凸显的是对爱情中的性因素的正视,以及与自我意识觉醒维系在一起的生命意识和“身体”意识的自觉。[2]但此后逐渐形成的“性还原为性本身”的倾向,则意味着爱情书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还原”的往往就是人们常说的“无爱之性”。而这种爱情书写的“性还原”倾向的生成,也自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性。一方面,曾几何时,文坛上的爱情书写所强调和追求的,往往就是突破、“解放”或“深刻”。其突破和解放,所指向的首先就是原欲及其性描写的尺度问题,就是其书写重心由“情”向“欲”、由“爱”向“性”的转移;其“深刻”所指的也是对所谓“生命力”的表现,而其“生命力”又往往是降格和简化而为“本能”的。另一方面,爱情书写的“性还原”倾向的生成,也离不开某些外部因素的助推。这种助推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阅读期待尤其是批评界的反应,即往往越是那种“大尺度”的性描写,越会赢得“突破”、“深刻”之誉,而“纯情”叙事则似乎越来越小心翼翼,以免某种所谓“保守”、“传统”之讥。二是外部现实语境的变化尤其是有目共睹的性观念的开放,对文学创作中的“性还原”现象的巨大影响,人们对于文学创作中的不论何种程度的“纯粹而彻底”的性描写,往往都会给予所谓“合情合理”、“人性化”之类的默许和宽容。但不论怎样,当这种由“情”向“性”的倾斜发展到“性还原”的极端之后,其物极必反式的“情还原”的再逆转及其纯情叙事倾向的生成,同样也是具有其必然性的。
近年来的纯情叙事和“情还原”的再逆转,并非意味着爱情书写又退回到当初那种“爱情荒漠”的起点上去了,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作家们对情与欲的关系乃至对“人”的认知,都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升华。显而易见,1990年代文坛上的“私人化写作”及其“性还原”倾向,它所集中关注的是人的本能欲望,凸显的是欲对情的支配和冲淡,是性对爱的冲决和淹没,也是本能欲望对的“人”的统御和扭曲。而近些年来的纯情叙事和“情还原”,既不存在回避爱情关系中的性欲因素和本能冲动的问题,更不是出于什么外部因素的制约,它所体现的则是作家在爱情书写中对情与欲的关系的理性看取,是情对欲的主导和制约,所凸显的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的自觉,是“人”在现代物化大潮中的主体意识的强化。比如,近年来以书写都市年轻白领的情感和婚恋生活而引人瞩目的上海女作家潘向黎,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风格标志便是纯情叙事。她的作品中绝不缺少都市时尚元素如酒吧、美容院、迪厅、大型购物中心以及品牌消费、行为艺术等,但作家没有沿袭那种关于“上海滩”的食色暴力及其现代光影迷幻的书写定式,而是聚焦于新一代都市青年的本色性灵和朴素、真诚的情爱追求,张扬的是现代都市商业文化和物化大潮中的本色而真诚的都市情感。在这里,主人公们绝非那种受本能的食色欲望所支配和奴役的人,更不是在都市喧嚣中迷失自我的本能欲望的符号。《缅桂花》写的是常被称为“盛产爱情故事”的作家笔会,但其男女主人公从业务切磋、舞会交谊到笔会结束时相互送行,呈现出来的是一次次坦诚的心灵交流,作品并没有落入那种“一夜情”、婚外恋的媚俗套路,其间彰显的是天然、真诚而美好的情谊。《轻触微温》的爱情故事是以美容院为背景而展开的,但作品所营造的、也是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交流中体现出来的,是素朴、真挚和唯美的氛围和情调,这种叙事氛围足以让读者忽略其背景的休闲性以及都市喧嚣的存在。《倾听夜色》正面讲述的同样是淳朴的爱情故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改变的”是人与人的真情交往及其素洁而诚挚的人性情态,主人公坚称“只有对此深信不移的人,才配活在这个世上”。总之,作家所书写的是一种“保全了本色,保全了天然”的都市爱情,[3](P4)这也是别一种“上海滩”纯情叙事。它不仅颠覆了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上海滩想象”,同时也以其鲜明而独特的色泽,汇入并强化了当今爱情书写的“情还原”的审美取向。可以说,它标志着一种由“肉”到“灵”、由“食色崇拜”到“真情还原”的爱情书写基点的变化,更标志着一种对本色而天然的人性以及健全的“人”的认知升华。再如,铁凝的新作《海姆立克急救》则从另一层面,隐喻式地传达了关于情、欲冲突的反思及其真情的回归。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丈夫的忏悔:在妻子由于吃饭时被骨头噎住喉咙而意外去世之后,情感出轨的丈夫以一种仪式性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重复动作,来表达自己对多年夫妻的真挚爱情的眷念以及对妻子的忏悔之情。同时,小说还喻示着男主人公对其情感和灵魂迷失的自我拯救的努力,更喻示着他在经历了“破坏性的激情”之后的爱的回归,及其对淳真之爱的理解的升华。读者从中也不难感受到,这是一个健全、理性的心灵的回归,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升华。
近年来的纯情叙事的回归倾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刻的自我调整,即逐渐从对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和生命哲学的偏狭理解中摆脱出来,使爱情书写重新植根于东方传统伦理的积极元素的沃土中,并为传统伦理观念注入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生命活力。如上所述,文坛上的爱情书写整体上曾呈现出一味追求突破、超越或“深刻”的倾向,而这种突破、超越和“深刻”的衡量标尺,则主要是横向移植过来的某些时髦理论,如“精神分析”及其性本能的“原动力”说,现代西方哲学界颇为流行的“全面异化”理论,以及现代版的“人性恶”观点等。在新时期之初这些理论及其相应的文学思潮被译介进来时,人们的理解也许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这并没有妨碍作家们以此为支撑的“创新”冲动,以致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当时文坛上所调侃的“每一个新潮作家背后都站着一位西方现代派作家”。这种争相依托某种理论而求新求异的“集体焦虑”现象,自然首先体现在那些所谓“仿现代派”、“先锋派”、“新潮派”作家的创作中,如余华在1980年代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说,整体上呈现出的便是对于残忍、冷酷等负面人性的展示,其亲情、爱情书写每每形成的也多是“颤栗效应”。与此同时,许多已经形成了自我的艺术风格且为读者所充分肯定的作家,也往往在这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潮的诱发下,而刻意打破自我的标志性风格而转向某种“热点”、时髦的“深刻”追求。如早期连续发表了《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作品的铁凝,即以其清纯、诗情、委婉细腻的艺术风格著称,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她不久便产生了一种“老怕自己落后”的焦虑,“太过求变”,[4](P236)从而在《玫瑰门》《大浴女》等作品中,其人性、爱情认知基点及书写风格也迅即表现出向粗鄙、丑陋化书写的转变。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倾向又逐渐出现逆转,先锋派、新潮派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原来所热衷的“深刻”追求,以致其“转向”一时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而其转向的标志之一便是对淳朴真情的青睐,如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作家超越了自己此前专注于负面人性创作取向的新的结晶,也标志着作家真正实现了正面张扬婚姻家庭中的素朴情爱的转向,实现了由追求“理论深度”向追求“艺术深度”的转向,从而赢得了社会阅读群体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对于“人”来说,性爱这一生命的最高级、最辉煌的表现形式,恰恰也是最低级、最原始的生命表现形式。而文学在何种层面上去认知它,以何种分寸、何种方式去书写它,这似乎对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学创作都是一道难题,是对作家的认知力的一种检验。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表明,爱情书写如果痴迷于“未经文化修饰的生命状态”和性本能,那并非意味着它就代表了所谓生命哲学的“深度”,反过来,凸显传统婚恋中的人性之善和凡俗的真情之美,也并非意味着其人性认知的表面化。如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讲述一对清贫的农民工夫妻的爱情故事,他们分别在两个城市打工,中秋节这天不约而同地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各自买好礼物而踏上看望对方的列车;结果双方三次往返扑空,三度彼此错过,“惊喜”的初衷变成了“月圆人不圆”的遗憾。但不能不承认,这平实又带有“残缺”意味的故事中,充盈着凡俗生活的诗意和真情的“圆满”,展示的是朴素、至纯而至深的人性人情。丈夫心中那一再泛起的妻子用洗衣盆装上清水看水中月亮时的纯真和浪漫,却具有强烈的美学感染力;普通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那丝丝辛酸和淡淡悲凉,尤其是其中所灌注的温馨柔情和人性温暖,更是真诚而深刻的。再如温亚军《下水》的主人公是在京城为饭店清洗牛羊下水的农民工夫妻,他们的身份似乎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但他们讲诚信,重自律,宁可自己多付出辛劳也不做有可能污染城市水源的事,而费力地将脏水提到远处灌进污水道,为了城市人的平安就餐决不用化学药物清洗下水;他们常与在京城读大学的儿子通话;却刻意不让儿子知道自己也在京城打工的真相;他们住地下暖气管道,起早贪黑,但也享受着尘世真情的欢愉和人生的美好。在作家真切、朴素的书写中,这对农民工夫妻的音容举止、心灵信念,都得到了立体而深刻的揭示;夫妻相濡以沫的真情,恰是其深层人性的一种展示。同时,读者可以感受到,在这种纯情叙事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种坚实的人生哲学观念做支撑的。用作家郭文斌的话来说,这就是东方的、传统的“安详”哲学。而更完美呈现其“安详”哲学的,则是纯情叙事中常见的那种“能唤醒你的灵魂,能让你对世界万物心存敬畏、感激,能让你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能使人心生宁静的文字”。[5]
[1]李新宇.爱神的重塑——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2]吴培显,赵 林.论20世纪末小说爱情主题的拓展和深化[J].理论学刊,2006(10).
[3]潘向黎.我不识见曾梦见,白水青菜(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4]铁 凝.铁凝、贺绍俊对话录[A].贺绍俊.铁凝评传[C].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5]宁夏作家郭文斌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N].宁夏日报,2007-10-26.
〔责任编辑 裴兴荣〕
The Recent New Trend of Literary Writing of Love
WU Yu-y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410006)
Recently writing of love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literary arena,and pure love narration is quietly returning.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process from breaking the forbidden love to "returning to love itself",and to "original sex".Social reading expectation has turned from cheer for large scale description of sex to call for the pure narration of love like Under the Hawthorn Tree.When "love"inclines to "sex"to the extreme degreee,the generation of"original love "reverses.This reverse tendencey of pure love narration marks the writer's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and desire,and even human beings,forming the inner sublimation,and showing that a kind of self adjustment is occurring in recent literary arena.
writing of love;original sex;original love;reverse
I207.427;I24.7
A
1674-0882(2017)05-0060-04
2017-04-25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叙事话语范式升华与中国当代小说演进的关系研究”(13k035)
吴玉永(1978-),男,山东单县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