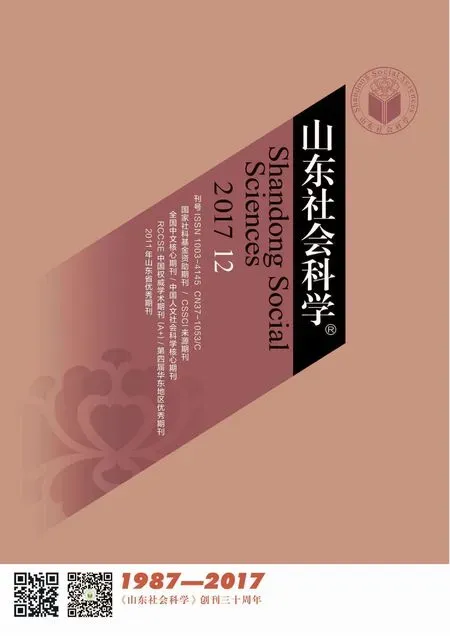儒家以史解《诗》的解释学批评
2017-04-02郭持华
郭持华
儒家以史解《诗》的解释学批评
郭持华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汉儒的《诗经》阐释担当着复兴文化传统、重建意识形态的历史重任,通经致用构成了他们重释传统经典的独特立场。《毛诗序》承继了孟子“知人论世”的历史解释方法,通过“叙故实而推诗义”的阐释实践,在诗人、社会、事件、作品、阐释者等各要素之间建构了一种解释学循环。这种中国特色的解释学循环对典籍阐释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以史解 《诗》;解释学循环
对历史流传物进行“历史的理解”,即通过对作者的经历、思想以及作品叙事化内容的深刻把握来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早已为理论家们所认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在德国解释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阿斯特对理解的三种区分中,“历史的理解”关涉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包括揭示著述者的精神、观点和倾向。①[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语法学、诠释学和批评学的基本原理》,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稍后的施莱尔马赫认为文本是作者思想、生活和历史的表现,而理解与解释就是通过“客观的重构”与“主观的重构”回到作者的时代和环境,以重新体验和再次认识文本所据以产生的这种思想、生活和历史。②[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讲演纲要》,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19世纪后期,狄尔泰进一步对历史的理解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他认为,人是一种心理的、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可视为一个小宇宙,它必然反映着周围的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这个大宇宙,因而理解一个作为个人精神之客观化物的文本,必须深入而系统地考察这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③[英]H.P.里克曼:《狄尔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在中国的典籍阐释传统中,最早明确意识到应该结合作者生平经历与思想来阐释其文本的理论家是孟子,他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经学勃兴,《左传》在对《春秋》的阐释中,又创立了一种“以事解经”的方法,即通过历史史实的引证与丰富来挖掘《春秋》“微言”中的义理。古文经学以《毛诗序》为代表的《诗经》阐释,则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这两种知“人”(作者)和知“事”(诗歌本事)的方法,多方搜集材料,深入考察历史,努力重构诗人创作诗歌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追溯诗句所指涉的具体历史事件,力图通过对诗作者本人以及诗本事的把握来阐释诗歌文本的意义。
一、通经致用:儒家以史解《诗》的阐释立场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任何理解与阐释都为特定历史语境所规定,“理解的历史性”被提升为解释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今天在我们看来堪为抒情典范之作的《诗经》,早期儒家尤其是汉代《毛诗序》却热衷于对它进行历史叙事化的解读,这首先与儒家释《诗》的特定历史语境和阐释立场有着密切关系。就文化思想建设的语境特征而言,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王朝在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后上层建筑建设的当务之急。一方面,对于武攻文卫的王朝政治来说,它急需充分利用结晶于“诗”“书”“礼”“乐”之中的传统文化来整合意识形态,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几经沉浮的儒家来说,通过自我调整以迎合权力需要,从纯粹的精神主义和道德主义走向政治的实用主义,是其能够从百家中超拔出来独尊于时代的历史性选择。
在这一实用主义转向的过程中,儒家典籍文本逐渐走向经学化。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所说“‘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①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精辟地指出了汉儒怀抱经世致用的立场与诉求走进儒家典籍从而使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转型。如何从时代问题和现实需要出发,创造性地阐释以《诗》《书》《礼》《易》《春秋》为生动体现的儒家传统典籍文本,从中爬梳出用以作为“世法”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秩序理念,揭示出其经邦济国的现实意义,构成了汉代儒者阐释传统的立场与目标诉求。此时,传世典籍的阐释担当着复兴文化传统、重建意识形态的历史重任,成了一种“返本而开新”、经世以致用的实用手段,成了一种打通文本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区隔的实践行为。阐释者透过历史流传的经典文本而力求昭示先王治国之“政典”,体认古圣之思想精髓,揭示经典中原有的观念,目的在于为当今社会之发展提供思想坐标,将观念世界中的“道”与当下社会的现实运动关联起来,藉由历史文本的阐释来承续文化传统、规范现时世界。
经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是相当明确的,“经书标准性内容,对于人类精神所支配的种种生活来说,无论在内在的道德教化层面还是在外在的实际应用层面,都是广泛普遍的依据”②[日]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它必须有道德层面上的教化之用,能使人“温柔敦厚”;有政治层面上的实际之用,有助于统治者治国安邦。这种预设的功利取向极大地影响了儒生们对传统儒家典籍文本的研读与阐释,形成了他们经世致用的解释立场。他们按照时代的历史性需要来解释“诗三百”,执着地从这些来源不一、产地不一、作者不一、情感基调不一的诗篇中扒梳、寻觅古圣先王的治国之“迹”,努力稽考、夯实这些诗篇所关联或隐射到的社会历史事件,最终延展、引申出符合王权需要的种种政治理念,以及可以资政治世的种种历史借鉴,为汉代王权大一统之社会秩序提供思想的合法证明或理想的远景规划。
汉儒相信,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于史实,叙事中有价值判断,是褒贬隐而史实显;《诗经》则寓“本事”于“美”“刺”,抒情中不无现实针对性,是“美”“刺”显而“本事”隐。所以,汉儒的《诗经》阐释就力求溯源隐而不明的诗歌本事,使“美”“刺”情感具体化为历史事件,以期实现经邦济国的政治功利目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在汉代相继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在于他们以“诗”的历史化作为运载礼义道德、纲纪人伦的手段,更具有说服力和合理性,适应当时整合社会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要求,因此取得了尊位。
对《诗经》进行历史叙事化的阐释与解读,我们可以在毛诗《大序》中找到明确的理论表述。《大序》开篇便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这里明确肯定了诗歌是作者意志的抒发,甚至认为诗歌是人情感的产物。按照这一基本理念,汉儒似乎应该对诗三百作出抒情化的艺术解读,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却另辟蹊径,将诗人的“志”“情”牵附到了社会历史的“事”:“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其理论逻辑倒也简单:诗固然是“情动于中”“志之所之”的个人产物,但“一人”抒发的志意与情感却深深地关系到“一国”的大“事”。以一人言一国之事者,谓之《风》;而汇四方之《风》,言天下之事(王政废兴)者,谓之《雅》。按照孔颖达的《正义》:
一国之政事善恶,皆系属于一人之本意,如此作诗者,谓之风……“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诗作者固然是一人,抒发的是一人之本意,但这“一人”的本意实际上是“览一国之意”所形成的,所以也就牵系着“一国之政事善恶”。孔颖达的疏可以说准确地抓住了毛诗《大序》的逻辑。因循此一思路,毛诗《大序》将个体的志、意、情与国家的政事联系起来,也就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因为如此,《诗经》才可能具有经邦济国的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小序》对各首诗篇的历史叙事化解读,可以说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践行。
必须指出,与孔子“引礼归仁,以仁为本”的思想诉求相比,汉儒的阐释立场在追求道德教化的同时,更为强调政治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因此,同一部《诗经》,在孔子和汉儒的不同视野中所突出的意义也就各有侧重。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一言以蔽《诗经》曰“思无邪”,通过突出诗歌创作者的个体情志来强调诗歌的修身功能;而汉儒从政治实用的诉求出发,专以“美”“刺”阐释诗篇,努力淡化诗歌所蕴含的个体情志因素,突出诗歌的政治风教意义。具体篇章中也是如此。如对《周南·关雎》,孔子叹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从君子人格修养之中庸品格角度立论;而《毛诗序》则说本篇是歌颂“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毛《传》注说“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硬是从中阐释出了“夫妇、父子、君臣”的三纲,归旨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可以说,汉儒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儒,基于不同历史语境所形成的阐释立场差别,是《诗经》意义与功能从个体追求道德完善的内向指涉转向外在政治诉求的根本原因。
我们也必须看到,《诗经》的历史化并不完全是汉儒主观涂抹的结果,从文本自身言,它具有诱导人们进行历史叙事化解读的内在因素。各民族最早的歌谣本来就是记载历史的一种形式,一开始就兼具诗与史的双重性质。《尚书》讲“诗言志”,闻一多从训诂的角度提出“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层意思,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①闻一多:《歌与诗》,载《闻一多全集》卷一,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90页。《诗经》的这种“记忆”或“记录”功能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明显,诸如其中的《商颂·玄鸟》《大雅·生民》皆为殷、周部族起源的记录与传诵,《大雅》中的《公刘》《绵》《皇矣》《大明》则是对周人英雄祖先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记载与讴歌。《大雅·文王》《大雅·崧高》记录了父终子及的世袭制,《鲁颂·宫》《鄘风·桑中》记录了祭祀妣祖的母权遗俗、图腾崇拜等。即使是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情采并貌的《国风》,也包含了许多叙事的因子,如《周南·卷耳》《邶风·北门》;有的甚至本身就记叙了一个小故事,如《邶风·静女》《召南·野有死麇》等。由此观之,汉儒把《诗经》视为先王政典,把大部分诗篇看作与某王、某妃、某公、某事有关,在阐释中为“经”作“传”,稽考史事,溯源故实,作历史叙事化的解读与阐释,以求申广义理,这种解释方法的形成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
二、知人论世:作者与文本的解释学循环
先儒相信语言在表达意义时具有充足的功能,所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由之而推出语言与人的共在性,在语言和人之间设立起互为存在条件的亲密关系。②如《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既然言以足志,是故观其言,则能知其志,进而知其人。这样,先儒实际上已经在言与人之间确立了一条通道:知言,则知人。《论语·尧曰》便云“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耐人寻味的是,这条通道可以逆行而不悖,即通过知人而更好地知言。《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以知人论世为颂诗读书的前提条件,究其思想之实便是:知人,则知言。言与人共在,先儒潇洒地在二者之间穿梭自如、循环往返。将此理念移用于文本阐释,我们的合法推论如下:作者与作品互为存在条件,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作者,形成微言大义的语言阐释;反过来,通过作者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形成知人论世的历史阐释。而这条端点与终点相互命名、可以穿梭往返的通道又鲜明地昭示着:在知言与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解释循环。这种解释循环并不是西方解释学理论中所津津乐道的作品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循环,它发生在作者与作品之间:阐释作品必须了解作者及其身世、思想,但了解作者思想又必须借助相关历史文献,特别是他传世的作品。当然,往返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这种循环,并非原地绕圈子,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每一次都意味着更深入的摄取、领会。
《孟子·万章下》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原本有其具体的语境,诚如朱自清所说,它的本意“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即“尚(上)友古人”的途径。③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但任何一个历史的概念或命题,其“实然”状态(它实际表现出来并运用着的现实)恐怕比其“本然”状态(它在原初语境中的原意)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恰恰是解释学着力推崇的一个理念,即历史流传物总是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阐释,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呈现为持续变动的历史图像。只要立足于时代语境中的阐释合法而有效,并为相当多数的学术共同体认可,那么,历史图像的实际存在便是合理有据的。由于“知人论世”自身具有意义延展的广阔内涵空间,因此,即使在孟子的具体语境中,它的原意是“尚友古人”的途径,也并不妨碍在漫长的接受史上,后人将其充实、发展为我国最具影响的传统的文学解释与批评方法之一。
从“知人”到“论世”,也就是从揭示著述者心志情思到更深揭示这种心志情思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孟子把对“人”“世”的了解视为准确阐释诗歌(言)内容与意义的前提条件,在世、人、诗(言)三者之间,即社会、作者、作品之间,构筑起了逻辑的相关性和一致性,进而要求阐释者在这种多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中去更好地阐释作品的意义。孟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文学阐释的基本范式:即由对作者的理解进入对作品的理解,再由对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作者的理解;由对社会的理解进入对作品的理解,再由对作品的理解深化对社会的理解,每一次循环都是走向更深的理解。在《孟子》一书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孟子自己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去解读、阐释《诗经》中某些具体诗篇的案例。如《孟子·告子下》云: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 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
《小弁》一诗,毛诗《小序》云“太子之傅作也”,孔颖达正义认为是周幽王太子宜咎之傅代述太子之言,毛《传》则交代史实说:“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咎;又悦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咎,将杀之。”原来是幽王为了宠爱新欢,以至于驱逐亲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哀怨之情可见一斑。而《凯风》之诗,毛诗《小序》以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在夫死寡居后,“犹不能安于其室”,有思嫁之意,其子乃作诗委婉致意,自责不能安慰母心,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按孟子的看法,理解《小弁》诗句中何以有“怨”,《凯风》诗句中何以无“怨”的关键在于,应该准确掌握诗人抒情所针对的具体事件,应该深入了解诗人的身世遭遇。这个案例可以视为孟子对《诗经》单篇批评的典范,它体现出来的解释理念是:对诗篇意义的理解应以对诗人身世遭遇的深刻了解为基础(《小弁》何以怨,《凯风》何以不怨),只有洞悉诗人的心态才能实事求是地阐释诗句;反过来,诗句表达的感情又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诗人(《小弁》有怨体现了人子“亲亲”的仁,《凯风》不怨也体现了人子“亲亲”的仁)。简言之,在诗人与诗作之间的这种循环往返,是我们准确而深刻地阐释诗篇意义的有效方法。
三、叙故实而推诗义:文本与历史的解释学循环
孟子“知人论世”的历史解释法在汉代的《诗经》阐释实践中得到了深入拓展。与“知人论世”说强调把握诗作者经历遭遇、身世背景不同的是,汉儒对诗篇的历史化阐释更注重挖掘作品所指涉的具体社会历史事件,在诗人、社会、作品的三维构架中增添了一个“故实”的要素。《汉书·艺文志》说鲁、齐、韩三家今文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即谓三家诗的阐释大多是从《春秋》等史书以及诸子著作中引述周代种种故实,用以推演诗义。其实,后来取得独尊地位的毛诗,同样也是奉行着这条通过稽考本事来推演诗义的解释方法,并且总结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它首先在文本背后抬出作者,“诗者,志之所之也”,明确肯定《诗》三百篇中的每一篇都是作者“志”与“情”的产物。然后追溯这种“志”“情”的形成是感于物而动,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政通人和之时,“治世之音安以乐”,而当“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时候,诗人的“志”自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变风变雅”就产生了,体现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和“亡国之音哀以思”。在这一逻辑推导之下,诗歌就由表现诗人的“志”“情”走向了对诗人所处之“世”与“俗”的反映,诗作抒发的固然只是一人之本意,但实际上已经牵系着“一国之政事善恶”。所以,若要准确地阐明诗人的意图(“志”“情”),就必须考论诗人之“世”,溯源诗人得以触“情”兴“志”之“事”。简言之,对“诗本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诗本事”的理解之基础上。
远古的“诗三百”就这样被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舞台上。如果说孟子发现了诗人与诗作之间的一致性,那么汉儒对“诗本事”的勃勃兴致则说明他们更愿意从诗歌与社会历史的穿梭中来阐明诗义。《诗经》成了遥远历史的一幅广阔而生动的画卷,形象地展现着“王者之迹”的得失;历史成了诗篇背后隐而不明的宏大背景,无声地制约着诗人或“美”或“刺”的意图。他们遍取《春秋》《左传》《国语》等其他文本,广采杂说,从各类历史典籍中搜寻可以与诗篇相互佐证的史实材料,将色彩缤纷且风格各异的诗三百中的每一首诗都落实到王朝政治的本事中,一方面为作者的“情”“志”找到可靠的“世”“俗”来源,另一方面则成功地为自己的“美”“刺”阐释找到可信的历史依据。如《卫风·硕人》,毛诗《小序》先云“闵庄姜也”,紧接着就揭示所谓历史本事,“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①此说的史料根据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如《郑风·清人》,毛诗《小序》先云“刺文公也”,紧接着也是坐实历史本事:“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师其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①此说的史料根据见于《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在诗篇与历史之间架起往返自如的桥梁之后,汉儒不仅为抒情言志的诗句夯实了历史本事,而且进一步分析历史本事,从中概括出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形象,解剖他们治国得失的方方面面,展示他们“王者之迹”的形形色色,从而分别把他们树立为“美”的典范或“刺”的标本。例如:儒家心目中的圣贤之君文王,就被塑造成丕显文武、克慎明德、受命于天,能够彪炳千秋而为历世帝王效法的明主。《大雅·文王之什》共10篇,其中有8篇就被明确归旨于赞扬文王: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
《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
《棫朴》:“文王能官人也。”
《思齐》:“文王所以圣也。”
《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
《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功伐也。”
文王集天帝之命和明明之德于一身,是创业兴周的奠基者,所以便成为《毛诗序》所歌颂、取法的典范,具有垂范后世、法则仪象的意义。与文王形象相反,幽王则被描述成荒淫暴戾、失德无礼、谗谄败国的昏君。《小雅》自《节南山之什》到《鱼藻之什》共有44篇,其中38篇明确归旨于“刺幽王”。有的只是标明“刺幽王”之主旨,而未加申说,如《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鼓钟》《青蝇》等计9篇;其余29篇则明确指出了“刺”幽王的具体内容,兹选录4篇如下:
《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菜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裳裳者华》:“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
归纳起来,幽王正是一个昏君的全息“肖像”。个人不修仁德、荒淫残暴,治国不恤民情、不讲礼义,以至于“四夷交侵,下国背叛”,败国废政。《毛诗序》分别塑造了文王和幽王这两个人物形象,既巧妙地表达了自己或“美”或“刺”的价值关怀,又成功地赋予了传统典籍文本在当下参与政治建构的现实意义。《诗经》成了承载先王治国得失的形象画卷,成了经邦济国的生动材料。而这一目的的最终实现,正是汉儒从容地穿梭于诗歌与历史之间,将诗歌历史化的结果。
汉儒从经世致用的阐释原则出发,努力扒梳、寻觅甚至附会《诗经》中每一诗篇所包孕的资政意义,生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叙故实而推诗义”的历史解释方法。汉儒视野所及,不仅那些记载部落起源、先民英雄事迹的诗篇具有历史叙事性,而且那些乡间百姓“率性而作”的抒情歌谣同样也具有叙录历史的性质。情随事迁,心志感于外物,“美”“刺”的价值判断自有历史事实的合法依据,所以一人之志意情思,必然深刻地反映了一国之事。这样,来源甚广而且风格殊异的诗三百,就成了古代“王者之迹”的一幅广阔而生动的画卷。六经皆史,《诗经》概莫例外。汉儒在诗歌与社会历史之间架构起了一种新的解释学循环,这种“诗史互通”的理念,在宋代的“诗史”理论以及清人钱谦益的“诗史互证”、近人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实践中得到了深入发展。儒家历史叙事化解诗方法的这条历史发展轨迹及其收获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建构一种可能的中国诗学解释学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它将诗人、社会、事件、作品、阐释者等各要素充分组合起来,坚持认为对诗歌文本意义的阐释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单纯的读者和文本之间,同时还需要对其他诸要素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将文学意义的生成视为整个活动系统内诸功能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I0
A
1003-4145[2017]12-0059-05
2017-07-21
郭持华,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