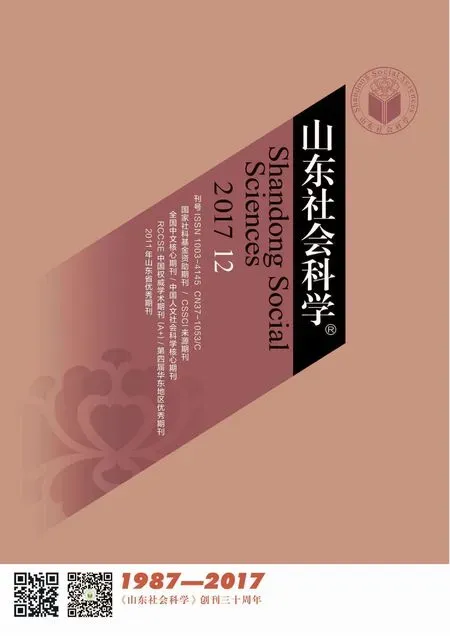从解释学看《诗经》的“圣”与“俗”
2017-04-02金元浦
金元浦
·文学解释学:《诗经》的阐释(学术主持人:金元浦)·
从解释学看《诗经》的“圣”与“俗”
金元浦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时代产生的无法企及也不可再造的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经历了长达两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化典籍中最丰富、影响最深远也最具生命力的成果之一,集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与人文积淀。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是一部传统经典的阐释史、传习史、翻新史和再造史,在《诗经》等传统文本的经典化—阐释—传播—消解—再阐释—再经典化的历史实践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呈现出日新又新的生命活力。
《诗经》;阐释学;阐释;经典;多义共生
近年来,在十八大精神鼓舞下,在习近平同志的强力引导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弘扬。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和内涵,今人却得之者寡。本文力图从当代解释学的角度,以《诗经》为例,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去洞察经典形成的历史过程和透过阐释解构经典—重塑经典的基本运行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着极其丰富的阐释学传统。从对《尚书·虞书》的解释和对《周礼》中的“六艺”的笺注开始,直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直有一条迥异于西方宗教阐释学的中国文学解释学的道路。比起西方从模仿说到典型说的文学解释模式,它是内生于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和承传过程的本然形态,是中国文学批评自身选择的发展方式。其非分析、非理式、非逻辑的审美浑沌性,阅读论、欣赏论、体验论的整体体悟方式和伦理化、道德化、人格化的艺术情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特点。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将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并与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丰富资源相结合,创立了当代中国的新文学阐释学。
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时代产生的无法企及也不可再造的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经历了长达两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化典籍中最丰富、影响最深远也最具生命力的成果之一,集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与人文积淀。
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是一部传统经典的阐释史、传习史、翻新史和再造史,在《诗经》等传统文本的经典化—阐释—传播—消解—再阐释—再经典化的历史实践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呈现出日新又新的生命活力,《诗经》等经典就在这一过程中延续、变革和发展。
一、《诗经》,原始宗教巫术活动的伴生物
《诗经》很圣,也很俗。《诗经》在其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完成了由“俗”至“圣”、由“里巷歌谣”到国家文化经典的建构,就其形成和起源来看,它是从俗世的生命延续、人的生产力再造逐渐升级为原始宗教巫术活动的伴生物。《诗经》中的很多诗就是描述先民们衣食男女的俗世生活的,比如被称之为“淫诗”的《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按朱熹《诗集传》的解释:“风雨晦冥,盖淫奔之时。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就其原初内容而言是记录男女“淫奔”之事,不可谓不俗。
此外,《诗经》中的大量篇章是用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的“祝”“咒”之辞。陈子展先生曾指出,“颂”是《诗经》中产生年代最早的一类作品,其实为“史巫尸祝之辞”,更多地保留了用于宗教礼仪活动的功能。①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5页。为什么在早于魏晋等“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前上千年的中国商周时代,能够产生今人看来如此丰富、成熟的诗歌作品?这只能从古代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生活形态入手去分析。由于低下的生产力、环境的严酷、识见的鄙陋,人类无法应对自然力的残酷侵袭,故而恭敬膜拜自然并使之成为神灵了。这种自然神崇拜的宗教巫术礼仪,是一种包含着宗教祝祷(乞求自然神灵与祖宗佑祜)、交感巫术(田猎与战争等的占卜诅咒法术)、生殖崇拜(子嗣繁衍及婚嫁祝咒)、欢乐庆典(重大战事、农事、迁徙的胜利或成功、战役复现再教育等)以及神话历史传统在内的浑然一体的典仪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诗、乐、舞混而为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史同一、祝巫同一、祝咒舞乐同一。也就是说,后世人们视为艺术的文学,那时还远未具备独立的条件,而只能浑融于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生活形态之中。在那一时代,由盲瞽人收集记录、演奏、传唱的东西,既是神话和传说,又是历史与诗歌,同时也是音乐与舞蹈,从实用演化而出非实用功能。因此由盲瞽人搜集整理的《诗经》本身集祝、咒、史、巫于一体,其本原形态应是原始宗教巫术活动的典仪之辞。
《诗经》中用于祝祷咒巫的篇章随处可见,叶舒宪先生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他认为,《诗经》中大量出现的“祈”“佑”“祷”“祝”等字,就其本义而言都是典型的宗教性术语,同远古初民生活中最具有社会性、也是最神圣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关。这些字在诗句中反复出现无疑为我们从宗教性的祈祝礼仪出发考察《诗经》的起源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内证”②参阅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祈,即祈祷、祝告,是世界上各种宗教所共有的礼仪形式。正如西方宗教把祷告看成是宗教生活中最关键的表达方式一样,《诗经》中也充分保留了中国商周初民的原始宗教祝祷之辞:
来假来飨,降福无疆。(《商颂·烈祖》)
绥我眉寿,黄耇无疆。(《商颂·烈祖》)
以介眉寿,永言保之。(《周颂·载见》)
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周颂·烈文》)
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楚茨》)
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信南山》)
这种祝祷建基于原始初民的宗教巫术信仰之上,到了《诗经》的年代,已大大普泛化为对神灵佑祜的一般祈祷,而可能逐渐失去对某一具体神灵的所指性。
原始宗教巫术礼仪的典仪之辞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众多地域的众多部族所积累、传诵,数量浩繁。到商周时代,随着奴隶制王权国家的确立,礼祀崇拜逐步向王权礼制之辞过渡。宗族祭祀礼仪向史转化,生殖崇拜向婚育祝咒转化,交感巫术向卜卦占星变化。孔子由诗三千删定为诗三百,实际上完成了诗由原始宗教巫术祝咒之辞向王权礼制伦理文化经典的过渡,是对商周之前漫漶于初民生活中的宗教典仪之辞的重新阐释。删诗,就是孔子对《诗经》进行的一种选择、一种诠释,其删节转换的新标准是“思无邪”。这看起来是一种复辟,实际上是“诗”的一次重大革新,也即以儒家原则对诗进行了观念化(原始意识形态化、原始政治化)改造,使之成为合于礼学儒家思想的经典。以复礼形式表现出来的由原始宗教向王权伦制的文化变革,是《诗经》阐释史上的第一次改变方向的重要标志。
谈到诗的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后世的解释多从作为文学艺术的诗的观念出发,终不切要领。须知其时并无后世人们公认的诗歌概念,又如何能够据以推衍判断这是讲诗歌艺术的功能?从原始宗教礼仪活动来阐释“兴观群怨”,则有豁然开朗之感。《诗经》中的兴,保留了原始巫术礼仪活动的“遗迹”,它是典仪活动的形式,由最初对某一事物的具体祝咒之辞逐步惯例化、仪式化,成为典仪中的礼辞,而后逐步发展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诗的引譬连类方式:巫术、占卜、卦辞的祝、咒→惯例习俗典仪的礼辞→礼辞的制式:引譬连类→后世的诗创作。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在那样一个文化发展的层次,要求人人学“诗”,如果真是后世人所谓的诗,那就太无道理了,即使在中国诗歌最辉煌的唐代也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诗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典仪之辞,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实际的效用。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重要的典仪、会晤、接见,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晨祝、晚祷之类活动,都须使用诗来进行颂祝或应答。从古代史著中我们看到,这些运用诗的人物与场合往往与诗的内容相去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这实际上是原始宗教巫礼典仪之辞的一种遗响。到春秋时代,这种最为繁盛而又普遍躬行于民间的形式已逐渐式微,但其典仪之辞作为一种文化惯例或风俗却留传下来了。这是兴的原始意义。
由此去看“兴观群怨”,将其放在商周初民日常的宗教巫术礼仪活动的背景中,就自然可以“观风俗之盛衰”,可以“群居相切磋”(诗作为典仪之辞,本身即为群众活动所需,亦为群众活动所创造),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通过王政礼制典仪来实现。这里的兴更多从祝衍化而成,而怨则更多与咒相接。
二、《诗经》的阐释与正典的确立和消解
西方基督教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对《圣经》的新阐释,并且从中体现着某种“阐释”的权力意味,《诗经》阐释的历史及其功能也与此相似。在中国历史上,《诗经》三百篇经典地位的确立与消解同样是与特定历史语境下对“诗”的不同解释密切相关的。《诗经》之为“经”的早期依据,正是诗本身在原始宗教礼仪活动中的至高地位。孔子删诗,是依照儒家原则对诗进行重新阐释的结果,表明了它由原始宗教巫术礼仪之辞向王权伦制的政治礼义之辞的变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它尽管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只能作为一种学说流传。《诗经》在传统社会的真正的经典地位的确立,还是在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还在于汉儒对《诗经》的再阐释,在于历代对《诗经》的经典地位的再巩固,其后尊经与非经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息,而尊经与非经斗争的焦点又在守《序》与废《序》之间。《诗经》在这里徘徊于儒家王政伦理经典与诗歌艺术经典之间。
西汉十四博士,治《诗经》者有鲁(中公所传)、齐(辕固生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说,都立于学官。赵毛苌亦传诗,称为毛诗,系汉哀帝、汉平帝间晚出的学派,终汉之世未立学官。三家官学为今文学派,毛诗则为古文学派。当年三家诗说对诗都有自己的阐释(据魏源考证三家当年都有序),然时移世易,均已亡佚,唯毛诗经郑玄作笺,独行于世。毛诗对《诗经》的阐释通过《序》流传下来,其影响最大者自然是《诗大序》,即毛传国风首篇《关睢》下的那篇序言。
今天的学者常常慨叹于汉儒对《诗经》的解释为何那样断章取义或主观臆断,其实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谓相当“合理”的解释。儒家诗教在确定《诗经》的经典地位时就确定了其为封建王权德政伦理教化服务的基本宗旨。虽然其先前的文本未变,但阐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革,阐释的意图、目标、指向已大大改变,因而其阐释义也必然发生重大改变。从阐释学的理论来看,阐释者有什么样的前理解(先有、先识、先见),向阐释对象提出了什么问题,阐释就可能被确定一个意义的流向。在毛诗《大序》中,这一总体指向已被确定:“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乎情,止乎礼义”,“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据此而得出《关睢》“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的理解,似乎顺乎其理,也与当时人们的期待视野相合。然而尊经非经的论争一直存在,自文学的自觉时代以来,一个不再浑融于封建王政伦理的相对独立的文学艺术类型逐渐形成,这样对于《诗经》本文原义的理解就自然产生重大分歧:究竟将《诗经》视为王政伦理教化的儒家经典呢,还是看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志言情的文学典范呢?这一尊经非经的论争又鲜明地表现为守《序》与废《序》的斗争。
对“诗序”的怀疑其实自汉代就已开始,包括对其作者的怀疑,以及对大小序的不同划分。郑玄《诗谱》认为《大序》是子夏(卜商)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竟,毛更足成之”。又有人说《小序》是东海卫敬仲(宏)所作,如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载:“初,九江谢曼卿著《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到唐代,韩愈就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而是“汉之学者所为”。及宋,守序废序的斗争才真正展开。欧阳修开始以“人情”说诗,求《诗经》之本义:“《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①[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六,载《通志堂经解》,中国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版。欧阳修在《诗本义》中改动毛诗之说一百余处,反思儒家经典中何以有如此之多的“淫诗”的存在,从内容上开始反诘《诗序》所度本义。朱熹的《诗集传》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将男女私情之诗归为“淫诗”一类,并非“刺诗”,而《大序》“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之意思尽穿戳凿坏了”,可见《序》未必是圣人所作。所以他的《诗集传》将《诗序》尽皆删削,告诫弟子,读《诗经》定“须先去了小序”,也“不可先看诸家注解”。
实际上,这一守《序》与废《序》的斗争一直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到清代,在“尊汉”“复古”的旗帜下,对废《序》派大举反攻,标举光复毛、郑之学。他们拘泥于名物训诂,谨守毛序,而回避对诗之本事与本意的探讨。像戴震这样的大家,亦敷衍曰:“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②[清]戴震:《杲溪诗经补注·自序》,黄山书社1994年版。嘉靖道光年间,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或毛郑并疏,或专毛废郑,或以礼解诗、谨尊师法,又反过来尊《序》崇《序》。闻一多先生后来说《诗经》的训诂学不是《诗经》,实际上又对《诗经》作了文学经典与语言训诂学经典的区分。
当然清季废《序》派对此亦殊觉不仪,每奋起反责,如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复张今文学派,再释《诗经》之意旨。像魏源《诗古微》不仅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认为《序》《传》均系伪作,不值得以“经”尊之,梁启超则厌恶《毛序》而喜欢《毛传》,但他已意识到《诗经》创作年代与作序年代之间存在的时间距离,认为“年代隔远的人作序,瞎说某篇某篇诗的本事本意,万不会对的”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这里,阐释的时间距离在某个时代,特别是阐释范式转换的时期,对阐释本义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总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诗经》到底是经学典籍还是文学典籍的争论,所以将《诗经》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回归其文学的本来面目就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诗经》阐释中的多义共生
对《诗经》三百篇的意义阐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致过,特别是《国风》。④关于《风》诗,历来的解释非常之多,现列举几种说法:1.《毛诗序》的“风化说”——即风化教育以感人,讽谕劝谏以规过,但谏者要讳曲而言。2.《汉书·五行志》的“风土说”——即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的浅近之言或富有乡土气息的音乐。3.欧阳修的“四义说”,认为《诗经》的含义有四种。4.朱熹的“沉潜讽诵说”,认为国风就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俗谣俚曲。5.梁启超的“讽诵说”,“风即讽字,但要训讽诵之讽,不是讽刺之讽。”等等。在《诗经》这样一部流传数千年的文化典籍中,除了人们想象中的本义外,还积淀着各个历史时代附加于其上的多重意蕴,即各种象征隐喻含义与由原义而生发出来的衍生义。其实,即使在《诗经》的每一文本中,也几乎都蕴含有多种层次的含义,比如欧阳修就认为“诗”的含义有四种: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物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固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为风、雅、颂,而此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怀,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权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义训,耻于不知而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已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①[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六,载《通志堂经解》,中国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版。
在欧阳修这里,《诗经》的意义被分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和经师之业四个层次。发乎人情、道乎哀乐,这是诗人写诗之一意,而其他几个层次则应当是历史流变中衍生或积淀于本意之上的含义。太师之职在于采诗录诗,对于民间各个地域、各个阶层的诗歌选择收集,据其功用分门别类,亦是一种阐释。圣人之志在于“修礼乐之坏”,正其雅颂,删其繁重,特别是将《诗经》列于六经,用于惩恶劝善,诗的意义和功用都发生了很大变革。至于经师之业,则是在诗的流传中,修整残缺,阐发圣人之意,他们各自为说,又阐发出诸多义蕴。显然,欧阳修早已发现历史沉积于《诗经》篇章之上的多重义蕴。在此多重义蕴中,究竟以何者为本呢?
其实在《诗经》阐释史上,寻找原义的努力从未停止过。欧阳修认为在诗的诸多含义中如何“曲尽人事”切近于《诗经》的本义,只能“以人情求之”,因为在他看来,自诗诞生以来,时代、朝代、人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弥合这一时间距离,只能找出古今同一的东西,这就是“人情”,因为“古今人情一也”,只能从这里直达本义。对此明代竟陵派钟惺说得更明白。他认为《诗》与说《诗》是不同的。《诗》只有一个,而说《诗》则可“散为万”,而且说《诗》不一定“皆有当于《诗》中”②[明]钟惺著、李先耕等标校:《隐秀轩集》卷二十三《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页。。这就是说,诗的本义只有一个,对诗的解说则可以有许多,而且可以发挥、可以更新。即使是自己先前作出的阐释,也可以“取而新之”。显然,他对诗的本义与多种衍生义有着明确的区分。
那么如何抵达诗的本义呢?朱熹曾主张一种“沉潜讽诵”法,就是要直接阅读文本,直接感知体验作品本身,“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③[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认为一首诗应该读它几百遍,读至火候,其本义自然从中流出。所谓“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就是要去除历史附加的种种成见,直面作品本义,其方法与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主张异曲同工。施莱尔马赫指出,理解实际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语言文字,任何理解都必须从这里开始,但这一层的理解都还只是文字字面的意义,尚未触动到更深层的精神世界。第二个层次的理解是心理层次的解释,它是一种由自我走出,进入他人内心的历程。为了抵达作品的本义,解释者必须否定自己的先入之见,走出他自己,以作为进入作者心境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转换,是解释者为了达致理解自愿作出的一种牺牲。解释者放弃了精神上原属于自己的东西,以便接纳作者的心境。朱熹的虚怀以待,正是力图通过“沉潜讽诵”完整地到达诗作的本义,复原作者的心境与意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品与解释者的张力与距离消失了,理解呈现出来了。
四、阐释的循环与历史语境
对于《诗经》这种年代久远、影响巨大的经典文本,在其文本与历代阐释者背后,都存在着由语言连接的历史背景关系,这一关系保证了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是一种人的历史存在的表现。在解释学看来,对于历史典籍的阐释,首先意味着对历史已提出一种双重的要求:一方面,它相信历史自身有一种主观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把历史的意义彰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也相信历史具有一种客观性,相信只要掌握恰当的方法,就能征服历史,保证历史的客观性不被任何个人的主观臆断所任意曲解。这样,阐释学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境:阐释者只能从个人这一认识主体的前理解出发来解释理解历史,个人的主体性实际上成了测定历史客观性与历史主观精神的准则,而历史真理与历史文章自身的意义,又被假定为独立于任何个别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历史的主观阐释在这里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循环:精神要在超越了任何个人主观性之后才能凸现历史的客观性;而要求超越或否定个人主体的历史客观性,又必须通过个人主体才能实现。
20世纪初以来的《诗经》阐释者受到近代西方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熏陶,在思维路径上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阐释者。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与《诗经》创作时代已有两三千年的时间距离,而这两三千多年中,《诗经》已积累了如此之多的阐释,如何以现代方式弥合这一时间距离,客观地重现《诗经》的历史语境,是20世纪诸多《诗经》阐释者的自觉目标。胡适当年就提出,“大胆地推翻两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解释,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首诗下个解释。”④胡适:《谈谈诗经》,载《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0页。闻一多先生则以为要回到本源的《诗经》,复原诗创作诞生时的历史语境,最大的障碍恰恰是古代圣人及其对诗的“点化”。如何去掉《诗经》中圣人的“点化”之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①闻一多:《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7页。
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现代阐释,是建立在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当程度的融合之上的。他提出了三条阐释的途径或准则②闻一多:《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6-39页。:
第一,文字的语言与语法阐释,要阐释《诗经》,首先要读懂《诗经》。古今的语言已发生很大变化,要读懂它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中国古代对《诗经》的文字考证阐释到乾隆时代已备极繁富细密,文字训诂的追索已难有突破。闻一多采用了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他辨认出《诗经》中大量使用的一种原始民间诗歌形式:廋语。作为古代诗歌特有的技巧,诗经中的《国风》等民间诗歌往往用象征廋语、谐声廋语和不自带意义的隐喻来阐释。
第二,寻找一种最合理的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作为受过西方现代科学熏陶的学人,闻一多清醒地看到《诗经》创作年代与今天的久远的时空距离。不以今天的眼光和心理去阅读和理解《诗经》,这需要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从现有的方法来看,恐怕也只能采取推论法。那么推论法的根据在哪里呢?闻一多感到阐释的困境:从空间方面看,缺少与《诗经》时代文化程度相当的歌谣;从时间方面看,三百篇之前和之后到汉代又有诗歌传统的中断,时空两方面的推论材料都没有,所谓客观的标准从何建立?闻一多的深刻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心理复原的困难。施莱尔马赫假设了放弃或清理个人精神心理中的先入之见,以中立的虚怀进入历史上创作者的心理的阐释方法;闻一多则以一种历史文化感证明了心理阐释的困难。他看到了历史和文化给人造成的心理差异,认为我们今天“文明人”的灵敏感、细腻情感,以及缜密思想都是几千年文化发展的结果,我们无法退回到《诗经》的“原始人”状态,无法以今人的心理悟入当年诗人的心理。对于阐释《诗经》来说,我们的幸与不幸,“总归该文化负责”,因为是文化使我们自己成了阐释《诗经》的“障碍物”。
第三,用文学的眼光来阐释《诗经》。这一途径是当代众多阐释者的共同目标,而于闻一多则更彻底。在他看来,对《诗经》的阐释应当回到诗,回到文学,回到艺术及其形式。这与他的偏于艺术形式的文学观念有关,也与他曾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诗人的个人经历与体验能力有关。把《诗经》当作诗来读,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千年来“诗以明道”“诗以载道”,千古不移,至今依然,所以闻一多才发现,此中最大的障碍是“圣人”及圣人们的“点化”之迹。倒是当年郭沫若的《诗经》选译《卷耳集》,首开中国现代史上“纯文学”白话《诗经》译本之先河。此书所译诸诗均选自“国风”,郭沫若称之为“优美的平民文学”。他所选的这40首诗,其中有21首系王柏明言要删的“淫诗”,郭沫若称之为“恋爱的情歌”。郭直言,他对各诗的解释,纯依个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而不再过多考虑古代传统对它究竟作何解释。虽然这种阐释往往离文本较远,成了个人借古诗以抒情畅意的手段,但却更具创造意味。
五、作为艺术本文的《诗经》
《诗经》是入乐的。众所周知,先秦时代,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诗经》的全部篇章都是配乐歌词,是依照音乐体式和文化功效,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的。《诗经》善用赋、比、兴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灵活增减,常以重章叠句、复沓回环的民间歌舞技法增强艺术效果,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诗经》中的诗篇往往是由盲瞽乐师来主持操演的,如《周颂·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从这首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周时的诗通过盲乐师演奏的情形。其实商时的音乐文化已高度发达,《墨子·公孟篇》就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说法,《山海经·大荒西经》就曾说《国风》乃乐曲:“太子长琴,始作乐风。”美籍学者王靖献从《诗经》中提到的各种乐器入手,指出早期的诗不是供书面欣赏的,而是乐队伴奏中演唱的,《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传唱于人们口耳之间,后来经歌手和乐师们的收集整理、加工提炼,到孔子时代基本定形。而陈世骧先生则指出:“无论如何,‘舞诗三百’等上下文指出一个事实,当时人们提到诗的时候,诵咏、音乐、舞蹈皆与诗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追溯诗的原始意义,探讨构成《诗经》一体的共同基础”①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其实古代学者对此也早有论述,朱熹就曾论及:“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四部丛刊初编本。
以意境为主形态的中国诗歌的生成与运作机制,是中国诗文化的内在精蕴,具有东方艺术精神的某种全息性,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关注的核心论题。因此,从《诗经》肇始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绵延数千年的诗文化:无诗,即无境界;无诗,即无高阶;无诗,即无品位;无诗,即无文化。前述先秦时代,人们甫一见面便吟诗作礼,正是古代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留给我们的遥远的遗响。
在论及作为艺术本文的《诗经》时,我们看到西方的《圣经》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偏重于音乐性的抽象艺术精神与《诗经》息息相通。希伯莱《圣经》是一种音乐化的本文,其《诗篇》和《雅歌》部分尤其如此。从现有《诗篇》的本文内容来看,《诗篇》中的诗文在古人吟诵时是由乐器伴奏并有某些特定曲调格式的。在《诗篇》的每篇开首,常常有“大卫的海”“可拉后裔的诗”“交于伶长”“调同百合花”“调同女音”等特定的说明,每隔一定段落,还有“细拉(Selah)”等字样加以揭示,表示此处唱歌人声音暂休止或停下来,而伴奏曲则可继续。今天我们已很难恢复当年人们吟《诗篇》时的音乐原音,但从其简约化的音乐要素来看,《圣经》时期的希伯莱音乐在形式、曲调变化等方面已有相当高度。现有《诗篇》中有极为丰富的曲调,这些曲调一般是按照所唱内容安排的,有着喜怒哀乐的不同感情色彩,如《诗篇》中常用的曲调:
百合花:第45篇、第69篇。
远离歌:第7篇。
玛斯几力:第 32、52、72 篇等。
这是颇令我们思索的。联系到今天广大青年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流行音乐、通俗歌曲,证明了音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原性生命存在。当年《诗经·国风》中的大量篇帙,都是男女抒怀相诱的情歌,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来,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汉书·五行志》认为《国风》就是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的浅近之言,陆侃如先生更直接提出“牝牡说”,即牝牡相诱的赠答之歌,就是当年青年男女们在民间传唱的富有乡土气息的流行音乐。人们总是以其所在时代的官方道德准则臧否《诗经》,其实,越是亘古,越是自由松弛的男女相悦相合。看今日世界原始部落及我国少数民族遗留的原始风俗,则可看出人类的生殖这个原始生产力繁衍的最重要方式,远远胜过后世设定的男女大防的封建禁忌。当然,古来的爱情也是在文化的不断发掘积淀中日益丰富、深化、想象化、经典化和现代化。
郑樵强调:“《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③[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7页。我认为此说亦当有两种解释:一则是为过去的“淫声”遮羞——那是原始时代牝牡相诱的“自然”或“本然”状态,因为不合现时规定的道德理念,所以要为其“讳”;二是原始时代以来民歌民调确实已经成为可以填词自编、即兴演唱、一般大众皆会哼唱的曲调、曲式,因而有中国几千年间几百种民间戏曲、地方小调大成,唯京剧因近代才“合成”,更多“人为”创新特色。顾颉刚也认为十五国风就是各地区有地域风格特色的声调,《诗经·国风》的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特质自不待言耳。
《诗经》音乐性中所蕴含的东方艺术精神,与希伯莱《圣经》中的抽象艺术精神相通,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是也。它更通灵于音乐,追求缥渺高远的艺术意境,而似乎更疏离于形象,更具情感性(情绪性),作为中国初始文学的经典文本,在数千年中一直聚讼纷纭。《诗经》的阐释史,就是中国文学漫长历史的一个缩影,就是中国文学自身“释经”式传承创新特征的集中展示,就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运行的基本方式与经典案例。所以,阐释《诗经》,其意义十分重大。
I0
A
1003-4145[2017]12-0052-07
主持人语:当传统文化以一种当代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在如何继承、如何弘扬之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阐释、如何解说、如何理解。现代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传释学)是西方引来的传统学科,其广涉哲学、古典学、心理学、文艺批评,乃至法律、医学等多个领域,历时久远。特别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解释学、伽达默尔当代哲学解释学,对世界当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西文明互鉴的交流对话中,通过接受、吸取、改造,而后依据中国批评传统,建设和创发了具有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学解释学。
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是一部传统经典的阐释史、传习史、翻新史和再造史。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先秦时代曾创造过辉煌的文学经典,因其内涵的丰富、创造的独特性和原发思维的丰富性,成为后世数千年难以企及的高峰。另一方面,惯于通变之术的中国文学阐释又在历史沿革中不断寻找不变之变,即通过解说、阐释、演绎来表述阐释者增加的内涵和义项,并同时削弱或删汰不欲彰显的内容,这是由于时代语境的变异、历史现实要求的变革、文化思想潮流转圜、阐释手段方法的精进等等。
当代中国文学解释学的发展,除了理论的构建,还必须进行具体案例的研究。一种解释范式,要想具有阐释的生命力,一定要在历史或现实的文学、文化的事件、文本、接受实践中证明自身阐释的有效性。这是中国文学解释学范式得以彰显自身阐释的必要作业。本期两篇文章,即将《诗经》放在文学阐释的纵向背景上来审视,借以展现传统历古至今的变异轨迹,也寻找中国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的路径。
2017-07-21
金元浦(1950—),浙江浦江人,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访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和文化创意产业。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