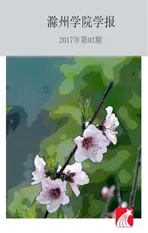严歌苓笔下王葡萄和扶桑人物形象探究
2017-03-30张晓明
张晓明
严歌苓笔下王葡萄和扶桑人物形象探究
张晓明
通过分析严歌苓代表作《第九个寡妇》和《扶桑》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和扶桑,从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缺乏性别意识的强大苦难承受力、地母般耀眼的神性光辉三方面比较研究她们多层次和丰富的文本形象,感受特殊年代风雨飘摇中的两位女性独特魅力,以期对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做进一步的探索。
王葡萄;扶桑;生命力;承受力;神性光辉
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的翘楚,在书写女性命运的道路上,伫立于新旧世纪的结合地带,以女性作为绝对主角,突破了传统女性书写的藩篱,书写她们受难式的生存,塑造了大量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本文以《第九个寡妇》和《扶桑》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和扶桑为代表,通过分析文本内容,从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缺乏性别意识的苦难承受力、地母般耀眼的神性光辉三方面揭开她们多层次和丰富的女性形象,以期对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做进一步的探索。
从小被卖到孙家的童养媳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女主人公)土改时,从死刑场上偷偷将被错划为恶霸的公公孙怀清救出,藏匿于红薯窖四十余年。扶桑(《扶桑》女主人公)19世纪末被拐到旧金山沦为娼妓,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依然“健壮、自由、无懈可击”地站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央,淡然安详地看着世间云卷云舒,周身宛若笼罩着神性光辉。“比于赤子”的王葡萄和“跪着的好女人”扶桑平凡低贱如草芥般,可身单力薄却不乏强悍的原始生命力,没受过任何教育却天然地恪守人性深处的道德准则,凭借自己的倔强和执著达到生命的“自在状态”。
一、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
王葡萄和扶桑生活在不同国度混沌纷繁的历史时期,在那些年代,为求苟活不惜出卖人格、牺牲尊严的人难以计数,而女性作为当时社会的弱者,更是卑微到泥土里。特殊年代的风雨飘摇反而将王葡萄和扶桑体内的生物性倒逼出来,一切为了生存下来。生活越施压,她们越用力反弹,活得越发生动。世人眼中的弱者凭借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因强大的求生本能幻化为生活意义上的强者。
吃饭是第一位的。王葡萄直视自己的生存欲望,不在乎谁上台执政、时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遇到再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兵荒、粮荒、虫荒来了,能躲就躲,躲过了就过了。在那个年代,粮食和物资因极缺而显得无比珍贵。葡萄为了一碗杂面条,能撕下脸皮和食堂的人大吵大闹,非要四个玉米面蒸馍的补偿。为了度过荒年,她想尽各种方法让腥臭的鱼可以下肚、教邻里李秀梅焙蝗虫、和瘸老虎一起去地里偷蜀黍;为了一袋海藻和男人五合大打出手。为了抢半打香皂,和英雄寡妇陶米儿闹得不可开交。到后来完全忘记是为什么而打,只是觉得跟灌了二两烧酒似的越打越带劲。王葡萄是野蛮的,“她王葡萄可不是那号孬蛋,拿着亏当油馍吃。别人分着什么,她王葡萄也得分着什么”[1]48,这出于原始生存本能的野蛮却又让人无法讨厌。
在情欲方面,她身边流连过不少男人:琴师朱梅、医生孙少勇、公社社长史东喜…… 虽然最终没有一个男人能与王葡萄长相厮守,可是王葡萄出于本能的与他们相爱,爱得那么淳朴、热烈,投入下一段感情时却又是那么自然、不刻意。她与公社社长史冬喜在坟院边的树林里野合,冬天冻得清鼻涕长流,夏天让小咬蚊叮一身疱疹,外界条件如此不堪,却因本真的欲望得到宣泄,“闹上饥荒,人走路都费气,她天天盼着天黑,和冬喜往床上一倒,就不饥了”[1]160。
三个月的漂洋过海,扶桑是被卖、被拐的女子中唯一不闹绝食的,别的女仔轻得“是根鸡毛掸子”,扶桑靠吃番薯吃到了一百斤。人贩子夜里跑来把拐来的那些熬不住默默死去“变了色也变了气味的女仔”扔进大海里,她却在船仓里睡得烂熟,一点也不知道。甚至是后来遇险快要死去的时候,救她的不是药,而是从尸体那里抢来的那碗饭。
被拐卖来被迫沦为娼妓的女子在恶劣的外部环境和无休止的折磨下,十八岁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双眼浑浊,早早颜色败尽而亡。扶桑却从不记嫖客的名字,接一个忘一个,逢人问起,只是一笑,这是一种动物的“忘性”,看似无情,却保护了扶桑。哪怕沉重如钢铁般的躯体死死地压下来,哪怕鲜红的血液从她的嘴唇、胸脯流出,但疼痛没了,扶桑依旧能“愈合”。她只会悄悄揪下或咬下嫖客的纽扣,作为接触过的追忆。凭借着动物般惊人的原始生命力,扶桑踏踏实实活到了九十多岁。
二、缺乏性别意识的强大苦难承受力
《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给小说的女主人公取名“王葡萄”,葡萄是一种在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果实,鲜美多汁;《扶桑》直接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扶桑是一种开放时间长、色彩艳丽的花,插枝即活。女主人公的名字直接强调了她们的女性身份,而王葡萄和扶桑作为女性却根本没有最基本的性别认知,她们的女性意识始终是被压抑和忽略的。王葡萄和扶桑生活的时代、地域大相径庭,她们宛如蚁偻,任人摆布,可是她们面对苦难的默默承受力是大得惊人的,一般男子都所不及。坎坷的命运、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外界环境,她们不能逃避也没法推卸,只能忘记自己的性别,忘记自己是柔弱的女性,展现出强大苦难承受力和包容隐忍。
王葡萄五个月身孕的时候还敢和魏坡媳妇比赛单手秋千。她其实骨子里充满了阳刚之气,为了保护大铁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和兵痞子大打出手。在社里没钱买猪食,只好把刚下崽的母猪卖掉,为了养活猪娃,去酒厂拉酒糟,去火车站拉泔水……想尽一切办法给猪娃找食粮。她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的活,独自一个人喂二十多头猪,连个帮手都不要。快过年了,别的养猪人家怕猪饿瘦了,不得不到过年就杀了,只有王葡萄家的两头猪天天上膘。不仅如此,她还头脑灵、方法多,从秋天攒的蜀黍棒子上打主意,把蜀黍棒子剁了磨成粉煮给猪吃,到了腊月初八,去收购站猪一上磅,都是“一百八九十斤”。
王葡萄从小孑然一身,卖到孙家后先是死了丈夫,后来公公也难逃一劫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只能呆在暗无天日的地窖里,家里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人身上。王葡萄挑起的是一般男性都无法承担的重责,拥有的是比男性还要宽厚的肩膀,在饥荒年代,不仅自己生存下来,还用最大胆的办法设法保全了公公。与此对比,面对侮辱和对自己和家庭“声誉的绑架”小说中的男性瘸老虎和谢哲学都选择了自尽,这其实是一种更不负责任的逃避。
王葡萄是有大智慧的,她不讲理却比任何人都重“理”,这“理”是她自己朴素的“生存哲学”:切切实实是为自己而活,完全不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她一个人养活公公,给侏儒抚养的儿子送药品、食物、衣服,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保持人性不扭曲。能为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放弃与少勇结婚,放弃自己的孩子,这是对男性社会为了一己私利置父母养育之恩于不顾的谴责,孙怀清的亲生儿子都做不到,而买来的童养媳葡萄做到了。她这一生过得实在清楚明白极了,活着就为了干活干得漂亮,干一天漂亮活吃下一口馍,心里别提多美了!
扶桑的脚是典型的女性小脚,如玉兰花苞一般,可她的心却如同最顽强的荆棘,坚韧坚强承受一切不利条件,她对苦难承受和包容不仅使自己活了下来,还以温顺化解了唐人街最残暴的强盗大勇的戾气,以包容征服了白人少年克里斯。扶桑是最温柔的女性,却令最凶悍的男性俯首;扶桑是最普通不过的东方女性,却令西方少年痴迷一生。
扶桑身为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不仅不知晓自己的权利,甚至对加诸自己身上的男性压迫也表现漠然,没有任何对男性淫威的抗拒和痛恨。恰恰相反,在被克里斯救离妓院后,她反而憔悴不堪;被重新抢回妓院后,再度焕发生命别样的光彩。摧残她、迫害她的男权体制反而让她更加自如的生活下去,扶桑拥有的是多么令人咂舌的承受力。难怪,她那对苦难的无限包容成为漂泊一世的男性的最终港湾。在大勇的心底深处,扶桑就是他的后路,是他回家路上的指明灯。在作品中,拥有最后救赎力量恰恰是单薄如纸、承担一切苦难的弱女子扶桑。
三、地母般耀眼的神性光辉
作品中,王葡萄和扶桑凭借是母性的光热,化解一切凌辱,无言地承受外力的摧残,陈思和先生将这样的女性称为“中国民间地母之神”,“她们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她(们)默默地承受一切,却保护和孕育了鲜活的生命源头”[2]。他认为这类女性形象“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3]。严歌苓自己把这种母性的光热称为“最高层的雌性”,她把这些女人视作是“天然保持着佛性”的女人,她们是大地的母亲,有泥土般的真诚,因其包容一切故而散发着光和热。
王葡萄和扶桑似乎从来都不迷茫踟蹰,也不犹豫和计较,做任何事都是出本能,这本身就不自觉地使她们夹带了某种光环。王葡萄的眼神不会避人,看得人心里起毛、手里冒汗。她不扭捏,不违背天性,不贪图名份,一眼看破真相——孙少勇的妻子“她是不会跟你好好过的”。男人们都不懂她使什么魔怔,能让他们在瞧不上她烦她厌她的同时,又把她爱死?她靠自己的本能去对抗整个世界的蜚短流长,自我解放,自己解开束缚自己人性的道德枷锁,“她情愿给谁东西的时候,是天底下最大方的人”[1]145。在朴作家跌入人生低谷时,是王葡萄呵护保全了他的精神世界;在孙少勇人性迷失的时候,是王葡萄在关键时候提供了他救治自己父亲继而实现人性复苏的平台。她无私地帮助李秀梅和瘸老虎一家,最后还收养了女知青遗弃的女儿。从王葡萄把公公二大藏在红薯窖里开始,二大已经完全失去了主权地位,而王葡萄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的照顾,早已升华成了地母般耀眼的神性光辉。
小说结尾,作者苦心营造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局,通过临死之际的孙怀清之口讲述了史屯人祖祖辈辈都在寻找的祖奶奶,她唯一的特征就是特别会剪迷魂阵窗花。而文章中也一再或明或暗向读者展示王葡萄最出名的手艺就是剪迷魂阵窗花。王葡萄是不是就是能福佑族人的祖奶奶灵魂转世?作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巧妙地给王葡萄这一女性形象笼罩了神性的光辉。
扶桑身上似乎天然地焕发着母性,这种母性是多元的,既有宽恕宽容,也有甘于自身毁灭的成全。无论她处在什么不利地位,她都温顺得像一只羔羊。她就那么笑着,那么不自觉散发着包容一切的母性光辉。一开始,是扶桑身上极端的东方情调诱使少年的克里斯对她痴迷不已,而多年之后克里斯发现令自己念念不忘的是“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4]106的母性,即使在遍体麟伤的时候,“她嘴角上翘,天生的两撇微笑,一切都是那巨大的苦难变成对于她的成全。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4]107。她似乎具有那种只接受事情中的苦难,而不接收其中侮辱的魔力。在儒家传统文化里,跪有谢罪的意味,文章中也多次提到扶桑的跪,扶桑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文中还多次谈到扶桑的自由,那自由“绝不是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也绝不是任何人能收回或给予的”[4]201。她在充满敌意的异国城市给自己找到了一片自由,一种超出宿命的自由。扶桑本人比自由含义含蓄丰富得多,这不可捉摸的含义不仅照亮了她自己,也照亮了她周围的气氛和周围环绕的人。她平实和真切的“地母形象”却恰恰是她最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在无数男人为她冲锋陷阵、尽力争取时,她脸上没有一丝喜色;大勇要再次出卖她时,她没有一丝要反抗的迹象;就连大勇决定把她嫁掉时,她还是平静得像波澜不惊的湖水;大勇死后,她虽知这就是她在故乡的丈夫却依然不动声色。只有扶桑能使大勇甘愿做乏味的规矩人,扶桑其实就是他心心念念却又无法直面的故乡妻子,她出现的那天,“他将会就地一滚,滚去一身兽皮,如同被巫术变出千形百状的东西最终还原成人”[4]。
四、结语
扶桑和王葡萄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扶桑像“异国他乡的一朵蔷薇”[5]97,王葡萄则被喻为“沙漠中的一股清泉”[5]98,在命运起伏的大海里,她们脆弱的如同破败的桅杆,但从不屈服,靠着生命的本能一路飘摇着。“弱者不弱”虽然被认为是严歌苓对女性创伤的自我安慰,但同时这也是边缘女性无可奈何采取的生存策略,是对她们美好人性的巨大肯定。扶桑最后嫁给了克里斯,安然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成为旧金山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而王葡萄藏匿公公这一秘密被人发现后,史家屯村民们甚至自觉加入到对这一秘密的保守中。彼时,乡村嫉妒、仇恨的毒瘤被纯洁美好的人性慢慢过滤,将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
[1]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1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 陈思和.读《第九个寡妇》[A].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思和卷[C].1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3):102.
[4] 严歌苓.扶桑[M].1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杨意.从本我和自我浅析扶桑和王葡萄人物形象[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2)4.
责任编辑:李应青
Image Exploration of Wang Putao and Fu Sang in the Yan Geling’s Masterpiece:TheNinthWidowandFuSang
Zhang Xiaoming
Based on the heroines Wang Putao and Fu Sang in Yan Geling’s masterpieces:TheNinthWidowandFuSa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ulti-level and rich text image by three- aspect comparative research from animals original vitality, lack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hardship endurance, and the motherly divine glory, and feels the unique charm of two women in special times for promoting further exploration of Yan Geling’s women writing.
Wang Putao; Fu Sang; original vitality; hardship endurance; divine glory
I206.6
A
1673-1794(2017)03-0053-04
张晓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北京 100081)。
2017-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