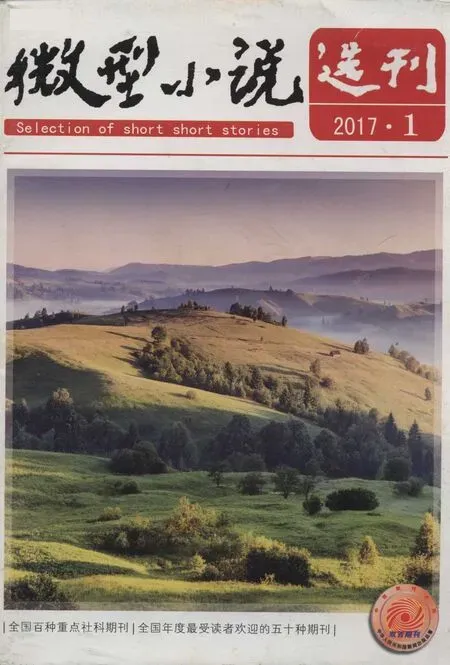消失的舌头
2017-03-30徐永辉
□徐永辉
消失的舌头
□徐永辉

二丙的舌头没有了。
那天,邻居三婶迎头遇到二丙,跟他打招呼。二丙的嘴张张合合,却没看到他的舌头,也听不到他说的话。三婶一惊,忙问:“二丙,你咋回事,舌头没有了?”她不肯相信,走到近前往二丙嘴里一看,只有牙齿。
我们晓庄是远近闻名的雄辩村。大人、孩子,走路、干活,甚至吃饭睡觉的时候,嘴巴都不闲着:
“那是谁家的羊,咋不拴起来?”
“为啥说是羊?叫它狗不一样吗?”
“羊就是羊,怎么能叫狗呢?”
“它叫啥,不过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如果当初叫它猪,你现在还说是羊吗?”
据村志记载,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由于世世代代训练,我们的舌头变异了,厚、长,又特别灵活,伸出来,可以轻而易举到达额头。用它洗脸、画画、写字的,不乏其人。据说,以前有个人,舌头比象鼻子还长,不仅能擀面、纺车,还能把棍棒舞得虎虎生风。为了炫耀,我们都把舌头耷拉在下巴底下。
为了激励后代,先人们还自发组织了辩论会,三年举办一次,年满十八周岁的男子必须参加。先以家庭为单位选出优胜者参加家族辩论,再选出家族中的第一名参加决赛。一方把另一方驳得哑口无言,算胜出。
凡是在辩论会上不发言,或撒谎骗人者,舌头会自动消失。凡是没有独立见解,跟着别人学舌的,舌头会失去一半。
二丙是几十年来唯一受到惩罚的人。他是孤儿,老实,木讷。平时,你问一句,他哼一声。只要不问,一年半载也难开金口。在家族辩论会上,也有人试着引导他。徒劳。
半晌午,我们几个蹲在路口上议论二丙的时候,三婶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地过来了,还没到近前就问:“谁看见一只公鸡了吗?”她边说边比画,“这么大,毛通红,闺女给拿的,没舍得吃,你看,一转眼不见了。”
我们都安慰她:“不能少,不定跑哪旮旯里去了,再仔细找找。”
我们村古风犹存,好多年没少过东西了。
被三婶一搅和,我才想起来是去找乌木的。乌木家大门洞开,我站在院子里大喊:“有人吗?有人吗?”
没有回应。突然,厨房里传来轻微的响动。我走过去,一把推开紧闭的门,咯噔愣住了。乌木也愣了。他手里抱着一只没褪完毛的红公鸡。晚上,乌木请我喝酒,炖的公鸡肉。三杯酒下肚,乌木说:“咱打开天窗说亮话,等一会儿我把鸡毛埋在二丙家门前,明天你就说是他吃的。”
“这……”
“这什么这?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反正不会说话。”
“这不是欺负人吗?”
乌木脸一寒,酒杯一顿:“事不大,你看着办吧。”
我为难死了。乌木是出了名的小诸葛,坏点子一眨巴眼一个,得罪他,我这辈子别想安生了。又怪法律太仁慈,如果抓住小偷就砍头,老子怕他作甚?又后悔得要命,干吗去那么巧啊?
天刚一亮,我就带着三婶扒出了赃物,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昨天傍晚我路过二丙家的时候,听到砰砰的剁骨头声,偷偷伸头一看,案子下的鸡毛还没掩埋呢。”
大家都深信不疑。
乌木先骂开了:“二丙,看你狗日的平时老实巴交,原来是装的。”
在我们这儿,偷盗是被认为最无能、最无耻的事情,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往他身上吐口水,任何人都不再搭理他。
二丙张着大嘴,扑腾扑腾直跺脚。又啪啪地拍自己的大腿、屁股,眼泪像屋檐下的雨水,连成两条线。
三婶不忍,说:“算了算了,一只鸡,谁吃不一样?”
其他人也软了心肠,反过来安慰二丙:“你也是个苦人,一年到头不见荤腥,一时嘴馋也正常,算了算了。”
二丙喘着粗气,泪珠依然滚滚不止。渐渐地,清亮的泪水变成了红色—他在流血。我的目光像受惊的苍蝇,仓皇地乱飞,两只手互相搓来搓去,嘴张开几次,又合上了。
当鲜血浸透胸前衣服的时候,二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我终于受不了了,大声说:“鸡是乌木偷吃的,他逼我赖二丙。”我正要把昨天的事情详细说出来,忽然感觉发不出声音了,嘴里也空空荡荡。
一个孩子指着我大叫起来:“舌头,他的舌头没有了。”
我的头一蒙。我不死心,拼命张嘴,依然发不出丝毫声音。我掐自己的肉,撕扯自己的头发,如果,如……果。
没有如果。
(原载《芒种》2016年第9期作者自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