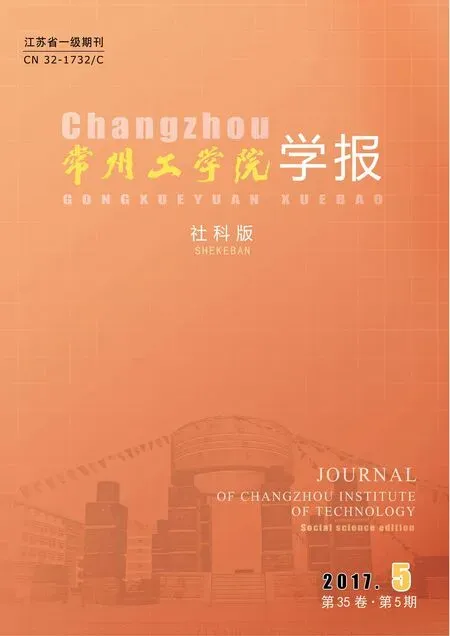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中的男性形象
2017-03-28徐小芳
徐小芳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朱熹文旅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中的男性形象
徐小芳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朱熹文旅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克兰福镇》是盖斯凯尔夫人早期的重要作品。该书虚构了一个超然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大龄单身女性社区,而其中也有颇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如代表贵族阶级“道德权威”的詹金斯先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经济权威”的史密斯先生,新绅士形象布朗上尉与霍尔布洛克,等。文章逐一分析这些男性形象后指出他们不仅是理解书中女性社区的一面镜子,也是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及其社会理想的重要锁钥。
《克兰福镇》;盖斯凯尔夫人;男性形象
I106.4
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1810—1865),原名伊丽莎白·克莱格亨·斯蒂文森(Elizabeth Cleghorn Stevenson),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以写社会问题小说、工业小说、乡村小说著称。《克兰福镇》(Cranford,1853)是其早期重要的代表作,她也因此常被称为“写《克兰福镇》的盖斯凯尔”。
在《克兰福镇》中,盖斯凯尔夫人虚构了一个超然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大龄单身女性社区,那里生活着贾米逊夫人、狄布拉·詹金斯和玛蒂尔德·詹金斯姐妹、福列斯特夫人、波尔小姐等遗老遗少。长期以来,有关这部作品的解读与研讨主要集中于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路径多为女权主义批评视域,认为该书的主题是批判父权与夫权,“对男人的政治压迫和性爱压迫进行了强烈抨击”[1]209。一般而论,女性作家撰写的女性题材方面的小说都可广义地称为女性小说,《克兰福镇》确实有对男权社会的讽刺与批判,有凸显女性的“自主”与“权利”意识,它无疑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但若将其主题界定为批判男性与男权,不仅是过度解读其中的女权主义思想,而且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有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此类问题。“如果说,盖斯凯尔对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深有反思,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说,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父权,反对新教伦理,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2]这种认识偏差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者未能正确把握作品中的男性形象。
《克兰福镇》篇幅不长,全书共16章。非常有意思的是,小说大部分的章节标题与故事情节都与男士有关,其中提到的男性人物主要有格拉玛男爵、布朗上尉、前教区长詹金斯先生、霍尔布洛克、莫勒弗瑞勋爵、魔术师勃鲁诺尼、彼得、玛丽·史密斯的父亲、农民道孙、约翰逊老板、男仆、木工等。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有世俗贵族、宗教贵族、乡绅、中产阶级、贫民、仆人;从家庭关系上看,有父亲、丈夫、兄弟、儿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重点上看,有贵族阶级“道德权威”詹金斯先生,有新绅士形象布朗上尉与霍尔布洛克,有新兴资产阶级“经济权威”史密斯先生,有离经叛道的浪子彼得,等等。这些男性形象不仅有助于理解书中女性人物,而且也是把握作者写作意图及其社会理想的关键所在。
一、贵族阶级的“道德权威”: 詹金斯先生
在西方,贵族阶级主要包括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其中世俗贵族指世袭的亲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拥有议会上院出席权的狭义贵族和包括从男爵到骑士的广义贵族。宗教贵族指教会中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掌握着在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教,也具有较高的地位。首先,詹金斯先生是教区长,高级神职人员,热心布道讲道,“在巡回审判期间对法官宣讲的祈祷书”还付梓出版[3]61,住的公馆里厅舍楼阁甚多[3]76,用着三个女仆和一个男仆[3]83,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宗教贵族。因而,在《克兰福镇》中,詹金斯先生这一男性形象首先代表的是当时日益没落的贵族阶级。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被视为现实主义的标杆、“高度现实主义”的代表[4]3-4。这种标杆性反映了她真实地揭示当时阶级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小说中通过“旧信”的回忆,艺术性地再现了詹金斯先生家庭从兴盛到没落的过程,以小见大地描绘了贵族阶级在工业化浪潮面前的历史命运。
其次,詹金斯先生还是“男权社会”的代表。他对待妻子及子女的态度说明他不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他事业心强,热衷布道,兢兢业业,但生活中的事情他却从不上心,甚至不解风情。他可能是一位好教士,但不是一位好父亲。在孩子眼里“父亲就像亚哈随鲁王那么威严可怕”[3]75,他和子女说话常常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3]80。他抱残守缺,以“门第”与“等级”的偏见,棒打鸳鸯,拆散了玛蒂和自由民托马斯·霍尔布洛克的婚姻,尽管玛蒂本人“十分情愿”,但是“他们就是不赞成玛蒂嫁给地位比她低的人”[3]41。在彼得的教育问题上,他专断蛮横,彼得的离家出走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詹金斯”是贵族阶级道德权威的“符号”。詹金斯先生是教区长,管理教区风俗礼仪的各类事务,“生前受到本地人的敬重”[3]195,是名副其实的道德权威、宗教权威。詹金斯先生去世之后,承接他衣钵的是对约翰逊文体驾驭得炉火纯青的詹金斯小姐。她的领袖地位与道德权威的正统性来自她父亲詹金斯先生,“詹金斯小姐长久以来是克兰福镇的领袖”[3]34。尽管在小说中,詹金斯小姐的戏份很少,在第二章之后就撒手人寰了,但其影响力无处不在,特别是她深深地影响了妹妹玛蒂。粗略地看,围绕玛蒂的那些故事情节,很多都是如何走出姐姐的影子,比如如何调教女仆,如何接待男宾,该不该去拜访老情人托马斯·霍尔布洛克,是否可以允许女仆谈恋爱,等等。小说中总是重复玛蒂的声音:“我真不清楚姐姐那时是怎样安排这一切的。她最有办法了”[3]35,“要是狄布拉在世的话,她是一定知道怎样接待男客的”[3]38,“要是姐姐在世是不会赞成的”[3]44。不仅她的妹妹如此,甚至整个克兰福镇亦然,“现在她去世了,人们几乎弄不清楚该如何举办茶会了”[3]34,“詹金斯小姐一死,再没人熟悉待人处事那套规矩礼节了”[3]90。詹金斯父女的去世,一定程度上宣告贵族阶级的道德日暮西山,将势必被新的道德符号、道德谱系、道德形象所取代。
二、新绅士:布朗上尉与托马斯·霍尔布洛克
在《克兰福镇》中,布朗上尉被认为是理想的男性形象的典范。或许是为了刻意突出新旧绅士的“标准”不同,无论是布朗上尉还是自由民托马斯·霍尔布洛克,都不是出身高贵的人,布朗上尉不仅不是衣食无忧,还一副穷酸样,招致克兰福镇“高贵”的女士们的鄙夷。作品中就是通过这一群人的眼光来看待布朗上尉这位“入侵”[3]5者的,她们对他的态度从反感到接纳,从接纳再到尊敬,再从尊敬到奉为权威,形象地描绘了一位新绅士,尤其是其男性之美。第一,“他有男人家的卓越常识”,“谁家有做不来的事,他总有法子对付”。第二,他有男人的勇敢,“谁家烟囱漏烟,他都无所畏惧地走上楼去”。第三,他有男子汉的大度,“过去遭人白眼,他毫无觉察,现在受人爱戴,还是毫无觉察,依旧自行其是”[3]6。第四,他没有大男子主义,“上尉立刻不动声色地做起男子该做的事来。他招呼着各位女客替那位漂亮的女仆给女士们倒茶,送牛油面包。这些事他做起来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好像男性照料女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愧为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3]10。第五,他“心肠万分厚道”,对待生病的大女儿如此,对待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如此,以致为了营救一个小孩而丧身在列车的车轮之下。第六,他还是一个有“趣味”的人,爱好文学。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车祸,布朗上尉的新绅士形象的叙述戛然而止。在1865年2月写给罗斯金的信中,盖斯凯尔带着无比惋惜的口吻提到布朗上尉之死,她说《克兰福镇》在《家常话》最初发表时只是一个短篇故事,自己从没计划过把它写成连载,鉴于篇幅的考虑,只好“极不情愿地把他杀死了”[5]718。为了弥补这种缺憾,特别是新绅士形象还不够丰满,盖斯凯尔夫人描写了玛蒂的老情人托马斯·霍尔布洛克这位新绅士,尽管书中多次提到他爱好文学,爱好读书,在田园里经常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诵,并盛赞“除了过世的教区长外,没有谁能像他朗诵得那么悦耳动听,感情丰富”[3]41。在形象的塑造上以下三点得到了突出,第一,他不攀附门第,“他和许多与他境况相似的人们不同,不愿挤到乡绅这个阶层里去。他不让人家称他为‘乡绅’托马斯·霍尔布洛克,甚至把用‘乡绅’称呼他的信件都退了回去,他对镇上送信的女人说他的名字只是托马斯·霍尔布洛克先生,一个自由民”[3]40-41。第二,他对繁文缛节的旧礼仪说“不”,“凡是与做人之道无关的种种讲究一律嗤之以鼻”[3]41。第三,他有忠贞不渝、宽容的美德。托马斯·霍尔布洛克因求婚玛蒂未果而终身未婚,而对当初扼杀这桩婚姻的詹金斯小姐并没有充满仇恨,他说:“您那可怜的姐姐啊!唉!唉!谁又没有错处呢?”[3]43
通过布朗上尉与自由民托马斯·霍尔布洛克,盖斯凯尔夫人树起了她心目中的新绅士形象,其标准的核心不再是身份、门第、等级的高贵,更不是财富的富足,而是要有智慧、勇敢、坚毅、大度与宽容等美德。
三、“经济权威”、新兴商业资本家:史密斯先生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男性形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玛丽·史密斯的父亲,尽管他本人在克兰福镇仅出现一次,但他的出现是小说故事情节的转折点——银行破产致使玛蒂倾家荡产,小说中为他的露面浓墨重彩地做了铺垫。在作品中,玛丽·史密斯4次提及自己的父亲。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经济权威”的形象。
第一次是贝蒂·巴尔格小姐宴请克兰福镇女士们参加茶会,她担心玛丽·史密斯的门第与身份可能遭到同伴们的讥笑,因为这些女士对“等级界限完全在行”。“我父亲搬到德伦布尔去了,这一来很可能去做‘可怕的棉花交易’,那么就降低了全家的身份,够不上是‘贵族社会’的人了。”[3]86-87这样,作品交代了史密斯的身份,不是“旧式”贵族,而是新兴的商业资本家。
第二次是在玛蒂投资入股的县镇银行即将破产之前,父亲寄给她一封信。“父亲的信一看就知是男子写的,也就是说一点趣味也没有,谈到的不外乎是他身体甚好,近日阴雨连绵,营业销路呆滞,以及流言甚多之类,他又问我玛蒂手中是否仍然持有县镇银行的股票;他说最近该行名声不佳,对此他早在意料中,数年以前曾劝阻詹金斯小姐勿购该行股票,詹金斯小姐未能听从(我知道她就是这一次没听他的话)。父亲写道此乃该聪颖的女士唯一的不明智行动。如若发生不幸之事,我自不该抽身离去弃玛蒂而不顾云云”[3]165-166。这封信的信息量很多,既交代了玛蒂投资入股县镇银行的前因后果,也刻画了这位商人的“经济权威”形象。
第三次是史密斯先生帮助玛蒂打理银行破产后的事宜。尽管小说中用墨不多,但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格形象:富有责任心,乐于助人,“父亲从德伦布尔赶来帮玛蒂小姐也是硬挤出来的时间,当时他自己的事务也不怎么顺当”,父亲“头脑敏锐,处事果断,办理这类事务最为拿手”[3]193。
第四次是通过与玛蒂进行对比,揭示玛丽·史密斯父亲的商业理念。面对破产,面对穷人手上持有的县镇银行钞票一文不值时,玛蒂执意要干史密斯先生认为的“傻事”,“按照做人的道理来讲,作为股东,我也应该把钱还给这位好老乡”[3]172。由于信奉“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史密斯先生对玛蒂变卖家具“颇感怀疑”[3]194。玛蒂甚至善良地揣测那些董事管理不善,有负别人所托,良心上也一定很痛苦[3]192。她想到的不是自己会“倾家荡产”如何,而是“银行如果倒闭,拿着我们钞票的老实人要蒙受损失”[3]172。在经商之道上,玛蒂不搞相互拆台的“竞争”,不会认为同行是冤家。在为维持生计而筹备经营茶叶时,她非常担心影响同行约翰逊老板的生意,为此特意去征求他的意见。这个举动被“经济权威”史密斯先生认为是“胡闹”,“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地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3]198。
对“经济权威”、新兴商业资本家史密斯先生,盖斯凯尔夫人秉持辩证的态度,一方面高度赞赏其处事风格、商业头脑与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对其“精明”的商业原则持保留的态度,甚至毫不留情地狠狠地反讽了一把:在克兰福镇,对人毫不设防的玛蒂受到了约翰逊老板的照顾和顾客的信任而生意兴旺,而“经济权威”史密斯先生处处小心提防,还是被骗走了上千镑的钱[3]199。
四、结语
从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大多基于一种社会性别政治的考量。然而,正如开篇所强调的,分析《克兰福镇》中男性形象的主要出发点却是试图稀释那种过度突出该作品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主张。从男性形象的研讨而言,一方面,盖斯凯尔夫人这部作品并没有将“男性”与“女性”视为对立的“两极”,而是着力于两性关系的和谐。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传统社会都是以男性为中心,不同程度地存在性别歧视、性别冲突与对立。在古代中国,女子要“从父”“从夫”“从子”。在近代西方,女性同样生活在男权社会中,没有逃脱受压迫、受歧视的命运。在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文化大肆宣扬“淑女”礼仪与规范,试图禁锢她们,阻止她们走向社会,让她们甘愿做“家里的天使”。长期以来,批评界在解读《克兰福镇》时,较为关注的是“女人王国”对现实的“男权社会”的反讽,而没有深入理解作者寻求两性关系和谐所做的努力。小说中,布朗、彼得、史密斯这些形象的出场,很大程度上诠释了小说家的深层意图,即克服性别歧视,男性离不开女性,女性也离不开男性,男士与女士应相互帮扶,同舟共济。
另一方面,从这些男性形象的代表性而言,盖斯凯尔夫人主要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变革”与“发展”的进步意识立论,思考克兰福镇乡村社会的前途与命运,寻求各阶级与阶层和谐发展之道。布朗上尉与前教区长詹金斯先生代表新旧绅士形象。布朗上尉与詹金斯小姐代表着“经典”与“时尚”的不同趣味。“以狄布拉·詹金斯小姐为首的‘亚马逊族’女性喜欢的是以约翰逊博士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古典式哲思和归隐出世的田园生活方式;其文化象征符号是花园和家庭。而布朗上尉喜欢的却是以狄更斯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工业化和重商入世的城市生活方式;其文化象征符号是铁路和工厂。”[6]史密斯与玛蒂信奉着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商业伦理。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在《克兰福镇》中,盖斯凯尔夫人没有简单、片面、线性地看待这些“新”与“旧”、“经典”与“时尚”、“传统”与“现代”,而是坚持客观、辩证的双轨思维,用“传统”批判“现代”,用“现代”批判“传统”,既正视乡村田园牧歌式生活一去不复返之事实,也深刻揭示了“机械时代”的突出社会问题,表露了作者建构“新克兰福镇”的社会理想。
[1]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周颖.《克兰福镇》的反讽:与米勒先生商榷[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11):401-424.
[3]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M].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GASKELL E.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M].Manchester:Manchester UP,1997.
[6]陈礼珍.出版形式与讲述模式的错位:论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J].江西社会科学,2011(11):121-124.
.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5.012
2017-03-30
徐小芳(1980— ),女,副教授。
2017—2018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研究课题(1710004);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规划课题(azjxh1641);安徽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RW-41)
A
1673-0887(2017)05-0054-04
责任编辑:赵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