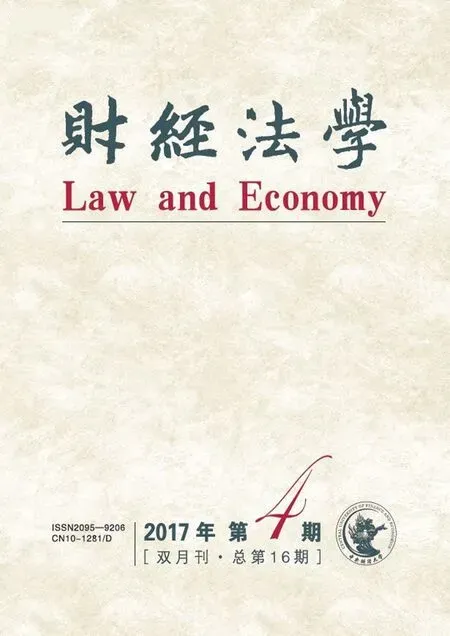裁量与裁量收缩
——一个宪法、行政法结合部问题
2017-03-27卡尔埃博哈特海因福尔克施莱特托马斯施米茨
[德]卡尔-埃博哈特·海因 福尔克·施莱特 托马斯·施米茨 著
曾 韬 译
一、引言
行政机关活动空间的内容和范围是一般行政法教义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此领域中,人们通常将问题细分为构成要件方面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和法律后果方面基于裁量的酌定空间的赋予。[注]BverwG,GewArch,1977,S.24,26 f.; OVG Münster,NVwZ 1988,S.178:Ossenbühl,Rechtsquellen und Rechtsbindugen der Verwaltung,in:Erschsen (Hrsg.),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0.Aufl.1995,§10 Rn.10,m.w.N.; Maur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0.Aufl.1995,§ 7 Rn.26; Wornmann,Das Spiel mit den Spielräumen,NWVBL.1989,S.342,343; 48,56,59; Ossenbühl,a.a.O.,§ 10 Rn.10,m.w.N.; Pietzcker,Der Anspruch auf ermessensfehlerfreie Entscheidung,JuS 1982,S.106,107:Richter/Schuppert,Casebook Verwaltungsrecht,2.Aufl.1995,S.41; Sachs,in:Stelkens/Bonk/Sachs/Leonhardt,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4.Aufl.1993,Rn.17 ff.,insbes.23.本文无意深入讨论这一体系性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英国法和法国法均无构成要件方面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和法律后果方面基于裁量的酌定空间的赋予的区分,vgl.Starck,Verwaltungsermessen im modernen Staat-Rechtsvergleichender Generalbericht,in:Bullinger(Hrsg.),Verwaltungsermessen im modernen Staat,Landesberichte und Generalbericht der Tagung für Rechtsvergleichung 1985 in Göttingen,1986,S.26 f。过去受到重点讨论的主要是不确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问题,[注]Vgl.z.B.Busch,in:Knack,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5.Aufl.1996,§ 40 Anm.6 ff.,m.w.N.; Kopp,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6.Aufl.1996,§ 40 Rn.38 ff.,m.w.N.近年来,审查密度问题因联邦宪法法院的相关判决而尤为受到关注(BverfGE 84,34,49; 84,59,77 ff.; BverfG NVwZ 1992,S.55; BverfG NJW 1993,S.917).vgl.etwa Schulze-Fielitz,Neue Kriterien für die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ontrolldichte bei der Anwendung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e,JZ 1993,S.772 ff,; Sendler,Die neue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zu den Anforderungen an die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ontrolle,DVBL.1994,S.1089 ff.; Pieroth/Kernm,Beurteilungsspielraum und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ontrolldichte be der Anerkennung eines besonderen pädagogischen Interesses an privaten Grundschulen-BverfGE 88,40,JuS 1995,S.780 ff.; Hofmann,Der Beitrag der neueren Rechtsprechung de BverfG zur Dogmatik des Beurteilungsspielraums,NVwZ 1995,S.740 ff.; Brohm,Ermessen und Beurteilungsspielraum im Grundrechtsbereich,JZ 1995,S.369 ff。本文将要讨论法律后果裁量(Rechtsfolgeermessen)的一个“经典”问题,一个尽管近来在学理上日益受到重视,[注]Vgl.Insbes.Dietlein,Der Anspruch auf polizei-oder ordnungsbehördliches Einschreiten,DVBL.1991,S.685 ff.; Di Fabio,VerwArch 86 (1995),S.214 ff.; Gern,DVBL.1987,S.1194 ff.; Sarnighausen,Zum Nachbaranspruch auf baubehördliches Einschreiten,NJW 1993,S.1623 ff.; Wilke,Der Anspruch auf behördliches Einschreiten im Polizei-,Ordnungs-und Baurecht,Festschrift für Hans Ulrich Scupin,1983,S.831 ff.但研究程度在教义学上依然差强人意的问题[注]若干学者明确强调这一领域存在教义学上的缺失,例如:Gern,Die Ermessensreduzierung auf Null,DVBL.1987,S.1194; Drews/Wacker/Vogel/Martens,Gefahrenabwehr,9.Aufl.,1986,S.400,Fa babio特地指出,行政裁量限缩问题绝非行政法教义学的精彩之处,Di Fabio,VerwaArch 86 (1995),S.214,216。:裁量收缩(至零)(Ermessensreduktion auf Null)。尽管这一现象在行政法的各个领域中均不可忽视,[注]参见Di Fabio的详尽的、细分各个事项领域的概览即可,Di Fabio,VerwaArch 86 (1995),S.214,216 ff。但其影响主要集中于警察法和秩序法之中——行政机关的介入义务问题以及个别情形中的不作为义务问题——因而本文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这一领域展开。裁量收缩问题在教义学上尤为令人感兴趣,因为从表面上看它能够将行政裁量学说归谬:裁量规范向行政机关赋予自主行动和筹划的余地,但这一余地却在裁量收缩的情形中大范围地、甚至完全消失,以至于行政机关被置于与羁束行政(gebundene Verwaltung)相类似的境地之中。更令人惊奇的是,某一规范的适用,既可能表现为“惯常”的决定,也可能表现为“裁量被收缩的”决定。人们因而有必要考虑,哪些——也可能是规范之外的——因素能够导致收缩现象的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回答下列问题的前提:决定性的因素何时能够导致裁量收缩,收缩到什么程度。
本文的研究过程由此得到了预定:首先需要对行政裁量和赋予裁量的规范的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论述,其次阐述裁量收缩的概念、过程和种类。紧接着应予分析的是,裁量收缩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都有哪些,以及它们基于什么方式和在什么范围上导致裁量收缩的出现。最后将在如何适用于个案方面进一步讨论本文提出的观点。
二、裁量与裁量规范
(一)作为保证个案正义之手段的行动余地的赋予
在法治国家之中,受平等原则影响尤深的正义观念,在抽象—一般的层面在法律规定的行动方式之中获得形式上的体现。正义观念的另一个方面为合理性(Billigkeit),也即个案正义。[注]Vgl.Starck,Das Verwaltungsermessen und dessen gerichtliche Kontrolle,in:Festschrift für Horst Sendler,1991,S.167,169 f.,jetzt auch in:ders.,Praxis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1994,S.223,226.Gern,DVBL.1987,1194,1199,Gern认为个案正义是法治国家原则的体现。立法者一般仅针对抽象—一般的情形而非个案做出决定,抽象—一般的法律并不能始终保障做出满足个案正义要求的决定:在其构成要件中,法律无法考虑到对于达成个案正义而言应予顾及的各种个案的特殊情形。对于那些相互之间并无或者没有显著差别的被规制的情形而言,这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通过解释抽象—一般层面中的概念便可得出对所有被规范涵盖的情形而言均为合宜的解决方法。在这些情形中无需向行政机关赋予特殊的行动余地。而在那些尽管存在一个统一的规制意图,但就所涉个案的特性而言具有较大辐射面的情形形态中,正义观念针对个案的合理性的面向的意义变得尤为突出,且需要以向决定个案的国家权力授予行动余地的方式合宜地顾及个案特性。[注]此外立法者也有必要通过授权制定抽象—一般的法规和规章的方式为行政机关赋予行动空间。此种所谓的“规范裁量”(Vgl.Sachs(Fn.1),§ 40 Rn.28 m.w.N.)并非本文的研究对象。
基于一般性的法律保留以及基本权利上的法律保留,作为国家权力之一部且在重大问题上[注]关于重要性理论,vgl.Schnapp,in:von Münch/Kunig(Hrsg.),Grundgesetz,Bd.1,4.Aufl.1992,Art.46 m.w.N.; Jarass/Pieroth,Grundgesetz,3.Aufl.1995,Art.20 Rn.30 f.; v.Arnim,Zur Wesenlichkeitstheorie“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DVBL.1987,S.1241 ff。具有最高民主正当性的立法者不可能完全放弃抽象—一般性的规定,而仅仅致力于能够通过行政机关合理处理(可能的情况下受到行政法院的控制)个案。[注]与之相对,在那些法律保留原则贯彻得并不充分的国家,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法律上不受控制的行动空间的情形也是可能的,例如法国,vgl.näher Schlette,Die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ontrolle von Ermessensakten in Frankreich,1991,S.98 f.,136.,148 ff.; Schmitz,Rechtsstaa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französischen Polizeirecht,1989,S.182 ff。如今,在克服存在于抽象的平等意义上的正义与个案正义之间的两难困境方面,立法者拥有多种多样的立法规制技术。如果立法者使用制定规则的方式,也就是说划分为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因而具备条件式结构的规范,[注]此外,立法者也可以使用——但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和明确性原则并不能仅仅止于使用——原则。与规则相比,原则仅仅表达引导性思想,但并不包含针对特定情形的法律后果规定。Esser,Grundsatz und Norm in der richterlichen Fortbildung des Privatrechts,3.Aufl.1974,S.51,95;Larenz,Richtiges Recht,1979,S.23 ff.已经具有就规则和原则进行此种区分的趋势;Mauerer (Fn.1),§ 7 Rn.2,63在依据如果—那么结构建构的传统、典型的法律规范和结果导向的法语句之间进行了类似的区分。本文不深入讨论Alex,Theorie der Grundrechte,Frankfurt 1986,S.75 ff.所强调的原则的作为优化命令(Optimierungsgeboten)的属性。较之规则,原则给行政机关赋予了更为广泛的行动空间。由于裁量收缩问题仅仅涉及法律后果裁量,且这一型构仅在条件式结构的规则的情形中才是相关的,故本文后续的研究并不讨论原则的问题。那么他既可以在构成要件方面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也可以在法律后果方面赋予裁量,乃至使用表现为联结条款(Koppelungsschrift)[注]Vgl.hierzu jeweils m.w.N.Richter/Schuppert(Fn.1),S.47 ff.; Seewald,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Jura 1980,S.175 ff.; Busch (Fn.2),§ 40 Anm.6.3; Maurer(Fn.1),§ 7,Rn.48 ff.; 关于相关司法裁判,vgl.Gemeins,Senat der obersten Gerichtshöfe des Bundes,BverwGE 39,355,362 ff.und BverwGE 45,162,164。的前两者的组合形态,为符合个案正义的行政行为留出余地。[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和法律后果裁量的赋予是不是行政机关决定职权本质上相同的或者不同种类的表现形式,是有争议的。Vgl.neben den oben (Fn.1)genannten Nachweisen Starck (Fn.6),S.167 m.w.N.Starck基于充分理由持有一致性观点以及由此导致的同样的有限的行政司法审查的观点,vgl.ders,,a.a.O.,S.167,169,juetzt auch in:ders.,Prasxis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1994,223,225; ähnlich bereits ders.,Diskussionsbeitrag,in:Götz/Klein/Starck(Hrsg.),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zwischen Gesetzgebung und richterlicher Kontrolle,1985,S.189,190; in die gleiche Richtung Herdegen,Beurteilungsspielraum und Ermessen im strukturellen Vergleich,JZ 1991,S.747 ff.m.w.N.zur älteren Literatur。对此问题本文不予表态。然而,就其功能而言——通过决定权限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为后者赋予自己的活动空间——二者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仅仅关注裁量规范,而在此可以确定的是,立法者赋予法律后果裁量的目的在于使得行政机关符合个案正义的决定具有可能性。
(二)裁量规范的授权性
那么,裁量余地是如何设定的呢?
正如业已指出的那样,规则一般会在抽象—一般层面表述一个构成要件,与之同时,此构成要件还会被规定一个特定的强制性法律后果。裁量规范的特殊性在于,在满足法定构成要件(无论其范围有多大)的情况下,它并未规定一个特定的强制性法律后果。行政机关由此被赋予的行动余地可能具有相互差异显著的各种样态。仅规定一种法律后果、但同时对是否对此种后果做出决定行为赋予酌定权限的规定,以及完全赋权行政机关确定法律后果的规定(例如“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表述),[注]危险防范法中的警事一般性规定经常会出现此种表述,例如Art.11 Bay PAG,§ 11 NgefAG,§ 14 NWOBG。构成了其可能性的两极。无论裁量决定自由的范围有多么大,裁量规范的特殊性在于,其在法律后果方面是(部分)开放的。法律中的此种“开放地带”的后果则为,行政行为并不完全由立法者决定,相反,行政机关——在各种各异的变种之中——被赋予了开放的行为选择。就此类行为选择的赋予而言,裁量规范具有授权属性(delegatorischer Charakter):基于个案合理性考量的必要性而导致的做出决定的不可能性,[注]同样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立法者能够做出决定、但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做出最终决定,行政机关因而负担了做出决定的任务。此种情形不在本文的考虑范围之内。立法者在抽象—一般层面未做决定之处,决定的权限在具体层面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
(三)选择裁量与决定裁量
对法律后果裁量造成的决定权限的转移,人们进行了决定裁量(Entschließungserm-essen)和选择裁量(Aauswahlermessen)的细分,前者涉及“是否”介入,后者涉及如何介入。[注]Vgl.z.B.Wolff/Bachof/Stober(Fn.2),§ 31 Rn.35:Maurer(Fn.1),§ 7 Rn.7:Busch(Fn.2),§ 40 Anm.7.2:Ule/Laubinger,Verwaltungsverfahrensrecht,4.Aufl.Rn.26; 专门就警察法和秩序法领域进行的区分,vgl.Rachor,Das Polizeihandeln,in:Lisken/Denninger(Hrsg.),Handbuch des Polizei-und Ordnungsrecht,2.Aufl.1996,Rn.F 55:Schenke,Polizei-und Ordnungsrecht,in:Steiner(Hrsg.),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5.Aufl.1995,Rn.1167 ff。这一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存在仅仅设定一个决定裁量(规定特定、但选择做出的法律后果)的规范,也相对较少地存在仅设定一个选择裁量的规范。在最经常出现的二者相结合的情形中,这一区分就暴露了弱点。[注]考虑到《行政程序法》第36条向行政机关赋予的为非羁束决定设定附款的(裁量)权限,大部分这样的情形可能表面上属于纯粹的决定裁量,但实际上是一种组合形态:《行政程序法》第36条列出的并分阶排布的各种常见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当然并非在所有的情形中均是如此——必须被归入选择裁量这一形式之中。尽管在此种情形中也能在观念中保留此种区分,但这种区分在实践中就不再有意义,因为如果不考虑具体的行动可能性,[注]Götz的看法与之类似。他因而强调裁量决定的一体性。他指出,在“是否”和“如何”问题之外,“何时”问题也是裁量决定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这一问题通常为人忽略,Götz,Allgemeines Polizeit-und Ordnungsrecht,12.Aufl.1995,Rn.349。事实上关于“何时”问题的决定是行使裁量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其在个案中可能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只有鉴于被具体考虑的行动可能性,“何时”问题才能获得有意义的解决。因而“何时”行动问题与“是否”和“如何”是密不可分的。Götz的看法也是如此。选择行动时间的自由本身并不是裁量规范决定性因素,否则实在行政法教义学赖以为基础的羁束行政和裁量决定之间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人们必须承认的是,即便是在羁束行政的情形之中,行政机关在此方面也拥有一定的自主余地。人们无法对“是否”介入做出合理的正确决定。
就进行审查的法院的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在课予义务之诉(Verpflichtungsklage)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法院做出一个课予义务判决,也就是说法院认定行政机关必须以特定方式采取行动,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只有考虑到公民追求的“如何”介入,且排除一切其他行动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出关于“是否”介入的课予义务判决。如果法院做出一个确认判决,原则上为行政机关设定介入义务,但并未确认行政机关做出公民追求的具体的行政行为的义务。在表面上看,此种判决仅就“是否”介入,而未就“如何”介入做出决定。进一步的观察则表明,即便在此情形中对于二者进行清楚区分也是不可行的:在驳回公民提起的义务诉请的同时认可行动的义务的前提为,其他的行动可能性已在法院的考察之中,且在其享有的审查密度的框架中,法院对这些其他行动可能性在“是否”介入方面的能力的评价不是负面的。即便是在撤销之诉的情形中,其争议对象仅为某一特定的行政行为,此种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合比例性的审查框架中,法院必须考虑是否存在更为温和的替代性手段。
基于上述的思考,应该同时可以看到,对行政机关行动自由所做的“是否”和“如何”裁量的区分问题以及司法审查问题已经涉及裁量收缩问题。对此,下文还会做进一步的探讨。
三、裁量收缩的概念、过程和种类
在前文中,裁量规范在法律后果方面的局部开放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决定权限向行政机关的转移,被认为是裁量规范的主要特征,而裁量收缩现象的主要特点则为裁量规范原本赋予的个案自主余地的(至少部分地)消失。裁量收缩概念[注]在文献和司法裁判中被使用的“裁量的收缩化”(Ermessensreduzierung)[Busch (Fn.2),§ 40,Anm.10.3.2; Wolff/Bachof/Stober (Fn.2),§ 31 Rn.55; Finkelnburg/Ortloff,Öffentliches Baurecht,Bd.II:Bauordnungsrecht,Nachbarschutz,Rechtsschutz,3.Aful.1994,S.215]或者“裁量限缩化”(Ermessensschrumpfung)[usch (Fn.2),§ 40,Anm.10.3.2; Wolff/Bachof/Stober (Fn.2),§ 31 Rn. 55; Stelkens,Das Verwaltungsverfahren,1991,Rn.452]概念在此被理解为同义语。的内容因而是所有出现于个案中的立法者赋予的行政机关自主空间的窄化。
故而,在裁量收缩的情形中,规范针对不特定多数情形赋予的自主余地并非在抽象—一般的层面被收回。规范在个案中的适用是否会出现裁量收缩现象,对于规范本身设定的自主余地的范围没有影响:规范在所有情形中都是不变如一的。因此,裁量收缩现象是由裁量规范之外的法律因素以及个案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后者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裁量规范的目的正在于促成个案正义的实现。在引言中提到的矛盾——规范原本设定的自主空间似乎因裁量收缩而被收回——由此得到化解。被赋予的自主空间的收缩并非抽象—一般地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个案,[注]A.A.Püttn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7.Aufl.1995,S.54.相反,收缩仅基于一个特定个案的特殊情况和仅针对这一个案。[注]相关文献一再强调此点,vgl.z.B.Sarnighausen,NJW 1993,S.1623,1625:Wolff/Bachof/Stober (Fn.2),§ 31 Rn.55; Maurer (Fn.1),§ 7 Rn.24; Gern,DVBL.1987,S.1194。
同时可以看到的是,司法裁判在某些情形中进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定裁量余地的限制,例如原本作为裁量规定的《联邦建设法》第35条第2款被变通地解释为羁束规定[注]BverwGE 18,247,250 f.; 25,161,162; Hoppel/Grotefels,Öffentliches Baurecht,1995,§ 8 Rn.78.对此持批评态度的,Ortloff,Ermessen in § 35II BauGB-Hat das Gesetz doch Recht?,NVwZ 1988,S.320 ff。关于《手工业法》第16条第3款的司法观点与之相似,行政法院认为裁量在此情形中一般基于授权的目的收缩至零,例如VGH Kassel,NVwZ 1991,S.280。,以及借助目的裁量(intendiertes Ermessen)这一法学型构(Rechtsfigur)实现的“可以—规定”转换为“应该—规定”[注]BverwGE 72,1,6; 91,82,90; BverwG,NVwZ 1987,S.601; BverwG,NJW 1987,S.1564,1565.这一司法观点因其在职权上造成的广泛实际影响而为多数意见批评,vgl.z.B.Maurer (Fn.1),§ 7 Rn.12; Peine,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2.Aufl.1995,Rn.69; Stelkens,Die Rolle der Verwaltungsgerichte bei der Umsetzung de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NWVBL.1989,335,339; ders.(Fn.18),Rn.396; ders.,in:Stelkens/Bonk (Fn.1),§ 39 Rn.26; Sacchs,in:Stelkens/Bonk (Fn.1),§ 40 Rn.15。关于目的裁量详细的批判观点,Volkmann,Das intendierte“ Verwaltungsermessen,DÖV 1996,S.282 ff。的变通性解释,不能归入裁量收缩现象之中,[注]这种区分在学理上和裁判中并非总是得到遵循,vgl.etwa Di Fabio,VerwArch 86 (1995),S.214,229,und OVG Koblenz,GewArch 1994,S.203,204。因为上述现象会不受个案的影响而直接触及规范赋予的自主空间的范围。
裁量收缩程度最强及其最重要和最令人感兴趣的情形——尤其就审查的角度而言——是所谓的“裁量收缩至零”。在此情形之中,在无瑕疵裁量(ermessensfehlerfrei)的意义上,只有唯一的一种行动可能性是合法的,而其他的可能性均表现为有裁量瑕疵的。[注]Kopp (Fn.2),§ 40 Rn.11; Sachs,in:Stelkens/Bonk (Fn.1),§ 40 Rn.32; Stelkens (Fn.18),Rn.452; OVG Münster,NJW 1984,883; Wolff/Bachof/Stober (Fn.2),§ 31 Rn.55.因此,裁量收缩至零的显著特点是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应予做出决定的别无选择性(Alternativenlosigkeit)。[注]Gerhardt关于此点的意见殊值赞同,Gerhardt,in; Schoch/Schmidt-Aßmann/Pietzner (Hrsg.),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Losblatt),1996,§ 114,Rn.27。由此,不再存在行政机关的自主决定,[注]学理上和司法中的主流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第46条和《行政法院法》第113条所涉的情形为羁束决定,vgl.Kopp (Fn.2),§ 46,Rn.31,m.w.N.; Ule/Laubinger (Fn.15),§ 58 Rn.23,m.w.N.; Kopp,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10.Aufl.1994,§ 113,Rn.86,m.w.N。尽管鉴于此种情形中出现的裁量的收缩此种观点是令人信服的,但绝非理所当然:假如就上述规范而言,在认定羁束决定和非羁束决定的时候以授权基础为准,那么必须看到,授权规范在抽象—一般的层面依然保有其作为裁量规范的属性(持此见者,Meyer/Borgs-Maciejewski,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2.Aufl.1982,§ 40 Rn.7)。其自主决定的自由真实地收缩“至零”(auf Null),而非“至一”(auf eins)[注]持此见者,Menger/Erichsen,Höchstrichterliche Rechtsprechung zum Verwaltungsrecht,VerwArch 1967,179。,因为在只有一种合法的行动可能性的情形中,不是存在一种自主余地,而是没有自主余地。[注]Menger/Erichsen错误地使用了“裁量收缩至一”的概念,Menger/Erichsen,a.a.O.收缩涉及的是裁量,而非剩余行动可能性的数目。在此种决定自由的完全丧失、而非部分窄化的情形中,使用“裁量收缩至零”的概念才是合适的。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中会出现裁量收缩至零?为处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回到决定裁量和选择裁量的区分上来。如果一个规范仅仅赋予了决定裁量,那么行政机关在具体情形中应该[注]Vgl.z.B.BVerwGE 54,54(中止妊娠许可令的做出); 61,105(居留许可的做出);BverwG,NJW 1990,S.1059(星期日营业禁令方面的特许);BVerwGE 95,15(关于承认某一教育机构作为传授事故地点急救措施和急救事物教学机构的资质)。或者不得[注]Vgl.z.B.BVerwGE 59,112; 61,32; 62,215; 81,155(关于驱逐令的不合法性)。实现法律规定的法律后果之时,裁量便已收缩至零。如果规范表现为选择裁量和决定裁量的组合形态,问题较为复杂。在此情形中,只有如前面所述那样相互联结的两种自主余地均完全消失,人们才能言及裁量收缩至零。一方面鉴于决定裁量和选择裁量的关联,另一方面鉴于只存在一种行动可能性的情形中才得以认定裁量收缩至零的存在,人们有理由主张,在组合形态的情形中,对于认定裁量的完全限缩而言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是选择裁量的消失。行政机关有义务介入、但依然可以自主决定手段[注]Vgl.z.B.BVerwGE 11,95,97; BverwGE,VerwRspr 20,S.588,589.的这种在学理上和裁判中通常被认为是裁量收缩至零的情形,虽然毫无疑问是裁量收缩的情形,但绝非裁量收缩至零的情形。[注]在学理上有人一揽子将把警察法上的介入义务认定为裁量收缩至零的情形,说明此种差异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遵循,vgl.z.B.Ossenbühl (Fn.1),§ 10 Rn.21 und Maurer (Fn.1),§ 7 Rn.24。
四、裁量收缩的决定因素
在阐明裁量收缩的概念、过程和种类之后,应予分析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则为,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裁量的收缩。
(一)事实与法律因素的结合
前文的论述至少表明,个案的特殊情况对于认定裁量收缩具有(协同)决定性意义。然而,此种情况本身只是一种纯粹的事实条件,不足以说明裁量收缩这一法律现象。超越了收缩了的裁量余地的决定是有裁量瑕疵的,因而是违法的。因此,同步出现的必然还有法律上的因素,其与个案情况的结合导致了法律赋予的行政裁量余地的收缩的必要性。
依据一个可回溯至联邦行政法院相当早的判例、[注]BVerwGE 11,95,97; ähnlich BverwG,DVBL.1969,586.由此联邦行政法院采纳了民事法院在关于国家责任的司法裁判中业已确定的路线,vgl.RG,JW 1939,S.239,240; RGZ 162,273,275; BGH,VerwRspr 11,S.462; 14,S.830,831。且在学理上[注]Götz (Anm.17),Rn.354; Schoch,Grundfälle zum Polizei-und Ordnungsrecht,JuS 1994,755,758; Schenke (Fn.15),Rn.II 70; Maurer (Fn.1),§ 7 Rn.24; Martens,Wandlungen im Recht der Gefahrenabwehr,DÖV 1982,S.89,97 f.; Hoppe/Grotefels (Fn.21),§ 15 Rn.88,§ 17 Rn.68; Finkelnburg/ Ortloff (Fn.18),S.213.关于早期文献的指引,Drews/Wacke/Vogel/Martens (Fn.3),S.399。和司法裁判中[注]明确表述这一标准的,OVG Berlin,NJW 1980,S.2484; VG Berlin,NJW 1981,S.1748,1749; OVG Münster,NVwZ 1983,S.101,S.102; VGH Kassel,NJW 1984,S.2305。关于早期的司法裁判,Drews/Wacke/Vogel/Martens (Fn.3),S.399。这一标准在某些判决中并未明确得到表述,但显然是以其为依据的,OVG Münster,GewArch 1991,S.185; BayVGH,BayVBL.1991,S.759; VGH Mannheim,VBLBW 1992,S.103,104 und VBLBW 1992,S.148,149。获得广泛认可的观点,在风险防范领域中,[注]在其他领域中,可能应该采用由其事项本身特性所决定的其他的标准。对此详尽的论证,OVG Münster,NWVBL.1995,S.160,162(关于铁路建设承包人土地占有提前指定的强制执行的裁量收缩的例子)。但这只是极为罕见的情形。大多数风险防范领域之外的情形都可以通过针对相关领域的特点、模仿这个标准发展出来的标准得到解决,正如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的例子所展现的那样。裁量收缩出现于严重威胁重要法益的情形中。[注]对局限于重要法益持不同意见的:OVG Berlin,NJW 1983,S.777,778(其所反对的裁判:VG Berlin,NJW 1981,S.1748,1749); Wilke (Fn.4),S.831,834,838 ff。此外,在建设法的领域中有时也会采用要求较为宽松的标准,下文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这一表述隐含了前述对于出现裁量收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和法律因素的结合。“严重的威胁”这一要件是指向各个案件的事实情况的;与之相对,“重要法益的威胁”则涉及法律因素。后一方面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地研究:在教义学上,特别是结合行政法和宪法现有的教义学上的型构,如何解释主要是某些特定的法益在这一问题上是有决定意义的?它们分别是哪些法益?它们在何时如此重要,以至于能够限制乃至剥夺行政机关的自主行动余地?
(二)决定性的法律因素
1.行政法的规范目的
在行政法教义学的层面上,就各个相关法律的目的所进行的目的论论证为此提供了一个参考因素,毕竟在行使裁量权的框架内法律目的具有重要的引导功能(参见《行政程序法》第40条、《行政法院法》第114条)。就警察法上的干预授权的问题而言——如前所述,这一授权的行使经常会出现裁量收缩问题——可以明确的是,通行观点认为,此种授权通过指涉“保护公共安全”这一目的回溯至法益,更确切地说,回溯至那些由裁量规范之外的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就给付行政(Leistungsverwaltung)而言,裁量规范的目的一般也与涉法的益(rechtlichrelevante Güte)密切相关。在行政法的层面上因而可以明确的是,作为裁量收缩的法律因素的向各个法定目的关涉的法益的回溯基本上是与裁量决定的属性相适应的。当然,在“特定——在警察法上的一般授权中甚至可能是所有的——法益在裁量决定的框架中一般而言具有一定作用”之外,这并没有更多的说明作用。仍然没有得到说明的是,哪些法益以什么方式导致了裁量的收缩。
2.宪法法益
前述表述以法益的重要性为准绳。然而,这一要件并不明确,需要为法律上的标准所充实。法益的重要性的一个指征是其在法律层级(Rechtshierarchie)内的位置。
(1)考量宪法法益的必要性
最为重要的法益是那些处于宪法法律层级之中的法益,因为依据《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效力,立法者、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均受其约束。[注]关于宪法至上原则,Starck,in:Starck/Weber (Hrsg.),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Westeuropa,Bd.1,1986,S.11 ff.; 现在也载于ders.,Der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sstaat,S.33 ff.; Starck,Verfassung und Gesetz,in:ders.(Hrsg.),Rangordnung der Gesetze,1995,S.29 ff。如果立法者——通过重要决定实现宪法规范的具体化的任务主要由其承担——通过法律后果裁量的设置将针对具体个案的进一步的决定权限移交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其(裁量)决定行为中也应遵守宪法。由此至少可以确定,在宪法规范之中得到保护的法益是重要的法益,在裁量决定之中应得到重视,在可能的个案之中可能会造成裁量的收缩。[注]毫无疑问不可排除的是,被宪法以下的规范保护的法益在个案之中可能也是重要的。然而,此类法益大多都体现为宪法法益的具体化。关于宪法上的保护义务领域中宪法法益与一般法律法益之间的关系,vgl.Hain,Das Untermaßverbot in der Kontroverse,ZG 1996,S.75,77 f。其所反对的意见为Dietlein,Das Untermaßverbot,ZG 1995,131,136 ff。在宪法规定的层面上,特别是在基本权利规定的层面上,基于臆想的较低的“重要性”完全排除受特定宪法规范所保护的宪法法益作为裁量收缩的决定因素,以前面的论述来衡量是不正确的,因为宪法的至上性涉及所有宪法规范,它们均以相同的方式约束行政机关。
就基本权利而言,在影响行政决定的程度方面,充其量能够根据各个限制保留(Schrankenvorbehalt)各异的设置进行区别对待。限制保留尽管主要是针对立法者的,但只要其中表达了对基本权利的价值的预先衡量,其在行政决定之中也应予遵循,假如行政机关被赋予了自己的自主余地。然而,就个案的特殊情况而言,通过严格的限制保留对某一基本权利的优待,并不必然会导致受到如此优待的基本权利的优先性,以及出现以此优待本身为根据的裁量收缩。此外,基本权利可限制性的程度这一面向并不能在所有的情形中都能引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依据《基本法》第2条第3款,生命和身体的不可侵犯性的基本权利只被规定了简易的限制保留,但其毫无疑问保护了一项特别重要的法益,[注]Vgl.BVerGE 49,24,53; ferner BVerGE 39,1,36; 88,203; Hermes,Das Grundrecht auf Schutz von Leben und Gesundheit,1987,passim.且依据通行的观点绝对能够为裁量收缩提供理由。一般而言,较之后续的基本权利,人的尊严保障应该在更强的程度上得到遵循,毕竟依据《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其效力是不得变更,且被通行观点看作最高宪法法益。[注]Vgl.z.B.BVerfGE 5,85,204; 6,32,36,41; 32,98,108; 50,166,175; 54,341,357; 72,155,170; 75,369,380; 79,256,268; Hain,Rundfunkfreiheit und Rundfunkordnung,1993,S.59 f.; Jarass/Pieroth (Fn.8),Art.1 Rn.2; Schlette,Kunstfreiheit contra Feiertagsschutz-ein Anwendungsfall der Lehre von den verfassungsimmanenten Schranken,JA 1996,955,957; Stern,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d.III/1,1988,S.27.由于生命权作为“人之尊严的活力基础”(vgl.BVerfGE 39,1,42; 49,24,53; Pieroth/Schlink,Staatsrecht II,11 Aufl.1995,Rn.428 )已被《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1句同时保护,上面提到的涉及生命权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1句得到解决。通过这种方式,生命权的特殊意义能够得到合理的照顾。
考虑到宪法至上性和由此决定的在进行裁量决定时必须遵守其规定的必要性,行政裁量的收缩总是不断地且主要是以宪法规范的介入——特别是基本权利——为依据,[注]Vgl.etwa OVG Münster,DVBL.1992,S.1316 (Art.1 I GG); VGH Mannheim,NVwZ 1993,S.122.(Art.1 I GG); BVerwG,NJW 1979,S.561(Art.3 I GG); BVerwG,NJW 1990,S.1059 (Art.5 I GG); BVerwGE 95,15,19 f.(Art.12 I GG); BVerwGE 47,280,283 (Art.21 I,38 I GG).可能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以宪法法益为基础的裁量收缩因而展现了法律后果裁量的一个特点:在决定权限方面——为授权性所决定,裁量规范在法律和决定层级中下移了一个层次,而在法律上的决定标准方面升入一个较高的法律层级。
(2)宪法、特别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上的接入点
1)凭借认定宪法法益的“重要性”和行政机关在决定行为中对其予以尊重的义务尚不足以完全解决裁量收缩问题。自此只是阐明了宪法对此问题具有意义,宪法保障的法益何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导致裁量的收缩,仍待说明。此外,由于回溯宪法层面的无可回避性,这一问题也必然同时与宪法教义学问题,特别是基本权利教义学问题密切关联。
在回答待解答问题之时,正如马上将会展示的那样,首先应该进行如下区分:裁量收缩是指向一个(特定的)作为还是不作为。其原因在于,基本权利教义学存在防卫权的、对抗国家行为的自由权的维度[注]其为基本权利的经典功能,siehe BverfGE 7,198,204 f.; 50,290,337; Starck,Grundrechtliche und demokratische Freiheitsidee,in:Isensee/Kirchhof(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Bd.II,1987,§ 29 Rn.16 f; jetzt auch abgedruckt in:ders.,Der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sstaat,1995,S.161 ff.,168 f.; Starck,Die Verfassungsauslegung,in:Isensee/Kirchhof (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Bd.VII,1992,§ 164 Rn.34,43 ff.,47。和所谓的基本权利上的保护义务的区分,后者为国家设定积极进行保护的义务[注]基本权利的这一维度近来得到较多的关注,vgl.insbes.Isensee,Das Grundrecht auf Sicherheit,1983; ders.,Das Grundrecht als Abwehrrecht und als staatliche Schutzpflicht,in:Isensee/Kirchhof(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Bd.V,1992,§ 111; Robberts,Sicherheit als Menschenrecht,1987; Hermes (Fn.40); E.Klein,Grundrechtliche Schutzpflichten des Staates,NJW 1989,1633; Dietlein,Die Lehre von den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ten,1992; H.H.Klein,Die grundrechtliche Schutzpflicht,DVBL.1994,489; Starck,Grundrechtliche Schutzpflichten,in:ders.,Praxis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1994,S.46 ff.; Unruh,Zur Dogmatik der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ten,1996,均含有众多范围广泛的司法裁判的指引。近来,因尝试通过“不足禁令”这一法学型构对审查的密度进行明晰化,联邦宪法法院的第二次堕胎判决(BVerfGE 88,203,254 f.)尤为值得关注。。然而,基本权利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含有——在可能的情形中个人得以诉求的——保护义务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注]Starck对此持批判意见,Starck (Fn.44),S.46 ff。根据这一区分,防卫权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毫无疑问可以作为裁量收缩至行政机关的不行为[注]Vgl.etwa BVerwGE 59,112; 62,115,关于因《基本法》第2条第1款而不采取驱逐措施。有疑问的是,《基本法》第6条第1款能否阻止对已婚外国人的驱逐(关于此类案件,vgl. BverwGE 61,32,34; 81,155,162)。如果此间涉及的不是《基本法》第6条第1款中明确提到的保护功能,而是防卫维度,那么驱逐就表现为一个干预(Eingriff);vgl.dazu E.M.v.Münch,in:v.Münch/ Kunig (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1,4.Aufl.1992,Art.6 Rn.12。——此时方出现收缩至零——或者收缩至不为特定行为的基础;相反,裁量收缩至(特定的)作为只能由宪法上的保护义务导致,然而裁量于此并不必然收缩至零。尽管在很多情形中,从保护义务之中可以导出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但依然存在履行保护义务的多种行动可能性。联邦宪法法院曾多次——涉及立法者的保护义务——强调后一点。[注]Vgl.nur BVerfGE 39,1,44; 46,160,164; 56,54,80 ff.; 88,203,254.作为其例外情形,在文献中有关于立法者基于《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而被课予的一个义务——将脑死亡标准规定为法定死亡标准——的讨论。Vgl.Klinge,Todesbegriff,Totenschutz und Verfassung,1996,S.183 ff.,insbes.S.191.这意味着立法者在“是否”和“如何”两个方面均受到约束。如果立法者通过法律后果裁量的赋予将部分自身的行动自主空间移交给行政机关,且行政机关在此自主空间之内的决定行为必须受到与立法者所遵守的同样的宪法标准的衡量,那么可以认为,即便适用此种宪法标准于行政机关的个案之中,原则上依然留有行动的——尽管是因决定和审查的较多的具体入手点而较小的——自主空间,此自主空间仅极为例外地因极为特殊的个案情况基于裁量收缩而消失。根据这一层考虑在此可以指出,必须严格对待裁量收缩这一法学型构,特别是其收缩至零的情形。
2)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对裁量因保护义务而收缩至行为与裁量因防卫权而收缩至不作为所做的区分实际上并无意义。进一步而言,假如裁量收缩的成立仅仅取决于从宪法之中提炼的法益,那么相关宪法规范以什么样的特殊的功能保护相关法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只要援引作为宪法规范的客观法内容( objektiv-rechtlicher Gehalt)且为其所保护的法益便已足够,宪法法益基于《基本法》第1条第3款、第20条第3款在此种属性上对整个法秩序均有约束力。针对此种观点,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质疑:
a.此种观点首先会导致法律救济上的问题。如此一来,如同学界中一部分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个人行政诉讼法律救济必要的主观法成分(subjektiv-rechtliche Komponent)(参见《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必须[注]Vgl.insbes.Pietzcker,JuS 1982,106,108 f; Dietlein,DVBL.1991,686,689,关于风险防范法的一般条款。存在于普通法上的裁量规范本身。根据在主流观点看来在此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保护规范理论(Schutznormtheorie)[注]Vgl.dazu nur Hufen,Verwaltungsprozeßrecht,2.Aufl.1996,§ 14 Rn.94 ff.; Kopp (Fn.26),§ 42 Rn.48 ff.; Sachs,in:Stelkens/Bonk (Fn.1),§ 40 Rn.72; Wolff/Bachof/Stober (Fn.2),§ 43 Rn.12,jeweils m.w.N.,单个裁量规范本身——或者在某些情形中通过结合《行政程序法》第40条——能否被解释为主观法的规范,是存在很多疑问的。[注]人们在这一点上承认,并非所有裁量规范都向个人提供主观的无瑕疵的裁量权行使请求权,只有裁量规范的解释表明其也是服务于具体到个人的利益的,才能认为存在此种请求权。Vgl.Maurer (Fn.1),§ 8 Rn.15; Sachs,in:Stelkens/Bonk (Fn.1),§ 40 Rn.78 ff.,m.w.N.; Pietzcker,JuS 1982,106,108 ff.; Busch (Fn.2),§ 40 Anm.10.2 m.w.N。例如以“公共安全”为准绳的警察法上的一般授权本身——也就是说不援引该规范之外的具体到个人的法益——并不能被解释为主观法规范。[注]So aber Dietlein,DVBL.1991,685,689.此外,如前文所述,抽象—一般的裁量规范本身统一地为所有情形授予同样的自主余地。这一层认识不支持裁量收缩的成立仅依据裁量规范本身而无需援引裁量规范之外的具体到个人的法益的观点,同时也使得裁量规范作为能够引起裁量收缩的请求权基础的功能令人生疑,即便个别裁量规范本身可能具有主观法属性。因此从根本上讲,只有与诸如基本权利那样的主观法规范相结合,裁量规范才有可能成为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基础。
仅仅援引客观法内容——这在防卫权的维度上是毫无必要的,但就保护义务的维度而言似乎是有吸引力的——也会使依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和《联邦宪法法院法》第13条第8a项、第90条以下提起宪法诉愿的应予许可性的论证变得困难。尽管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客观法内容奠定的保护义务与公民要求保护的主观权利相应,[注]Vgl.BVerfGE 49,89,141 f; 53,30,57; 56,54,73 m.w.N.; 77,180,214; 77,381,402 f; 79,174,201 f.; siehe auch Isensee (Fn.44),§ 111 Rn.8.但Starck认为这样的观点缺乏有力的论证,因为正如该法院自身就此指出的那样,[注]Dazu bereits deutlich BVerfGE 7,198,LS 1.; 50,290,337,在这些判决中,防卫维度的优先性得到了强调;vgl.auch Hain (Fn.41),S.68 ff。作为个人权利的基本权利的首要意义在于防卫国家的干预。[注]Starck (Fn.44),S.46,64,71.
b.另外一种因素也不利于此种消弭保护面向和防卫面向之分的对基本权利的客观法上的宪法法益的提炼:正如业已点出的那样,为论证裁量的收缩,仅从宪法之中提炼法益,而不考虑保护这些法益的宪法规范的特殊功能,是行不通的。在进行裁量决定之时,如果必须回溯至宪法层面,那么各个对某种法益进行规制的宪法目的也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就会有可能违背制定宪法规范之时所追求的目的。
因此可以坚定地认为,在通过援引宪法规范推导裁量收缩至不作为和收缩至作为方面,防卫功能和保护功能之间的区分是有意义的。
3)出于周全性的考虑有必要最后提到的是,行政裁量的窄化也可能由平等权的规范性面相造成。学理上和司法裁判中长久以来讨论的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的情形就属于此类。[注]详见下文论述。
五、裁量“是否”及“如何”收缩
基于前面论述的宪法和行政法的交叉现象,现在有必要在行政裁量收缩的出现及其范围问题上对宪法教义学和行政法教义学进行同步化处理。在此必须特别留意的是,这一问题与权力分立领域中的司法审查密度问题是密切关联的。[注]就裁量问题泛泛地强调此点的,Pieroth/Keimm,JuS 1995,780; Starck (Fn.1),S.16; Schlette (Fn.9),S.111。下面的论述一方面以业已阐述的宪法和行政法的关联为基础,另一方面以宪法上尊重和保护义务之间的区分以及裁量收缩至作为和裁量收缩至不作为之间的区分为基础。
以此为基础,一个因防卫权潜在的有利于相对人的作用而使行政机关负担不作为义务或者不得采取特定措施的义务的裁量收缩(至零),仅当行政机关的行为违反了受到广泛认可的作为审查国家权力干预的标准的广义的比例原则[注]Dechsling,Das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ebot,1989; Hirschberg,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Göttingen 1981; Hain (Fn.41),S.75 ff.; Herzog,in:Maunz/Dürig,Grundgesetz,Bd.2,Art.20,Abschn.VII,Rn.71 ff.; Lerche,Übermass und Verfassungsrecht,1961; Starck,in:v.Mangoldt/Klein,Grundgesetz,3.Aufl.1985,Bd.1,Art.1 Rn.178 ff.之时,才能被认为成立。因此,前文业已介绍的在学理上和司法裁判中关于风险防范法的广被适用的表述[注]尽管这个表述是针对“介入义务”这一问题发展出来的,但亦可适用于此处讨论的情形。意义上的能够引起裁量收缩的对宪法法益“严重的威胁”成立的前提为,当一个(特定的)行为从比例原则的角度上看是过度的。
一个因宪法上的保护义务而迫使行政机关作为或者采取特定作为可能性的裁量收缩(至零)成立的前提为,若不如此行动宪法上的保护义务便无法履行。在第二次堕胎判决[注]BVerfGE 88,203,254 f; 针对这一判决的批判意见,vgl.Starck,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 Schutz des ungeborenen Lebens,in:ders.,Praxis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S.85 ff。之中,为厘定立法者的宪法上的——确切地说基本权利上的——保护义务的范围,联邦宪法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采纳了首先在学界中出现[注]Canaris,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AcP 184 (1984),S.202,228; ders.,Grundrechtswirkungen und 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 in der richterlichen Anwendung und Fortbildung des Privatrechts,JuS 1989,161 (163 f.); Isensee (Fn.44),§ 111,Rn.165; Götz,Innere Sicherheit,in:Isensee/Kirchhof(Hrsg.),HdStR,Bd.III,Heidelberg 1988,§ 79,Rn.30 f.; H.H.Klein,DVBL.1994,489 (495).的“不足禁令(Untermaßverbot)”这一型构。依据该院的论述,立法者有义务提供合理且本身有效的保护。如果不欲违反不足禁令,保护措施的设置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要求。根据前面已经得出的结论,[注]参见本文第四(二)部分。这一关于立法者的保护义务及其由此产生的行动义务的论述也适用于行政机关。与之相应,在保护义务的情形中,对宪法法益严重的威胁成立的前提为,行政机关不采取(特定)行动便不足以满足最低限度的对宪法法益的保障。采用最低限度标注符合严格对待裁量收缩这一法学型构的要求。
下面将会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并在接下来也会深入讨论平等权角度上的问题。
(一)保护的角度
联邦宪法法院针对保护义务依据不足禁令提出了本文使用的最低限度标准,就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最经常出现的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的冲突情形中[注]如果一个公民的保护请求权与另一个公民的防卫请求权陷入紧张关系,就会产生此种冲突。当然可能也存在履行保护义务并不必然干预第三人的权利的情形。关于不足禁令在此类情形中的意义,vgl.Hain,ZG 1996,75,82。,不足禁令并不具备独立的教义学上的功能。这一点在学理上已经获得认可。[注]Starck (Fn.44),S.46 (81 f.),85 (88 f); Hain,Der Gesetzgeber in der Klemme zwischen Übermaß-und Untermaßverbot?,DVBL.1993,982,983 f; ders.,ZG 1996,75; Unruh (Fn.44),S.83 ff; Stern,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d.III/2,1994,S.84 III 10,关于合宜性(Geeignetheit)标准,Schlette,Die Verfassungswidrigkeit des Ozon-Gesetzes,JZ 1996,327 (333)。在个案中,两种相互冲突的义务的范围问题事实上是通过广义的比例原则确定的,该原则从干预的角度上表现为过分禁令,从保护的角度上表现为不足禁令。此外还可以看到,冲突情形之中的裁量收缩问题必然是在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
然而,不足禁令的独立的教义学功能的缺乏及其从属于广义比例原则的属性并不能使宪法司法对最低限度保护意义上的保护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的表述变得无的放矢。需要讨论的是,最低限度何时未能满足?对个案特殊情况的考察于此并无作用,处理这一问题需要规范性标准。如果在教义学的层面上能够找出一个统一的尺度,鉴于各种具体的实际情况,能够据此尺度判断是否存在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者不为特定的行为)导致的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保护意义上的宪法法益的“严重威胁”,那将会带来极大的便利。
然而,人们只能从含有保护义务的规范之中找到规范性标准。如果在基本权利规范之中寻找规范性标准,问题显得较为复杂,因为人们从各个基本权利中找到的标准可能是互有差异的。考虑如下问题对此可能是有助益的:人的尊严是所有基本权利共同的核心,[注]Vgl.näher Dürig,Der Grundrechtsschu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AöR 81 (1956),S.117,121 ff.; Hain (Fn.41),S.48 ff.,m.w.N.Siehe auch Unruh (Fn.44),S.35.人的尊严条款实质上对人的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全面的根本性保护,[注]BVerfGE 5,85,205; Dürig,in:Maunz/Dürig,GG,Bd.1 Art.1 Rn.10 ff.,18; Art.3 Rn.3 ff.; Stern,Menschenwürde als Wurzel der Menschen-und Grundrechte,Festschrift für Hans Ulrich Scupin,1983,S.627,640 f; Starck (Fn.57),Art.1 Rn.7; Hain (Fn.41),S.60 ff.m.w.N.《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句第2项明确规定了相关保护义务。从中可以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个案的情况而言,如果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不为特定行为会导致基本权利的人的尊严之核受到损害,那么就存在收缩行政机关的裁量余地、迫使其(或以特定方式)介入的、不满足最低保护限度意义上的“严重威胁”。
然而有疑问的是,此种绕回基本权利上的人的尊严保护义务的(曲折)方法是否有必要。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基本权利到底是否含有保护义务。如果人们认为,保护义务只存在于客观法内容的层面,正如业已论述的那样[注]参见本文第四(二)2.(2)2)部分。,那么以主张裁量收缩至介入为目的的宪法诉愿的主观资格和个人依据《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的主观起诉资格均无法成立。人们甚至认为,除了《基本法》第6条第1款、第6款明确规定的几种例外情形,基本权利根本不含有——甚至是客观法意义上的——保护义务,其中仅仅存在防卫权。[注]也有人在学理上尝试将保护义务处理为主观防卫权的一个子集,Murswiek,Die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Risiken der Technik,1985,S.107 ff.; Schwabe,Problem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1977,S.213 ff.; 持反对意见的,Starck (Fn.44),S.46,73 f。这些观点的依据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生成历史、字面意思和实证法体系。[注]Starck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一点,但并未认可本文提到的从纯防卫权解释之中导出的结论,Starck (Fn.44),S.46,74。关于议会委员会的规制目的,Hermann v.Mangoldts,Abschnitt I,Die Grundrechte,in:Schriftlicher Bericht zum Entwurf des Grundgesetzes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nlage zu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 der 9.Sitzung des Parlamentarischen Rates am 6.Mai 1949,Bonn 1949,S.5 f.Siehe auch Hain (Fn.41),S.63 f。因此,裁量收缩至介入不能直接以基本权利为依据。相反,具体到个人的法益一般而言只能以《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句第2项为依据,毕竟此处明确地规定了“保护”。[注]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援引人的尊严并不会因其在各种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上的广泛的事项范围而使保护义务在事项上的覆盖范围受到限制,这一援引仅涉及审查密度。这种以人的尊严为依据的做法也能解决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和宪法诉愿资格问题,因为主流意见认为人的尊严条款含有主观权利。[注]Starck (Fn.57),Art.1 Rn.18; Zippelius (Drittbearb.),in:Bonner Kommentar,Art.1 Abs.1 u.2 Rn.24 ff.; Klinge (Fn.47),S.217 m.w.N.; a.A.Dürig,AöR 81(1956) S.117,119.将人的尊严作为裁量收缩的决定性因素的原因还在于,《基本法》79条第3款强调人的尊严在现行宪法秩序的框架之中是不得侵犯的,其要求在任何情形中——基于《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在所有行政决定之中——都必须得到遵守。
(二)防卫的角度
基于保护义务的裁量收缩的情形应该直接援引人的尊严,基于防卫角度的却并非如此。防卫权本身就能为裁量收缩至不作为(或者不采取特定措施)提供法律基础,且比例原则是与之相应的审查尺度。因而防卫权的情形及其法律基础与保护的情形有很大区别。
就裁量收缩的范围而言,这里也应该注意到,《基本法》第2条以下的自由权是从人的尊严条款派生出来的——除了个别明确规定的例外(例如《基本法》第6条第4款),且是以尊重义务(《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句第1项)为基础而实证化的。由此可以看出,“显著的威胁”问题在此种情形中也可以依据基本权利的人的尊严核心标准解决。因此,裁量收缩在防卫的情形中成立的前提原则上为,若非如此便不足以满足人的尊严为防卫权的保障设定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如此一来,比例原则作为过分禁令在防卫的角度上发挥着保障达到前述最低限度的作用。如果制宪者或者修宪者为个别基本权利较之所有基本权利共同的根源——人的尊严——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范性安排,在很多特殊的基本权利之中均应认可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具有严格的法律保留规定的,在解释相关基本权利的规定时可能会存在较大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会更多地造成裁量收缩的出现。[注]例如由风险防范法上的一般授权赋予的裁量余地被《基本法》第13条——尤其被其第3款规定严格的保留——造成的显著的收缩的表现为,会对住房的不可侵犯性造成干预的风险防范措施只在极为严格的条件下才是被许可的。在制定关于进入和搜查住房的风险防范法上的一般授权的过程中,这一点应该得到重视。从中可以看出,在保护和尊重义务处于冲突关系的情况中,可能会出现不对称的现象。这种可能性本身便已使得基于保护义务的裁量收缩至作为和基于防卫权的裁量收缩至不作为之间的区别必须得到坚守。
(三)平等的角度
平等权角度下的裁量收缩的切入点是先前的一个行为或者不作为(尤其是业已存在的合法的行政实践做法[注]较新的相关判决,vgl.BVerwGE 91,135,137 f.; BVerwG,NJW 1989,S.1446,1447; VGH Mannheim,NVwZ 1987,S.253,254; OVG Münster,NJW S.1990,1684; VGH Mannheim,NVwZ 1991,S.1199。以及指引此种实践的行政规定[注]Vgl.bereits BVerwGE 34,278,280f.; 35,159; 较新的判决,BVerwG,BayVBL.1988,S.25; BVerwG,DVBL.1995,S.627; OVG Münster,NWVBL.1990,S.128; weitere Nachweise bei Kopp (Fn.2),§ 40 Rn.26 und Redeker/v.Oertzen,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11.Aufl.1994,§ 42 Rn.149; 专门针对风险防范法的,vgl.Drews/Wacke/Vogel/Martens (Fn.3),S.393 ff。),因而人们一般将此现象称为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注]Vgl.z.B.Di Fabio,VerwArch 86 (1995),215,223 f.; Maurer (Fn.1),§ 7 Rdnr.235,§ 11 Rdnr.51,65,§ 24 Rdnr.21 f.; Kopp (Fn.2),§ 40 Rn.95; Busch (Fn.2),§ 40 Anm.9.5.1ff.; Ossenbühl (Fn.1),§ 10 Rn.20 Redeker/Oertzen (Fn.73),§ 42 Rdnr.149; Sachs,in:Stelkens/Bonk (Fn.1),§ 40 Rn.55; 专门针对风险防范法的,vgl.Drews/Wacke/Vogel/Martens (Fn.3),S.385 ff.(包含对较早文献的指引)Wilke就这一点所言的“基于不正当的消极性的裁量收缩”有失偏狭,他忽略了裁量收缩至不作为这一方面。平等权的规范性意涵既可以导致裁量收缩至行为,也能导致其收缩至不作为。在这一点上,此处的裁量收缩的情形也可以进行与自由权方面的防卫的情形和保护的情形之间的区分相类似的区分,尽管防卫权和保护义务与平等原则在出发点上存在差异。[注]防卫权和保护义务通常是在相互对立的法益的紧张关系中被激活,而平等原则涉及的是有可比性的两种法律地位之间的关系。
依传统的观点,平等原则中含有“本质上相同的不得恣意地不同对待,或者本质上不同的不得恣意地同样对待”的禁令[注]Vgl.BverfGE 4,144,155; 27,364,371 f.; 78,104,121; Gubelt,in:v.Münch/Kunig,GG,Bd.1,4.Aufl.1992,Art.3 Rn.11,m.w.N.因这一表述的不确定性而持批评意见的,Starck (Fn.57),Art.3 Rn.11; W.Böckenförde,Der allgemeine Gleichheitssatz und die Aufgabe des Richters,1957,S.49 ff。。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于1980年提出了所谓的“新表述”(neue Formel),依据这一表述,如果与其他规范相对人相比,一个规范相对人群体受到了不同的对待,但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的种类或者差异的重要性不足以为区别对待提供正当化理由,那么就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第1款。[注]BVerfGE 55,72,82; 此裁判意见此后得到一再确认,vgl.etwa BverfGE 67,231,236; 74,203,217; 82,60,86; 85,238,244.含有大量新近裁判指引的,Koenig,Die gesetzgeberische Bindung an den allgemeinen Gleichheitssatz-Eine Darstellung des Prüfungsaufbaus zur Rechtssetzungsgleichheit,JuS 1995,313,315。该院第二庭于1995年也采纳了这一“新表述”。[注]BVerfGE 92,277,318.这个判决表明“新表述”得到完全的贯彻,vgl.Schmitz,Verfassungsrechtsprechun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1995,European Review of Public Law.Vol.8 (1996),Nr.4。针对此种新的裁判意见,相关文献提出了“审查密度强化”的说法。[注]例如Gubelt (Fn.76),Art.3 Rn.14,m.w.N。
就这一问题,本文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深入探究:毫无疑问,先前的行为原则上能够约束行政机关。但同样可能的是,尽管具备很多相似性,新的案情可能在特定重要细节上存在自身特点,因而行政机关可以据此采取其他反应措施。这表明,案情的可比性或者不同性——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会导致自我约束正是以之为基础的——问题是决定性的,而且这一问题的判断含有评价性的因素。[注]关于这一问题,vgl.Starck (Fn.57),Art.3 Rn.12 ff。针对此种评价进行的司法审查,前面业已指出的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与平等原则的关联[注]参见本文第五(一)部分。——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依据。依据这一关联可以认为,以平等原则为依据的裁量收缩成立的前提为,若非如此人的尊严条款针对平等对待或者不平等对待在实质的理由方面设定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便无法满足。[注]就《基本法》第3条第3款意义上的特殊的平等规范而言,包含于这一规定之中的歧视禁令已经表现为鉴于人的尊严必须保证的最低限度的平等的进一步规定。由于这一歧视禁令强制性地规定了必须保障的最低限度的平等,其适用会自动引起裁量的收缩。然而,性别歧视禁令并不针对那些对于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的区别对待,有些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仅仅出现于男性或者仅仅出现于女性。
六、结论:作为认定裁量收缩之尺度的最低限度标准
(一)最低限度标准在个案中的运用
正如前文所述,必须严格对待裁量收缩(至零)这一型构。原则上而言,以(主观法上的)宪法规范为依据的(完全的)裁量窄化成立的前提为,若无行政机关的(特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为相关宪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而不满足最低限度标准的前提为,人的尊严在保护义务的情形中被侵犯,或者基本权利的尊严核心在防卫的情形中被侵犯。
是否存在不满足最低限度要求的情形,只能根据个案的情况判断。个案的实际情况于此有意义,是由裁量决定促成个案正义实现的性质决定的。[注]参见本文第二(一)部分。人们也承认,只能根据具体情境确定人的尊严对于法律决定意味着何种要求。[注]BVerfGE 30,1,25; BVerfG NJW 3315; Kunig,in:Münch/Kunig,GG,Bd.1,Art.1,Rdnr.22; Höfling,in:Sachs,GG,Art.1,Rdnr.12; Klinge (Fn.47),S.221 f.m.w.N.然而,最低限度标准及其与人的尊严的结合至少能够为个案中关于裁量收缩的决定提供一个指导思想。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不仅能够保障个案中行政决定和司法决定的一贯性,也能够在职权法的角度上确保行政机关的自主余地不被程度过强的司法审查压缩。[注]众所周知的是,关于裁量收缩的司法审查范围过广。针对裁量收缩的认定,Sachs,in:Stelkens/Bonk (Fn.1),§ 40 Rn.32; Stelkens (Fn.18),Rn.452。下面将在几个方面点明,最低限度标准对于个案都能提出何种要求。
应予保障最低限度的自由、平等以及原则上为人的尊严所保护的自由、平等的物理上的、实质上的前提条件是否要求裁量收缩至(特定的)行为或者不作为,取决于如无(特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上述法律地位在个案中会受到多强的损害。如果损害如此之强,以至于对所涉宪法法益的损害本身就应被视为对最低限度要求的违反,那么仅基于此点即可认定裁量收缩的存在。[注]例如,如果正在进行的暴力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了现时的生命危险,警察必须介入。
在此种不满足最低限度标准的状态的事前阶段,可能存在违反宪法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威胁,这也可能会导致裁量收缩。因即将出现的不满足最低限度标准的状态,一个对宪法法益较轻的损害就有可能强迫行政机关作为或者不作为,假如不存在或者仅存在以对立性法益为依据的较弱的理由。[注]反之可见:在冲突情形中,对宪法法益的损害越强,以对立宪法法益为依据的对抗裁量收缩的论据必须更为重要。由此可以看出,Götz[注]Götz,Die Entwicklung des allgemeinen Polizei-und Ordnungsrechts (1981 bis 1983),NVwZ 1984,211,216; 作为其后继者:Drews/Wacke/Vogel/Martens (Fn.3),S.400.描述的缺乏无裁量瑕疵地拒绝被欲求的措施的理由的情形,并非独立的、需依照异于本文提出的标准进行判断的裁量收缩的情形,此种情形需要依据本文意义上的最低标准的不满足予以判断。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完全缺乏阻止行政机关(进行特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理由的情形中,裁量收缩的认定也必须以值得重视的、显著的对宪法法益损害为基础。
此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仅在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者某种十分确定的行为对于保障相关宪法法益受到最低限度的尊重或保护是绝对必要的情形中,才能认定裁量收缩至零的存在。对具体情形中的宪法法益进行最低限度的保障假如存在多种同样合适的可能性,行政机关可以依据不受司法审查的目的标准做出决定。
此外,前面的论述再次表明,在保护权和防卫权相互冲突的情形中,审查裁量收缩问题必须顾及所有冲突中的权利,并通过权衡——需要注意到保护义务与防卫权之间存在的潜在的不对称性——做出决断。[注]本文采纳的人的尊严(保护义务的情形中)以及基本权利的尊严核心(防卫的情形中)从表面上看与将判断过程描述为权衡是有矛盾的。人的尊严基于其不可侵犯性从表面上看是不得权衡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的尊严保护所有人的自由(以及平等),因而在自由权的方面对人的尊严的损害仅在以下情形之中才能认为存在:当国家权利可能造成损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无法通过同样为尊严保障所保护的他人的自由获得正当化。然而,此种权衡并非完全可被司法审查,否则,人们努力探索得来的宪法规范对裁量决定的要求仅为最低限度的认识将被毁于一旦。在立法者对基本权利和保护义务进行具体化的方面,即使是联邦宪法法院也通过承认立法者的“评估专权”(Einschätzungsprärogativ)限制了司法审查的密度。[注]对于防卫情形具有根本性意义的:BVerfGE 50,290,332 ff.; 针对保护义务的:BVerfGE 88,203,262 f.,这个判决援引了前一判决,由此可以看出,该宪法法院认为在防卫和保护的情形中专权的范围是一致的。本文持有的最低限度观点(既在保护义务的方面,也在防卫权的方面)由此获得了承认。如果说由于立法者自身在抽象—一般的层面没有或者没有完全对宪法权利进行具体化,具体化这些权利的任务由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完成,那么行政机关同样也享有评估专权,确切地说,不仅仅在构成要件的方面,也在裁量上的法律后果方面。[注]法律后果方面的评估专权涉及的主要是各种可见的行动可能性可能的后果,以及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对于业已存在的危险情况的发展的影响。因此,相关评估可进行司法审查的地方在于其有理由性(Vertretbarkeit)。[注]持有此见的关于立法者的判决:BVerfGE 88,203,262。这一点也相应地适用于适用平等原则时所需进行的对案情可比性和差异性的判断。
当然,与立法者调整的抽象—一般的情形相比,个案的一般而言更为具体的情况能够为有理由性审查提供更多或者更为细密的审查着眼点。但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进行决定的时候处于什么样的时段,行政机关在这样的时段之中可能做出的评估是什么。因此,对于个案中的决定不能依据相对人或者法院在事后才能获得的认识,或者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只能通过细致、但极耗时间的研究才能获得的认识进行审查。在需要快速做出反应的情形中,不能在事后用过于严格的标准判断行政机关的评估。然而,鉴于个案的特殊情况而表现为紧急状况的情形中,对宪法法益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潜在的威胁通常是不利于裁量收缩的认定的。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裁量收缩使得行政机关负担了事实上不可能的行为,那么就不能认为存在裁量收缩。对于行政机关这也是适用的:任何人只在自身可能的范围内负担义务(nemo ultra posse obligatur)。[注]Vgl.dazu näher Di Fabio,VerwArch 86 (1995),S.214,231.
(二)后果:以建设法为例
前面的论述表明,对裁量收缩的认定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收缩至零而言。因此,出现中等程度的侵扰情形便已存在一般警察法和秩序法上的介入义务的主张,[注]持此见者:Drews/Wacke/Vogel/Martens,(Fn.3),S.401。或者针对所有此类案件不加分别地认为裁量于此情形中“一般”收缩至零,均是行不通的。[注]例如在前注〔21〕里提到的情形。如前所言,这些情形涉及的并不是(针对个案的)裁量收缩,而是抽象地将裁量规范转换性地解释为羁束性的权限或者应为—规定(Soll-Vorschrift)。在司法裁判中[注]OVG Münster,NJW 1984,S.883 (“为了受损害的邻居而介入的义务是常态,不采取干预措施是例外情形,且需要特别的理由。”); OVG Münster,BRS 25 Nr.194; OVG Münster,BRS 39 Nr.178; OVG Münster,VBLBW 1986,S.23;OVG Lüneberg,BRS 48 Nr.191; OVG Berlin,BRS 50 Nr.206; OVG Saarlouis,NVwZ 1983,S.685; VG Saarlouis,DVBL.1969,S.595.Vgl.a.die Darstellung bei Sarnighausen,NJW 1993,S.1623 ff.,此处还引用了大量未公开发表的判例。和在学理上[注]Finkelnburg/Ortloff (Fn.18),S.215 f.; Peine,Öff.Baurecht,2.Aufl.1993,S.275.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观点在这一点上特别令人忧虑。此种观点认为,在建设秩序法之中,在针对一个因违反保护相邻人的规定而(实质)违法的建设项目的介入问题上,在如下情形中一般会出现裁量收缩:行政机关有义务命令清除违法建设项目,而且这不仅仅适用于违章建筑的情形,也适用于相邻人已经通过司法途径实现了违法的建设许可的撤销的情形。[注]例如此处的介绍:Finkelnburg/Ortloff (Fn.18),S.214 f.,m.w.N。这里绝对不应存在一个行政机关的决定的——大概是从基于先前被撤销的违法建设许可而产生清除后果义务思想中推导出的[注]前面引用的判决就持有此见:OVG Münster,BRS 25 Nr.194; OVG Münster,BRS 39 Nr.178; ähnlich OVG Lüneburg,BRS 48,Nr.191。——自动机制。令人实在难以想象的是,在对相邻人仅有较小的侵害(而且拆毁可能会给业主带来显著的财产上的负担)的情形中,到底是基于何种理由行政机关有义务颁布清除命令,而在一般警察法中的有可比性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可以保持不作为,况且,相邻人针对侵害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主张权利;另外,建设法上的相关授权性规范根本不能为此种行政机关的裁量的收缩提供任何依据。
从本文提出的以宪法规范为依据的处理裁量收缩问题观点之中,可以为克服此种过分的对行政自主空间的限制提供额外的论据。尽管就此处讨论的情形而言,仅仅是普通法上的规定,而非宪法规范在裁量收缩问题上是相关的。然而,这一领域中相关相邻人保护规范一般而言包含的不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宪法法益的能够造成裁量收缩法益。事实上,在这些规定的后面一般隐藏着宪法法益,而建设法上的保护目的恰与其密切关联。举例而言,在那些确保足够的通风、采光和服务于消防目的[注]确切地说,既涉及建设用地本身,也涉及相邻关系,vgl.etwa Finkelnburg/Ortloff (Fn. 18),S.23; Peine (Fn.97),S.256; Oldiges,Baurecht,in:Steiner (Hrsg.),Bes.Verwaltungsrecht,5.Aufl.1995,Rn.290:OVG Berlin,DVBL.1993,S.120。的规定之后,存在着诸如生命、健康和所有权等宪法法益,它们在防卫权的角度上为《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和第14条所保护,其核心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句第2项意义上的保护义务的对象。基于宪法上被保护的法益的决定性,本文以这些法益为基础提出的关于裁量收缩的观点在上述情形中应该得到采用,尤其是其中包含的最低限度标准。因此,人们在这一领域之中应该持有的观点为,仅当相邻人持久性地受到侵害且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违反了保护和尊重[注]显而易见的是,在违章建筑情形中相邻人主张了其保护请求权,而在由行政机关做出的建设许可被撤销之后的行政机关的介入问题上,人们很难轻易断言相邻人是否在其基本权利上的防卫权利上受到侵害,或者说此种情形(基于原则上的建设自由和建设许可作为羁束决定的属性及其仅为开展建设的形式上的前置条件)也牵涉到保护义务的维度。由于——正如业已论述的那样——无论是在防卫权还是在保护义务的情形中都必须以较之文章征引的观点更为严格的态度认定裁量收缩的成立,本文出于篇幅原因对此问题不下定论。然而,被本文批判的观点已在一个较低的门槛上认可了裁量收缩的成立,而在这个门槛上,本文前面在审查密度方面对保护义务和防卫权的情形所做的区分根本无法被考虑在内。的最低限度时,[注]这并不是说行政机关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地容忍违反建设法的状态以及不必采取任何措施。在司法裁判中和在学理上一个与本文相似的严格主义的路线已隐约可见,但并未如本文那样在宪法的层面对其进行论证,vgl.VGH München,BRS 40 Nr.237; VGH München,BRS 48,Nr.174,175; Battis,Öffentliches Baurecht und Raumordnungsrecht,3.Aufl.1992,S.277.hnlich wohl auch Hoppel/Grotefels (Fn.21),§ 15 Rn.88,§ 17 Rn.68。才有可能造成裁量的收缩。
(三)结语
前面的论述表明,裁量收缩问题只有同时考虑到行政法和宪法上的因素才能得到解决,但这一认识在学理上和在司法裁判中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到充分的贯彻。
尽管宪法介入这一主要在行政法的视野内考虑的问题会导致行政法上的法学型构同时负担宪法上的尤其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上的问题的后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人们认真对待宪法的规范性的话。此外,与宪法产生关联以及对行政法和宪法上的规定进行同步化加工,能够通过引入关于认定裁量收缩的统一的标准克服这一问题上的决疑法式的裁判上的分裂现象,并促成更大的裁判的一贯性。而且,本文持有的最低限度标准也能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中促成平衡,并能够在合理的程度上克服司法机关对立法者赋予行政机关的自主空间的过分的干预。对于应予严格对待的作为例外情形的裁量收缩(至零)现象,Ehmke的呼吁极为正确:审查的极大化并不意味最优化。
在文末还应指出的是,在本文的框架中,涉及的是以开放的(例如基本权利的[注]Ehmke,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erwaltungsrecht,1960,S.47.)宪法规定为基础的裁量收缩的情形。本文所持的严格主义正是以此为根据的。相反,人们也应该看到,立法者绝对也有可能在普通法的层面上为保护特定的宪法法益为行政机关和审查法院制定更为细致的规范性尺度[注]然而立法者在保障对立的宪法权利方面不得违反应该遵守的最低限度。——例如通过规定羁束性的权限、应为规定(Soll-Vorschriften)以及针对选择裁量的更为细致规定——,只要这些尺度在抽象—一般的层面是能够规定的,且立法者不必因个案正义的原因而应该放弃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