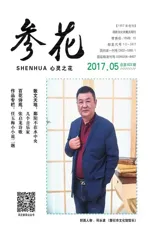现代性的漂浮困境
——论毕飞宇的小说《生活在天上》
2017-03-24苏枫
◎苏枫
现代性的漂浮困境
——论毕飞宇的小说《生活在天上》
◎苏枫
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现代时期所发生的断裂以其席卷全球的速度和范围而具有更为深远的变革意义。毕飞宇的小说《生活在天上》体察了处于时代之交的人们面临的困境:“脱域”后遭受到的种种冲击;旧的信任基础崩塌、新的信任基础还未建立的存在性焦虑;如此的焦虑带来寻求安全感的“再嵌入”的渴求,却屡次失败。再嵌入失败之后,我们有如困在茧中挣扎的蚕,将自我隔离,漂浮无依,留下的只有精神故乡消亡后的惶惑与孤独。
现代性 脱域 信任 再嵌入 漂浮
现代性具有其特有的形态:高速、全球性、物质丰裕。它将我们抛离出前所有之的社会秩序和轨道,进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模式。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使全球共享成为可能,也带来了充裕的产品。“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在让·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的现代世界中,人并非再是被人包围,而是被物包围,人们从过去的互动性中脱离出来,彼此陌生而疏远,成为一个个漂浮的孤独个体,即吉登斯所谓的“脱域”。处于世纪之交的1998年,毕飞宇用《生活在天上》对“脱域”后的人的存在形态进行关照,通过一个“异乡人”的他者视角,投射出生活在“美丽新世界”里的现代人的空洞与孤独。
一、脱域与文化冲突
小说在开头就为主人公设置了全新的时空环境:原本住在乡下的老人蚕婆婆被大儿子接到城里来。蚕婆婆从乡村进入到城市,可看作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进入,这种进入同时意味着从先前时空系统的脱离,即吉登斯所谓的“脱域”。“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18吉登斯认为,机械钟的出现使时间与空间相独立,时间的虚化成为空间虚化的前提,空间与地点的分离替代了其一致性。于是,人们从彼此熟悉的互动性关系和地域性关联当中被甩出,感到一阵阵的晕眩。蚕婆婆进入城市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且难以融入的世界,进了车库感到被浓烈的汽油味包裹,晕;坐电梯一开一停,晕;进了家门,闻到类似于车库的令人不舒服的皮革、木板、油漆的混杂气味,晕;在二十九层的阳台上俯瞰地面,还是晕。人们都以为蚕婆婆走出的那条青石板路是通向富贵和幸福之路,却不曾料想“脱域”之后面临的将是种种冲击,在湍急的现代洪流中被搅拌至晕眩。
“脱域”不仅是时空上的位移,而且它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3]文化在长期的积淀过程中具备了稳固的内在特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发生变动,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彼此都想征服或者同化对方之时,冲突和碰撞就产生了。蚕婆婆作为深受前现代文化洗礼的人,与已经被现代文化同化的大儿子之间,就存在明显的冲突。来看看这三段对话:
“儿,你不是住在城里吗?怎么住到天上来了?”
“不住到天上怎么能低头看人?”
“低头看别人,晕头的是自己。”
“低头看人头晕,仰头看人头疼。——还是晕点好,头一晕就像神仙。”[4]
蚕婆婆在乡村的生活是扎根于大地的,有脚下的那片土地作为维系和寄托,心里就是踏实的。住进了大儿子在城里的二十九楼的大房子,因大地消失产生的漂浮感让她感到一阵晕眩。反观大儿子,他十分得意于自己由资本和财富堆积起来的地位,并享受“低头看人”的乐趣。这个时候的大儿子已然被“人在人上”的“鬼”文化入侵,变成了人的异化的产物。
“这也遥控,那也遥控,城里人还长一双手做什么?”
“数钱。”[4]
在消费社会里,想要购买商品就必须获得财富,拥有财富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所以资本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于现代人的脑海,全身的触角只向一个方向伸展——资本。“劳碌惯了”的蚕婆婆却无法用摩挲过清凉绵软的桑蚕的手去数钱,触摸过生命的手绝不能对毫无生气的金钱产生丝毫亲近感。
“你再结一回,再生一个,我还有力气,我帮你们带孩子。”
“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只要有钱,夜夜我都可以当新郎。”[4]
鲍曼认为,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形成的生活模式是“液体化”了的,像所有的流体一样,这些模式并不能长久地保持其原有形态,相较而言,塑造其形态比保持其形状显得更容易些。蚕婆婆希望自家的血脉延续,反映了前现代社会的稳定性特征;大儿子努力从婚姻的稳定性中挣脱,在新鲜感的寻求中不断塑造自己的“新郎形象”,表现出现代性的流动特征。二者一经相遇,便产生出巨大的反差。
二、信任的变形
人的生存依赖于对所处环境的信任而产生的安全感,“脱域”和文化的断裂带来重新确立信任系统的问题。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环境的截然不同,必然带来信任关系的改变。蚕婆婆一直处在前现代社会的信任环境下,这种社会里,时空关系相对稳定和封闭,她所依赖的基础由亲缘关系、地域性社区、宗教、传统构成。亲缘关系是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依赖的普遍性纽带,蚕婆婆养蚕就像在养儿子。“这哪里是养蚕,这简直是坐月子。”[4]同时,她也是靠着养蚕养活儿子,维系起一种亲缘关系。再者,蚕婆婆希望给儿子带孩子,延续一种亲缘的关系,无奈被现代文化同化了的儿子已经将亲缘的记忆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地域性社区是为人所熟悉的一种环境,蚕婆婆对家乡话的渴望表现出她希望从陌生的环境回到熟悉的地域中,以重新获得如“合脚的旧皮鞋”一般的贴合感和舒适感。宗教宇宙观在伦理和时间方面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界的解释,是令信仰者感到安全的环境。蚕婆婆在二十九楼经历了孤独的时日后,她“终于决定到庙里烧几柱香”,和“死鬼”聊聊。宗教给予了她一个倾诉的出口,有助于焦虑感的排解和安全感的建立。在传统中,过去的时间会融入到现在的实践。“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2]92十几年来养蚕的习惯在蚕婆婆那里已经形成了传统,甚至已经成为了个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妈觉得要生病。妈不养蚕身上就有地方要生病。”[4]在养蚕的实践中,蚕婆婆可以深感安慰,完成本体性安全的建构。
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也依赖于信任,但信任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信任是在个人和具体对象的基础上产生的依赖态度,现代社会的信任建立在对系统和抽象对象的基础之上。“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抽象能力。”[2]23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脱域机制,这两种分别叫做“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的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象征标志即相互交流的媒介,货币符号是现代社会中象征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对货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信任分别建立在承认货币本身的价值和承认系统本身的运行上。大儿子有机地融合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组成的统一化、系统化的世界里,他信仰资本的超能力,认为富足的物质能让自己的母亲过上好日子,对来到城里的母亲的关心主要表现为提供足够的金钱,并试图使蚕婆婆尽快养成相信金钱的习惯。“养个好习惯,——记好了,只要一出家门,就得带钱。”蚕婆婆则是一脸懵懂,在两种信任体系的碰撞中不知所措。大儿子也享受于现代技术带来的快速、便捷的生活,他熟练地驾驶汽车,乘坐电梯,用全套高科技电器装饰自己的家。蚕婆婆却从生理到心理对现代产品有着排斥:“我一进城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运来运去的,总是停不下来。”[4]蚕婆婆朴实的真切的感受中,道出了现代人被控制、失去自我的异化状态,以及现代人的匆忙与躁动。蚕婆婆对于电器的遥控保持着警惕的态度,她不用音响设备听自己喜欢的越剧,甚至放弃了通过手机满足自己听家乡话的渴求的机会。旧的信任基础崩塌,新的信任基础还未建立,蚕婆婆在无边的空洞中对周围的环境缺乏安全感,进而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了焦虑。
三、无乡的惶惑
脱域之后产生的信任变形,就会使情绪转移到信任的对立状态——焦虑。人又有摆脱孤独、寻求安全感的本能愿望,所以有了“再嵌入”的渴求。“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2]69在无限延展的现代时空里,蚕婆婆手足无措,格格不入,感到深深的空洞与孤独,于是开始了对精神家园的回顾和再构。她有对亲缘关系的渴求:在悲伤的深夜追寻断桥镇的日子,那时劳碌而充实,单纯而温情的家庭记忆;跟儿子提出希望他结婚生子的愿望。也有对熟人社区的互动性向往:想让儿子跟自己说几句家乡话。还有寻求与逝去魂灵的交流,以及在二十九楼重操起养蚕的旧业,这时的蚕婆婆才仿佛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她恢复了生存的活力。“二十九层高楼上立即吹拂起一阵断桥镇的风,轻柔、圆润、濡湿,夹杂了柳絮、桑叶、水、蜜蜂和燕子窝的气味。”[4]理想中的家园走进了现实的生活,蚕婆婆在城市的浮沉中辟得了自己的栖息之地。
然而,再嵌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现代性的强力回击使得再嵌入的努力一一失败。大儿子婚姻破裂后也随之破裂掉了对亲缘关系的信任,蚕婆婆的亲缘嵌入失败。大儿子习惯于说普通话而拒绝母亲的请求,他试图用金钱来满足母亲,然而蚕婆婆拒绝接受手机通话。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过量的汽车造成的交通阻塞时常发生,也是一场堵车让蚕婆婆到庙里烧几柱香的愿望破灭。给蚕婆婆带来重生的蚕,也在即将上山之时,因蚕叶不足而未结成完整结实的茧,防盗门关闭的是通向明净、纯洁、富有生命力的理想家园的道路,里面禁锢的是一副副吐出了内在的躯壳。被同化了的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自觉困境的意识,所以毕飞宇选用一个从乡村进城的“他者”角度,来投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他对于人类生存的思考与追问:城市人(现代人)在堆积成山的工业产品带来的晕眩感之中,将体内残存的关于理想故乡(前现代社会)的记忆都吐了出来,成为一副空荡的躯壳,在现代社会里空洞又孤独地漂浮。那么今天,我们的生存意义又在何处?
四、结语
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个体,都经历过前现代向现代过渡之初的疏离感。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忘记了与蚕婆婆类似的不适感和对精神家园逐渐消亡的自觉和焦虑,而是不自觉地同大儿子一样沉溺在“美丽新世界”的幻象当中。毕飞宇敏锐地觉察到现代人“上得了天,下不了地”的漂浮处境和表面狂欢化、本质孤独化的存在状态,以清醒和警惕的态度、非强烈但坚韧的力量,阻止人的继续异化,复归人的人化。
[1]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毕飞宇.生活在天上[J].花城,1998(04).
(责任编辑 陈安丽)
苏枫,男,硕士,永城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及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