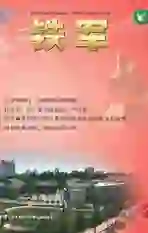铁血柔情
2017-03-24章熙建
章熙建
月黑风高的寒夜,茅山深处白雪皑皑,山路险峻,一阵突如天降的激烈枪声与杂乱吆喝打破了山野寂静。怀胎十月的新四军女战士阮方,身裹棉布大衣、肩负沉重背包,正艰难地行进在转移的队伍中。
这是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奉命向苏南转移途中,蓄谋已久的国民党军以7个师8万兵力悍然发起攻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猝然爆发。
就在罪恶枪声骤然爆响的一刻,阮方在茅山 险岩峭立的密林中,也陷入了命悬一线的绝境。“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的觊觎图谋已昭然若揭,新四军军部在制订作战方案时,考虑到兵站、医院和战地服务团等直属保障机构以知识分子和女战士居多,决定安排先行北撤。此时,阮方与新四军特务营教导员程业棠结婚刚满一年。
连续数日风雨兼程,北撤部队长途奔袭直入苏南茅山地区。刚刚攀上侧峰山腰,阮方蓦然感到腹中发生剧痛,踉跄奔走中又被一根匍匐于地的葛藤绊倒,使劲挣扎却怎么也爬不起身。眼看追兵的火把近在咫尺,她就势滚下草木葱郁的山坡。滚落间,阮方被一棵粗壮松树拦在半坡腰,而她也因后脑在树根上重重一磕而陷入昏厥。
剧痛中醒来时,阮方朦胧感觉自己正躺在一间昏暗的茅屋里。她不知道,夜色如魅,是战友们不顾敌人在山下点起长龙似的熊熊篝火,冒险摸黑找到她背到民兵队贾队长家。她更不知道,就在她遭遇险情的一刻,数百公里外的皖南泾县茂林,她的程教导员正率部在重兵围困中浴血搏杀。她只惶然地感觉一颗空悬的心冥冥中正向深渊坠去。
“哇……”一串清脆的啼哭倏然撕破冷寂夜幕,也唤醒了再度昏迷的阮方。一种生命本能的渴望,让阮方强撑着睁开眼,依稀闪入眼帘的,是饱经风霜的瘦削脸庞和布单包裹的粉红小脸,还有一个慈祥的声音:“妹子,是个漂亮男娃哩!”那一霎,一种陌生而久候的幸福感电流般贯穿全身,她只饱含感激地喊了声“大姐”便泪如雨下。
生子之险无疑惊心动魄,托孤之殇更是撕心裂肺。追兵在即,险厄相随,容不得半点儿女情长,探好路径的游击队员们必须赶在破晓前引导部队跳出包围圈。把尚未喝上一口母乳的孩子递给大姐的一刻,阮方足底如灌重铅,眼噙热泪一步三回首,最终一咬牙消失在夜幕笼罩的莽莽林海中。此后的漫漫8年间,无论激战山野抑或宿营丛林,只要一闭上眼睛,阮方脑海中就赫然浮现怀抱孩子倚靠柴扉的大姐,还有那缕寒风中飘忽的枯发。那真正是一种真情与生命的托付呵!
时光荏苒,1949年隆冬的晌午,一辆军用吉普沿着蜿蜒山道驶入茅山密林深处。开国将军程业棠携妻子阮方,在县乡领导的帮助下,四方打听一路寻找,终于叩开了贾大姐的茅屋木门。许是那份担忧在心底盘桓太久,贾大姐只是稍显吃惊,瞬間便认出了戎装一身的女军人——“你是新四军妹子?”那一刻,纵是久经战火熏染洗炼,悲怆盈胸的阮方也禁不住潸然泪下:伫立跟前的贾大姐尚不满50岁,可已过早地满头银发、身腰佝偻。一个俊俏的男孩拽着衣襟躲在她身后,扑闪明净的双眸打量陌生来人。直到贾大姐拽他到身前教他喊人,孩子才怯怯地学叫一声:“新四军叔叔!新四军阿姨!”
尽管途中与程业棠反复斟酌商议,商定见面时不露声色,视情确定认领与放弃两种选择。但那一瞬,阮方终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一把将孩子紧紧搂进怀里。
披着冬日午后慵倦的阳光,当年曾参加掩护行动的民兵营长按照阮方的叙述,带将军夫妇俩翻山越岭,找到数里之外那个夺命斜坡。伫立山腰的一刻,饶是已然时逾8年,阮方仍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株拦腰救命的千年苍松,竟是那般遒劲伟岸地矗立青山白云间,粗壮的树干需数人牵手才能围拢,葱翠华冠如同巨伞遮蔽着半壁山坡。松树下坡不足20米即是断崖,对面的峰峦壁立千仞,两峰间弥漫的氤氲衬托出幽谷深壑的阴森诡谲。难怪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夜,国民党追兵信心满满地在谷底燃火布阵,倘若没有游击队引导,纵使天兵神将也插翅难逃。
而更令阮方心生颤栗的,却是民兵营长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个秘密。阮方和战友从隐密栈道转移脱险后不到两个时辰,攀上主峰的追兵便封锁所有山道,逮捕了完成护送任务返回茅屋的贾队长。刚满19岁就担当起抗日救国重任的山民儿子,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半句实情,最终牺牲于敌军恼羞成怒的乱枪扫射。凶残的敌军仍然嗅到有个新四军女战士在茅屋产下婴儿的信息,多次派兵进山搜寻,并放火烧了茅屋,而坚强的大姐早已背着孩子躲进了深山老林。整整8年时间的餐风露宿、含辛茹苦,素昧平生的大姐咽下失子之痛,以超逾亲情的母爱默默呵护新四军战士的血脉!
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尽管自带了行军被褥,但下榻茅屋东厢房的将军夫妇,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环顾战后乡亲们自发相助重盖的简陋房舍,夫妻俩内心五味杂陈,这趟茅山之旅遭遇的心灵震撼,丝毫不逊于战争岁月腥风血雨的冲击。那声“新四军叔叔、新四军阿姨!”的稚嫩呼喊,唤起了铁血将军内心难以言状的酸楚,于阮方更有剜心一般的疼。而伴随痛楚的是一份深沉的感动,漫长而多舛的时光流逝,带给善良农妇很多改变和流失,但她心底仍然清晰鲜亮地珍藏着那个美丽的称谓;她甚至不知道那支舍身救国的队伍已改编为解放军,却以良知和爱心无怨无悔地坚守着一份承诺。
翌日清晨,将军夫妇悄然起床驱车下山。这一夜他们心照不宣地做出了决定,而西厢房的油灯也直亮到天明。同样是晌午时分,他们再次来到山腰茅舍,不同的是,大姐正牵着男孩伫立屋前枫树下。孩子面容洁净、衣着光鲜,棉袄外套还残留着簇新的线头,似乎是连夜缝制的,而大姐则双眼满布血丝,眉宇间显然新添了一丝恍惚和悲戚。将军夫妇见状对视无语,他们从车上搬下新买的棉被、衣物,还有红糖、菜油等食品,默默地搁在茅屋的杉木桌上,未了留下一个装有当月工资的信封,但未留只言片语。做完这一切,阮方蹲下身一把搂紧孩子,脸贴着脸良久不动,直到将军轻咳一声,这才猛然松手掩面奔向吉普车。那一刻,面色凝重的将军抬手向大姐庄重地敬了个军礼。
吉普车扬尘而去,瞬间消失于绿荫间。一阵山风掠过,山腰茅屋又恢复了宁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只是懵懂的男孩抬起头,蓦然发现娘亲脸上正滚落两行清泪。
阮方,上海人。1938年春,初中毕业尚不满17岁的阮方,怀揣抗日救亡的热忱奔赴延安,经培训被派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担任文化干事。不久即动员弟弟、妹妹参加新四军,弟弟成长为骁勇善战的营长牺牲于抗日前线,妹妹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职于南京军事学院。1986年,开国将军程业棠在上海病逝。将军逝世10周年纪念日,阮方深情端详战友夫君的相片,四目相对的霎那倏然有种被电击的感觉。或许就是这一刻,将军生命中始终不能释怀的一份牵挂,与她心底长久淤积的一个情结相重叠,于此,阮方瞒着孩子开始着手撰写将军的回忆录。一年后的7月6日,病榻上的阮方,在深情注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程业棠将军回忆录》中,面露欣慰追随将军而去。
将军夫妇一生共生育8个子女。如今65岁的长女程胜利曾撰文回忆,若不是母亲出版的回忆录,他们兴许永远不知道还有一个身世跌宕凄婉的哥哥。只是父母生前于此始终守口如瓶,待到他们得知真相时,一切都已铸成了永远的谜!
清音一曲意在弦。将军夫妇于山腰茅屋的最后惜别,以及那一连串颇具蹊跷的举动,其实蕴寓着一份决绝的割舍,且决意不留痕迹、再无牵扯。可以想象,那个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时刻,将军夫妇的情感始终被理性牵引着,纵是亲情骨血,然生于大山须归于大山,受惠人民必反哺人民。自茅山返回,对于生子之险、托子之殇,及寻子之艰、别子之痛,将军夫妇一生始终讳莫如深。其实不难读解,穿越弹雨硝烟、经历生难死别的铁血军人,对于血缘与血脉的认知,无疑已进入一种淡泊空灵的境界,因而甘愿以自身承载牺牲与痛苦,遵从一份生命的自然与宁静。
我们或许无缘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不能忘却苦难辉煌中的那些细节:怀有热烈赤诚的爱,却无法拥有稳定的家园;有了颠沛漂泊的家,却难以使之维系于一份完整的温馨。弹片飞溅割裂亲情,弹雨飞流支离血脉,而鲜艳并恒久地绽放其中的,就是铁血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