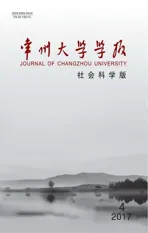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考述
2017-03-23赵延旭
赵延旭
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考述
赵延旭
北朝时期颁布了一系列的生态保护诏令,主要涵盖了林木资源保护与动物资源保护两个方面。禁伐树木、森林防火、节约用材以及鼓励植树等诏令的颁发,客观上保护了这一时期的林木资源。与此同时,禁止猎杀、捕贡和畜养动物等诏令,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保护动物资源的作用。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虽具有不稳定性,颁行的主观目的亦在于维护政治安定,而且属于以义务为本位的律法,但其无疑为当时生态保护立法的主要形式,对于北朝时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对后世生态保护律法的颁行亦影响深远。
北朝;林木资源;动物资源;保护;诏令
自古以来,生态环境便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生态保护诏令作为国家政令的主要内容,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体现政权对于生态环境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此时生态状况的集中反映。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摩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集结者是也。”[1]北朝时期各项制度多承自汉魏,转而为隋唐所沿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生态保护诏令亦不例外,因此,梳理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有助于深化此时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理清汉唐时期生态保护的历史脉络。
长期以来,前辈学者关于生态史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夏明方等著《生态史研究》、尹伟伦等著《中国林业与生态史研究》、赵杏根所著《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史》等均对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宏观的阐述,王子今所著《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张显运所著《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则对秦汉及宋代的生态环境予以分析和研究,然而,针对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成果寥寥,笔者在此仅以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为对象,对其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保护林木资源的诏令
森林植被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林木亦为农业社会主要的经济来源,故而历代政权多有保护林木、植树造林之举,如汉文帝“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2]124,汉景帝亦“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2]152。拓跋鲜卑为草原部族,其生存与延续本就与森林草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孝文帝时期推行汉化改革,效仿圣贤君主,因而此后颁布了诸多保护林木资源的诏令。北朝时期,保护林木资源的诏令主要涵盖了禁伐林木、森林防火、节约用材以及鼓励植树等方面。
北朝时期严禁砍伐帝陵附近地区的林木。《魏书·孝文帝纪(下)》有载:“又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踏。”[3]179孝明帝时,由于“古帝诸陵,多见践籍”[3]224,又“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3]224,以此保护陵园地区的林木,此举为后世王朝继承和借鉴。《唐律疏议·贼盗》载:“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4]302与此同时,军事行动亦不得随意破坏树木。《魏书·道武帝纪》载:“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3]28《周书·武帝纪下》亦载:“(建德四年,575年)八月癸卯,入于齐境。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5]93违反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对于“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3]186,即便战争之中必须采伐树木时,也需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足见北朝时期对于林木保护的重视。
《管子·立政》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火是森林植被存在的巨大威胁,因此,“修火宪,敬山泽”,历代政权都将森林禁火视为国策。《周礼·夏官司马》载:“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公认为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火灾刑罚条文”[6]。1975年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田律》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可见秦朝对于山野行火也是严格限制。及至北朝时期,亦极为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九年,558年)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7]64将行火燎野的时间严格限制在冬季一月,从而有效降低了山林火灾爆发的机率,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林木资源的效果。
《淮南子·说山训》曰:“上求材,臣残木。”规模宏大的土木建筑也是材木损耗的重要原因,故而北朝帝王多有罢停建设以节省用材之诏。《魏书·孝文帝纪(下)》载:“(太和十一年,487年)冬十月辛未,诏罢起部无益之作。”[3]162此后,宣武帝“以戎旅大兴,诏罢诸作”[3]201,孝明帝时亦诏“土木作役,权皆休罢”[3]224。至北周武帝,又诏曰:“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彻。缮造之宜,务从卑朴。”[5]103此外,这一时期对于各级官吏的工程兴造也进行了限制,“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3]233。北朝时期对于皇室及官僚大兴土木行为的罢停与管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对用材的限制,有保护林木的效果”[8]。
除上文所述对于原有林木资源的保护外,北朝时期还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栽植各类树木的诏令。
首先为经济林的栽植。早于延兴二年(472年),孝文帝就曾下诏“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3]137,要求各州郡长官督课所辖百姓栽植蔬菜、果木。此后,孝文帝又于太和九年(485年)“下诏均给天下之田”[3]2853,其中对于栽植树木的桑田也做了具体的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3]2854均田令中明确要求在桑田之内必须栽植桑树、枣树、榆树三类经济林木,这主要是由于桑叶可以饲蚕,枣实能够佐食,榆树可供材用,对于维持百姓正常生活的意义重大。同时,均田令对经济林木的栽植数量也进行了限定:对于限期内不能完成植树任务的百姓,国家将收回已授予的土地;而对于能够完成植树任务的百姓,桑田便可成为百姓“身终不还”、世代经营的世业田。自此之后,均田令为北朝历代所承继,《隋书·食货志》载齐河清三年(565年)诏曰:“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9]均田制的颁行使栽植经济林木成为百姓的法定义务,从而调动了农民经营林木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北朝时期还多次诏命州郡牧守劝课农桑。正如《魏书·太武帝纪(下)》所载:“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听妄有征发。”[3]96《魏书·孝文帝纪(上)》载:“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3]143对于惰于农桑的百姓,严令加以惩处。《北齐书·文宣帝纪》亦载:“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7]53其中,劝勉百姓积极种植树木便是劝课农桑最为重要的内容,所以说,此时劝课农桑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林木的栽植,对于扩大农耕区域的人工经济林培育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为行道树的栽植。《国语·周语》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我国栽植行道树的传统可追溯至周朝。此后,路旁栽植林木的传统为历代王朝所承袭。《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2]1102可见其时行道树的栽植范围广泛、规模宏大。又《晋书·苻坚载记(上)》所载:“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10]由此可见,松、槐、柳等行道树的栽植成为盛世王朝的重要标志,故而历代王朝多有鼓励栽植行道树之诏。
北朝时期,对于行道树的栽植亦极为重视。《周书·韦孝宽传》载:“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见后,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5]538北朝时期通过颁发诏令,提倡各地种植行道树,并对栽植密度进行规定,自此栽植行道树的风气盛行一时,史载洛阳城内“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11]161,永宁寺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奔云之润;清风送凉,岂籍合欢之发”[11]4。行道树的栽植无疑起到了保路护路、美化环境的效用。
再次为墓树与庆功树的栽植。据《白虎通·崩薨》转引春秋《含文嘉》载:“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可见坟墓附近地区栽植林木的习俗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形成了依据身份贵贱和地位高低确定栽植树种的制度,北朝时期则继续沿袭了栽植墓树的习俗。《魏书·孝文帝纪(下)》载:“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3]177孝文帝就曾下诏于孔子墓园之中栽植柏树,修饰坟茔,以示尊贤之意。与此同时,北朝时期亦提倡庆功树的栽植。史载沙苑之战后,周文帝“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5]24。伴随墓树与庆功树栽植诏令的颁发,北朝时期的植树之风逐渐形成,如甄琛“于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3]607,樊逊“性至孝,丧父,负土成坟,植柏方数十亩,朝夕号慕”[7]1524。此时的墓志铭中亦多有“丘陇寂漠,松槚成行”[12]263“楸梧春绿,松栝冬青”[12]444之语,墓树与庆功树栽植之风盛行,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意义亦不容忽视。
二、保护动物资源的诏令
动物资源是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而射猎则是拓跋鲜卑早期重要的社会活动,正如《魏书·序纪》所载之拓跋先民:“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3]1频繁的射猎活动极大破坏了此时的动物资源,因此,随着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逐渐深入,拓跋君主骁勇喜武的风气渐息,孝文帝后保护动物资源的诏令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对于动物资源的保护主要通过禁止猎杀、捕贡及畜养动物等诏令的颁发得以实现。
(一)禁止猎杀动物
北朝建立伊始,受原始渔猎生活习俗的影响,诸帝射猎活动极为频繁。《魏书·道武帝纪》载:“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3]41明元帝“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3。太武帝“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还”[3]75。足见其时帝王的校猎范围之广,活动之频繁,杀伐之众,对于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至文成帝时,由于“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3]121,故而诏令“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赉”[3]121。自此以后,北朝帝王的射猎活动逐渐减少,孝文帝“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3]187。帝王射猎活动的减少甚至停罢,有效遏制了这一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捕杀。
除此之外,北朝时期日常生活中对于禽畜等动物也采取了保护措施。《魏书·孝文帝纪(上)》载:“(延兴五年,475年)六月庚午,禁杀牛马。”[3]141宣武帝“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3]209,孝明帝又“重申杀牛之禁”[3]224,齐文宣帝“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7]63,武成帝“诏断屠杀以顺春令”[7]90,周武帝时亦“禁屠宰”[5]66。北朝时期减少游猎活动以及禁止屠杀禽畜等诏令的颁发,客观上均起到了保护动物资源的效果。
(二)禁止捕贡动物
《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其中,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可见早在夏朝之时,野生动物便成为地方向中央贡献的方物之一。此后,历代政权统治期间,地方均需向朝廷定期贡献其特产的野生动物。北朝时期,各地州郡及邻国的贡献之物中亦不乏珍贵的野生动物。《魏书·文成帝纪》载:“库莫奚国献名马,有一角,状如麟”[3]113,“居常王献驯象三”[3]119,“破洛那国献汗血马”[3]123。《魏书·孝文帝纪》载:“(延兴五年,475年)五月丁酉,契丹、库莫奚国各遣使献名马。”[3]141频繁捕贡对于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年)八月“诏罢诸州禽兽之贡”[3]146,停止各州向中央贡献野生动物。太和六年(482年)三月行幸华林园虎圈时又诏:“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3]151北魏时期诏令禁止地方向朝廷进献各类珍禽异兽,从而间接地减少了各地对于野生动物的捕杀,对于此时动物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三)禁止畜养动物
除上文所述禁止时人猎杀动物、地方捕贡动物外,北朝时期亦严禁皇宫内外畜养鹰鹞等猛禽。《魏书·孝文帝纪(上)》载:“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3]141明令禁止畜养鹰鹞,并提倡相互检举揭发。其后,又“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3]148,试图以此根除宫廷内部畜养鹰鹞之习。此后,帝王禁止畜养鹰鹞的诏令多有颁行。孝静帝时期诏令“后园鹰犬,悉皆放弃”[3]305,齐文宣帝时期亦“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7]63,齐后主时“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7]102。与此同时,北朝时期还诏令将圈养于苑囿之中的野兽放归山林。《魏书·孝明帝纪》载:“(熙平元年,516年)庚午,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3]224魏前废帝时亦诏:“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11]162至周武帝“宕昌遣使献生猛兽二,诏放之南山”[5]68。北朝时期禁止畜养并放还野生动物的诏令,对动物资源无疑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三、生态保护诏令的特点
通过上文对于北朝时期林木资源和动物资源相关诏令的梳理,不难发现,此时生态保护诏令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其一,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具有不稳定性。北朝起自公元386年魏朝建立,终于公元581年周朝禅代于隋,历时近200年。其间政权更替频繁,战乱纷争不断,动荡的政局必然导致政令的相对不稳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政权统治时期,除均田令外,其他生态保护诏令无不时设时废,难以连续、有效地执行。即便同一帝王在不同的执政时期,其对于林木资源和动物资源的保护态度也不尽一致。如上文所述,历代帝王多有罢停工程以节省材木之诏,但这些诏令却收效甚微。北朝实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繁荣时期,帝王、宗室、官僚多热衷于营造园林,与之相应,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寺院园林数量众多且规模宏大。以宣武帝为例,尽管早期曾“以戎旅大兴,诏罢诸作”[3]201,但其在洛阳城内便营造了瑶光、景明、永明三座寺院,其中瑶光寺“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11]46,景明寺“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11]132,永明寺亦“房庑连亘,一千余间”[11]235,修造规模如此宏大的寺院,耗材数量必然不在少数。又如禁止捕贡动物,孝文帝时已“诏罢诸州禽兽之贡”[3]146,即停罢各州向宫廷进献野生动物,而孝庄帝时又“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11]161,下令临近山地的郡县抓捕猛虎送往华林园以供赏玩,至此,孝文帝禁止捕贡动物的诏令也成为一纸具文。北魏宣武帝的大兴土木,以及孝文帝、孝庄帝对于捕贡野生动物先后发布的截然不同的诏令,足证此时生态保护诏令的不稳定性。
其二,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以维护政治安定为目的。“维护专制王权是我国古代森林资源保护立法一脉相承、经世不变的宏观价值取向。”[13]涵盖了林木资源、动物资源的生态保护立法亦不例外。尽管北朝时期颁发了一系列生态保护诏令,但此时的统治者对于林木与动物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无深刻的认识,北朝帝王颁发诏令的主观目的往往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如战争之中严禁采伐百姓树木的诏令,多颁行于王朝建立伊始或领土扩张之时,其目的在于安抚百姓、邀买民心。而均田令与劝课农桑等诏令的发布则旨在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又如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帝以旱故,减膳彻悬,禁断屠杀”[3]208,齐武成帝河清元年(562年)“诏断屠杀以顺春令”[7]90,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亦“禁屠宰,旱故也”[5]66,可见其时禁止屠杀也是统治者因迫于形势所采取的缓解旱情、顺应时令的应急措施。至于鼓励栽植庆功树以及禁止捕贡、畜养动物等诏令,则不失为帝王提高其政治威望的有效手段。尽管如此,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保护林木资源与动物资源的效果。
其三,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属义务本位的律法。所谓义务本位,即以义务为法律的中心,法律内容主要为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目的在于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设定不同的义务,以维护身份秩序。中国古代“对环境及资源的保护不是以保护社会成员的环境权利为内容”[14],综观此时的生态保护诏令,“主要以禁令的形式予以颁发,是对人的行为的某些消极性的评价或限制”[13]。如上文所述,北朝时期的生态保护诏令具体表现为禁止在帝王陵墓附近地区采伐林木和耕种土地、禁止于规定时间外行火燎野、禁止大兴土木耗费材木,禁止畜养鹰鹞等猛禽,农民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植树任务,则要收回被授予的土地,对于不能勤劳农桑者,也要受到严格的惩罚,等等,可见这些诏令无一体现社会成员的权利,均为对社会成员禁令或义务的要求。可以说,“诏令是我国古代森林资源保护立法的主要形式,鲜明地体现了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1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北朝时期颁布了诸多生态保护诏令,主要涵盖了林木资源保护与动物资源保护两个方面。此时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发,主要集中于孝文帝时期,这与当时推行的汉化改革不无关系,此后历代帝王承袭效仿,逐渐形成了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体系。这一时期,对于林木资源的保护主要涵盖了禁伐林木、森林防火、节约用材以及鼓励栽植经济林、行道树、墓树与庆功树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动物资源的保护则主要表现为禁止猎杀、捕贡以及畜养动物等诏令的颁行。北朝时期,无论林木资源抑或动物资源的保护诏令多具有不稳定性,其颁行的主观目的在于安抚百姓、发展经济、提高威望以巩固自身统治,此时的生态保护诏令属于义务本位的律法。
然而,由于北朝正律之中鲜见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处于“法自君出”“言出法随”的专制社会,帝王诏令自然成为此时生态保护立法的主要形式。同时,禁伐林木、森林防火以及鼓励植树等生态保护诏令也对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生态保护法律日益健全和规范。《唐律疏议·杂律》载:“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4]433可见唐代林木保护与森林防火的相关律法即为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的继承和补充,北朝时期生态保护诏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法规的重要意义不可小觑。
[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4.
[2]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岳纯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6]聂焱如.我国古代防火及火灾刑罚[J].现代职业安全,2009(3):71-73.
[7]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8]陶泳,刘锡涛.唐代林业职官和护林诏令及造林活动[J].中国城市林业,2011,9(4):45-47.
[9]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77.
[1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1102.
[11]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3]赵美珍,邓慧明.我国古代森林资源保护立法之考量[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2(2):48-51.
[14]张梓太.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意识浅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35(4):155-160.
A Discussion about Edic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Zhao Yanxu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 series of edic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were promulgated, mainly concerning forest vegetation and animal resources protection. By promulgating edicts of prohibiting logging, preventing forest fire, saving timber and encouraging trees planting, objectively forest vegetation were protected. At the same time, edicts of prohibiting hunting, prohibiting tributes and keeping animals also protected animal resources. Although edic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ere unstable, the subjective purpose was to safeguard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they belonged to the law of obligation, these edicts were still the main form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promulg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 Northern Dynasties; forest resources; animal resources; protection; edicts
赵延旭,历史学博士,河北工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
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研究”(SQ161113)。
K239.2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4.013
2017-05-16;责任编辑: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