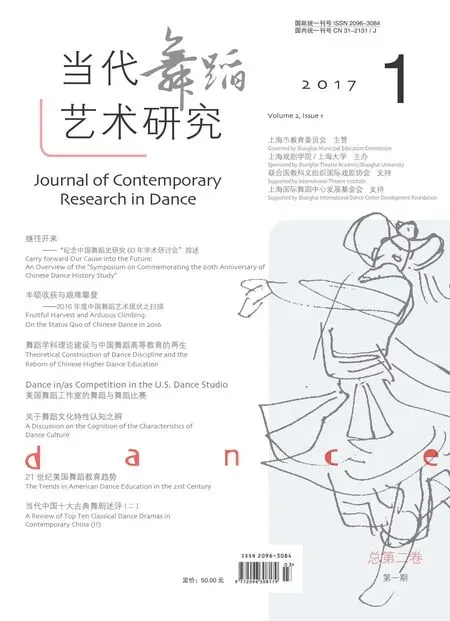扬本性 去同质 显个性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获奖作品点评
2017-03-23张麟
张 麟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于2016年12月9日落下帷幕。作为中国舞蹈界舞剧·舞蹈诗创作方面的最高评奖活动之一,此次比赛集中对近几年出现的舞剧作品进行了评选,从近60多部舞剧中选出了五部进入决赛的作品,分别是《杜甫》《仓央嘉措》《家》《哈姆雷特》和《朱》。总体来说,这五部舞剧在编舞、制作等方面都趋于精良,由此可见整体舞剧舞蹈诗创作的质量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五部作品的创作都在某些方面试图解决舞剧创作中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也暴露出舞剧艺术创作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
一、舞剧的本体叙事层面的得与失
真正意义上的舞剧叙事是受制于舞蹈艺术的本体特征的。作为一门用肢体语言传情的艺术,在对客观世界的反应手段和方式上与语言小说等截然不同的,也和戏剧截然不同。因此,客观上要有叙事身份转变和叙事时空转变,舞剧导演要对故事文本或文学台本原本的时空进行处理,从而构建出舞台特有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方面,笔者认为舞剧《杜甫》和《哈姆雷特》做了比较好的探索。这两部以塑造人物形象为目的的舞剧,暂不论其舞剧形象是否塑造成功,仅从结构层面来分析,这两部舞剧都在努力实现着舞剧艺术的本体叙事结构。《杜甫》在主体结构上运用了双重时空共呈的结构手段,把身居残酷现实中的杜甫和心怀家国美好志向的杜甫同时呈现了出来,通过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来铺陈舞剧结构,自然地实现了时空上的切换。这种结构方式本身已经形成了编导主体叙事的语言,在舞剧第一幕中时空突转,从步入仕途直接切到苍生现实,对比强烈!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车轮的辗转,为官十年,那个满怀功名抱负的杜甫已经渐渐远去,留下一个心系苍生百姓、直面黑暗社会的杜甫。剧中两个杜甫的设计也是作品在原文本结构上的进一步开掘,意在表达杜甫内心的焦灼与现实的激烈碰撞。第二幕是家国罹难的场景,时空转换,现实与回忆共呈,再次给开掘人物内心、塑造人物形象留足了抒写的空间。
舞剧《哈姆雷特》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演绎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经典,用舞蹈艺术的魅力揭示了人性,较好地用舞蹈艺术自身的特点来刻画人物;舞段设计合理细致,与情节结构很好地融合。舞剧以人物心理发展为线索,打破了时空的顺时结构,自由而紧凑;通过这样的结构,编导试图去刻画一个内心煎熬、备受命运驱使和人性拷问的悲剧人物。舞剧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作品的特定时空——处于挣扎在生存还是死亡、虐杀还是逃离漩涡中的哈姆雷特,在这个限定的当下时空中,结合主人公内心的挣扎,时空自然而然地晕染开来,舞剧编导在主体表现意识的指导下,对莎士比亚戏剧原作中的事件重新加以使用,这些事件既属于原作中的故事,也服务于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塑造。除此之外,舞剧用舞美重塑了舞台,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舞蹈空间,这个空间具有双重意味,一是代表着哈姆雷特的心之窟,那是一处心牢,紧紧地锁住了哈姆雷特,让他纠结、压抑、愤懑、生不如死;二是代表着弥漫着屠杀、欺骗与伪善的皇宫。具有象征意味的舞美设计也作为一种语言、一种有效的手段,参与了叙事。
相比上述两部作品,笔者认为舞剧《仓央嘉措》和《家》在结构层面就显得有些不足。《仓央嘉措》采用倒叙的方式,展现了仓央嘉措追求自由、冲破世俗与枷锁的不平凡的人生。作品出现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在叙述上的转换,开始的序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当下的时空拉回到过去,再现了仓央嘉措幸福的少年时光。但结构上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转化和衔接没有处理好,尤其是现实环境下残酷压抑的空间和想象中自由空间的对比没有做足,因此使得仓央嘉措的形象还不够突出。也正是由于结构问题,导致该剧到了第四幕时还以交待仓央嘉措的经历纵贯整部作品,从而有种用舞蹈描述仓央嘉措生平的感觉。舞蹈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舞剧在叙述层面必须通过时空的处理来构成潜在的语言,这些语言既是对文本文字语言的补充和解释,又是舞蹈自身言说的特殊方式。二重空间的构造恰恰构成了舞剧的潜台词、人物内心的潜台词。笔者认为这恰恰就是舞剧本体叙事层面可以大加利用的地方。在此次舞剧、舞蹈诗比赛期间举行的创作论坛中,著名舞蹈编导高成明认为:目前舞剧创作缺少创新,二重空间的使用等已经不足为奇,应该加强舞剧艺术的表现手段。笔者认为,二重空间的使用在中国舞剧创作的发展历程中不是首创,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舞剧中,这种结构方式就已经出现。但是“出现”并不意味着认同,“出现”也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构方式已经成为舞剧本体叙事手段的一个特征,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大部分的舞剧创作至今在结构层面依然难以找到舞剧艺术本性的结构方式,依然被文学牵着鼻子走。由此,笔者认为时空结构的艺术手段不应被视为是否创新的关注点,而应该视为舞剧本体叙事特征和手段的一个基本要素。作为基本要素,那就不是新旧的问题,而是编导是否真正有能力来驾驭和使用的问题。
二、人物形象塑造的成与败
此次决赛展演的五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与“形象”相关。笔者认为,对塑造人物形象的舞剧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构思与呈现的问题;而人物构思方面又主要是对所要刻画人物的深刻剖析,找到人物最典型、最核心、最内在的本质特征。那么,特定人物的这一本质特征又是如何通过舞蹈语言来呈现的呢?笔者认为就是在环境中塑造人,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中展现人。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结构方式来凸现环境与人的冲突、通过舞蹈段落的组合来展示冲突中人物的内心、通过环境的渲染来深化或升华人物的形象。
从这个层面着眼,笔者认为舞剧《哈姆雷特》是相对成功的,编导始终在哈姆雷特与周遭不同的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来塑造哈姆雷特。这些不同的人物不仅仅作为事件出现,更是作为代表与人物内心情感相对应的一种环境要素而出现。《哈姆雷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有不足,主要体现在每次人物回到当下现实既定时空时,端坐在凳子上后的肢体语言与舞台中后区过去时空中正在演进的故事场景缺少关联。另外,重点突出人物内心情感起承转合的独舞舞段,在情感张力和动作层次方面不够细致。
就舞剧《家》而言,笔者认为原作中有巴金先生的变现意图,这个意图并不在于塑造几个人物形象,而是透过这些不同个性的人物来反映一个社会现实。基于此,那么舞剧《家》的导演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目的一定是和导演的叙事结构和视角密不可分的。该剧编导在对群体形象的处理上过于谨慎,在觉新、鸣凤、瑞珏等人物的选择上视角欠缺、主次不明,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缘于该剧的结构层面缺少了编导自己的视角。编导在塑造不同的人物个性层面上恰恰缺少了“人物之间对比关系”的艺术手段,尤其是没有设置同一个特定环境中不同人物的行动与内心展现层面的共时呈现。尽管该剧中舞段丰富多变,但从情感和形象角度来评判的话似乎都还不够火候。
舞剧《仓央嘉措》在人物塑造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舞蹈编排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则是十分动人的。编导巧妙地用袈裟作为道具,仓央嘉措所有的情感的波澜起伏和生活际遇都在演员的肢体动作与袈裟颇具象征意味的配合中呈现出来,加之饰演仓央嘉措的演员从身心层面的完美状态,都为这个人物的塑造增添光芒。而如果是从剧本角度来考虑,笔者认为这个人物略显单薄,除了人们对于仓央嘉措已知的生平和动人的情诗以外,在对其多维深度开掘上有所欠缺。著名的舞蹈理论家刘青弋教授在看完该剧后认为:“从创作者意在表现主人翁是人不是神,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对黑暗势力之于人性的压抑进行勇敢地反抗角度,舞剧具有特定的积极意义和艺术价值;成年仓央嘉措的扮演者的表演亦可圈可点;但是从对一个藏族宗教领袖人物的塑造角度来说,这样的表现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仓央嘉措这个谜一样的历史人物究竟如何解读?他作为藏族宗教领袖和天下苍生百姓命运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的情诗是否只是解读为个人的儿女情长?……”刘青弋教授的看法亦从某种角度说明了舞剧在深入开掘人物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方面有待加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在此次展演论坛中指出:“敢于塑造人物这是中国舞剧发展的一个进步。但是问题也很多,很多舞剧人物形象其实是不成立的、模糊的,换一套衣服、换一个音乐似乎也可以成为其他的人物。如何塑造出‘那一个’,塑造出鲜活的、特定的、个性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确实还需要各位舞蹈界同仁继续努力探索。”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 ”获奖作品WINNER OF “THE 10TH ‘LOTUS AWARDS’ CHINA NATIONAL DANCE COMPETITION” DANCE DRAMA AND DANCE POETRY AWARDS
导演:佟睿睿
编剧:罗怀臻
作曲:郭思达
编舞:何滔、佟睿睿
主演:朱洁静、王佳俊
制作演出单位:上海歌舞团
摄影:沈建中
DANCE DRAMACRESTED IBISES
DIRECTOR: TONG RUI-RUI
SCENARIO: LUO HUAI-ZHEN
ORIGINAL MUSIC: GUO SI-DA
CHOREOGRAPHERS: HE TAO & TONG RUI-RUI
PRINCIPAL DANCERS: ZHU JIE-JING & WANG JIA-JUN
PRODUCTION & PRESENTATION: SHANGHAI DANCE THEATRE
PHOTO BY SHEN JIAN-ZHONG

“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获奖作品Winner of “The 10th ‘Lotus Awards’ China National Dance Competition” Dance Drama and Dance Poetry Awards
舞剧《哈姆雷特》
编导:德里克-迪恩
主演:吴虎生、范晓枫、戚冰雪
制作演出单位:上海芭蕾舞团、上海大剧院
摄影:沈建中
DANCE DRAMAHAMLET
CHOREOGRAPHER: DEREK DEANE
PRINCIPAL DANCERS: WU HU-SHENG, FAN XIAO-FENG AND QI BING-XUE
PRODUCTION & PRESENTATION: SHANGHAI BALLET & SHANGHAI GRAND THEATER
PHOTO BY SHEN JIAN-ZHONG
展演间隙,笔者采访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罗斌副主席提到当前中国舞剧创作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他指出在此次参加展演初评的剧目中也非常突出地暴露出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最终进入决赛展演的五个剧目没有出现“同质化”,但在具体舞蹈语言的编排上同样也显现出类似的问题。例如“双人舞”的编排与人物和情感脱节,更多是身体技术层面的呈现,又如独舞的编排也和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特定心理情感脱节,体现出的依然是演员自己的身体技巧和动作特质。舞蹈语言在动作质感层面都比较中性,缺少与舞剧的“剧”相吻合的独特的空间形式、力量变化、衔接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