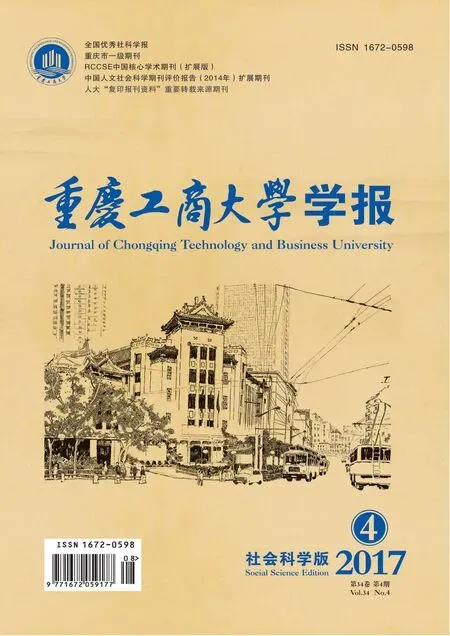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2017-03-22林移刚
林移刚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学系,重庆 400031)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林移刚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学系,重庆 400031)
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发展促成了祠庙、会馆等信仰中心的大量兴建和兴盛;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神、水神、财神等神灵被大量崇祀;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尤为兴盛。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清代地方经济。祠庙、会馆的兴建促进场镇的形成和繁荣;不断积累的祠庙经济日益成为地方经济体系的重要补充;异常突出和活跃的庙会、迎神赛会对于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开发格局也同样是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民间信仰;地方经济;民俗
民间信仰是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普遍性的、与制度性宗教及民间宗教相区别的、以神灵信仰为核心的准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形式及程度往往决定民间信仰的种类、更替与兴衰。民间信仰的传播和兴盛也会对经济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此,郭伟平[1]、黄洁琼[2]、王健[3]等学者都有相应研究成果。在清初注入式的移民运动的背景下,四川民间信仰的主体和内容发生重要变化,四川经济经历了从衰败、复苏到繁荣的过程。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形成以及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但是,学界对于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关注较少。本文通过对清代四川社会祠庙设置、神灵供奉以及迎神赛会等民间信仰的具体表现和活动场域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经济发展进程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解四川区域文化的建构过程提供新的视角。
一、地方经济对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民间信仰等意识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四川民间信仰体系的重建和兴盛是在区域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之后出现的。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信仰提供了物质方面的保障,使信仰主体从数量到生活质量方面都有质的飞跃。清代四川经济发展对民间信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促成信仰中心的兴盛及转型
祠庙是民间信仰的展示中心,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的互动许多都是通过祠庙实现的。祠庙的兴建与兴衰、神灵的供奉及变化等都与地方经济息息相关。随着清初经济的复苏,四川经济慢慢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雍正、乾隆之后进入了繁荣时期。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商业重新繁荣起来,出现了“商贾辐辏,街道肩摩,百货骈集”[5]卷2《风俗》的景象。地区之间的商业流通异常活跃,《成都竹枝词》描绘了川西经济中心——成都的商业枢纽地位:“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油,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6]87伴随着经济交流的活跃,场镇数量迅速增长。清末,成都所辖成都、华阳两县场镇居然有近50个,[7]541-542令人咋舌。这些场镇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交通线上,“居民懋迁”“货积如山”[8]185。
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心(包括城市和场镇)的繁荣使得兴建祠庙、会馆成为可能。清代中期之后,大量祠庙、会馆在商业和经济繁荣的府、州、县甚至乡场首先出现。祠庙、会馆分布较多者,也是当时经济相对较发达者。清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同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在诸多社会压力面前,人们迫切需要精神的释放,向神灵诉说或求助成为常见的选择。对移民社会来说,兴建会馆作为移民聚乡情、襄义举并以神灵的名义团结乡里的整合中心的愿望日显迫切,民间信仰社会减压阀的功能因此得到体现。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更高需求也使得会馆从最初的聚乡情的移民信仰中心慢慢地向商业中心转化,经济功能愈加明显,体现出公所的色彩,再后变为商会,神灵崇拜在会馆中被慢慢淡化。
(二)经济发展使某些神灵被大量崇祀
民间信仰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在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确定的,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息息相关。清代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神灵如社神、田祖、土地神、牛神、瘟神、驱蝗神等备受推崇;四川境内河流纵横,农业生产时常经受水涝灾害,因此水神系统特别发达,既有江渎神、赵昱、李冰父子(川主)与大禹等本土水神,又有天后、真武、杨泗、萧晏二公等外来的水神。清代四川商业的繁荣使得商业人口所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世俗社会普通大众的共同愿望,因此财神信仰在城乡地区特别兴盛,不仅财神庙香火旺盛,而且各路财神统统得到崇祀,既有本土财神赵公明,又有外来财神五显神、五通神或五路神等,还有全国性大财神关羽,农村地区则在家堂中供奉四官财神;在旱涝多灾的清代四川,告别病恙、保持健康成为许多人共同的追求,而医疗水平低下、医风不正的现实又使得老百姓只能将健康的愿望诉求于神灵,因此药王孙思邈在得到医药行业奉祀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广泛的信众群;清初大量为了谋生计的经济型移民进入四川,不仅带来了四川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也带来了大量的神灵信仰,而随后的移民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使得这些神灵信仰最后融入四川原有神灵体系。
(三)手工业的繁荣使行业神崇拜兴盛
清代四川商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城乡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商业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城乡手工业的竞争态势,又刺激了手工业新的发展甚至革命。清政府明确废除匠籍的制度使手工业者获得了身份自由。同时,清政府还缩小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部分取消了官方垄断,改变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行业的发展需要正常的规范体系和市场秩序,还需要各种要素来整合行业的力量,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势头,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正是迎合这种需要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繁荣的背景下而兴盛起来。因为养蚕丝织业的发达,清代四川蚕神祭祀活动非常活跃。“蚕事毕,户闻煮茧之香,廛列贸丝之市。榖击肩摩,沽酒市脯,谢蚕母赐佑,乐妇子之欢腾。”[9]卷3《风俗》人们一般都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浴蚕,祀蚕神”[10]卷3《风俗》。嘉道时,黄勤业在《蜀游日记》写道:“(过荣县),行经蚕市,渐闻鼓声隐隐,由远而近,土人咸曰:祭马头娘也。”[11]
行业的发展促成了祠庙的大量兴建,祠庙成为行业发展的见证和重要表现,并进一步促进和刺激行业的发展,为行业发展提供精神方面的保障。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县域,铜梁县内行业神庙的兴旺景象可谓典型,不仅数量非常多,而且种类齐全,有各地皆有的药王庙、鲁班庙、罗祖庙、老君庙、财神庙、杜康先师庙、蒙恬将军庙等,也有四川常见的紫云宫、蚕娘圣母庙、牛王庙、华佗祖师庙、孙膑祖师庙,还有分工很细的梅葛二仙庙、詹皇庙、机仙圣母庙、葛仙庙、五显灵官庙等祖师庙,可见商业之繁荣。其中,造纸业为铜梁第一大产业,因此各地皆有蔡伦庙。[12]128-130
二、民间信仰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民间信仰会以各种形式反作用于地方经济,对地方经济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神灵信仰不仅在民众面对危难时提供一种心灵慰藉,还对民众行为具有约束力。它使人们在商业交易中遵守诚信原则,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有效运转。
(一)祠庙的兴建促进了场镇的形成和繁荣
四川的一些小城与乡镇的形成,与会馆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初移民入川时,初期的定居点往往满目疮痍,经济萧条,出于聚乡情、敬神明的需求,移民在荒野之处开始建造会馆。随着移民不断聚集,会馆越来越多,商家小贩云集会馆做起买卖,会馆周边逐渐修成街房,集市与场镇于是成规模。金堂县广兴场,明末毁于战火。清初来川移民先后集资修建了广东、两湖、贵州、江西等省会馆,从此香客会众络绎不绝,商贩云集。此后,贵州、江西会馆及城隍庙会首集议出资,各修一段街房,首尾相衔,遂成集镇。故该场镇又有“三节镇”之别名。[13]33射洪县太和镇有“五省会馆在此兴场立市”的说法,即五个省的移民到此来后,又有其原籍的商人利用同乡关系,不断来往做生意,形成了同乡接待联系的场所,因此,会馆的建设对该地繁荣商业、兴场立市起了促进作用。
会馆和祠庙的兴建还促进了清代四川部分行业的繁荣和发展。湖北黄州人善于经商,四川某些县乡建立的黄州会馆从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和某些行业的发展。如新津县太平乡的黄州会馆,在满足黄州同乡迎麻庥、聚乡情需求的同时,也成为黄州人的商务活动中心,同时也是黄州商人的花纱交易集散地。内江城区的江西商人,以其同乡会馆——万寿宫以中心经营着一批从事金、银、锡、铜器品的商贸业务,促进了清代内江银、铜、锡等工艺的发展和繁荣。陕西商人在内江城内以陕西会馆为中心经营大量棉花贸易的店铺,不仅使其“陕棉”畅销内江,转运川东南,并使陕商在内江成为了富裕的商帮——“花帮”,同时,还促进了内江棉花贸易的繁荣,树立了内江棉花贸易在四川的重要地位。
(二)祠庙经济是地方经济的重要补充
祠庙的存在与延续、修葺等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祠庙开展正常的联谊、祭拜以及庙会等大型活动需要经费,所以产生了“祠庙经济”,[14]254一般的祠庙都“各有底金产业”。[15]卷2《坛庙》如灌县的二王庙,至新中国成立前,其庙产还有田地600亩、山林一匹。[16]275特别是各地移民所建会馆,都拥有一定的产业和经济基础。如南川县,“会馆建自客籍……均于营造外,或置田租,或存款生息,平日招人主守焚献,赀产主权,庙首操之”。[17]卷5《礼仪》广东移民在各地所建南华宫产业都颇为可观,如九尺镇的南华宫有田40余亩,敖平镇南华宫则有庙产50余亩;新津县普兴乡南华宫有庙产92亩。[18]江油县的湖广会馆拥有铺面达100余间,用以出租,江西会馆则有田产达400余亩之多。[19]
这些庙产除了用来维持负责人和经营者的衣食住行及各类信仰事务以外,还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31-35民国时期,铜梁县各地的文庙、武庙、书院、义学等均各有田地,由各首事轮流经营,亦县属财政之一小部分。该县的书院和义学其实大多来自清代的祠庙、会馆。[12]206清末民初,会馆往往动用其产业来参与地区文化事业以及经济发展。民国《新都县志》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邑人李吉安在南华宫开办小学,每年由神会捐银151两,钱160千作为经费。[21]第二篇《政纪志》宣统元年(1914年),彭山县建国民学校时,“原提南华宫所有关帝会租谷三十石、财神会租谷五石、六祖会街房十间,年收银四十元;花生斗一张,年收银二十元”。[8]卷2《民俗》会馆产业在清代四川甚至还成为地方税收来源之一。民国《重修什邡县志》载:“清康雍乾嘉时代,各省人来什者,先后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取租金为演剧、酬神、焚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愈多,至光绪中为极盛。光绪壬寅(1902年)开办学堂,政府通令抽收寺产,以备经费,然仅十分中取二,神会仍然无损”。[22]卷7《礼俗》
祠庙经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依托祠庙、会馆所建的社仓、义仓。清代的地方仓储是“省建永济仓,府建丰裕仓,州县有常平监仓,乡镇设社仓、义仓,边远地区置营屯仓”,“地方另外还设有义仓、积谷仓等”。[23]511-515清代四川乡镇的社仓、义仓多设置于寺院、祠庙和会馆中,如铜梁县,全县社仓共二十八处、安居社仓十六处,绝大多数都设置在寺院和祠庙中。[12]196到民国时期,官方管理的积谷仓廒也绝大多数设置于寺院、祠庙和会馆中。在铜梁县,民国时期的91间积谷仓廒中,设置在仓圣宫、禹王宫、川主庙、濂溪祠、王爷庙等民间信仰祠庙中点有38间,置于总神庙中有35间,置于文庙中有7间,置于乡公所中有4间。[12]197-198这种情况在清代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在荣县,同样多个祠庙都有社仓和义仓。如炎帝宫,“县东程家场山门外右有仁义仓五间”;神农庙,“县东程家场,离场二里内,有中和仓三间”;湖广会馆,县东贡井,“乾隆十八年设立社仓三间”;虞家庙,“乾隆十八年设立社仓”;东岳庙,“县东五十里,长山桥官山上近场口,设立社仓五间。”[24]卷8《舆地志·坛庙》这些社仓、义仓等的设立使得祠庙又称为地方仓储机构,成为社会功能承载和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
(三)庙会、迎神赛会促进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发展
庙会,又名“赛会”,*《说文》曰:“赛,报也。”所谓报,即酬谢神灵,又称“社赛”“社会”“社火”“祠赛”,都是以春秋社祭为中心的民间宗教集会,后来则成为以神祠为中心的民众宗教集会的泛称。是一种以祭祀神灵为中心,在寺庙或其附近举行的包括宗教内容在内、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以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为目的的群众集会。《岁华谱》谓:“赛会,承平之遗风,从民乐也。”[25]卷16,引元费著《岁华谱》最早的庙会主要由组织性宗教人士发起,释道信众参与,仪式、内容源自释道经典,其组织形式、功能皆因释道教义而生,组织性宗教在整个香会、醮会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清代四川,这种类型的庙会已经不多,虽然此时的庙会也基本上皆由某一具体神灵的信仰产生,释道人士也要参与负责主持仪式,包括打醮、建会等,但他们只是此类集会的参与者或组织者之一,而非主导者,整个集会与释道经典、教义关系不是十分密切,主要是源自民众祠神信仰中最普遍的邀福免灾、酬神感恩心理,参与者既有神灵的信仰者,也与地缘因素相关。清代四川庙会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乡村的春秋社祭,是古代社祭春祈秋报传统的延续。*指古代先民进入农耕时期的“社祭”,是祭祀后土神的。仪式一般都比较简单,往往有男女巫师主持,有娱神的舞蹈和表演,也有敬神、犒劳神灵的献祭仪式,在祭祀结束后,整个村庄的百姓聚餐,一片祥和喜庆的景象。
第二类,以某一特定神灵为中心的小型集会,参与者都属于同一职业或某一特定群体,其实这是村社赛神的延续和发展,是最主要的类型,上述土地会、药王会、田祖会等以及各省会馆在所祀主神诞辰时举行的集会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类以村社、省籍或行业为单位的民众宗教集会十分普遍,规模可大可小,对地方政治经济影响最大,在纳入士人视野时,往往被视为官民合乐、政治清明的表现。
第三类,非常时期的迎神赛会,如为祈雨祷旱、禳除蝗灾、瘟疫而举行地方性宗教集会。由于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往往不限于一村一乡,而是数县数州,乃至数省,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为禳除灾害而举行的集会多由地方长官组织,仪式操作人员则常常包括当地释道人士和巫觋。当然,有时也由退休官员、本地士绅或寓寄当地的官员主持。
作为区域基层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经济网络,庙会是四川农村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其独特的重要作用。经济史家全汉升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道出了庙会与场市的关系。在庙会中,由于人们对神祇的拜祭,人员流动大,且神祇所在地成为中心,很容易形成市场,以满足拜祭者的商业需求。在某些地区,庙会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农村集市,甚至超过集市。段玉明教授指出了寺庙文化对经济交流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庙市的墟市化在明、清时期是一不可遏制的趋势。[26]274-290
清代四川庙会非常活跃,各种类型庙会文化趋于成熟,在经费运营、活动安排和保障措施都方面都有突出表现,这对于地区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庙会期间无不演剧酬神,多地或“各有基金”,[27]卷7《风土志·习俗》或“比户合钱演戏似酬神”,往往因人们“彼此争先”,导致“乐部为之增价”。[28]卷18《风俗志》二月二十五日的绵竹岳王会,“演剧以酬,四方携褚帛而来者,不下万人”。新繁城隍会,“庙中则演剧酬神,牲宰交错;于衢则高涨彩幔,缀以花灯”。[29]卷3《地舆志下·风俗》清代竹枝词中对灌县“二王宫”庙会的描绘也完全是一副繁荣景象:
了愿酬神六月中,虔诚拜到“二王宫”。人来莫向南关去,逝水推波路不通。
信是人间“五洞天”,清奇秀丽实岿然。青城览毕归来后,即便愚夫亦说仙。[6] 3221
因此,清代四川的各种各样的庙会与其说是祀神的神会,不如说是集文化、商业、娱乐竞技与宗教与一炉的大集会,各种行业、各种营生琳琅满目,其中的商业色彩非常浓郁,所谓庙会已经变成纯粹的具有娱乐色彩的商贸集会,其对地方经济的价值远远大于对神灵的祭祀价值。
虽然庙会作为一种低级的经济交流形式,其参加者主要是城镇小手工业者、近郊农民和城市平民,但是,庙会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四川地区,其意义仍然非常突出。作为经济交流较为发达地区稳定集市的有益补充,四川庙会对于祈神禳灾、调节民众单调、紧张的生活以及凝聚社区团结等多方面都有着非常突出的意义。
三、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格局造成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经济发展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与差异在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四川在清代中期后进入了封建社会手工业最繁盛的时期。行业的发展需要正常的规范体系和市场秩序,还需要各种要素来整合行业的力量,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和发展势头,清代四川行业神信仰正是迎合这种需要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繁荣的背景下而兴盛起来。民国《新繁县志》反映的只是行业神信仰兴旺之冰山一角:
民业则各祀其所始。纸业祀蔡伦,泥木石业祀鲁班,五金业祀老君,酒业祀杜康,机织业祀机仙,靛染业祀梅葛仙翁,豆腐业祀淮南王,鞋业祀孙膑,织履业祀刘备,缝衣业祀轩辕,理发业祀罗祖,屠宰业祀桓侯,厨业祀詹王,医业祀孙思邈,演剧祀唐明皇,胥吏祀萧曹,船户祀王爷,商人则通祀财神。[29]卷3,《地舆志下·风俗》
(一)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与行业神信仰差异
在世俗的观念中,行业神或为祖师神,或为单纯的行业保护神,都能掌管行业,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并保障行业中个人和行会利益。[30]区域经济体系的构成和产业结构方式的差异会在行业神信仰方面得到体现。在最紧迫、最受重视的行业或最繁荣、最有特色的行业中,其行业整合的需求更大,行业神信仰也就更兴盛。咸丰《阆中县志》云:至人家隙地在皆种者,则无过于桑。川北大绸擅名蜀中,丝织业的发展使得蚕神信仰盛极一时。驱蝗神刘猛将也深受敬仰。清代四川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县城和市镇的建设使木厂一片兴旺景象,“冬春,匠作背运庸力之人,不下数万”,[31]卷3,《风俗》因此,鲁班成为传统手工业中最受崇祀的神灵。*在清代四川各地都有崇祀鲁班的祠庙。如光绪《续增乐至县志》卷1,《祠庙》:“鲁班庙,在砚山麓,同治八年邑木帮人公建”;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9,《祠庙志》:“鲁班庙,(酉秀黔)无专祠,或附于各庙,工师匠人之所祭也。光绪《重修彭水县志》卷2,《祠庙志·通祀》:县志庙在小北门外,郁山镇亦有之,名巧圣宫,咸丰十一年发逆入郁山,毁于火。”民国《泸县志》卷1,《舆地志 坛庙》:“公输宫:在城南垣,祀公输般,旧为禹王宫,乾隆十七年建。咸丰四年重建,易今名。”
行业神崇拜和行业的垄断和竞争态势也有关系,当行业处于寡头垄断(比如完全的官方垄断)阶段的时候,行业神已经成为垄断者的工具,神的地位和作用就将被弱化。清代四川井盐制造业和冶铁业都因为技术的改良等原因达到空前繁荣的状况,但是这些都是官府垄断的行业,因此行业神崇拜并不发达。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商业人口所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世俗社会普通大众的共同愿望,因此财神被许多行业作为行业神并虔诚奉祀。在旱涝多灾的清代四川,告别病恙、保持健康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药王在得到医药行业奉祀的同时也获取了更广泛的信众群。
(二)区域经济格局差异与行业神信仰区域差异
历史时期四川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开发格局不是同步的,在不同时期各区的产业结构也不一致,折射在民间信仰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蓝勇先生曾以政区、移民、方言、民俗、民风(个性特征)与文化区域的关系等为主导因子对古代四川进行了文化区的划分,其“对四川三大民俗区的形成依据的主要历史文化积累主要是明清时期”。[32]民间信仰是四川“地方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导因子之一。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同样可以参照蓝勇先生的分类方式将其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
川西平原自古以来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农业经济在四川最为发达,人们有更多的精力用于娱乐和发展文化,商业最为繁荣。在传统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川西平原市侩气息最为浓厚,并因此形成了居民尚游乐、重饮食的传统。川西民间信仰区的民间信仰中与农业相关神灵和祀神活动备受重视,各种信仰活动更具商业意味和娱乐色彩。川东民间信仰区山高水险,古代森林茂密,先秦时以狩猎渔猎经济为主,在明清以前狩猎经济仍有一定地位,但农业文化的影响占有绝对地位,商业文化相对于成都平原就十分薄弱。川南民间信仰区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川东民间信仰区基本相同,但是由于远离中原地区,开发相对较晚,明末清初以后因为战乱影响较小而慢慢发展起来,因此,保留了许多土著和少数民族的古老民间信仰。
四、结语
民间信仰的内容、形式及其变迁都以某一时代、某个区域的地方经济状况为依据,并以各种方式反作用于地方经济。从清代四川社会情形看来,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的互动更多呈现为良性。但是,泛滥的、过分商业化的神灵崇拜和祭祀活动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清代四川某些地区过于铺张和密集的迎神赛会、以盈利为目的各种行业神、财神崇祀等活动就对地方经济有过多的消耗,其消极作用可见一斑。因此,在努力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对于城乡地区方兴未艾的民间信仰,我们不能一味将其斥为封建迷信,在关注民间信仰消极作用的同时,要关注民间信仰在实现地方社会整合、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的作用,要加强对民间信仰的引导与管理,使其更多地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1] 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J].农业考古,2012(3).
[2] 黄洁琼.唐宋闽南民间信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初探[J].龙岩学院学报,2005(8).
[3] 王健.民间信仰与明清江南的经济、社会空间:以苏松为中心[C].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青年学者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林移刚.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5] 李玉宣,衷兴鉴.重修成都县志[M].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6] 林孔翼.成都竹枝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8]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1.
[9] (清)武丕文,欧培槐.江油县志[M].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刻本.
[10] (清)史钦义.彭山县志[M].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刻本.
[11] 王文才.成都城坊考[M].成都:巴蜀书社,1986:87.
[12] 郭朗溪.新修铜梁县志[Z].铜梁县地方志办公室印,1982.
[13] 王雪梅.四川会馆[M].成都:巴蜀书社,2009.
[14] 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 陈谦,陈世虞.犍为县志[M].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6] 胡昭曦.四川古史考察札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17] 罗云程,柳琅声,韦麟书.南川县志[M].民国二十年南京明明印刷局铅印本.
[18] 刘正刚.试论清代四川南华宫的社会活动[J].暨南学报(哲社版),1997(4).
[19] 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J].中国史研究,1996(4).
[20] 蓝勇,黄权生.“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1] 陈习删,闰昌术.新都县志[M].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22] 王文照,曾庆奎,吴江.重修什邡县志[M].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23]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4] 廖世英,赵熙,虞兆清.荣县志[M].民国十八年刻本.
[25] 萧应明,曾世礼,庄喜.蓬溪县志[M].民国二十四年刻本.
[26] 段玉明.西南寺庙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7] 王鉴清,黄涛,施纪云.涪陵县续修涪州志[M].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28] 汪仲夔,熊卿云,洪烈森.德阳县志[M].民国二十六年修,二十八年铅石合印本.
[29] 侯俊德.新繁县志[M].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
[30] 李乔.中国行业神信仰[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2-4.
[31] 岳永武,郑钟灵.阆中县志[M].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32]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
(责任编校:杨 睿)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 Relig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at the Qing Dynasty
LIN Yi-gang
(DepartmentofSociology,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religions and economy of Sichuan in Qing dynasty were complementarily connected. On the one h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sperity of a large number of temples and other guild belief cente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d to more gods’ worship, such as God of agriculture, water god, God of wealth. Handicrafts’ prosperity caused the industry gods worship especially prospero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pular religions reacted to the local economy in Qing dynasty in a variety of forms. Temple hall construction everywher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owns. The continued accumulation of temple economy increasingly becam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local economic system. Prominent and active temple, an idolatrous process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nd trade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wa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opular religions.
popular religions; local economy; folk custom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4.013
2016-11-30
重庆市201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4BS061)“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及其现实价值研究——基于多向移民中社会整合的视角”;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XZS031)“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研究”
林移刚(1978—),男,湖南省洞口县人;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社会史、农村社会学及涉外社会工作研究。
F129.5
A
1672- 0598(2017)04- 0097- 07